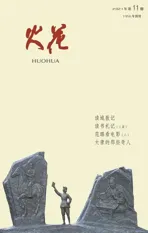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五)
2021-11-11鲁顺民陈克海
鲁顺民 陈克海
第五章 吃糕
一、“七字经”
早在2016年工作队驻村开始,大家就意识到,像过去撒胡椒面缝缝补补、小补小修式的扶贫肯定难以长久,未来如何发展?扶贫成果如何持久?迁出原址重建新村就是考虑方案之一。尽管当时全局性的易地扶贫搬迁方案还在酝酿过程中,但把村民迁出老村子是大家的共识。
事实上,也不仅仅是岢岚县,世纪之初有一个数字,山西省贫困地区有9万多户、50多万人分散居住在6690多个山庄窝铺。干部们总结,这些地方“四多六难”,文盲多、光棍多、残障多、穷人多;耕种难、行路难、吃水难、通电难、上学难、结婚难。“四多六难”,赵家洼一样不少。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全国各地都把易地移民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就山西省而言,1996年到2000年,全省共安排移民开发补助资金8134万元,移民搬迁8万人,搬迁基本上稳定解决了温饱。
新一轮脱贫攻坚,统筹考虑水土资源条件和城镇化进程、搬迁对象意愿,把解决不安全住房,尤其是“土窑洞”作为易地搬迁工作重点。
易地扶贫搬迁,也不是新一轮脱贫攻坚才有,是中国扶贫走过将近四十年的过程中探索出来的有效办法。
山西省“十三五”脱贫攻坚,八大工程二十个专项行动,易地移民搬迁被称为最大的工程。从2016年开始,全省将分批对7993个贫困村中的3350个深度贫困自然村实施整体易地搬迁,涉及人口38万,同时还有7至8万非建档立卡户同步搬迁。
岢岚县从2016年开始,在山西省率先实施易地移民搬迁,备受瞩目,为全省性的易地移民搬迁“撕开了口子”。岢岚县易地移民搬迁,不是简单易地,不是简单搬迁,把农民全“赶”进楼房,而是全县总体规划,紧盯“美丽乡村建设”,县城集中安置点安置一批,中心集镇再安置一批,然后再在中心村安置一批。
县城集中安置点,乃位于县城的广惠园移民新村。广惠园新村之外,尚规划有宋家沟、阳坪村、团城村、吴家堡村、高家会村、马家河村、王家岔村、后温泉村8个中心集镇安置点,除此之外,还有店坪村等若干个中心村安置点。
这是所谓岢岚县“1+8+N”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模式。
城、镇、村协调发展,再引入乡村旅游、电商,以及其它新的生态业态,带动整村提升。
岢岚县走得比较早。走得早,是因为岢岚县像赵家洼这样的山庄窝铺太多。岢岚一县,向来是村多村小而且村散,赵家洼行政村3个自然村,“谁也瞭不见谁”,相距10里有余。赵家洼村只剩下6户13口人,在岢岚县还不算人数最少的,全县还有“一户村”“一人村”,人丁零落,深处山间,自然条件恶劣。
迁出老村,重建新村,工作队把这作为一个重点征求过大家的意见。
重建新村当然好啦!村民大部分都同意。这道理显而易见,其实也没有多少道理可讲。长期过度依赖农耕谋生的村民早就用脚投了一票,同意是没有问题的。在村的,刘大叔、李虎仁没问题,王大娘早就想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其他人呢,一说建新村,挪穷窝,也不知道具体蓝图是个什么样子,嘴上不表态,其实心里哪有个愿意株守老村的?
人都跑光了,留下三户两户,没有人烟,不惧豺狼虎豹吧,也没有个邻居照应,就是进来个贼娃子也应付不了。
但是,真正确定要搬迁,“1+8+N”甚为具体,搬迁的地点基本明确,愿意进城进城,不愿意进城则在阳坪乡中心集镇安置,全部要离开村庄到另外一个地方,大家兴奋的心情一下子不见了。说是愁吧,也确实就是愁,说是不愿意吧,还不是完全不愿意。心上总是泼烦,甚至有些心慌。
本来,易地扶贫搬迁,就远不是给贫困户找一个适合生存,生产、生活都方便的地方安顿住下来那么简单,更不是一纸行政命令能够解决。
村里人说起自家村自家地自家的出产,有时也是辄有怨言,尽管知道“人挪活,树挪死”“挪新窝,断穷根”的道理,但正经连根拔起,既要搬迁,还是易地,哪有那么容易?
金银可丢,热土难离。
住惯的坡坡不觉陡。
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家的土窝窝。
破家值万贯,搬家三年穷。
矛盾频出。
矛盾也甚为具体。
陈福庆他们就得给做工作。做工作的范围,就不止留在赵家洼这些朝夕相处的大爷、大娘、大婶、大叔了,全村17户贫困户,包括在村里有房有地的都要一一征求意见。
易地搬迁的,不仅仅赵家洼。
但赵家洼村的易地移民搬迁关乎一县的全局。尤其是总书记考察的新闻效应之下,赵家洼村的搬迁工作全县瞩目,全省关注。
岢岚县全县有115个村落需要整体搬迁,仅阳坪乡一个乡,就有18个深度贫困自然村,要分两批实施易地搬迁。2017年搬迁包括赵家洼村在内的8个村,涉及贫困户65户117人,同步搬迁15户41人,还有15户35人需要通过投亲靠友迁往中心村进行所谓“插花搬迁”。2018年整行政村搬迁1个,贫困户36户59人,同步搬迁12户29人,整自然村搬迁7个,贫困户37户65人,同步搬迁户30户49人,插花搬迁65户152人。
具体到赵家洼村,涉及18户35人。
但大家有顾虑。
比如刘大叔,他的顾虑很具体。
他对陈福庆讲:我今年70岁了,也就快不能“动弹”,几乎等于没有劳动力,到外头,打工都没人要。现在是在家里守着老妈妈,种地还能解决口粮。老妈妈百年之后,老两口还在村里守个甚?甚也不方便。我倒想进城里住,可是买菜花钱,住房花钱,将来如何生活?
老刘说得在理。
陈福庆跟他一项一项讲。
先说怎么搬。按省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每一个贫困户易地补偿款是3.88万元,刘大叔一家,老两口加上老母亲,3口人补偿就是11万多元。当然,这些补贴都用在房屋建设上面,不发给贫困户本人。下来,你搬出去,村里旧房子,要拆除复垦,房屋、窑洞、畜舍,甚至厕所都要作价进行货币化补偿。搬迁住新房,国家本着一个原则,就是贫困户搬迁不举债,随迁户搬迁少举债,说白了,就是盖好房子让你去住,交给你钥匙就行。
到县城广惠园移民新村,按政策,贫困户每人的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刘大叔一家三口,那就是75平方米,甚至更大。
刘大叔疑惑,75平方米是多大?而且是楼房。
——有没有我现在这摊子大?
刘福有问陈福庆,陈福庆就笑了。
——你就是两处院子的房子加起来也就这么大!
刘福有的嘴张得老大说,不可能啊!
“下来,原来的林地、耕地,包括房前屋后的树木产权还属于你,过去该给你的退耕款还是你的,这也不用担心。”
“总之是,大爷你能搬还是搬,不要犹豫。‘十二五’期间你没赶上搬,‘十三五’再误过,又是五年。搬,总比不搬强,不说别的,你在村里有个头疼脑热,叫医生、买药就不方便,而且随着年龄增大,将越来越不方便。现在是工作队在村里,工作队如果不在,吃水都是问题。”
刘大叔想一想,也确实是这么回事。
刘大叔如此想,曹大叔呢,也是这么个心思。杨玉才杨大叔、张秀清张大哥,家里各有一群羊,怎么处理?其实,为了搬迁,为了换水土,县里早就考虑到给适当的补偿,不用担心。
易地搬迁,说是大工程,实际上是大学问。易地搬迁,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里头要解决的问题太多。总结起来有七大项,就是“人、钱、地、房、树、村、稳”,七个方面,七大问题,都需要协调好,处理好。
“七字经”总结起来,就是解决“人往哪里搬、钱从哪里筹、地在哪里划、房屋如何建、生态如何护、新村如何管、收入如何增”。
新村如何管,那是工作队将来的事情,即便解释,刘大叔也未必清楚,但陈福庆知道,刘大叔还是担心一个“稳”字。进了城,柴米油盐,抬手动脚都需要钱,不种地,收入哪里来?
易地扶贫要“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像刘大叔、王大娘、曹大叔,还有随迁户杨玉才,不在村的贾高枝,虽然上了年纪,但还有一定劳动能力,更不用说像张秀清这样还属于壮劳力的贫困户,工作队和县人大机关已经商量好,迁出去之后,要千方百计为他们再就业创造机会。
这也不是赵家洼一村的事情。
工作队做搬迁说服工作,做搬迁准备工作,“人、钱、地、房、树、村、稳”“人、钱、地、房、树、村、稳”,天天念的是这“七字经”。
刘大叔说:要是这么个搬法,咱还有甚意见?搬!
二、探房
2017年8月16日 星期三
陪刘大叔、曹大叔进城看房子。
早6点起床,顺路去王大娘家看房子。太阳已经照到了对面的山顶,王大娘还没起来。见刘大叔顶子的烟筒无烟,杨大婶起来了。听见铁栅栏开了,曹大叔也起来了。看来村里只有王大娘还没有起来。
快10点,赶忙叫上刘大叔、曹大叔准备进城。
一会儿刘大叔和曹大叔下来了,坐上车就走。大约二十分钟后,来到了广惠园移民新村。
曹大叔在7号楼3单元2层东户,刘大叔在5号楼5单元2层东户。去物业取了钥匙,先去了刘大叔家。刚开门,正好里边工人师傅在做木工,柜子已经做好,床也做好了,门还没有安上,已经定做了。
刘大叔仔细端详了半天,一间屋子一间屋子看,我问比咱现在的房子好多了吧?刘大叔高兴得像个小孩似的笑了。
刘大叔说:村里的房子最多时住过二十几个人,那铺炕上有一回就睡过8个人。现在好了,再也不发愁女儿回娘家挤得没地方住了。
从刘大叔家出来,我们一起到了曹大叔家。一开门,里边白白的墙,门已经装好了,木工活已经做完了。曹大叔高兴得,从一个屋子走到另一个屋子,仔细端详着每一件物品,从地板到柜子,到屋顶的造型。“比村子的房子不知要强多少倍。”大叔自言自语地说。
12点多,从房子里出来,刘大叔说要去买药,曹大叔说要去买醋。我开车直接去了五台山大药房,把车停好,刘大叔去买药,曹大叔去买醋。
一会儿两人回来了,上了车,刘大叔和曹大叔要回村,我说吃了饭再走吧。今天我请客。刘大叔和曹大叔,怎么能让你请呢?那多不好意思。我说没事,我经常吃大家的饭,今天就让我来请一回吧,不然的话也不公平。到北大街找了一间小饭馆,刘大叔和曹大叔一人要了一瓶啤酒,我点了两个肉菜,还有一个凉菜。曹大叔不让上了,说吃不了浪费。服务员问要什么主食,刘大叔说,我吃饱了,不要。我和曹大叔也没有要。
吃完饭,刘大叔急着回去放牛,便开车回到了村里。
这是陈福庆《民情日志》摘录,2017年最忙碌的那一段时间的一个上午。他带着刘福有和曹六仁前往广惠园移民小区看房子。
一轮讨论,一轮自愿报名,赵家洼村共有18户35人搬迁,其中杨玉才一家4口为随迁户。县城广惠园新村集中安置点将安置12户29人,阳坪中心村集中安置4户4人,其他插花安置2户2人。
刘福有、王三女、曹六仁、张秀清、李虎仁、杨玉才在村的6户全部迁到广惠园新村,在搬迁前的一个多月,各自的房子都已经定了下来。
在村里住了一辈子的老农民,一下子让搬进城里住敞亮的楼房,楼宇相瞩,人声鼎沸,房子里有上下水、卫生间、厨房、地暖。一间一间打量,一件一件抚摸,新房子油漆、胶水、甲醛味还未散尽,但闻到的分明是未来生活的味道,未来生活的模样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无疑,还将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
一切,都远远超出他们对易地搬迁的预想,或者说,眼前的一切,远在他们的想象之外。再过几个月,他们将是这里的主人。做这样新居的主人是什么样子?还停留在想象之中。
广惠园新村,规划700亩土地,分三期工程,将建设3486套保障性住房,能够容纳20000人居住,中学、医院、幼儿园,基础设施相当齐全。岢岚县推进“城乡一体化,三年大变样”,广惠园新村是最大的民生工程。
刘福有、曹六仁、张秀清、杨玉才,按照家里人口,其新房为80多平方米,两室一厅,新房的面积远远超过在村里三间正房的总和。过去建房,每间房一丈宽、一丈五入深,左不过15平方米,三间向阳正房加起来的建筑面积也不过45平方米,到了冬天,还未必每间房都生火,一家人只能挤在狭小的15平方米空间里,“一个炕上睡过8个人”,其苦况如何!
3486套房,2万人,现代化小区,不说放在岢岚县,就是在晋西北诸县的县城里,这也应该是最大的居民聚落。楼宇设计、雨污分流、绿化面积、公共设施、功能区划分,都按照现代都市居民小区图样展开,不必多说,刘大叔、曹大叔他们放心也在情理之中。刘大叔已经开始憧憬,“再不发愁女儿回娘家挤得没地方住了”。远景不远,要求不高,可实实在在。
是啊,其他不敢想。连他们自己都感到,入住环境变了,自己也要跟着变,如何生活,生活成什么样子,考验不小。
县城安置中心如此,中心集镇安置点如何呢?
岢岚县的“1+8+N”,8个中心集镇安置点,都分布在乡镇所在地,交通方便,生活方便,办事也方便。
以宋家沟中心集镇安置点为例。
岚漪河出管涔山,东西贯穿岢岚县境,分出东西两川,阳坪乡位于西川,宋家沟位于东川,东西两川,同吃一条河的水。
陈福庆作为人大工作人员,曾到宋家沟做过人大工作方面的调查。乡党委副书记范利飞告诉他说,过去在岢岚县各乡镇中,宋家沟至少在村容村貌这一方面来说,不算差,甚至可以说是最好的,是模范。但是乡里干部就不敢把人领到桥东那一头。因为桥东那一头与桥西比起来,简直就是两重天。同是一个村,桥西靠近乡政府这一头,学校、卫生所、商店都在这边,民居也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和进入2000年之后两轮乡村“盖房热”,尽管风格不一样,外观上显得驳杂一些,但齐整得很。一过桥东,却都是旧房,有民国时期的建筑,甚至还有前清房舍,有些常年没人住的房,塌得眦牙咧嘴就剩下木头架子。好一点的,也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盖的,但质量不行,土坯墙,石木结构,几十年过去,也就陈旧不堪。街巷都是土路,刮风尘土飞扬,下雨一片泥泞。
宋家沟中心集镇安置点的民居设计,也是费了心,县上请来中国乡建院专门搞全县的中心集镇安置点设计。其设计不独超前、现代,而且传统、乡土。
宋家沟如此,一县的中心集镇安置点皆然。
中国乡建院的规划和设计理念就是“把乡村建得更像乡村”,这个话难理解,实际上很直观。设计有这么四个原则,第一是立足脱贫;第二,着眼小康,比原来建筑要强一些,建筑质量、整体设计着眼未来的实现小康社会,你不能说建起来还跟原来的农村一个样子;第三,特色风貌,就是结合当地民居特点进行设计;第四,绿色宜居,安全适用,美观经济。
乡建院的设计团队很用心,对整个宋家沟,包括其他7个中心集镇安置点,不是新建,也不是重建,而是着眼于修复。他们有一个原则,整村设计,“原址、原貌、原大小”,利用旧宅基地,收集旧建筑构件。旧村改造不用说,旧街旧房,尽量按原样修整;新建房,尽量采用旧建筑构件,旧梁旧瓦旧砖,连街上的铺街石都是从本山取来的石料,体现节能、绿色理念。村里的民居建筑,旧房改造过的像新房,新建的房舍,看起来也跟旧有房屋风格一致。
习总书记从赵家洼村考察出来的第二站就是宋家沟。
宋家沟从规划到设计在2016年就开始了,到2017年把规划与设计具体落到地面,几乎动员了全乡的力量集中建设,仅用了75天,一座漂亮、宜居的村落就伫立在岚漪河边。
宋家沟搬下来的村子共14个,有的是插花搬迁,其中有4个村属于整村搬迁,分别是牛碾沟、长崖子、甘沟、吴家岔。现在宋家沟为471户1042人,搬下145户265人。这里头人口对不上,是因为整村搬迁之后,原自然村要销号,把户口就迁到了宋家沟。比方有的村,迁下20户,还有30户,但这个村就销号了,就是说不存在这个户了。这30户也把户口挂在村里,这样,户籍人口就比常住人口要多得多。
这座新村,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形成的新闻效应影响持久,意想不到贏得“三晋第一村”美誉,逢周末和节假日,自驾来此旅游的游客最多的时候达到1万人。2018年5月,被评定为3A级景区。
乡镇一级安置中心如此,阖县最大的移民社区建设哪里能含糊?
刘福有探家的时候,新房精装修交付,热水器、燃气灶具、床、沙发、茶几、立柜,甚至连沙发上面的大幅照片都统一布置,照片上方,是习总书记到他家跟他拉家常的情景,还有一小幅照片,是刘福有在赵家洼村旧居的照片,这些由县新闻办、县人大统一采集印制。
刘福有家如此,曹六仁、张秀清家也是如此,王三女、李虎仁的新居面积小一些,为50平方米,两个人因为年纪大,申请的是广惠园新村的一楼,为的是进出方便。
村民离开老村迁新居,只需要置买一台电视、一个冰箱,带着铺盖即可入住。
刘福有给县人大领导提了个建议:他睡不惯床,可不可以在主卧室盘一副炕?
县人大领导笑起来,炕可以盘,但不能是村里那种老火炕,没法子生火。但可以不用买床,同样的价钱建议木工师傅用木架子搭一个木板炕,这样既可以睡炕,下面还可以做一个储物柜。
“这样好。”刘福有说。
“过去其实早就想搬,就是搬不起。现在有这好政策,哪个不想搬?”曹六仁说。
三、惜别
接下来的日子不声不响往前走。
下过一场雨,地里的庄稼活泛了许多,正是百谷灌浆的时分,夜里如果仔细听,可以听到地里的玉米嘎巴嘎巴拔节的声音,土豆的花在夜里就闭了,薄雾扯上来,仿佛在做一场梦。豌豆、黑豆、莜面、胡麻这些晋西北特有的大田植物还需要一个季节才可以成熟。
夜里的星星好亮。
可不是嘛,秋天到了。
山里昼夜温差大,一过中秋节,早霜就会落下来。
城里广惠园那一头各家的新居都已经装修完毕,自然吸引来各家的亲人们去看过不止一回,已经铺排好的陈设无疑给筹划未来生活提供着极好的蓝本,你一言,我一语,你说置个这,他说添个那,闺女来了往哪住,引回儿媳住哪间,大家是纷纷出主意。
欢喜的远不是户主本人。
赵家洼这一头呢?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主人们和他们的老屋正在等待一场惜别。
这时候,刘大叔、曹大叔、杨大叔,还有秀清哥他们,才觉得这一场搬迁真是不简单。按照搬迁政策,老屋在搬迁之后要拆掉复垦,也就是说,人搬走当天,房子马上就要拆掉,再变为耕地,植树造林,恢复生态。这倒在情理之中。这一轮易地扶贫搬迁,拆迁复垦补偿款本来就是建设新居成本的一部分,不然怎么可能搬铺盖就能住上新楼房?再说,宅基地原来不就是草,不就是树?咱们压在人家头上住了几十年。
只是,这房子啊,比不得大地方,比不得富庶地方,简陋是简陋一些,墙上的泥,哪一把没有和过三次?垒墙的石头,哪一块没有摸过三遍?还有柱,还有檩,还有椽,哪一根不沉睡着一段艰难?
曹六仁坐在那里扳指头数,说:“我这房子,住了整整41年。那时候村里不让滥砍滥伐,椽檩木料都是从中寨那边买下,然后再用骡子驮回来,驮了几遭,好不容易搭挂(注:搭建)起这么几间。啊呀,这要拆!还真舍不得。”
刘大叔开朗,说他盖房那会儿:“这房子,我也住了有三十几年四十年,我爹人精,人家也不管你,说是叫咱早成人哩,二十大几,开会我是户主,出工我是劳力,盖房子,只能抽空盖。人家就是不闻不问,反正也盖起啦。我这房子现在看着疲沓,最红火的时候,每天都是十几口人吃饭。”
大家说起当年的盖房,一家起屋,全村人都来帮忙。有匠艺的,做大工,垒砖起墙,搭架上瓦;有一把力气的,做泼笨活路,和泥,搭泥,搬砖做小工。说着说着就说远了。当年盖房,料备好,全村青壮后生不用动员就都来了,说是个大事,从打硪夯地基到上梁覆瓦,其实也就几天的工夫。那时刘福有三十出头,曹六仁二十出头,杨玉才二十出头,一个一个数算起来,都年轻得有些不大真实,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几乎变魔术一样,一处房舍起来,篱笆做墙,编木为扉。然后是另一家,隔年再有两三家,炊烟起处,鸡犬相闻,村郭俨然。
山村合力造屋,是那个物质匮乏时代一代农民的青春欢歌。老屋盛下满满四十多年日月,还有那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几位老人坐在一起,这是恒久的话题之一。这些记忆连同许许多多关于乡村的物事,构成乡村密码的最基本单元,也许,只有他们听得懂,能体味得到。
秋夜里,如果仔细听,墙缝里仿佛还残留着当年打硪夯基时候唱下的调调。
但这些,几天之后会轰然倒塌拆掉,想想那情景,谁的心上都像被尖锐物品戳着一样疼痛。陈福庆当然知道,他也是村里生村里长的人,父辈对房舍的那种感情,他是知道的。那一段时间,他简直不敢跟大家对视,仿佛倒是自己做下什么亏心事似的。他也是怕自己一提,勾起大家伤心。
再则,新楼房好是好,可是破家值万贯,这些农具,还有日积月累积攒下的“泼行烂李”往哪里搁?这些,工作队都想到了,和乡里协调,在宋木沟村找了个地方,赵家洼村村民的农具、存粮统统在那里集中保管,农具需要的时候再用,存粮和存料则可以择机出售。但这也让大家担心,东西寄在别的村子,人家会上心给你保管?万一丢了怎么办?
零零碎碎,牵扯出一件,会生出两件。搬家三年穷,这要舍下多少东西?
六户人家,每天在院里收拾自家的东西,挑挑拣拣,放下这件,拿起那件,总是不舍。有一次,陈福庆来刘福有家,刘大叔正在收拾空房子里的存粮,忽然提出两个老油壶,是过去那种驴皮牛皮磴起来的老油壶。
老汉笑笑:看看,不搬家不知道,家里还有这文物呢。
他准备把两个油壶子扔掉,犹豫了半天,又放回屋里:说不定有甚用场呢。
老油壶都舍不得扔,何况其他。
房子是这样,东西是这样,村子呢?大家都不愿意提这个话题。人全部搬走,房子全部推倒复垦,村名将从民政部门彻底销号,村子也就不存在了。大赵家洼,小赵家洼,当年两个“赵不到一起”的赵家兄弟,从宁武、静乐山里来到岢岚山里开辟鸿蒙,时间不足百年,人口养育了四代,土里埋着一代人。
刘福有念叨,再回咱这村村里,就是给老人点纸(注:上坟)回来一下了。
语气里,是不尽的忧伤与惆怅。
然后他说:“咱百年之后,还得埋回这村村里呢,咋就不回来了?咱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最后还要埋在这里哩!”
下来,是张秀清和杨玉才家的两群羊。
张秀清和杨玉才两家的羊群合起来有300多只。两群羊,是另外一茬庄禾,是两家人的主要现金来源,每年出栏30多只,一只羊,毛收入1000多元,两家人一年从羊身上获得将近三万元,刨去各种成本,也有两万多。
搬进城里,小区里没有羊舍,这羊怎么办?只能卖掉了。
找来“牙子”(注:经纪人),这两年行情却上不去。张秀清家大小150多只羊,大羊多一些,均价600元;杨玉才家那一群,小羊多一些,刨去“牙子钱”(注:经纪佣金),每只均价才430元,真是卖不上个价。
易地移民搬迁,关于出迁户养羊,有相应的补偿,一只羊补助150元。几个回合,讨价还价,终于张秀清和老杨把最后一只羊送上农用车。过去羊舍里羊铃叮咚,娘带孩儿孩跪乳,娘母子一家一家挤挤挨挨,现在彻底空了,只闻得见弥漫开来的羊粪味道。
两个人张罗完毕,拍拍手:羊卖了,咱还做甚?
羊一卖,这就等于把一个产业给放到一边去了,生活还得重新谋划。
还有刘大叔家的牛。
刘大叔家的牛有些麻烦,也不是牛麻烦,而是刘大婶杨娥子麻烦。老刘叹说:我家里那个啊。
刘福有养有两头大犍牛。这两头牛可是老刘家的大功臣,即便耕地退耕还林,一退再退,到2017年刘福有两口还作务着20多亩地。老两口毕竟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若不是这两头大犍牛,哪里能够作务过来?耕、种、收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托付给这两个老伙计了。
村里坡地多,机械不好作业,春天耕地全靠牛工,而村里也只有老刘还费心费力养着这两头牛,耕完自家的,还被雇去给别人家出牛工,甚至本村耕完,还要到外村去。一亩地牛工是50元钱,一个春天,两头老牛可以为老刘增加四五千块钱的收入。
只是,老牛闲散的时候多,还需要老刘每天牵进沟里去放。近两三年,回村种地的人越来越少,先有三十几户,后有二十几户,到2016年,干脆只剩下12户,种百十亩地。而且都拣坪地种,坡耕地或退耕还林,或者等待退耕还林,坪地可机耕,使唤排牛的人家也就稀了。养牛,仅仅是自用,左邻右舍偶尔用一下,说好出三百五百牛工钱,老刘哪里好意思接手要这个钱?乡里乡亲,谁还没有个作难的时候。
两头犍牛成了村里额外的“剩余劳动力”。但两口子精心“务育”(注:饲养)两头牛,那真是精心再精心,刘福有从“分开地”那一年开始养牛,一直到现在,三十多年间,老牛老了,孽生下小牛再养,养过个七八头牛,是村上养牛的好把式。从“牛咩咩”(注:牛犊)养成身强力壮的大黄牛,与养大一个儿子所费的力差不多。说是两头牛,其实跟家里两口人差不多。
可是,要搬到城里,牛肯定要卖掉。城里又没牛圈,城里到处都是混凝土地柏油路,不生青草不长庄稼,就是让你养,平常给它们吃什么?到哪里给它们打青草,到哪里给它们饮水,在哪里给它们拌料?也是个养不活。
老刘每天起来喂牛,每天上午下午出去放牛,晚上回来给牛拌料,半夜再给加夜草,甚至,老两口一个喂草,一个切草,任凭嚓嚓嚓嚓的声音在夜里响起来,谁都不说话。老刘看老伴,老伴已经把眼泪扑簌簌掉下来。老刘心里也“不好活”,给牛喂草的时候,不由用手抚摸一下两个老伙计的头。两个老伙计呢,却不知道他心里的难受,主动用头配合他的抚摸,甚至会用舌头舔他一下。
别房子,别村子,看着两头老牛的眼神,老刘觉得,真真割舍不下的却是它们。阳婆上来照满天,套上犁耙到山畔。黄土地里刨黄土地里翻,老黄牛把你从早陪到晚。庄稼汉一辈子说不尽的故事里,你应该是主角哩。兄弟,这一出《老牛别》不好唱啊。
老伴杨娥子心上更难活,老刘知道,老伴心上一旦不好活,不说话,不闹腾,就会不停“做营生”,不停地做,收拾完家收拾院,收拾完院再急匆匆到牛圈里看一眼老牛,下地割一抱青玉米回来扔进去。然后,抹一把泪。
好几天晚上,睡着睡着,老刘就被惊醒了,他听见老伴在哭。他睁开眼,长叹一声,抽颗烟,陪着老伴。老伴说:梦见牛被人买了去,要往“杀坊”(注:屠宰场)送哩!
老刘说:瞎想甚呢!嘴上这样说,老刘明白,卖牛,先得过老伴这一关。
终于忍不住,杨娥子刘大婶找到陈福庆,没说两句话先流下泪来:“能不能跟领导说一说,不要叫卖我那牛?”
四、安锅
进入农历八月,正是乡间搬家的好月份。
岢岚民间有禁忌,举凡进行婚丧嫁娶、起屋盖厦、搬家扫除,讲究“张王李赵六腊月,乱家百姓三九月。”时进八月,百无禁忌。
但搬迁新居,又有讲究,须拣三、六、九的吉日,择好日子前去“安锅”,即到新居立灶,把灶神从旧居移到新居那里,从此,就意味着成为新居的主人了。
“安锅”立灶,仍有讲究。搬家那一天,要在早上不见太阳,把锅碗瓢盆一切炊具都搬到新房去,旧宅起灶之前,在锅里烙一张饼,不能翻身,只烙一面,待烙到半熟,取出之后,再到新居那里烙另一面。除一应炊具要在当天早晨搬过去,床上铺盖被褥一应用品也要铺陈完毕。
搬家“安锅”,先在旧居这里响三个麻雷子炮,到新居那边也要响三个麻雷子炮。
全村6户人家迁居的日子定在9月22日,那一天是农历的八月初三,是个“好日子”。按照风俗,各家各户需要把东西先搬过去,东西搬过去,再说人。
因为总书记肯定岢岚县易地扶贫搬迁在赵家洼,总书记入户探访的三家贫困户也在赵家洼,三户贫困户又全部要搬到县城的广惠园移民新村,所以赵家洼的搬迁被视为全县易地扶贫搬迁的一个开端、一个起点、一个象征。老刘、老曹、老杨、王三女,还有张秀清、李虎仁,他们在头一天就忙开了。忙,并不是自己着急,是有许多人前来帮忙。
除了雇来搬家抬东西的,还有县里的领导,县人大的工作人员几乎倾巢出动齐聚赵家洼,当然,还有记者,长枪短炮一群人。
定下日子八月初三,六户人家先过县城新居去“安锅”,顺带搬着一应炊具过去。这个仪式很隆重。到太阳跳头,人已经走了一拨。铺盖、必要的行李,再搬一次,又是一拨。家已经收拾停当,人就要离开了。
陈福庆一家一家往过巡查,张秀清年轻力壮,收拾得最快,妻子赵改兰也精干,但赵改兰把东西装上车,回头看老房子一眼,陈福庆发现,她的脸上已经挂满泪珠。
刘福有的老娘,九十多岁。刘福有安顿好城里一应“安锅”事宜,又坐车十几公里回到村子。九十多岁的老娘,早已经失去劳动能力,颤颤巍巍在炕上躺了两年多。老娘年轻时候的照片就摆在柜子上面,那是一张年轻的、清秀的、健朗的面孔,多少年,这是刘家老屋里的魂。刘大叔常说,有娘在,自己就没长大。但现在,她却衰迈不堪。衰迈之躯,要再搬一次家。刘福有最不放心自己的老娘,他特意赶回来要亲自把老娘带到城里的新居去。
老娘由几个人抬着,抬进陈福庆那辆奇瑞QQ车里。老娘一动身,这老屋的生气顿时就减了不知道多少,刘大叔真想大哭一场。路上,怕老人晕车,陈福庆把车子开得很慢。车子经过八月的庄稼田,经过玉米地,玉米棒子吐了紫色缨穗,正是煮着吃的好时候;再经过一大片刚刚收起花朵的土豆地,土豆一收花,茎下的土豆正在一个一个生长着;还有莜麦地,一层雾刚起来,银灰色的莜麦苗左左右右铺陈开来,乍一看去,那是另外一重雾;还有小豆苗,还有豌豆苗,还有黑豆苗,这些刘福有闭上眼睛也能数出来的事物,他还是不住往车窗外头看。
经过一个村子,是宋木沟,再转一个弯,过了岚漪河,就上了干线公路,是赵二坡。雨季来临,岚漪河里的水白浪掠岸,两边的柳树、杨树还有其它杂树长得正旺,旺得发一种墨黑,岚漪河两岸的草铺下密实实一摊,草坡里有各式各样的野花开放。
说到阳坪一带,赵二坡、宋木沟,再往里,大小赵家洼,也是山清水秀,杂花遍野的,怎么就留不住个人?人说美丽富饶,其实是有的美丽的地方不富饶,富饶的地方还未必美丽。
车子很快开进广惠园移民新村,楼宇相望,一派新景。车子停在刘福有家单元门那里,县里的干部也聚下一群,大家纷纷过来,开门的开门,扶人的扶人,老太太佝偻着身子让扶下来,才迷迷瞪瞪说:“咱这是到哪里了?”
刘福有说:“这是到咱家了!”
老太太这才明白,大家大笑起来。但是,她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眼前这庞大的建筑群跟自己有什么联系。老太太一辈子要强,要说也是经见过世面的,但这样多的楼,周围又这样多的人,她哪里见过?
之所以来这么多人,是因为,6户人家过来“安锅”,仪式仅仅是仪式,只有这位最年长的长辈,把她的脚踏到移民新村的土地上,才意味着整个村子全部迁移过来。
老太太被扶下车,刘福有才做了难。他挑的楼层是二楼,现在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大错误。让老太太上二楼,短短一层楼梯,对于九十多岁的娘来说,远比从赵家洼住了四十多年的老屋迁到城里更艰难,不啻跨越峻岭崇山。
老娘九十多岁,就如同赵家洼村落一样大小,走过不足百年的历史,今天迁入崭新的新村。
刘福有张罗着准备把老娘背上去,还不待他弯下腰,陈福庆已经搀起老奶奶,几个人帮忙,把老奶奶背在背上。
当时县委宣传部的领导也在场,说起当时,看见陈福庆背起老奶奶,眼睛里转出泪花:“我们的扶贫干部没明没夜替老百姓着想,真是太辛苦了,跟老百姓就处成这种关系,真是太感人了。”
新屋,新居,老奶奶被安置在装修时做的“炕”上。杨娥子刘大婶说是舍不得离开老村子,但是确定搬迁之后,她就准备着新居里的铺的盖的,把压箱底的簇新被褥全拿出来备新房子使用。
厨间已经收拾好,一桶水盛得满满当当。这也是“安锅”的风俗要求。
“安锅”已毕,告一段落,但仅仅是告一段落。安顿新居,中午要“吃糕”。“吃糕”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婚丧嫁娶,起屋上梁,包括喜迁新居,都要请亲朋好友吃宴席。宴席的主角是吃油炸糕。所以,如果路遇熟人,你问他:干啥去?他若答:吃糕去。肯定是去参加亲戚宴会,这是大事。
“吃糕”的油炸糕,要在旧居里炸好,然后拿到新居这一头同大家共享。那一天,男人们忙着在城里“安锅”,村里的女人们也没闲着。忙什么?忙着“炸糕”。
过去村里“吃糕”,工序繁琐。先由女人们淘洗黍米,淘过之后,再由男人们在碓臼里“捣糕”,然后上笼蒸,待黍子面蒸熟,趁热里再由男人们“揣糕”,待糕“揣”好,再用麻绳线勒出圆形黄米糕上胡麻油来炸。这一套劳作,不啻是一个仪式过程。
现在做不必如此繁杂,确定好“安锅”日子,大家就买好糕面,几个妇女在秀清家里蒸了半个上午,炸糕炸了半个上午,等赶到大家把糕运到新居那一头,糕还热腾腾、香喷喷。
6户人家,分三摊子“吃糕”,刘福有家一摊,张秀清家又一摊,李虎仁由弟弟李云虎张罗,也摆下一摊。三摊子都请了驻村的工作队员,队长老周周胜贤,老曹曹元庆,小周周继平,当然,还有第一书记陈福庆,他们分成三摊子被扯到各家去。
几户人家都没有叫旁人来参加喜迁新居的“吃糕”宴,叫的全是工作队员。老刘说:“来来来,你们今天得来,没有你们忙前忙后,我就是把自己一个人弄到这里来都没信心。你们就是我们的亲戚——比亲戚还亲。”
这是“吃糕”。“吃糕”之后,“安锅”定居的仪式便全部结束了。老刘其实是喝好酒了,那一天,多喝了两杯,喝完就有些头晕的,但是他又不能歇着。“安锅”完毕,并不意味着家全部搬完,在搬完东西之前,按照风俗,中午绝不能因为这因为那躺在床上休息。
家还要搬两天,从22号一直搬到24号。由县人大工作队帮忙,再雇用农用车,把家里的杂物,还有卸下来的牛栏羊栏木头,全部搬到宋木沟村保管起来。
在搬家之前,各家的多余存粮都由工作队联系卖了出去,留存的种子也妥善保管。各家一概杂物,则由乡里协调,在宋木沟村找一个地方保管起来。这样一家一家给搬,搬完这一家搬那一家,最后一家轮到老刘刘福有。
老刘的东西则要搬到玉龙村亲戚家里保管,东西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往玉龙村寄放的大宗物品,一类是要寄放在阳坪乡或者城里儿子刘永兵家的,再一类就是能够在新居里继续使用的。这样,东西要装三车,跑三趟。
搬家搬了好几天,9月24日就搬得差不多了。这一天,一大早陈福庆就叫老刘的儿子刘永兵,还有老刘一块回到村里,又是一上午忙乱。陈福庆的《民情日志》里这样记载这一天:
昨天搬了一天,还剩部分零碎东西没有收拾。一大早,我和老刘、永兵来到上房,继续收拾,东西分了三类,有上楼的,有去永兵处的,有去玉龙村的。
老刘有两个油篓,舍不得扔,大伙劝他丢下吧,但老刘执意要拿。还有许多旧衣服。
装车的工人师傅们有点急,想走了,我劝说了一会儿。其实他们不懂刘大叔的心思,我懂。刘大叔在这屋里住了将近一辈子,家里的牛、锅、勺子、凳子,各种物件,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他注入了太多的感情。他也知道,这些东西在以后的生活中用不着了,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对老朋友告别,对过去的一切告别。我叮嘱师傅们,一定要按照刘大叔的意思把这些东西寄放在玉龙村。
我自己也搬过家,感同身受。
我边搬家边安抚刘大叔的情绪,不时和他开个玩笑,畅谈一下以后的生活,还有现在的年轻人怎么生活。给他讲使用微信的好处,可以买东西,不用把钱装在身上。如果在这里再待下去,就与现代文明隔绝了,不了解外边的世界。
我劝他,现在种田,也不像过去那样,如果不科学,也打不下多少粮食。像河北、黑龙江,那些地方的人种田,都是现代化、机械化,您在这儿种,还得拿个镢头一棵禾苗子一棵禾苗子地挖,既费时,又费力。咱们赶上了好时代,国家不让每一个人在小康路上掉队,别人喝牛奶,吃面包,我们还在这儿啃馒头,喝稀饭,同样能填饱肚子,但生活质量不一样。
我劝他,别人坐上车就到了医院,生病能及时得到救治,在这儿全靠乡医疗队,乡医疗队就那么几个人,全乡1000多号人,把阳坪乡所有村子全部跑遍也得好几天,还没有现代的医疗设备,给您确诊不了病情。救护车拉您到县城,最快也得30分钟吧。
刘大叔心里其实轻松得很,我只不过用这种方式化解他的愁绪。此时此刻,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故土难离,什么叫乡愁。
乡愁就是刘大叔和杨婶子对老牛的轻轻诉说,轻轻地抚摸。
乡愁就是刘大叔家早晨烟囱上的那一缕一缕青烟。
乡愁是改兰大姐搬家时的晶莹的泪珠。
乡愁是那口老水井哗哗的提水声。
那一天,老刘的两头牛也卖了。“牙子”不用联系,人家的鼻子隔十里就能闻得见钱味道,一番讨价还价,工作队再说合,两头牛作价3万元。这个价钱还公道。22号“安锅”,刘福有就没有在新房子里住,“吃糕”完毕,陈福庆又开车把他送回村里,牛得照顾。牛要出卖,他舍不得,要好好陪陪老伙计。
刘福有在院里收拾这收拾那,这也舍不得扔,那也舍不得扔,等得外头的司机都着急。最舍不得的,实际上还是牛。“牙子”是两个人,两个人进了村,刘福有领到老屋前头,两头牛正在那里吃草。早就相看过牛,两头大黄犍牛让两个“牙子”很满意。现在再相看一回,两天里没什么变化。“牙子”把一沓钱递过来,刘福有再递给老伴,老伴接了钱,手软得连钱都不能数,眼泪哗哗哗哗就流了下来。老伴把钱递给刘福有,跑到牛栏边,又给老牛抱了一抱青玉米,说:“你们欢欢吃些,你们欢欢吃些!”话未说完,已经吸吸溜溜哭得不成样子。
她扁个嘴对牛经纪说:“你们不能杀我那牛啊,要杀我就不卖了。”
牛经纪说:“大娘,我们不杀,你一万个放心。”
牛被牵出来。陈福庆怕刘大叔难受,一个劲安慰他。刘福有说:“我不咋,得小心我那老婆子难受哩!”
牛好像知道要离开刘福有,就不跟牛经纪走,刘福有见状,上前来拉住一头牛的缰绳,这才缓缓地把两头牛拉到牛经纪开来的农用车旁边。后马槽架了板,刘福有站在车上往上拉牛。一头牛顺利上了车,但另一头扯着脖子怎么也不愿意上车。
刘福有一边轻轻牵,一边对牛说:“你来吧,我还在这呢怕甚?不怕,不怕,来,上来吧。”
牛听他这样说,犹豫了片刻,双蹄也就踏上木板。刘福有说:“看看,我还在这呢,怕甚?不怕,不怕。”
老伴杨娥子躲进屋里没出来。
轮到陈福庆难受,是在9月27号这一天。全村6户人家都搬完了,然后轮到搬工作站。
需要说明的是,大家回村来搬东西,拆迁的挖掘机就在一边待命。一家的东西前脚搬完,后脚房子都要拆掉、平整。拆房子的时候,陈福庆怕大家难受,都要等户主走了之后再拆。
这一天,搬完工作站的东西,无非是一些文件柜、厨具,倒也简单,大家你拿一件我拿一件就装了车。车子发动之前,蓝烟缭绕响了几个炮,炮仗在旷野里炸响,嘎啦啦啦传得挺远。
老刘搬家还不利索,旧院子里有一些零碎东西还没有搬完,最重要的一件,是刘福有老娘的棺木。棺木早在他父亲去世之前就已经备好,一直放在空房子里头,这是一家财富的重要构成,老人年迈,唯一让她感到欣慰的,就是自己已经有了“家当”,这个家当的有无,跟有没有住的房舍同等重要。这个“家当”属于大件,玉龙村亲戚家里无法安放,只能送到宋木沟妥善保管好。
那一天中午,工作站拆掉了,陈福庆提议,咱们这也算搬家,中午吃一顿糕,也算吃个搬家饭。工作站和乡里的同志都同意。看着瞬间拆倒的工作站,大家都很感慨,便都赞成,说:“这个搬家饭,一定要吃。”
搬家饭需要回城里去吃的,地点是在工作队队员周继平的家里。近中午,周继平的妻子炒了几个菜,煮几盘饺子下锅,再炸几盘油糕,三下五除二摆起一桌。大家吃着,老刘刘福有和乡亲们也在,老刘好喝两杯,就给他弄了一点酒,自酌自饮起来。直到饮到面膛红润,他才问:“你们怎么不喝酒?”
陈福庆说:“现在是工作时间,中午不能喝酒的。”
老刘明白了,理解,说:“噢。”说完,又滋的一声下去一杯。站起来,他说:“我喝得有点多,连腿都拉不动了一下午的事情,全托付陈书记了。”
下午,要把刘福有院里的零乱东西和拆下来的木头,还有他老娘的棺木拉到宋木沟去,老刘却回新居沉沉睡了一大觉,没有去。陈福庆怎么不明白?刘福有实在是不想看自己那处住了四十多年的老屋瞬间变成一片废墟的情景啊。
拆了工作站,陈福庆才觉得自己与赵家洼相处这一年多时间,绝不仅仅是时间的累积,这个地方跟自己的人生有太多瓜葛,理不清,扯不断。陈福庆要比老刘更难受。这一天的《民情日志》里如是说:
待了一年六个月的工作站,一眨眼间便成了一片平地。拆掉的是衰败,是落后,是贫穷,是守旧的思想,只有彻底拆掉守旧的观点,才能真正建立起小康的家园。尽管这里也有工作队太多的不舍,但为了乡亲们能早点走出山沟,过上幸福生活,拆旧是必须的,这也是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