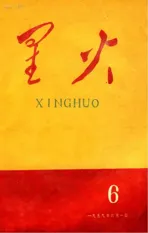黑骡王子
2021-11-09大象
大象
1
我们家里的那头骡子跑丢的时候,爷爷正在街上跟打烧饼的王二说话。他跟王二说好了,让对方给他加工一个烧饼,上面要密密麻麻地沾满芝麻。这是他多年的一个梦想。爷爷没有别的爱好,他有时候喜欢吃口好的。他远远看着人群从街上叫喊着奔跑过去,心里骂了句娘。他提好趿拉在脚上的布鞋,没来得及跟王二说一声,就朝远处溅起一片尘土的人群奔去。那个烧饼刚刚贴进炉里,还没熟透,自然就还没有揭下来。王二媳妇在后面大声朝他喊着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清。
爷爷和村里众人一起把那头骡子找回来时,天已经黑了。他跑到王二家里,想要回那个已经付了钱的烧饼,但是,那个烧饼已经让王二家的孩子们分吃了。王二有些不耐烦地把钱退给了他,并说叔啊,你就不是吃烧饼的命。王二媳妇也凑过来打趣说,叔啊,这个烧饼沾了有五个烧饼的芝麻,给你留了一个下午。现在炉子凉了,炭也灭了,你老人家却来了。
这一回,爷爷是料定可以吃上沾满芝麻的烧饼的,所以,在离开家之前,还特意带上了我。他背着手朝家里走时,嘴里不停地埋怨着黑王子。黑王子呀,黑王子,你怎么就不能让我吃口好的呢?我这辈子也没亏待过你,每顿都给你最好的草料,还放了你爱吃的豆饼,你为啥就不能也让我吃口好的?我跟在爷爷背后,觉得他的样子有些好笑。黑王子是他那头黑骡子的绰号。爷爷说,从集上看到它的那一眼,他就觉得这名字非它莫属。但是,我们平常却并不这样叫它,我们只叫它老黑。因为我们都听说过“白马王子”,却没听说过“黑骡王子”。
这样走了一路,爷爷才叹了口气说,算了算了,这次就算能吃上烧饼,也没有羊肉搭配。你不知道,烧饼配羊肉才好吃呢。刚揭下炉的烧饼,热腾腾,香喷喷,从一边撕开一个小口儿,五香味儿便飘了出来。这时,趁热把切碎的羊肉塞进去,按一按,狠狠咬上一大口,那才叫过瘾呢。爷爷的话,勾出了我喉咙里的馋虫,让我的口水都淌了出来。我禁不住跑到前边,抬起头问,爷爷爷爷,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烧饼夹肉呢?爷爷说,不急,下一回县里卤肉店的老李来了,我让他先给咱爷俩整半斤羊肉。
我和爷爷回到香油坊的时候,黑骡子正在拉磨。它去浪了整整一个下午,今天该干的活儿还没有干完。它早该知道,主人不会轻易饶它,想偷懒,可没有那么容易。我看着磨棚里的骡子,又想起它白天逃跑时候的情景。那天,金立家轧麦子,金黄的麦秸摊在麦场上,一边儿树底下还停放着青色的石磙。因为黑骡子出了一上午的力,金立媳妇中午特意给它弄了草料和豆饼。他们全家回家吃饭的时候,给它解开了笼套,只是用一根绳子拴在麦场边的大柳树下。金立媳妇后来说,当时骡子显得驯顺而安稳。它耷拉着眼皮,卧在地上,似乎打算好了,要趁着空闲睡一场午觉。
当然,事实证明,这一切只是在为它的逃跑打掩护。在金立全家人吃完饭回来的时候,看着树上被它咬断的缰绳才恍然大悟,这是一次有预谋的出逃。或许,它已经等待了许久,谋划了很久。那时候,骡子是宝贝,如果弄丢了骡子,他们全家这一季就算白忙活了。金立媳妇吓得两腿瘫软,坐在地上不能起来。金立顾不得她,一边往村中跑,一边大喊起来。他的喊声惊动了四邻。村子中正在吃饭或者睡午觉的男人们都跑了出来。
最后跑出的是二叔和父亲。二叔不慌不忙,他似乎心里有数。因为对于这头骡子来说,这样的离家出走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而且,每一次都是以乖乖地回来而告终。有一次,黑骡子是从白洼林场找回来的。大家远远地发现它时,它正站在那高高的河堤上,时而来回奔跑,时而低头啜几口青草,时而啃一啃那些香甜的榆树皮。有一次,他从村子里一气跑到了三十里外的县城。村人发现它时,它正低头,专心地咀嚼着人家晾晒在地上的酒糟。这次捕捉,不费吹灰之力。可能是因为吃了太多酒糟的缘故,它回来的路上东倒西歪。那之后的两三天里,它拉磨时四条腿儿还有些搅拌。
有一次,黑骡子是跑到了邻村一个农户家里。那家喂了一头褐色的母骡子。那骡子眼睫毛很长,眉眼很好看。尤其是两只耳朵,雪白的,像两只可爱的兔子耳朵。村里人赶到那里时,发现它正跟那只母骡子耳鬓厮磨。大家不由分说地奔过去,七手八脚将它按倒在地上。黑骡子委屈地叫着,甚至衔掉二叔的帽子,用蹄子踢踏起来。二叔在村人面前丢了丑,捡起帽子,气急败坏地朝它裆里的那条大棍扇了两个巴掌。在回来的路上,村里人一直在议论骡子这驴马交配的杂种,何以也发起情来,它们不是不能繁衍后代的吗?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是爷爷一句话做了总结。爷爷说,这就像人家说的一桌满汉全席,咱吃不上归吃不上,还不能想想吗?
这一次,骡子去了县城的文化广场。文化广场正巧有一个业余的四平调戏班在唱戏。跟往常一样,广场上坐了一群老头老太太。他们骑着三轮车来到这里,每人搬着一个小马扎。那头骡子就在文化广场不远处的土坡上,一棵婆娑的合欢树树荫下,卧在那里。它那样子,仿佛正支着耳朵,远远地听着啥。人们都有些惊讶,怯怯地不敢靠近。有人说,这骡子成精了呀,还是个戏迷!
父亲和二叔也犹豫地站在那里,他们倒不是觉得它成精,主要是怕万一惊了他,乱跑起来,会冲撞了场上的那些老人。他们手脚都不灵便,万一有个闪失,那可等着给他们养老吧。但是,这一次,竟然是骡子先看到了二叔。它眨巴眨巴眼睛,浑身的肌肉连续抖动了几下,便站了起来。村里人都拿出了藏在身后的绳子、笼套、木叉等工具,紧一紧身子,拉开了追赶捉拿的架势。但是,这次骡子并没朝远处奔跑,而是犹豫片刻,就朝着二叔踏踏地走了过来。整个捕捉过程有惊无险,很多人甚至感觉到有些小小的失落。
2
我们家的香油坊是爷爷一手兴办起来的,现在他退居二线,把这个行当交给了父亲和二叔。他们两人各从爷爷那里继承了一半的股份。当然,也包括这头黑骡子。爷爷走进磨坊,很心疼地摸了摸骡子的鬃毛,喃喃地问:老黑,你要去哪里呢?你心里惦记着谁?你这一趟一趟地出去,又一趟一趟地被抓回来,你倒是长点本事,撒开蹄子,一气跑出镇子,跑出这个县和这个省,一气跑到内蒙古大草原上去,才算你有本事呢!在那里,说不定就会有一个俊美的母骡子等着你哩!
骡子的鼻腔里“吭吭”了两声,仿佛在提醒爷爷,它听懂了主人的话。但是,脚底下却不停歇,就像一台上足了发条的机器,围着沉重的酱红色磨盘,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它的皮毛因为被汗水浸湿,颜色不再那样均匀,变得深一块浅一块。它身上的肌肉,也时不时因为痉挛,而不住猛烈跳动着。爷爷自说自话,完全不顾一旁添芝麻的二叔的唉声叹气,也不管弄油饼的母亲投过来的白眼。
爷爷在那儿吸了一袋烟,就领着我,从磨坊里走出来了。在我们脚刚刚跨出门槛的那一刻,二叔从后面开了腔。爹,二叔说,今天这么多活儿都堆在了一起,你老人家能不能搭把手。爷爷听见他的话,却只是有些不屑地“哼”了一声,便走出门,走进了夜色。在夜色中,爷爷轻轻抚摸着我的脑袋,温和地说,乖孙子,跟爷爷喝酒去,爷爷那里有猪头肉。
在路上,我问爷爷,大黑骡子真能听懂你的话吗?爷爷叹口气说,它懂个啥?它如果能听懂,就会挣断缰绳,奔跑着去那个遥远的,我口中说的草原,去过自己想要的好日子。爷爷“嘿嘿”笑了两声,然后说,去吃好的喝好的。
那时候,二叔家五个孩子,我们家三个孩子。虽然家里有一座香油坊,但生活过得并不富裕。爷爷的好吃懒做,让母亲和婶婶心里很是不快。虽然表面上不说,可背后总要暗暗嘀咕。按照村里人的说法,爷爷隔三差五便要吃一次猪头肉,或猪耳朵,或猪下水。卖这些东西的是县城义和卤肉铺的李老板。他骑着自行车,后座上的竹筐里装满这些东西。
每过几天,他就要到村里来一次。母亲说,他一到我家门前,就要停下车子,点上一支烟,装作要歇上一会儿。他的目的,当然是等爷爷出去买。有一次,我家的院门“哐当”一声开了。正蹲在地上的李老板一下站起来,朝着我家的院门笑脸相迎。这一回,他看到的却是我的奶奶。那天,我爷爷去了五六里外的洼里干活,还没回来。
李老板显得有些尴尬,没话找话地问:吃猪头肉的在家吗?这话让奶奶羞愧得不行,回答说,吃猪头肉的没在家。说完竟然忘了开门干啥,羞惭惭地扭头回去了。那时候,各家都不富裕,好吃懒做,是会被人笑话的。这件事后来就成了公开的秘密。我们全家老小,都可以拿来说笑。甚至后来成为全村人熟知的典故,成为大家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但就算这样,也并没有改变爷爷的生活习惯。
我是爷爷最疼爱的孙子。据我所知,村人的那些传言,并不属实。爷爷爱吃卤肉是真,但也并不像大家说的,买得那样勤。他往往是好几个月才买一次,买的量也很少。拿回去切成薄薄的片儿,扣在瓷碗里,喝酒的时候,用筷子衔上一片两片,丢给挨在桌子对面的我。然后,他舔一舔筷头儿,喝一口酒。这是我跟爷爷的秘密,我不愿告诉人。爷爷对这些肉的味道仿佛很喜欢,常常说“你吃肉,我吃味”。
他常常装出很在行的样子,说县里这家卤肉店的肘子好吃,那家烧鸡店的鸡腿地道。他最为佩服的,要数义和卤肉店李老板的手艺。说真是不一般,做出来的东西色香味俱全。我便明白了,爷爷除了吃味,还看色,还闻香。这样,我便心安理得地饕餮起来。我们家有八个孩子,叔叔家五个都是女娃。我有两个姐姐,我是家里的独苗。前些年,婶子想要生个男娃,最终肚子不争气,只得放弃了。
其实,爷爷喝酒的时候,吃得最多的是一种花生米。那花生米用盐水浸过,再晾晒炒制,吃起来有盐味儿,花椒茴香味儿,酥脆可口。爷爷把那些花生米装在一个塑料桶里,吃时就倒出一点。我有时候好奇地问爷爷,你真的不喜欢吃肉吗?爷爷说,这世界上还有不喜欢吃肉的人?将来有钱了,一定要把想吃的东西都吃个够。我看着爷爷兴奋的眼神,还有那个让酒精烧得红彤彤的脸庞,对他说的那种生活也心生向往。
爷爷曾经偷偷地跟我说,人活一辈子,就是为了吃口好的,穿件好的。不然,还有个啥念想?如果连想吃口啥都吃不上,那不是连个动物也不如了?我不管他们说啥,我的猪头肉是照吃,酒也照喝!爷爷唠叨着。虽然他常这样说,可是我却感到,他活得似乎并不如意。因为很多他想吃的,都还没有吃到。例如,北京全聚德的烤鸭,新疆吐鲁番的葡萄,烟台莱阳的大鸭梨,南京的咸水鸭。这些都是他经常惦记的。他常常说,连想吃点儿啥都吃不上,这日子过的,真没意思。
那时候,除了香油坊,家里的大人还要干地里的农活,负担就比村里其他人重了很多。爷爷把香油坊交给两个儿子之后,开始的两年,整日游手好闲,在村里村外逛来逛去。在抢收抢种的时节,有人问他:你是个二流子吗?他不屑地回答:我退休了呀!人家就望着他的背影,等他走远,“呸”地往地下吐一口浓痰。他经常骑着一辆半新的大金鹿自行车,铃铛一按很清脆,链瓦和辐条也擦得亮晶晶的。在夏天里,他会戴上一顶礼帽,《上海滩》里周润发戴的那一种。
有一年,不知他从哪儿弄了一条半旧的石青色牛仔裤。那时候,牛仔裤在城里刚刚时兴,电视上港台片里时髦的年轻男女,都是这副打扮,但是,爷爷却弄了一条,还整天穿在身上。他跟村里其他老人不一样,从不打牌,也不听戏,更不钓鱼,整天就是在村里村外闲逛。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弄吃的。柳树的嫩芽出来时,摘了吃柳树的嫩芽;杨花刚长成能吃时,摘了吃杨树的嫩花。荠菜、槐花、榆钱就更不用说了。
夏天里可以吃的就更多。蝗虫的后腿儿可以烧着吃;青蛙的后腿可以炖菜下酒;田鼠和蛇也可以捉来打牙祭。这些我都是不吃的,嫌恶心。有一回,爷爷逮着一只野鸽子,喊我去吃,鸡蛋大小的一坨肉。我尝了一点儿,有些土腥气。爷爷说:咦!要吃走兽,还是狗肉;要吃飞禽,还是波鸽(鸽子)鹌鹑!我没有分辩,心里想那是鸽子吗?那只是野鸽子,学名鹧鸪。
3
那时候最忙的,便是收麦的季节。麦子成熟了,要赶着收获,不然麦粒儿就会掉在地里;收到家里还要赶紧脱粒,不然的话,一场雨下来,麦子淋了雨生了芽子,这一年就只能吃漆黑牙碜的面粉。有一年收麦,母亲和二婶联合起来,特意找到爷爷,跟他商量着,想让他照看我们几个小孩。她们的要求当然被爷爷断然拒绝了。爷爷没有抬头,只是冷笑了一下,嘴唇间露出一点儿白牙,有些不屑地说,我才不干这个。我知道,干这个要担责任的!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干脆不干,好歹都不用担责任。
虽然,爷爷宣称不看我家和叔叔家的孩子,开始的几年也一直坚持着,但到了我小时候,情况还是不得不发生了转变。在我之前,妈妈生的两个都是女孩,婶婶家里也只是几个女娃。在我出生以后,母亲一下子有了底气,终于开始了新一轮改变现状的努力。再加上,以前虽然爷爷从不照看孙子,可奶奶却欢喜地担负起了这一任务。她就算下地干活儿,也身上背着一个,手里牵着一个。有时候,跟的多了,她还会把我们全部放在板车上,她一个人推着。用奶奶的话说,这叫“虱子多了不觉咬”。这也就是说,爷爷在很多年里,之所以落得轻松,很大程度上是把这项负担转嫁给了奶奶。
有一年麦收,奶奶扭了腰,只能卧床休息,几个孩子便没了着落。有一天,大姐跟着母亲父亲去地里玩儿,不小心用镰刀割伤了手。母亲把她带到镇上卫生所,包扎之后,便拖着她回了娘家。她临走给父亲撂下狠话,说孩子谁也不用看了,她自己看,带回娘家看。孩子也不用姓程了,改姓李算了。那时候,我还没有掐奶。她的狠心离去,让我的吃饭问题没有了着落。但是,母亲到娘家之后才发现了这一问题。又赶来接我时,我已经被爷爷抱着藏到邻居家里去了。母亲空手而归,没有得到我这个本来可以用来要挟婆家的重要砝码。
那天中午,我嗷嗷待哺,只能吃些面汤充饥。傍晚时分,父亲套上骡车,去李庄将母亲和姐姐接了回来。父亲给老丈母娘带去了两只老母鸡,同时带去的,还有爷爷的一句话,“看孩子的事儿好商量”。这句话为爷爷以后讨价还价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其结果,是爷爷答应看娃,却只答应看男娃,也就是只看我。虽然,看似双方都做出了妥协,可毕竟爷爷再不能跟以前一样游手好闲。更重要的,他原来的那种强硬态度和高傲姿态已经一扫而光。他像一只斗败的大公鸡一样,从此以后,每当见到母亲,眼神漂移躲闪,有时候甚至怯怯的。
虽然表面尊重着,可从那以后,母亲对于爷爷,常常没有好话。母亲生气了,便会在背地里骂爷爷。母亲说,这个怪老头,从前就不是什么好人;他要是好人,解放前也不会当逃兵。我问母亲为什么,母亲说,他心里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这件事儿,我曾委婉地问过爷爷。他不承认他当过逃兵,只说自己是一个老革命,本来应该吃国家粮,享受更高待遇的。
那为什么却没有享受,反而回来做了一个农民呢?我心里一直有这个疑惑。但爷爷说到这里,便打住了。后来有一次,奶奶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她说,那是因为当时爷爷看人家卖香油挣钱,便回老家开了香油坊,改行卖香油了。当时,爷爷也在场,这个说法至少得到了爷爷的默认。
这事如果是真的,多少有些荒唐,但不得不说也真是符合爷爷的性格。正所谓求仁得仁,爷爷回来开香油坊之后,还真的发了些小财。他买了几亩地,还买了这头黑骡子。当然,后来不管是骡子还是地,都充了公。这黑骡子重新回到爷爷手中,是在分了地之后。那时,农村又重新鼓励大家做小买卖,爷爷就用积攒下来的钱把它买了回来。当时,很多人都不赞成爷爷这样做。因为,骡子的寿命顶多三十来年,而那头骡子,少说也得二十多岁了。而且,在队里的时候,养成一个坏毛病,就是好吃懒做,还喜欢逃跑。
这头骡子个头很大,叫声非常响亮,但是它每年都要逃跑几次,尤其是在耕种和收获的时候。那时,村里只有一匹马,一头牛,一匹骡子,一台十二马力的拖拉机,都是生产队留下的。因为农业还远远没有实现机械化,拉车、耕地、耘草,都离不开牲口。我们家的这头大黑骡子除了拉磨磨香油,春秋两季,还要负担全村好多人家种种收收的任务。每当那时,黑骡子总会伺机逃跑。
这头骡子几乎帮村里所有人家都耕过地,所以,在它逃跑后,只要父亲或者二叔一声吆喝,全村的男劳力都会丢下手头的活计,集合起来,加入寻找骡子的队伍。这让黑骡子在有生之年做过的无数次的努力,最终都没有如愿以偿。
4
大家是从那次发现骡子跑去县城听戏,意识到它已经步入老年的。骡子的确老了,它在拉磨的时候,步子都有些趔趄。我听父亲母亲叔叔婶婶他们几个私下里讨论过一次,说如果这头骡子哪一天真的走了,如何处理它?母亲不假思索地说,应该把它埋了!母亲的话让我暗暗感动,并由衷地佩服她的有情有义。她的话让磨坊里的气氛显得有些肃穆,大家都不吭声。最后还是爷爷打破了沉默的僵局。他说,畜生就该是有畜生的死法儿,有一个地方才是它最合理的归宿。我们心里都明白,那个所谓的最好的归宿,就是卖给县里的卤肉铺子。
我没想到爷爷会说出这样的话,我心里暗暗埋怨他,并为骡子摊上这么一个主人感到不值。不但要送到卤肉铺子,说不定,他还要跟李老板要点儿心肝或肚子之类的下酒菜哩!我总担心,那黑骡子会在磨盘边走着走着,便一头栽倒在那里,再也起不来。但是,那骡子还没有到老死的那一天,就又一次逃跑了。黑骡子最后这次逃跑时,我正犯着阑尾炎,在床上疼得打滚儿。骡子跑了,骡子跑了,我听到父亲和二叔的脚步声,听到村里人的叫喊声。人头攒动,人群汹涌,不住地从窗外的街道上滚滚而过。爷爷叫来村里的赤脚医生给我打了一针,我的疼痛才稍微得到了些缓解。
在找人给我打完针后,爷爷也去追赶那头骡子了。也就是这一次,他把自己那条宝贝牛仔裤跌破了,膝盖那儿破了一个口子。
那天,爷爷骑着自行车,到镇上粮食市附近,就看着一群人赶着骡子过来了。爷爷也许是想下车捉它,也许是想把自行车横在那里,挡住骡子的去路。不管怎么说,他那么一拐弯儿,不慎滑倒了,膝盖上跌破了一个口子。他从地上爬起来时,村人都赶了过来。他们七嘴八舌,关切地问摔坏了没有。爷爷不理他们,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破洞里露出的一块肉。过了半天才摇摇头,脸上显出惋惜的神情。大家看他没事,又要追着骡子奔去。可是这一次,爷爷拦住了大家。他说,让它跑吧,让它跑吧!它跑够了,总会回来的。就算不回来,又有啥?爱干啥,让它干点儿啥去吧!
大家面面相觑,但看爷爷说得严肃,想想也有道理,便泄了气。他娘的,回来我好好收拾它!二叔说。父亲也叹了口气,跟大伙儿说:俺爹说了不让找,都回吧,谢谢了!他们刚一回来,便挨了母亲和婶婶的一顿数落。母亲说,是死是活,是好是歹,总要知道个结果。这样任它哪儿去,不管不问,算什么呢?叔叔说,老马识途,骡子也一样。它会回来的。父亲说,它这一把年纪了,想出去散散心,就让它去吧。它为咱们大家活了一辈子,也该为自己活一次。
你这个糊涂虫,母亲数落道,它如果被车撞了怎么办?如果被坏人打伤了怎么办?
这样,一家人惴惴不安地等待了一夜,也没见黑骡子回来。第二天天不亮,父亲和二叔他们就又喊了几个村人,出去找骡子了。那天上午,因为阑尾还有些疼,我又打了一针。打完针之后,我跟一边的爷爷说,爷爷,你去找骡子吧。爷爷说不找了,它愿意上哪里去就上哪里去吧。你爹昨天说得对,这辈子,他给咱家出了太多的力,应该去散散心了,应该让它去干点它自己愿意干的事儿了。
我感到爷爷的话有些好笑,又不敢笑,因为怕肚子疼。我说,一头骡子,除了拉磨和下地干活,还能有什么事儿可以干呢?爷爷说,那可不一定,你不是骡子,你又怎么知道骡子心里怎么想的呢?傍晚,父亲回来了,二叔回来了,母亲和婶子也回来了。他们一回来就瘫倒在椅子上。二叔大骂起来,这个畜生,它是反了天了!等找着它,我非要揭了它的皮!爷爷无声地笑了起来。他老了,掉了一颗门牙、一颗犬牙,槽牙全掉光了,这让他说话有些漏气,声音显得有些滑稽。他说,别傻啦,这一回,你们找不到它的,除非它心软了,自己回来。以前的那些回,如果不是它心软,也不会让你们找到的。大家听了爷爷的话,都不吭声。二叔白了他一眼,小声道,真是老糊涂了。
虽然当初是爷爷拿主意,不让大家去找,但在骡子跑掉以后,尤其是到了第三天以后,他还是开始显得有些惶惶不安。他们又去找骡子了,爷爷跟我待在家里。爷爷有些内疚地说,这次骡子跑丢之前,喂草料的时候,因为老家伙有些挑食,我破例打了它两鞭子!爷爷说完,去到院子里。我从窗口望出去,看到他往骡子的石槽里加了些草料,又把有些受潮的豆饼摊开,晾晒在屋檐下的石头台阶上。
他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已经洗净晾晒干的那条牛仔裤。牛仔裤破了,只有叠起来放在箱子里了。奶奶有缝纫机,之前曾经提到要给他修一修,但他不肯,他不相信奶奶的技术。那时候,社会上还没有流行乞丐服,如果流行,我想爷爷肯定会堂而皇之地穿出去的。我问爷爷打算拿牛仔裤怎么样?爷爷说,不穿了,以后有了钱,买一条新的。我知道,这只不过是托辞罢了。他开了一辈子香油坊,有两个儿子,都是村子里的富户,他怎么会买不起一条牛仔裤呢?
那些年,我跟爷爷晚上是睡在同一条炕上的。那天晚上,他辗转反侧,好久没有睡着。我知道他有心事,也许他在想他的那头黑骡子。我知道他没睡着,便问他,你年轻的时候当兵,怎么就回来了?不回来,你就是老革命,我不是成了高干子弟?
爷爷在黑暗里一笑,说傻孩子,爷爷不回来就没有你了!我当了大官,还不娶个城里的漂亮娘们,还能找你奶奶?他说话的声音有些伤感,似乎考虑了许久,才开口说:我其实也不想回来,我回来是被逼的!那时候,南征北战,你老奶奶总担心我会被敌人打死!我再不回来,你老奶奶就要变疯了!所以,给部队上打了报告,还背了一个处分,回来了。人这辈子,能为自己活几回呢?
我感觉喉咙里干干涩涩的,半天才问,爷爷,你不后悔?爷爷说,后悔啥?后悔也没用。
这番对话,让我心里有些怅惘,想起爷爷满脸的皱纹,想起他苍白的胡须和头发,想起他一笑起来残缺不全的牙齿和光秃秃的牙床。当年,爷爷从部队回来时,肯定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爷爷老了,像家里的这头骡子一样。那是我小学最后一个暑假,开学之后,我就要升入镇上的那座初中,再也不用爷爷照看。爷爷老了,我也长大了。
第二天早上,黑骡子已经整整跑丢三天三夜了。爷爷终于忍不住了,他骑上了他那辆大金鹿的自行车,出去找骡子了。那头骡子是在爷爷离开后的第二天傍晚,自己跑回来的。我们大家都欣喜若狂,但都不知道它怎么回来的,也不知道他这几天都去了哪里。仿佛一觉醒来,它正在牲口棚里站着,甜美地咀嚼着爷爷给它留下的草料。
那天,直到夜色深了,我们才想起,应该派人去把爷爷找回来。全村的男人都出动了,去了镇上、县里、火车站和汽车站,但到处都没有爷爷的影子。我们不知道爷爷去了哪里。直到爷爷失踪一个月之后,奶奶才抹着眼泪向大家宣告,老头子可能不回来了,因为,他拿走了他自己攒了一辈子的那份“私房钱”。那私房钱他这辈子一直藏在那顶礼帽的夹层里,奶奶早就知道,只是没有说破。这一回,爷爷把那顶礼帽戴走了。奶奶的话让好多人都哭了起来。可是我却知道,也许爷爷再也不会回来了,也许哪一天,他会穿着一条崭新的牛仔裤,重新回到程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