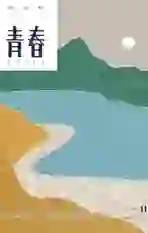残碑里的时光
2021-11-04周吉敏
周吉敏
1
山水是禅。
洞宫山脉自闽北入浙南后,在温州西部,向东和北延伸扩展成南雁荡山脉、北雁荡山脉和括苍山脉。泽雅在南雁荡山脉的盘根错节处。境内,峡谷深幽,青峰千仞,涧水在青绿间奔走。泽雅以西,南雁荡山脉延展出崎云小山脉,瑞安、泽雅与丽水市青田县交界于此,主峰海拔1164.8米,峰下有五代时古刹极乐禅寺,寺碑记载:
极乐禅刹甲于永嘉西路诸山。唐季龙纪间,镜清恷禅师创始于孤峰之顶,名极云。谒灵峰者□若陟于磴,莫不争先而趋焉。大德伏虎以骑,鹿训以跨,出入乎浮岚集翠之表……
——唐昭宗龙纪年,也就是公元889年,镜清恷禅师云游至永嘉(温州)西面山中,见峡谷、瀑布、激流、森林、草地,氤氲着独特而神秘的气息,有虎、鹿、羚羊等精灵们在林野中生息雀跃。又登上高峰,见烟云缥缈中青山万重,如如不动。镜清恷禅师在峰顶建了一座禅院,取名极云寺。
镜清恷禅师讲经时,老虎自林中而出,鹿也欢欣而至,伏在禅师身旁。禅师也经常骑着老虎,或跨着鹿,穿行在云岚和绿野间。虎和鹿是灵善之物。特别是虎,集猛兽罕有的三个特点于一身,一是辟邪,《风俗通义》中谓:“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二是虎能听佛法,具有灵善之性。三是虎能感应人间善恶,维持正义。历史文献和志书中,常有禅师伏虎驯鹿的记载。民间传说,永嘉建郡城时,一只白鹿从林中衔花而来,绕河谷平原一圈又跃入林中,人们视为祥瑞,按白鹿足迹建城郭,城就叫白鹿城。鹿城之名,温州至今还在沿用。
极乐禅寺逐渐成为温州西部著名的禅寺。孤峰之上,烟云缭绕,梵音在峡谷中流转。信众不畏山峰险峻,虔诚地争先前来拜谒。施主夏九,发善心,捐出自家的良田作为极乐禅寺的恒产,供养寺僧。到了基禅师时,因寺在孤峰上搬运物品太艰难,把寺移到前山向阳的地方,也方便从事耕种。
极乐禅寺从唐代,两宋,到元代,从镜清恷禅师、基禅师、荣禅师、无暇璨禅师、华谷声禅师,四百多年的时间里,在山谷中历风沐雨,花开花落。
元至正年间,铁关武公来镇守极乐寺山门,发愿重振寺宇庄严。施主林君美,是瑞安三川人,为人耿介,才德超群,喜欢与僧人交游,常携友人到极乐寺与铁关谈禅。一日,谈禅之余,乐然捐出自家膏腴之田的租谷百石,补足重建极乐禅寺的经费,同时,又刻大士妙相两座,刻成之后,又捐了一些租谷。极乐禅寺焕然一新。古有夏九与镜清恷禅师,亦有林君美与铁关武公。他们的善举,刻在碑上,垂范后世。
撰写极乐寺碑文的作者是时任温州路永嘉县尹林慧生。明万历《温州府志》记为林泉生,字清源,元莆田人,至顺元年进士,官至翰林直学士。林县长“文词名海内”,是“闽中文学四名士”之一。林慧生作为地方官,弘扬地方美德是他的职责所在,其中也有他与君美以及极乐寺铁关禅师的友谊。元代,温州佛教发展的特点是士大夫仰慕寺院的清雅脱俗的环境,与当地高僧大德交往密切,或携手出游,或坐禅论道,或茗茶弈棋,在唱和酬答中交流思想,也常为佛教僧人撰写一些碑铭、僧赞、诗序等文。林慧生与林君美想必是这股文化潮流的先锋。
极乐寺碑立于元至正三年(1343),至今已有600多年。想着,一个有阳光的上午,拓碑人把一张宣纸像一张网似的铺在极乐寺碑上,小心翼翼地把一個个字从时间的海中打捞上来。雪白的纸上,一个个黑色的字慢慢地苏醒过来。
从碑文中我们看见了一座禅寺的兴衰,人们的善举,还有文人、仕宦与寺僧的交游,相对应的是宗教文化、农耕文化与士人文化。
2
佛教东来。但没有人知道佛教何时在东海一隅的温州落地,或许是东海的长风带来,或许从东瓯王的翎羽上飘落下来,或许从青瓷熊熊的火焰中飞溅出来。但是,一位诗人带来佛教的思想,却是永嘉山水可以作证的事实。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谢灵运被贬谪,任永嘉郡守。心不甘情不愿,赴任日期一再迁延,原定夏末到任,直到秋天才顺着瓯江而下,踏上这座滨海小城。这位满腹郁闷的诗人,给温州带来文学的才华,也带来了佛教思想。
谢灵运与佛徒有相当深的因缘,他与慧琳友善,同为庐陵王义真的入幕之宾。曾见高僧慧远于匡庐,其他如法勖、僧维、昙隆、法疏等人,也都与之有过交游。前往永嘉,可能有几位僧人同行,到了永嘉后,这些僧人也随从灵运出游,并时常在一起诵经论道。
一日,谢灵运与僧友,去郡城西面的瞿溪山访僧。他们驾一叶扁舟,从郡衙门前的河道出发,出城南,折向西,往峰峦叠嶂处而去。一路上,一个个海迹湖,像明亮的眼睛,照亮谢灵运晦暗的心情。谢灵运登瞿溪山后,写下《过瞿溪山饭僧》:“迎旭凌绝嶝,映泫归溆浦。钻燧断山木,掩岸墐石户……望岭眷灵鹫,延心念净土。若乘四等观,永拔三界苦。”诗中详细描述山民原始的生活,赞美僧友秉志高洁的修行,是谢灵运求助佛教思想摆脱现实苦闷的心灵表达。
谢灵运在永嘉写作了著名的《与诸道人辩宗论》,讨论“渐悟”和“顿悟”,辨析成佛之道。谢灵运的“顿悟”之义源于道生。王弘把谢灵运的书送示道生,道生对谢灵运的阐释总体认可。许倬云在《万古江河》里写道:“竺道生发‘人人皆有佛”的论断,开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理论……竺道生的顿悟论,也可能有孟子学说的影响。后世禅宗由此肇始。”
谢灵运称得上是佛学家,而不是一位佛徒。《金刚经》中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令人精神为之一凛的醒世之言,谢灵运没能据为己有。他太爱生了,他执着于眼前的享受,太害怕一切消失殆尽,因而求助于佛家的思想。
谢灵运在《石壁精舍还湖中》中写道:“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这“清晖”,是自然山水的光芒,也是谢灵运的佛教思想遇上永嘉未染尘的山水迸发出的智慧的光芒。谢灵运其实是山水光芒的采集者,这是他另一个隐匿的身份,连他自己都不会觉察到。谢灵运的山水慧光,一直滋养着后世的诗人,才有了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等等。
据考证,从刘宋开始,瓯窑上开始出现莲花纹。可以说,谢灵运在温州,倡导了一种精神至上的文化生活。他的佛教思想像水一样渗入温州的泥土,培植了一片适宜佛教文化传播的土壤,特别是禅宗。
谢灵运也曾沿瓯江逆流而上,进入戍浦江,游览藤桥的石鼓山,留下山水诗《登上戍石鼓山》。“日没涧增波,云生岭逾叠。”夕阳西下,瓯江潮涨,戍浦江随着也涨起来,潮水会一直涨到层层云岭之后,那里是江的源头——泽雅。
瞿溪与泽雅,分居一道山脉的两面,一墙之隔,接壤生息。泽雅与藤桥,是一脉之水,相依相通。一向热爱寻求人迹罕至的险峻之地,以征服高山大川为兴趣的谢灵运,没有翻过瞿溪山,也没有继续溯戍浦江而上到达源头,诗人的目光无法抵达山水更深处。
在谢灵运的刘宋时,泽雅还没有人烟,还是一块化外之地。那里或许居住着没有随东瓯王内迁江淮的“瓯人”遗民,或许峡谷里还有灭国后避入深山的“越人”,他们在山中就像谢灵运在《瞿溪山饭僧》诗中描述的山民那樣,用泥土涂塞门户,截断树木,钻木取火,过着原始的生活。
到了唐朝,佛教大盛,杜牧诗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况,同样也可以用来描述温州。一座座寺宇在温州山水间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据《温州通史·汉唐卷》载,中和元年至天复二年间(881—902),二十余年间温州地区增加了二十所寺院,极乐禅寺是其中一所。而温州地区佛教发展的繁盛时期则在吴越国(906—978),在此七十年间,温州地区新建了八十六所寺院。
极乐寺,这一朵禅花,开放在繁花凋零的晚唐,孤峰之上的梵音,开启了泽雅文化之先声。催开这朵禅花是唐后期的社会动荡。虽然温州偏安东海一隅,但每一次帝国心脏的搏动,自然牵动着每一根毛细血管。战乱,寺院禅林是那滔滔洪水中的一艘方舟,深山冷岙成为生命的庇护所。
泽雅的高山峡谷中,文明延宕而迟缓。宋时,泽雅属永嘉县泰清乡,有“梅溪里”的记载;明清时属永嘉县泰清乡二十三都,以溪山清胜故名。泽雅,最初只是一个村落名。明弘治《温州府志》作“寨下”,万历《温州府志》作“泽雅”。“寨下”与“泽雅”方言谐音,应是方言雅化而来。时代变迁,行政建制更换,山里200多个自然村落,现在隶属于泽雅镇。不论是“梅溪”“泰清”,还是“泽雅”,从地名里就已看到一片清明的溪山。在明朝,或是宋朝,或是更早的时间,泽雅山民利用山水资源手工造纸,技术与《天工开物》里的造纸如出一辙,延续至今。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文字对于这一方水土却极其吝啬,历代志书文献除了记录几个地名,竟然没有记载这片土地的任何消息。为文字提供安生之所的泽雅,却被文字遗忘。极乐寺碑文成了记录泽雅的历史文章。
布罗代尔说:“宗教是文明最强有力的特征。”刻在石头上的极乐寺碑文,让后人得以窥见千年之前泽雅那一方水土的精神气象——唐时的泽雅高山峡谷中,人还没有多少说话的余地,这里充满着花朵、草树、溪流、山风、雨雪这些土著的声音。而佛祖,在群峰之上拈花微笑。
3
进山,开车与步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沿着古道,血肉之躯踩踏在山体上,是亘古的行走,令人血液澎湃,唤醒人与山最原始的关系。
六年前,我曾沿着古道上北林垟。粗石砌筑成的山道,沿着山势“之”字形延伸,连起一座座山。日光从浓密的竹林中漏下来,投在覆着苍苔的古道上,虽是白日,此中也有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之禅境。那三两声鸟鸣,穿透密林,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禅心也可体会。中国的艺术意境,是人与山水合一的诗意境界。诗也是中国原始的宗教。在山水间参禅、悟道,才得天地真意。
走出丛林,到了山顶,山谷里的人家也就一览无遗了。继续行走和攀登,不断有新的山景和隐匿山间的房屋出现,像捉迷藏,永远指向无尽的山的深处。他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一直在心头像叶子在风中翻飞。这些仍在山里生活的人家,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依着日出日落与季节的轮回,生活的节奏也是天地的节奏。从喧嚣的城市到寂静的山中,才能真正领受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智慧。
车在山间盘旋上升,耳朵似被堵了一层东西似的嗡嗡作响,不断提醒我山的高度,也提醒着我曾经拥有现在已失去的山性。
车窗外,山色葱郁沛然,一路不见村落人家。但我知道那些叫坑源、黄山、石坑的村落,就藏在峡谷里。他们的祖先藏起自己生命的来路,让深山锁住后人飞翔的翅膀。但终究是锁不住的,千百年之后,他们的后人又开始往山外迁徙,如今峡谷中的村落大都已是空村,人烟少。这是人类迁徙的本能。
北林垟属于高山盆地,山间“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恍若“武陵桃源”。村头正建起一片现代建筑,叫“田园综合体”。这是一个现代概念,可以理解为具有吃饭、睡觉、休闲、旅游、养生等功能的乡村田园设施。做这样的事,一千多年前的陶潜是鼻祖。从历史的那只眼看,只是人类迁徙的一种方式而已。避乱,开垦,隐居,躲祸等,都是祖先迈开脚步迁徏的理由。当田野上的人走向城市,城市趋于饱和后,一些人回到乡村。这是自然的轮回。
从村尾一座小山的脚下进去,绕过这道山的屏障,里面豁然开朗,呈现在眼前的竟然是一个巨大的湖,一个异常饱满、深邃、仁慈的湖。哦,不,是群山合围中的一片广阔的田野,平铺的青禾,荡漾的绿光迷了我的眼。竹林像成批的绿色云朵,也像一条大河,在巍峨的山体上飘荡,抑或流淌。让人分不清绿色是从高山流淌下来,还是从田野涨上去。
晚稻正扬花灌浆,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稻米香,馋得让人想吃一碗香喷喷的尝新饭。我呼吸着,张开贪婪的嘴,在心里大声呼喊——“是谁在这山谷里种下第一株禾苗呀?”翠色逼人,风从山上跑下来,从我扬起的双臂下穿过,绿野上倏忽闪过一袭袈裟,隐入对面山脊相交处。看到那里有两片竹林像两扇大门,像守护着什么似的。
贴着山边的小径走是一种奇妙的感觉,迂回曲折,由远而近,像去寻访一位故人。走到了山襟交叠处,才知是一条小峡谷,涧水潺潺有声。小径往左分叉出小径,弯弯曲曲,然后被一条粗石垒砌的小小的单孔石拱桥接到对面。一块缺了上半截的石碑站在那儿。这是我从书上看到的“极乐寺碑”吗?
碑上附着一层青色的苔衣。凑近看,依稀看见一些浅浅的字迹。拔了一把草,擦去青苔,辨认出“温州路”和“佛”这几个字。“路”是宋元时期的行政区域名,在宋相当于明清时的省,在元代相当于明清时的府。碑文字迹模糊,不知道碑上刻的是什么内容。发现石碑的反面也刻有字,辨认出“青田縣二都根頭信士林二位拾银二钱”,还有“库门坳”。这是我看过的极乐寺碑文中没有载录的内容。给村人电话,说为了防盗,把碑埋地下了。那这块又是什么碑?折下一片南瓜叶去溪涧兜水,打湿石碑后,希望能辨认出碑上的字。叶兜里的水,走到半途差不多已漏尽。在古物面前,我们是那么的徒劳和无助。
再次进山时,我们用水冲洗石碑,用铁刷清除碑上的青苔。石碑吃了水后,竟然整块暗了下去,那些字没有浮上来,反而像溺水了一样,沉到时间的深海里去。我们扑到石碑面前,细细搜寻,想把它们打捞上来,除了上次认出的“温州路”“佛”,这次认出了“夏九”,足以让我们断定这块残碑就是极乐寺碑。
不知極乐寺碑损坏于何时?耳边仿佛传来一声闷响,似雷声消逝在山的那边。距今600多年的极乐寺碑断了。没有人知道。一株南瓜藤从旁边的田园里爬过来,卧在石碑身旁,开了一朵黄灿灿的花。
4
极乐寺与这块残碑,隔着一小片梯田。四季豆的藤蔓已开始渐渐枯萎,茄子虽还开着花,结得果实不是驼背就是躬腰。秋的肃杀之气已悄然而至。只有稻禾越发茁壮,酝酿着登上季节金灿灿的巅峰。
天地间的荣枯兴衰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大地上的事物消失又轮回。眼前的极乐寺,五间平房,简陋,寂静。从唐代到现在,生生灭灭,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没有被湮没。
寺坐西朝东。站在寺前极目远眺,四围青山如屏,千亩稻田尽收眼底。寺在山的皱叠处,深藏不露,外面进来看不到寺,而寺内看外面却一览无遗。明弘治《温州府志》记载:“极乐禅寺在泰清乡后梁龙德间建。”应是基禅师搬极乐禅寺到前山的时间,指的是现址。
极乐寺所在的高山盆地有两条山岭,通往瑞安。寺前岭,我曾走过,翻过山去,是瑞安的朱山、东元等地。这几个地方与泽雅一样,都是造纸古村,峡谷山涧中遗留着错落的水碓和纸槽,旧日造纸盛况可见一斑,尤其是山涧中的村人讲的不是瑞安方言,而是泽雅方言,祖上应是为寻觅适合造纸的水源从泽雅这边搬迁过去。另一条叫和尚岭,翻过山是瑞安山后,这条岭估计是极乐寺的僧人修建,才有此名。
寺前岭曾走过太平军的铁马。1862年2月,太平军进攻温州,四次攻不下温州府城。太平军将领白承恩便出奇计,亲率精锐部,从青田万山越白沙岭突入瑞安飞云小港,另派偏师绕道永嘉林垟(今瓯海区北林垟),翻越朱山,在瑶庄会合,到河上桥,在大岭巧摆荷包阵,令千余乡兵陷入包围,白承恩部乘胜进驻潮至一带,而后长驱直指瑞安县城,在桃花垟中了埋伏,白承恩死于抬枪之下。白承恩是温州平阳人,熟悉温州地形。白承恩派出的偏师就是经极乐寺旁的黄泥岭往瑞安朱山方向。山涧中有一条石桥名“火烧桥”,原是一条木桥,当年清兵与太平军在这里对峙烧毁了木桥,后才修建为石拱桥。传说,白承恩的军队把军粮、物资藏在极乐寺,作为攻打温州的后方仓库。现在当地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极乐极乐,三步下三步落,谁人得到谁人与寺院对半夺。”像一句开启宝藏的秘诀。
民间传说里,极乐寺有九十九个和尚,为凑足一百个,打了一个石和尚站在寺前,往后,寺院就衰落了。传说虽是佛家教化人凡事不能做得太满,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极乐寺曾经的规模。北林垟现年97岁的老人黄有花回忆,极乐寺原有三进,自己年少时曾去烧过香、点过灯,寺前的梯田以前都是极乐寺的范围。二十世纪的1939年,极乐寺毁于山洪泥石流,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98年,才在原址上重建,也就是现在五间简易的平房。从寺门边的一块碑文得知,极乐寺最近一次修复是在2005年秋,村民募捐修整了寺前的路、寺门、屋瓦,还通上电。这块碑与那块残碑,距离不过十米,隔了600多年的时光,极乐寺播下的那一颗善的种子,一直在这片土地上开出花来。寺后有一口井,山泉从石头缝里渗出,汪汪一潭,不枯不溢。
我望向刚才走过的小径,这条被脚印踏平的石板路,回响着遥远的信息。山野藏匿的秘密,与脚下蓬勃的野草,枯荣与共。
5
那一个人影在我的意念里挥之不去,有时清晰,我清晰地感受到他就前面的田野上耕耘的某个时刻;有时模糊,不过是风起时刹那寂灭的一个念头。
再次进山,已是一个月后。绿色的山谷,已变成金色,阳光有了金属般的声音。我是为那个人来的。他是“夏九”。极乐寺碑文中记述他捐出自己的良田,作为极乐寺的恒产,供养寺僧。夏九是记录在案的有名有姓的泽雅高山峡谷中的唐朝居民。
夏是一个古老的姓氏,是中国最早的朝代夏朝大禹后裔的姓氏。夏氏从何时迁入东海一隅的温州。古老中国的人口流向,对应着一次次历史的大动荡。西晋的“五胡乱华”,唐朝的“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北宋的“靖康之难”,战乱的大灾难,迫使中原人带着族群,向着南方,一批批上路。
历史大迁徙的洪流中,哪个身影是夏九,或是夏九的族人?1988年版《瑞安市地名志》载,夏仁明,唐僖宗时避董昌乱(875)自山阴迁闽东赤岸转迁瑞安苔湖。文成《会稽郡夏氏宗谱》记载:夏仁俊,唐中和元年(881)自会稽县(今属绍兴市)迁居安固县(今瑞安市)白云山下岙底村(今泰顺县莒江乡下村村),因父于刘汉宏叛唐时义诤被杀,隐居下岙村。这两支迁入温州的夏氏,是夏九那一支吗?夏九行九,前面还有夏一、夏二、夏三……迁徙北林垟高山盆地中的夏九这一支,可能已是一个望族。
温州偏安一隅,社会相对稳定,不论是黄巢起义,还是接着的五代十国,没有发生过战乱杀戮之大祸,反成避乱之民的流入地。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黄巢从仙霞岭入闽血腥屠杀,闽北居民大批流入温州。这也是继两晋“五胡乱华”流入温州的第二批人口。而浙东地区不断发生的农民起义,如天宝三年(774)的吴令光起义、浙东“海盗”起义、宝应元年(762)舟山岛袁晁起义、大中十三年(859)浙东裘甫起义、乾符二年(875)浙西王郢起义等,都直接波及温州,促使一些人离开易动乱的河谷和滨海地带,进入山区。
顾况《仙游记》载:
温州人李庭等,大历六年,入山斫树,迷不知路,逢见漈水。漈水者,东越方言,以挂泉为漈。中有人烟鸡犬之候,寻声渡水,忽到一处,约在瓯闽之间,云古莽然之墟。有好田、泉竹、果药,连栋架险,三百余家。四面高山,回还深映,有象耕雁耘,人甚知礼。野鸟名鸲,飞行似鹤。人舍中,唯祭得杀,无故不得杀之,杀则地震。有一老人,为众所伏,容貌甚和。岁收数百匹布,以备寒暑。乍见外人,亦甚惊讶。问所从来,袁晁贼平未,时政何若,具以实告。因曰:愿来就居,得否?云:此间地窄,不足以容。为致饮食,申以主敬。既而辞行,斫树记道。还家,及复前踪,群山万首,不可寻省。
这俨然是唐代的“桃花源记”。顾况在温州任职,这个故事不致全无踪影。动荡的晚唐,夏九他们或许从河谷平原出发,朝着西面的这片高山峡谷而来,“寻得桃源好避秦”。
山峦叠翠的山间盆地,带给夏九安宁的气息。他在这片莽苍的山谷里站定,将锄头举过头顶,用力楔入茂盛的草丛,当一股泥土的腥香涌上来,从萋萋的荒草地漫过时,脸上不禁泛起微笑。然后,一锄,一锄……黑色的浪花,绵延开来。一场雨水后,一片茸茸的绿色长了出来,再给几天南方的好天气,稻谷的清香就开始山谷里流动。人的繁衍也如草木,夏九的族人也像一把种子在山谷里撒开来。
不知道现在北林垟还有多少夏九后裔?問当地村民李宗玉。“现在当地没有一个人夏的。”他们去了哪儿?夏九一族消失的只留下一个人名。这令人匪夷所思。
李宗玉给我讲了一个当地的传说:“最早是夏姓和叶姓搬来住在北林垟。后来,夏和叶两个家族都染上瘟疫,只留下叶家一个孩子,是后来搬来的陈姓人的外甥,就由舅舅养大,跟着姓了陈。随着陈姓家族在当地不断壮大,陈家人排挤这位外姓人,已经长大的叶氏后人,就搬出来自立门户,就是现在的下垟村,还在家庙里立了夏九牌位,称‘夏九明王。”
传说是风书写的历史。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信息。穿过金色的稻田,下垟村从金色的稻浪中像一座小岛浮上来。蜿蜒的村道上晒着谷子,羽毛雪白的鸭子在水塘里扑打着翅膀,南瓜、冬瓜卧在矮墙上晒着太阳。好一个安适的小村。
“吱嘎”一声,仿佛打开的不是庙门,而是一扇时间之门。我走了进去。“原来夏九在此!”一个弃世如此之久的人,没有被时间湮没。“夏九”正襟危坐在神座上,目光从我头顶越过,投向门外那一片金色的田园。姓陈的叶氏后人立夏九为家神,让族人世代供奉,此中又有什么隐秘的原因?问村人,没有人知道答案。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李宗玉又带我们去了一个当地人叫“夏叶宕”的地方,据说是夏家和叶家最早的居住之处。此地离下垟村不远,山形如抱窝的母鸡,满山竹林,任意生长。竹林中卧着一段青黑色的断墙。一些砌墙的方石散落于林中,又半入土壤。他们就住在这里吗?虽然隔着时间的帷幕,他们的气息还是在竹林间弥漫,仿佛手一伸就能握住。
再次去看极乐寺残碑,手指从“夏九”上拂过。寺前的田园里,下垟村的陈林云和他的儿子正在收割稻谷,身影仿佛就是千年前的夏九。
秋光清澈,风从广阔的田野上吹过,时间的深度消失了。远山的草树微微摆动,有两个人影从对面的葱岭上下来,大袖翻飞,穿过金色的稻田,朝着我们这边走来,已听到他们的谈笑声。一位高声吟道:
“雁荡峰头春水生,无边木叶作秋声。六龙卷海上霄汉,万马嘶风下雪城。春尽不知阳鸟去,岩高惟许白云行。故人家住青山下,野竹寒流亦有情。”
“君美兄,我在雁荡山作的这首诗,如何?”说着就朗声笑起来。
“慧生兄的这首《题大龙湫和李五峰韵》写得豪健,与兄台相比,我的那些诗文就显得小家子气了。”
“贤弟谦虚了,铁关禅师重振极乐寺宇,你捐出百石租谷助缘,让人感佩。”
“我们此番前去极乐寺也是‘故人家住青山下,野竹寒流亦有情。之意境也。”
“快快走,铁关禅师已在等我们了。”
极乐寺残碑,立在山谷里,像老僧入定。山无语,水潺潺,白云千载空悠然。远望,旷野那边炊烟升起,鸡犬之声相闻,仿佛还是唐朝。
责任编辑 菡 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