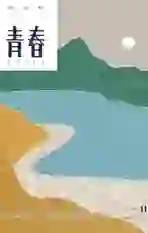干洗店(外一篇)
2021-11-04杨帆
回想起来,两个人是在好得像一个人的时候离的婚。他在派出所上班,她则在他们结婚四年后下岗了。就在下岗后的那10个月里,他们的感情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他认为是因为她的变化。以前他累得像条死狗回到家,还要和她抓阄翻点子猜拳,谁运气不好腕力不足谁做饭。她很少陪他看足球赛,但踢起皮球来无师自通。结婚后她乳腺增生支气管炎甲亢脾虚,什么麻烦得什么。和这些病一起得的是一大摞荣誉证书,什么难得得什么。这是她和她自己之间的仗,本来打得兴兴头头,不料厂子垮了。
一夜之间,她失去了两个作战对象。
她觉得主要是他的变化。回到家,她只好和锅碗瓢盆打仗了,本来和他还有得一拼,谁知他的脾气突然好起来。他主动帮她干家务。再就是他打来的电话多了。他上班的时候她就睡觉,睡闷闷的觉,他在电话里啰里啰唆问她干了什么,正在干什么,等下干什么。这些问题有时要分好几次问完,因为工作的性质,他刚刚还在办公室,说不定一会儿就在哪个乡了。他被案子牵到什么地方,电话线也就把她牵到什么地方。一个电话往往说不了几句就挂了。得闲了他又打。她被那线牵得团团转。她把这种行为定义为“查岗”,他听了倒很高兴。问完翻来覆去的几个问题,他常叫她出去散散心,别老窝在家。但要是家里没人接电话,他又会往她所有的朋友处打电话,好像她会人间蒸发,有一次甚至匪夷所思打到她原来厂子里。厂子已被夷为平地,一夜之间竖起了几十栋待售的高楼。他听着那边嘟嘟的忙音,脸上的表情肯定很憨。她想起来就要发笑,心里暖洋洋。她不知道这温暖究竟是原来一直存在着,还是冬天的冷给衬托出来的。
可是他们离婚了。
事情的起因是她终于忍受不了终日的睡觉,走出家门四处应聘。他也知道她整天躺着很闷,他在晚上就很缠绵,似乎想调剂一下她对睡觉的反感。他给她带来许多报纸,和她头碰头地寻找合适的单位。一天,她从报纸上看到她心仪的一个单位正在招聘,带着资料就去了。当晚,她心情很好,枕着他的胳膊给他讲她的应聘过程。那一夜的月光,有一点点恍惚,至今她不清楚他们为什么离婚。或许她不该告诉他,那位经理面试时对她很欣赏,应聘结束还提出一起赴一个饭局。在她拒绝后,经理开车把她送回了家。脖子下的胳膊不知什么时候抽了回去。他撑起上身仔细地看她,然后问她打算怎么办。她被打量得莫名其妙,有一点点冷。她拔着他下巴的胡子茬说,你就这么不自信。
他拿下她的手,认真地说,不是自信不自信的问题。
接着他请她动动脑子,那些称赞不过是糖衣炮弹,请吃饭是第二步腐蚀,送她是为了摸清她的住址。一旦天天共事,他就会绞尽脑汁,迟早把她追到手。本来,那是个不错的晚上,月亮很圆,很白,不用开灯就很有气氛。因为首战告捷,那是下岗10个月以来她心情最好的一天。现在,她有些扫兴,不能忍受,他居然不认为那些称赞是对她的客观评价。她气愤地打断他,你这么不相信我!她从床头柜翻出她得的那些奖状证书,摊了一床。她还指着他们身上的床罩说,这不是我评上工作积极分子那年得的吗?
他质问她,是我们的家重要,还是工作重要?
她说,没有可比性。你的怀疑只是一种可能,结果没有出现之前,危险和不危险各占一半。我为了那也许不存在的百分之五十的危险就该放弃一份理想的工作吗?
他用一种阴郁的眼光看着她,然后说,我说不过你,反正,就是有百分之一的危险,我都不让你去。这百分之一,就能毁了这个家。
他还说,万一你被那样怎么办?
她嚷着,那离婚好了!
半个月后她接到了录取通知。她花了一下午打腹稿。他平时有点小气,对,从钱这个角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是她拿手的,最重要的是表明自己的忠贞不贰。她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弄得他有点摸不着头脑,连额前那撮头发也硬硬地翘得讶异。他早忘了那桩事,也许以为那事在自己的警示下无疾而终。一提起他就警惕起来。他从她怀里拔出脑袋,定定地看她。她没想到他富贵不能淫温柔不能屈。她气得甩手跑出房间,哭得梨花带雨。
一连几天他们不说话。
几天后,他守不住了。以前他会嬉皮笑脸,搂搂抱抱,甚至甩着一条丝巾翩翩起舞;要么就买花,低调认错加灼热表白。这几样他屡试不爽。这次他求和的态度不比往日。他打定主意要说服她,于是照搬了他们所长开会时的作态,正气凛然,长篇大论,不容打断。从此,在饭桌上、马桶边、床头,他随时摆出长谈的架势,从任何一样东西或一句话切入主题,迅速铺开阵地。从一个角上发动进攻,慢慢覆盖全局。他顾自讲,她几次插话不进,干脆剪起手指甲,雪白的月牙弹射到他脸上去。后来她只好跑到门外去。跑了几次,都被他气急败坏追回来,回到家他更是唾沫如滔滔江水,就算她用棉被包住了脑袋,涛声依旧。
她旁敲侧击过身边女伴对此事的反应,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应该坚持自己的决定,否决或者慢慢打消丈夫的想法。而她缺乏的正是应对他“以爱的名义实施的强盗行径”的方法。这是她最要好的女友苗苗给他下的定义,苗苗甚至建议她搬到自己家小住上一段日子,先把工作干上,等他来接时生米煮成熟饭,加上小别在他心头滋生的思念,不怕他不屈服。
开始她认为这不失为一个好点子,苗苗都帮她把衣服拣好了,临到出门,她又退缩了。一想到他那种定定的眼神,因为她的消极抵抗,而在他眼底攀长出的绝望的红血丝,她推翻了自己的决定。她说,他回家看不到我,是会着急的。他一着急,脑子就乱,办案的时候怎能乱脑子呢。再说,他准会找到这里来,到时候还不是闹得你这儿鸡犬不宁。苗苗啧啧啧地撇嘴说,看不得你这样,夫妻那回事谁不知道,一仗决胜负。她说,奇怪,我为什么要跟他打仗啊。苗苗说,是啊,你们自己人嘛,是我在挑拨离间,行不行?平时在我们面前酷得不行,一到他那里,三下两下就被摆平了。她说,你不了解他,他会和我离婚的。苗苗说,他爱你,就不会!
她还是放弃了那个工作。虽然在苗苗她们面前有些抬不起头来,毕竟日子是自己在过。有时也承认苗苗的话有道理,但她还是不想跟他打什么仗。自从下岗之后,她的斗志就没有那么旺盛了。她从中领悟到,最好的武器不是锋利的刀剑,是爱。她早在他面前败了,输得心甘情愿。她在失败中体验到一种痒丝丝的、类似于初恋时的感觉。由这甜蜜蔓延开去,是无边无际的恐惧。他使她恐惧,她能嗅到爱到盡头的危险气息。从他那个“百分之一”理论里,她同样看到了恐惧。爱里调进了恐惧,两个作战了多年的人掉进了软弱而漂浮的状态中。虽然在厂里那么多年,她不曾意识到,但这是千真万确的,她对他的依恋程度是她自己无法估计的,甚至她在厂里的雄心勃勃完全可能是因为他——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就像她的病曾引起他的爱怜,她认为还该用一点点敬意来中和那爱怜,这样她在他心中的形象才酸碱适度,才不致扁平失血。
她去别的单位应聘,一连试了几个都没后话。每当她拖着身子回到家,有时会抱怨:“如果去了那个单位,就不用这么东跑西跑了。”他有时会早早回家,做好饭菜端到她手里。他的菜越烧越好吃了,即使是一块豆腐,他也能做得有滋有味。以前他不喜欢做饭,即使她加班到很晚,也要等她回来炒菜。吃着他做的饭菜,她感到一种茫然的幸福。吃饭的时候她偶尔也说:“如果去了那个单位,我们就不用这么节省了。”类似的话她随口说过三两次,惋惜,自嘲,最后那次是玩笑的口气。原话依稀是“如果那里再招聘,我说不定还应聘不上了”。他突然爆发了,你能不能闭嘴!
当时他在洗碗,碗在水槽里乒哩乓啷一阵响,像一座塔的倒塌。他呼拉一把扯下围裙,粗声说他不能帮她找到工作,他没有办法,他只是一个小小公务员。他阻止她跳进那个男人的陷阱,她却这么后悔,一再抱怨,还想再去应聘。这是对他的莫大侮辱和伤害,简直让他心灰意冷。难道她希望委身于人?她惊呆了。她流泪,愤怒地回应,我必须放弃这机会来证明爱你吗?我只有牺牲我喜欢的事情才算爱你?你这样疑神疑鬼就是爱我吗?对,我是后悔,后悔也有错吗?我后悔还伤害你了?那你真脆弱。你的脆弱自己负责,我跳不跳陷阱我自己负责!
如果他搂过她说些软话,事情就不会发展成那样。他寸步不让。他甚至翻起以前的老底,把一次她和前男友路遇叙旧的事抖出来,质问她这是不是疑神疑鬼,为什么受伤害的永远是他,而她对他的爱情不屑一顾。那段日子,他几乎发疯了,一头红着眼的狼,只会暴起伤人。而她也气疯了,震惊的眼泪像忘了关上的水龙头,哗哗宣泄着心头的屈辱和失败感。她找到那家单位,那个职位还在。当天她就上班了。
几天后他们离婚了。
事情太突然,还没让人反应过来,一切已经结束。在这场决斗中,他们已经一决雌雄。胜利的快意并没有如期造访。她后悔了。确切地说她在去离婚的路上就后悔了,那时愤怒还在,已是强弩之末。在她还没有冷静下来的时候,就预先后悔了。她只想证明对错,但代价有些大。一直指望他开口,他一个字都不说,她也不说。
他们再没碰上过。
少了他,房子大了,空了,不叫家了,而仅仅是住所。她很怕回屋子。和人约会,又担心他会打电话回家。她和人约会常心不在焉,接二连三用他的名字来喊对方。
她只有工作时不想他。她工作依然勤恳,是那种没有血肉的忙碌。她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她工作的动力。她依然获得一致好评,但她已经不兴奋了。离婚,对她意味着所有的仗打完了。她赢了吗?是的,她赢了。那位经理先生果然是个绅士,他对她发乎情止乎礼,或者根本就是一种超越性别的欣赏,反正他没给她更多的机会来分辨他的心思。他新娶了一位美丽的太太,需要花很多工夫对付。
还是她赢了。
她局部地赢了。她正是为了这赢,才输掉她所有。此时她情愿在他手上输一千次,但是有的输,一次就够了。悲哀不仅限于此。只有跟他的战争,才是战争。只有他参与的输赢,才是输赢。他不在,输亦何畏,赢亦何味。
她到他们经常散步的南湖一带转悠,有时一个人,有时身边有个男人。但碰不上他。有时候她都奇怪,为什么恋爱之前,他和她素不相识,总能碰到。他们就是在多次不期而遇之后,才顺从着心里加剧的异样感觉走到一起的。现在看来,那是缘分在牵引着他俩。而如今,缘分散尽,再怎么都没法遇到了。
她在他下班的途中逗留,在他最要好的哥们的音响店里盘旋,频频光顾他最爱吃的烧烤摊。她只在那家干洗店碰見过他的一件毛衫。她仰头看着,那是他经常穿的一件,米色,很柔软。他穿着它的时候整个人就温情起来,连眼睛都显得湿漉漉的。看着他穿这件毛衫,她常常想,为什么这么好的男人就让她遇上了?她因此喜欢看到一切穿毛衫的男人,觉得他们心里也同样有着温暖的情绪,否则怎么喜欢穿毛衫呢?甚至她讨厌的部门主管,有一次穿了件毛衫,她莫名觉得他和以前不同。她脸上一定是笑了,主管很惊讶,也回报了一个迟疑的笑容。现在,她的脸贴上去,茸茸的,有他的心跳留在上面,而那浓重的汗油味似乎没完全被机器清除掉。每次他换下毛衫,她总爱把脸贴在上面,深深地吸。那温暖的感觉恍如隔世。她的眼睛渐渐湿润了,用手捂了好久,直到店主惊骇地把毛衫夺回去。
难道他们再也无法相遇?
终于在一个有着洁白阳光的午后,他们在老地方见面了。
他们的老地方是一个小小的茶吧。婚后他们忙于战事,茶吧气氛不适合,来得懒。他先到,她到的时候,窗外的阳光很好。他的眼睛温情脉脉。整整一个下午,他们不是对视傻笑,就是食欲很好地吃喝,什么完整话也说不出来。
天,一瞬间黑下来。这让他们变得聪明了一点。两人沿湖散步,他趁着黑握住她手的时候,舒服地叹了一口气:“如果不是你约我,我们只怕还在死撑着。”她惊讶地说:“什么?我约你?不是你约我吗?”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落款是她的名字。而她马上从提包里也拿出一封信,信里的语气与他收到的那封如出一辙,也约在老地方见面。就着月色两封信摊开来,两人面面相觑。
她笑了,他也笑。
她说:“一定是你那哥们,你对他说过老地方的对不对?”
他抓过她的手,热乎乎地说:“管他呢,你回来就好了。”
他还说:“说不定,是老天看我们这么苦,给我们讲和来了。”
她偎在他怀里有种融化的感觉。她知道是他的毛衫太暖了。这份暖,如今真真切切回到了她身上。这或许是毛衫与初冬打的第一仗吧。
鬼知道是谁写的那两封信呢。
夜雨
季东放下第十三个电话,需要喝一杯。威士忌在杯底溅起一朵大水花,水花层叠之际,电话响了。阿姨的嗓音间杂着威士忌撞击冰块的声响,她用享用过午后甜点的喉音赞美某女品德,照旧是这世上唯一匹配得上他的。笼统地说,季东属于那类穿Armani西装提LV包喷Burberry香的人,会议,谈判,联谊,相亲,都是卸不去这套行头的。这恐怕是至今未婚的原因之一。季东检讨着,环顾巨大的工作间,慢慢倒了一大口,咽下去。冰凉一大片,浸透了胸腔。
同季东打过交道的生意人大都能记住他,一个目光炯炯、气宇轩昂,持续交谈一整晚还精神振奋的青年人。此刻,季东正将车钥匙交给服务生,裹着夜色走进一间金碧辉煌的大厅。7号是季东预定的桌子。他要在这里,花点时间等一个女人。再花上长一点的时间和这女人共进晚餐。这视情况而定。季东的睡眠一直不好,要靠女人才能沉入梦乡。这当然不是说季东找到了良方。忽略季东没有时间结识女人不计,他还有个不良习惯:能在第一时间判别一个女人的质地。多年来,这造成了季东睡眠的持续动荡。
假如女人一时真伪难辨,他会待长一点。上周末是十八分钟。等了一刻钟,在那个童花头的女人出现三分钟后,他欠身离开。应该承认一刻钟对于相亲是合适的时间,童花头对于一个青春尚存的女人也合适。假如该女没有大笑,露出一颗偏僻的金牙,他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知道她的底细。半年来,他浪费了不止这一个夜晚。他没有请她吃饭,也不责怪她败了他胃口。他对于对面玻璃门里自己扬长而去的背影倍感怜惜。
今天这位“外贸专业”“芳龄三八”“容貌俏丽”等等的女人到了,在侧对面略微站了一站。她迟到了几分钟?女人目不转睛望着季东,当然季东也在不错眼珠地看她。女人当然不会二十四岁。她谎报了年龄——这让他微感怅然,这不应该是梁媛舒做的事情。
季东!是你吗?她用那种沙哑的嗓音说。还有她的长直发,眼线略长的眼睛,加上姓梁,都是对的。时隔七年,她的变化不算大。季东笑了笑,我一直说给你打电话,总没有打。梁媛舒问,打电话做什么?季东笑说,老同学嘛,在一个城市,保持联系很有必要。梁媛舒说,你保持得挺好。
过了一会,咖啡来了。季东说,你怎么样?这些年过得好吧?还好吧,梁媛舒一笑,买保险找我哟,听说你发展得不错。季东说,公司不大不小,各方面还专业。老同学就该相互帮衬嘛。当年你标枪厉害,男生排着队,做梦都想被你扎中。梁媛舒笑,你那时候瘦的,王老师说你吃大排简直穷凶极恶。季东哈哈一笑,穷凶极恶,我排大头后面。
梁媛舒端坐在对面,灯火下,一个金红色的蜡人,像某个经年的梦境。季东不由踌躇起来,仿佛面对一幅不具名的油画,走近了看不清,要离得远了,才不至于被带进画里。
人生路上季东算得上老司机。抛开这套行头,几年前他作为一个打手的面目清晰可见,为不算显赫的家族,为向上的心,冲锋陷阵。一天下来要跑的道,要冲的关,要过的场面,多得让他飞速建立起四通八达的交通库。时而上天桥,时而钻地道,季东进退自如首尾呼应。凸起的青筋,太阳的吻痕,最初的羞赧或愤怒,露珠一般在他的面部消失了。如今他可以踩刹车,也有加油门的余地。有余地的人生是成功的人生,对这一点季东从不怀疑。
大头不知这阵忙什么,约出来坐坐?
梁媛舒垂下眼皮,搅动咖啡,今天我来是给人打前阵——别翻脸,都说我表妹才貌双全。季东定了定神,说,今天这样见面,比打电话要好。大头公司开得大,他常谈起你。
他买保险可以找我,梁媛舒喝光杯子里的东西,说,我该走了。
赶场子?
你也不小了。时光宝贵——我走了。季东不说话,望着她往包里塞手套,塞手机。她刚一起身,季东探过身来,盖住她的手,说不忙走。
这时有个妙龄女子出现了。梁媛舒扯过挎包就走。
夜正馥郁,应和着梁媛舒大好韶华,月光般流一地。来的时候还没有月亮,此时它昭昭当空,亮得有些异样。梁媛舒跑出大门,拐进巷子里,心里记着要去这巷里寻一个缝补的店面,这是几日前想好的,小礼帽上挂了一个洞,小蝴蝶结也有些歪,在掉下来之前务必找到那家店。梁媛舒歪歪斜斜走着,鞋跟把地面敲得很响。她还从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春夜,会有这样的月色,会走在这样暗的巷子里。这世上只剩下梁媛舒的鞋跟,和瀑布般的奢华月色。季东赶到的时候,巷子走穿了,店面还是没有出现。有可能收工了,关门了,迁走了。因为久没走这巷子,有些情况已不在掌握中。梁媛舒手拎着帽子,捶着小腿,停在巷口一家音像店旁。夜深了,店里放着很有质感的爵士乐,一支喑哑的女声摇摇晃晃。整条路在飘荡。季东手插裤兜背着月光走来,满地是他的影子。梁媛舒想撇掉高跟鞋,走在他影子里。手在他手里。时间停在他探手过来的那一刻。
房间里空气有些不够。他背对着月亮,月光有些暗淡。她怀疑会下雨。浔城春天就是这样,没有规律可循。雨果真在后半夜下起来了,她聽到窗子外的细沙声,陌生的窗子外的天地,新鲜,阔大,充满雨声。梁媛舒摸黑下地,把窗帘拉开,一道闪电劈来,劈落了手里的纱。雨打进房间,越来越粗。中途季东被雷惊醒,抱住她又睡了。那种隐隐的闷雷,脚步很慢,奔跑到很远,还在不断传来。
早上季东醒来。周遭是雪白的墙壁,可疑的暗红地毯和窗帘。他的衣服长长短短搭在沙发上,她的包和帽子在桌上。他望着白得刺眼的墙,意识一点点恢复。手机里几十个未接来电。有关大头的出场,他设想过多个版本。但梁媛舒跑了。一切乱套了。在大头等电话期间,他和梁媛舒先后睡着了。那么大的月亮,后来怎么下起雨来。他仿佛说了好些话,言不由衷的那些。她把他掐出一些橘色月牙。浴室传来细碎水声,季东晃了晃脑袋,水声大了一些。有人从浴室出来了。有人朝他眼睛里吹气,睁开,知道你醒了。陌生气味的发丝伸进了耳朵,她俯下身子。从她领口散出一些温醇的香气,像是混合了虎皮兰和面包的气味。梁媛舒离开了床,趴在镜子前化妆。包里的东西倒了一桌,她飞快地捡起它们,又放下它们。
窗口淌进一地清早的阳光,直拉到门口。梁媛舒站在一层金色浮尘里换鞋,帽子盖住重重的发髻,裙子原来是珊瑚色。她稳住了身形,换好另一只鞋。等她抬起下巴,季东看到一张陌生的脸,一层橘色绒毛现在在阳光里,紧张地闪烁起来。
作者简介
杨帆,著有小说集《瞿紫的阳台》《黄金屋》《天鹅》《后情书》等。鲁迅文学院第13届作家高研班、第28届深造班学员。大益文学院签约作家。
责任编辑 菡 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