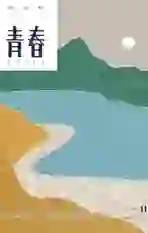盂
2021-11-04高逸云
高逸云
女人总以固定的姿势站在固定的窗里抽烟,一边靠尼古丁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一边保佑自己的乳房平安。
他的阳台上挂着一排衬衫和T恤,仿佛帷幕。他坐在客厅中央的摇椅里,左手同样夹着一根烟,透过帷幕观看站在对面窗里抽烟的女人。
女人从不看向对面任何一个阳台。她并不关心对面的楼里是否依然有人居住。此时的女人已经掐掉烟蒂,转过身消失在窗户里。
夜幕已经降临,阳台外只剩下事不关己的黑暗底色。阳台上的衣服和下午保持着一样的节奏轻微晃动,只是现在它们成了主角。
他开始逐一思索起这些衣服的年岁。最年轻的也有十几岁。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十几年没买过衣服了。那些衣服瞬间像酒一样被标上年份,成为他心里新的勋章。
他已经在客厅中央的摇椅上度过了白天到夜晚的过渡时光。他还准备继续坐下去,把事情弄清楚,看看岁月的褶皱里是否还夹着未被发现的金币。
他的左右两侧是三个有着一刷水黄色柳木壁柜和地板的房间。这些房间和柜子里除了堆放陈年的衣物被褥之外,也有些不寻常的东西。曾经有三代人共用這间客厅,如今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他把摇椅放在了客厅中央。在黄色柳木打造的角柜上有一只白色瓷瓶,瓶里有一朵尼龙材质的红色玫瑰。这朵玫瑰被清水和岁月冲洗过,略微褪色,摸上去有些扎手。三十年前,这朵崭新的玫瑰被四只手放在一个铁艺相框前。相框里的两个人正是这四只手的主人。女人穿着婚纱,手里拿着一朵玫瑰;男人打着领结,俯首看着女人手里的玫瑰。现在,男人以同样的视角打量这朵玫瑰,只是女人白皙的手变成了眼前的白瓷花瓶。他想起三十年前的那天,他在照相馆门口递给女人这朵玫瑰时的场景。他一只手半插进西裤的口袋,另一只手捏住玫瑰的花柄,如一个凯旋的英雄款款走到她面前。女人的黑色长发,如盛夏之雨般垂落,她浅笑着接过玫瑰。于是这朵玫瑰就盛开在盛夏之雨前。女人笑着问他:“为什么买一朵假花?”他没想过女人会这么问,好在他足够聪明,他告诉女人:“永远不败。”然后,他们并肩走进照相馆。
随着女人的到来,他很快成为一个父亲。而盛夏之雨却没能在他的秋日长久停留。岁月的寒风中除了他踽踽独行外,还有一个已经长大成年的儿子。儿子与他的距离并不比前妻离他近多少。儿子离开他的那天,只是平淡地告诉他:“爸爸,你不要左右我的想法。从这些年的实事来看,你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儿子眼里,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谈话和普通的告别,儿子并没有要和他划清界限,儿子也一定会在他老了之后赡养他。然而儿子的离去,让他作为一个父亲感受到被抛弃。
他想起了另一次似曾相识的抛弃。
在他二十岁夏季的某一天,他记得父亲是如何意气风发地带他出门,又是如何默不作声地带他回家。那一年他考上了北方一座城市的大学,这是父亲此生最为骄傲的事情。他记得那天自己还在睡梦里,就已经在鸟叫声中跟随父亲出门。父亲为他跟邻居借了一辆自行车,父亲自己有一辆自行车。前一天,他们为两辆车打好气,第二天便骑着赶往江边的渡口。他们为自己和自行车分别买了票,登上轮渡。这一天,他们要前往长江对岸有火车站的城市,购买他几天后北上的火车票。
在这之前,父亲并没有出过几次远门。这一次,父亲决定购买卧铺车票。父亲相信,卧铺票比硬座票贵几倍,买的人一定不多。当他们大汗淋漓地站在售票窗口时,却被告知只有硬座车票。父亲几乎将头探进售票窗口,最终售票员给了他一张靠窗的座位。跟靠近水泄不通的过道座位比起来,这张靠窗的座位已经是很大的恩赐了。
父亲带着他在车站附近吃了一碗酱油锅盖面,要了一碟当地有名的水晶肴肉。父亲告诉他,水晶肴肉是这里的特产,一定要就着当地的香醋,算是点睛之笔。父亲还说,你以后出门,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特色,不要省钱。说这些话时,父亲暂时忘记了没买到卧铺票的失落,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神色。当肴肉上来时,父亲脸上的满足凝固成了一副面具,然后这副面具被拿走了。父亲没想到用来盛肴肉的不是盘子而是碟子,碟子里只有四块肴肉。那四块方方正正的肴肉确实如水晶一般晶莹剔透,上面铺了一层姜丝,旁边也确实配了一碟香醋。父亲略带尴尬地笑着说:“君子淡尝其味,赶紧吃吧。”最后,那碟肴肉他吃了三块,父亲吃了一块。
一连几天,父亲忧心忡忡,直到一个来做客的人无意中透露自己的亲戚刚好是那趟火车的列车长。从不求人的父亲第一次问别人能不能为他“想想办法”。在朋友的指导下,父亲又托人买了两包凤凰牌香烟。
北上的日子终于被盼到了眼前。临行那天,家里来了很多人。那些人和他的母亲一起把他们送到路口。母亲的脸上挂着眼泪和笑容。他的兴奋一时被伤感取代了。 他们和人群一起挤上开往渡口的班车,挤进对岸城市的站台,挤进前往北方的车厢。父亲要他先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不要乱跑,自己坐在另一个靠近过道的座位上。过道里的屁股和像屁股一样的包裹压着父亲,父亲只得不停朝里避让,同时不断抬头张望。他透过父亲脸上架着的厚厚镜片,看到镜片里一沓沓变形的人影。
火车开动了,父亲艰难地站起身,可过道里的“压力”太大,父亲立刻又被压在了座位上。父亲扶了扶眼镜,拍拍前面人背着的胳膊,斯文地说:“同志,麻烦让我出去。”前面人的身体扭动了,让出一条窄窄的缝。父亲又艰难地站起来,扶好眼镜。父亲被渐渐吸入了窄缝,前面那位同志的屁股立刻落在了父亲的座位上。
父亲的包里揣着两包凤凰牌香烟。车厢里人与人像一个个细胞一样挤在一起。父亲艰难地从这些细胞的缝隙中挤进了餐车。父亲在餐车里寻找戴列车长袖标的人。餐车里不再那么拥挤,但父亲却无处可坐。父亲倚着摇晃的车厢,注视着餐车里那些买了座位洋洋得意的旅客,和在此谈笑风生的工作人员。父亲尽量不碍别人的事。列车员告诉他这里不能站人,他只弯下腰,低下头,有些心虚地赔笑着说:“我等列车长。”
父亲不知道等了多久,雄姿英发的列车长终于出现了。但他很快又消失了。当列车长再次出现时,父亲生怕他再次消失,便一直跟在列车长身后。他实在不知道怎么打断列车长的走动,只好跟着他艰难地又一次挤过一节节车厢。最后列车长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父亲也终于有机会从包里掏出朋友写的纸条和那两包凤凰牌香烟。
父亲回来时神采奕奕,他们得到了两张硬卧车票。卧铺车厢清静了很多,他们体会到了身为贵宾的荣耀。他们在车厢里满足地走过去又走回来,最后在下铺客人的床沿坐下,吃起随身带着的馒头。父亲年轻时做过几年中学教师,主动用普通话和别的贵宾交流起来。很快,周围的人都知道了这位父亲的儿子即将前往北方的大学深造。第二天早上醒来,火车还未到站,父亲已经坐在窗前观看外面北方的景色。他简单洗漱后在父亲对面坐下,父亲看看他又看看窗外,一时不知到站前还能说些什么话。父亲面朝火车前进的方向,北方的光打在父亲脸上,他仿佛看到父亲和窗外的景色一同远去了。
他们跟随前来迎新的学生,倒了几班车,终于来到学校门前。那天天气很热,父亲却穿着衬衫打着领带。父亲站在校门前仰望着。他看到校门很大,父亲背上的包袱很大,只有父亲很小。父亲渺小的身体在来来回回的年轻人中晃动,仿佛一根水草顽强地抵御着鱼群游过的浪潮。他后来想,没上过大学,恰恰是父亲此生最为遗憾的事情。在父亲年轻的时候,曾连续两年夺得全市高考文科状元。也是在那时候,父親被打上了“右派子弟”的标签。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父亲恰好三十一岁。那时候国家放开的高考年龄是三十周岁以内。父亲就这样和他的另一种人生擦肩而过。
他发现,只有他的父亲千里迢迢将他送到学校。
当晚,父亲和他一起躺在他的床铺上。北方夏天的夜晚,带着一丝令人新奇的凉爽。他们一起畅想着他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和指日可待的远大前程,他们畅想着毕业后是留在北方继续发展还是回到南方建设家乡,他们畅想着有朝一日他也成了父亲……日子被他们无穷无尽地勾勒着、修改着,一瞬间,他以为自己在和同学说话。直到父亲又跟他老生常谈起来:
“还是那三个忠告。第一……”
“多读书!”这一次他没有不耐烦,而是笑着抢着说了。
“第二?”父亲又回归了父亲的严厉。
“第二,非中外名著不读。”他故意放慢语速,觉得父亲既好笑又可爱。也是在那一刻,他突然从父亲的严肃中意识到父亲的苍老。
“爸,话不能这么说呀,那您写的小说我是读还是不读呢?”他赶紧补充道。
“我不能保证我写的小说将来是不是名著,所以你还是得读。”父亲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第三,读点哲学书,黑格尔必须要读。对吧?”他问父亲。
父亲说:“对,黑格尔必须要读。”父亲还说:“我劝你还要读一些中国古典戏剧,这些作品都经过了几百年的千锤百炼,是千古绝唱。你要提高自己的人文修养,知识面越宽越好……”
他看着父亲月光下闪闪发光的脸,闪闪发光的眼睛,闪闪发光的嘴角和胡茬,想着父亲真是想把他往文艺工作者上培养啊。他渐渐睡着了,父亲的说话声在夜色中渐渐远去。
第二天父亲和他一起逛了市区一个有名的景点。当父亲再次把他送回宿舍,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和同学打成一团了。父亲打开包,从里面掏出一件东西递在他手上。那是一支英雄金笔。父亲曾答应他,若他金榜题名,会送他一支派克金笔。他知道,若不是托人换卧铺票,托人买凤凰烟,这一定是一支派克金笔。他看着父亲,父亲也看着他,父子俩相视一笑。他看到父亲眯起的眼睛里有了些许泪光,他也知道父亲一定也发现了他眼里的泪光。他想:扯平了。于是他们父子俩继续相视而笑着,像第一次长久的重逢,也像第一次长久的离别。最后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父亲临走前给他把两个热水瓶都灌满了水,再一次以神圣的目光环视了那间挤满上下铺的屋子,然后背上那只已经空了一大半的黑色布包离开了。
父亲的包里除了一张回去的硬座车票外,再没有什么了。当他在一个新的早晨再次醒来,父亲乘坐的火车窗外已经出现了熟悉的南方景色。那一刻,他怅然若失,他担心却又不可避免地意识到,他把父亲抛弃了。
此时他所居住的用黄色柳木装饰的房子是曾经父亲单位分的公房。他曾有过自己的房子,后来全部赔进了自己的生意。他也想过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如今只有他孤身一人住在父亲的房子里。而他的父母,却因为他的到来重回老家居住。父亲回老家后不再写小说,开始写起了回忆录。父亲面对不同的人生阶段,只是换着不同的东西写而已。父亲一定会一直写下去,这是他唯一的方式,也是他唯一会的方式。
这一天,他在这所房子里想起了上一次父亲回到这里的情景。
父亲如今走路的姿势,像一棵勉强站直的老槐树。那天,父亲歪歪扭扭地拖着一个老式行李箱来敲他的门。父亲进门先看到了那张放在客厅中间的摇椅。然后,父亲绕过了摇椅,坐在沙发上。他则坐上摇椅。
父亲说:“把箱子打开。”
他打开箱子,看到了父亲的书。
“出版啦,不错嘛!”他说。
父亲说:“你看看反面。”
他于是翻到书的背面。
父亲凑近了一点,指着书背面的文字说:“史诗!看到没有?人家说我这是史诗!‘作者三十年磨一剑,成就一部奋斗者的史诗。史诗啊!”
“哦。”他说。
“你再翻到前面。”父亲回到了一开始的姿势。
于是他把书又翻到正面。
“看到什么出版社没有?我这个书全国新华书店有售。”父亲把“新华书店”四个字说得很长。“不是我兜着他们,是他们来找我的。”
“哦。”他说。
“你把网打开,把我名字输进去,就能看到这本书。我无意中发现台北的一家书店也在卖我这本书。”
“哦。”他说。
“不是我求着他们,是他们来找我的。”
“知道知道。”
“给你带十本,不够再找我要。你读读,请你的同学朋友也指正指正。”他印象里的父亲从未如此轻松欢快过。
“我读过呀!电子稿不就是我帮你打印的嘛,打印稿我也有。你不够怎么办?”
“我够了,不够也给你了。不够我上新华书店买去,全国新华书店销售!”父亲说得铿锵有力。
现在,父亲的这本书正站在他的书柜里,同曹雪芹的《红楼梦》、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马拉卡佐夫兄弟》和《白痴》,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站在一起。他想,作品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杰作都是为自己写的。
父亲的书让他又想到自己的儿子。他于是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了余额,才安心去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他端着水杯走进房间。黄色柳木床头柜的抽屉里是病历、各种药物的瓶瓶罐罐和一堆发票。床头柜里还有一张折成四分之一大小的白纸。这张纸上除了年久的斑驳褶皱和新添的折痕外,没有其他内容。这张纸已经被压到了抽屉的最下面。一年前他捐赠了那只青釉褐彩水盂。不久前这只水盂在市博物馆展出了。展牌上是这样写的:“唐·长沙窑青釉褐彩水盂。1994年X镇X村出土。器型规整,胎色青灰,胎质坚致,满施青釉,上有褐色斑点。釉色光亮,点彩随意。”
十几年前,一个朋友给了他这只水盂,他便明白那笔钱再也要不回来了。他曾找过不少途径想将这只水盂卖掉,但没有人能出到他认为合理的价格。他在古董市场复杂深奥的规则里,和这只水盂惺惺相惜起来。这是他唯一的财富,也是他唯一的赌注。他们开始相依为命了。而这张白纸就是多年来他一直用来包裹水盂的纸。
现在,他要去热自己的晚饭了。他往汤里撒了一些胡椒。他并没有遵从医生的嘱咐忌掉所有要忌口的东西,就连烟酒也没有完全忌掉。需要“忌”的东西多了,反而“无忌”了。
几年前,他的后腰第一次长了两个对称的硬币大小的疹子,越挠越痒。后来,这种对称的疹子开始频繁出现在他的后背上、四肢上、脸上。第一次有两个疹子出现在脸上时,他觉得自己十分滑稽。因为疹子总是对称分布,脸颊上的两个疹子让他觉得自己像木偶戏里的木偶。后来疹子开始大面积分布,他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容貌。很快,他就不担心容貌问题了,因为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就是痒。疹子一旦发作,他要面对的是无止境的痒进而是无止境的难眠长夜。
他得的是一种叫作慢性湿疹的疾病。他已经经历过家庭破碎、倾家荡产,他也能预见必将经历亲人离去、孤苦终身。然而在他已经历的、可预见的、甚至侥幸逃过的痛苦里,他没有想到还有一种新的痛苦。这种痛苦以痒的形式出现,这种痛苦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是否真的可以用“不幸”来形容,想到这里他又觉得自己败得轻如鸿毛。他现在矛盾痛苦又糊涂。
在他离婚的时候,人们告诉他“天涯何处无芳草”;在他破产的时候,人们告诉他“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但在慢性湿疹这件事上,没有人劝他“精神不滑坡”了。这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病,就像有些事不可能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样。于是他的痛苦里又多了一份格外的孤独。当他再想到父母,想到是他们的儿子在承受这一切时,又悲伤地意识到这痛苦永远不可能转化成荣耀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被这难受的永无止境的痒打败了,他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被打败了。
一年多以前,市政府给文联一笔资金,用于繁荣文学创作。父亲的作品得以入选。而出版费用仍需要父亲自费一部分。父亲犹豫了。不光是因为父亲一生清贫,更因为父亲清楚,自己到了这个岁数,这本书的出身和命运可能是自己一生的定义了。就像那只盂和他命运的关联。
他找到文联的同学,捐赠了与他相依为命的水盂。他的人生也许从此放弃固执,而往一条幽暗温暖的小路走去。他依然感到自己的人生被釜底抽薪,他捐赠了自己最后的幻想,他展开包裹它多年泛黄发脆的纸,他听见了簌簌的响声。
父亲的书顺利出版,他便坐在摇椅上等着父亲的到来。那天父亲兴致勃勃,甚至手舞足蹈。他并没能聚精会神地聽父亲的讲述,而是想起当年父亲带他骑自行车再坐轮渡去长江对岸买火车票,想起父亲指着江面自言自语道“烟波江上使人愁”啊!想起那四块肴肉,想到父亲随着火车窗外风景倒退,想到月光下父亲闪闪发光的脸。他想起第二天父亲先他醒来,用手指轻轻挠了他的掌心。母亲告诉过他,他小时候,每当有人挠他的掌心,他就会呵呵笑起来。
父亲在一通慷慨陈词后,给他留下十本书,歪歪扭扭地走了。他看着父亲老槐树般的背影从贴满充煤气、送快餐、治病、办证号码的楼道里缓慢而下。父亲曾给他留下一支英雄金笔后也是这样带着空空的行囊缓慢离开。父亲这次留下的,是父亲一生的东西。
那天送走父亲,他站在楼道里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了余额,然后回到自己的客厅中央。
责任编辑 陆 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