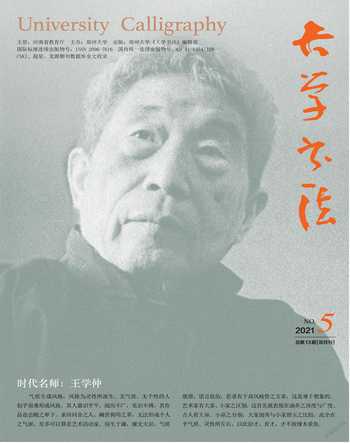海外书法教学的第三空间
2021-11-04李煜MarciaWatt
李煜 Marcia Watt

【内容摘要】本文关注如何通过教授书法的知识来促进海外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传统的教学方式往往用比较与反差的方法强调中国书法与西方书法的不同,以突出中国书法的优越性。本文认为这种方式有其局限性,不利于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理解与沟通。本文主张用“第三空间”的思维组织教学,帮助学生超越对中国书法与西方书法二元对立的理解模式,使他们不仅能了解两种艺术传统的独到之处,更能理解和欣赏它们之间的共通之处,不仅从两者中都得到丰富的滋养,更能从较高的层面上领会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与复杂性。在西方和中国书法传统之间的交叉影响越来越显著的现代,这一练习将对学生特别具有启发性与教育意义。
【关键词】西方书法;第三空间;书法教学理念;书法教学实践
美国少数有条件的大学给本科生开设中国书法入门课程,这样的课往往设置在东亚研究或亚洲研究系,时间一般为一个学期,除了指导学生使用笔墨临帖以外,课程的核心目的在于让学生通过学习中国书法,来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在这样的课程中,拿出一两节课的时间给学生介绍欧美书法的传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美国学习中国书法的大学生,虽然大部分对于用硬笔书写拉丁字母已经有丰富的个人体验,却缺少对其作为艺术形式的了解。而在中国书法课上專门拿出一节课来学习西方书法可以为学生进一步地理解中国书法提供参照思考的机会,与之相辅相成。那么,如何让学生通过学习西方书法来增进对于中国书法的理解呢?
在谈到西方书法与中国书法的话题时,较为传统的观点强调的是二者的差异,并主张用“比较与反差”的方法来上这节课:无论是在工具、技巧上,还是在审美原则及其哲学渊源上,都能显而易见地列举出中国书法与西方书法的不同,从而构架出两者几乎全然的对立。这种教学方式的目的在于通过体现中国书法在相比之下的博大精深来激发学生进一步理解与欣赏中国艺术传统的愿望。然而,这种方法往往忽略了两个看似完全不相关的艺术传统之间的相通之处。毕竟,西方书法与中国书法都源于书写,源于人们跨越时间与空间进行交流的基本愿望,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本文借用应用语言学中“第三性(thirdness)”的概念,并借鉴语言景观研究中第二语言教学法的发展,提出在中国书法海外教学的语境下为西方书法这一节课开创一个“第三空间(third space)”。通过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例,重点探讨中国书法在传统教学中被认为是“高”于西方书法的几个特点:风格(individuality)、自然性(spontaneity)、物像(presence of nature),它们是如何也体现在西方书法传统中的。中国书法与西方书法之间(即第一空间与第二空间之间)于是具有被“比较与反差”的教学方法与思维模式所忽略的共性。这表明开创一个第三空间以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中西对立是十分必要的。从第三空间的角度进行中国书法在海外的教学才能避免用本质主义(essentialist)的僵化观点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才能培养学生对中国书法传统和实践有更细致、更敏感和更为动态的理解。进而,在这个第三空间中,学生不仅能了解不同艺术传统的独到之处,更能理解和欣赏它们之间的共通之处,从两者中都得到丰富的滋养。
一、“比较与反差”法
从事第二语言与文化(Second Language and Culture)教学的专业人士们普遍认为比较法能够帮助学生发展跨语言和跨文化能力,并认为把它作为一种基本的教学方式是相当有益的。而“比较”本身也是美国二语教学的国家标准(ACTFL, 2014)中的内容标准的五项之一。这五项即“五个C”:交流(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s)、联系(Connections)、比较(Comparisons)和社区(Communities)。同样,在向非中国背景的学生教授中国书法时,与西方书法进行比较和对比具有可以为学生提供他们较熟悉的参照、有效阐明关键的概念差异等好处。
在海外的中国书法教学中,比较与反差的方法几乎总是以建立一种中西二分对立来表现中国艺术传统的优越性的。例如,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行的经典英文教科书——《中国书法:美学与技术入门》(Chinese calligraphy: An introduction to its aesthetic and technique; Chiang, 1973)中,作者指出了西方书法的两个“不足”,即形式上的缺乏和生命力的缺乏。他在评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古代西文手稿时写道:“从整体上看,我只能看到重复的圆、曲线,以及垂直和水平的直线,并且它们的动态形式也相似。”他推断西文书法在风格上缺乏变化是因为英文书写在技术上受到两个局限:一是罗马字母数目较少,二是英文词语由一个个字母从左到右线性排列书写。相比之下,汉字则“是以各种美丽的方式构造而成的”[1]。还认为使中国的毛笔书写在对比下显得更为优越的是,西文手稿中的文字“整齐、规则和对称,但它们是无生命的字母的集合——我们也是一直这样批评自己的印刷体的汉字的”[2]。
如此“扬中抑西”的比较方式并不只是关于中国书法的书籍独有的,在讲西方书法的书籍中也可以读到。例如,《完全书法家》(The complete calligrapher; Wong, 1999)一书的作者认为中国的毛笔书写和西方书法“差异大于相似”。在评论了二者的表面区别之后,作者继续说其与西文书写的不同:“东方的书法超越了语言的图形表示。它被认为是一种艺术形式,其美学考虑比其本身的含义更受重视或更具有价值……中国人对书法家的批评与尊敬与西方人对最优秀的画家的态度一样。”[3]在对比这两种传统时,作者暗示了西方书法在西方的艺术性和声望远低于中国书法在中国的艺术性和地位。
中国的毛笔书写和西方的硬笔书写真的没有共通之处吗?西方书法的确是一种较为低等的艺术形式,仅仅表现为“无生命的字母集合”吗?与其教授学生以简单的“是”或“否”来回答这些问题,把我们的思维局限于一种“或者中国或者西方”、非此即彼的两个空间的相互对立中,本文作者认为,不如以更有益于学生的视角在一个第三空间中对中西书法的关系“重新赋义,重新构架,重新构想和跨语境化(resignify them,reframe them,re-and transcontextualize them)”。在这个空间中,中西方之间的二分对立可以破解开来,从而引导我们获取新的见识与理解。
二、海外书法教学的第三空间
(一)第三空间的概念
在二语教育理论中,第三空间的概念(或作为一般原则的第三性)尤其重要。例如,克拉申(Kramsch)的研究提出将“第三地点(third place)”一词用作“一种隐喻,以帮助教师和学习者在话语中将自己定位在交流的二元和文化的二元之外”,以“超越国家语言的二元(L1-L2)和民族文化的二元(C1-C2)”[4]。科斯托格里斯(Kostogriz, 2002)在讨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扫盲(literacy)教学时,也对“第三空间(Thirdspace)”进行了阐述。马里诺斯基(Malinowski)借鉴了克拉申对第三空间的阐释,认为用这一概念组织在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中的语言学习活动是非常有效的,并解释说第三性的概念可以更广泛地阐明“语言教学法和语言景观研究中的多种视角”。
以上的理论概念与阐述对在海外开展中国书法的教育不无启发意义:我们认为第三性的原则也可用于创建一个帮助师生超越二元对立——尤其是人们已经在东西方书法传统之间划出的界限的——第三空间。从第三空间的视角来看,我们认为西方书法在重視风格、自然性,并在实践中有对自然物像方面的体现,这是与中国书法相通的。
(二)西方书法中的风格、自然性、物像
1.风格(individuality)
西方书法的风格个性首先表现为罗马字母书体的多样性。罗马帝国始于公元前27年,结束于公元476年,历时500多年。在此期间,罗马帝国的影响力遍及了小亚细亚、北非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其文化遗产之一即是非罗马人采用了罗马字母。帝国时期,人口聚居的地方彼此距离较远,较为孤立,因此虽然都使用罗马字母,书写中的风格特质却逐渐形成。图一显示了七种不同的书体,按时间顺序从最古老到最新排列。例如,图一第二行的书体来自8世纪中叶的意大利。笔尖的角度是平的,字母形态比较圆。此书体属于Uncial书体家族。第三行来自同一时期的英格兰,属于Insular Minuscule书体,字母的笔画较直,字母较高,字间距较小。即使在同一时期书写的手稿,各地的书体也有所不同,以至于可以通过书体辨别手稿的地理来源。
事实上,风格个性是西方书法传统的一个持久特征。尽管统治者曾努力统一欧洲使用的各种书体,但跨地区的差异仍然很大。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将自己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号称具备如古罗马帝国皇帝一般的力量与影响。为了保持和增强自己的力量,他试图统一书体,以改善帝国内部的文字交流。图一第四行是查理曼大帝尝试改革之前使用的书体之一,称为Merovingian。这种书体惯用连字(ligature),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字母以缩写形式连接在一起。书体本身像是由“密集的,打结的线”组成的一样,因此很难阅读。为了统一书写,查理曼大帝命令一位博学的和尚阿尔库因(Alcuin)设计出一种新书体。该书体现在称为Carolingian(图一,第五行)。Carolingian的文本通常行间距充足,即使在引入1200多年之后的今天也相当易读。但是,查理曼未能完全成功地推广使用这一新书体,意大利南部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沿岸就从未采用过,而Beneventan(图一,第六行)一直是这些地区的主要书体。这种书体的字母形状扁缩,主体部分偏圆,并使用令人觉得奇怪的曲线(特别注意“ h”)。即便是统一了书体的各个地区,不出几年就又发展出各自的个性化书体。直到1454年古腾堡(Gutenberg)印刷技术的发展,书写才促进开始再次标准化。Blackletter书体在北部占主导地位,Humanistic和Italic书体在南部占主导地位。
然而,即使在标准化之后,个体差异仍然很大。这从16世纪早期的意大利书写大师发行的书写练习册子中可以看出。书写大师们利用先进技术印制教材,把他们自己的书体传授给人们。其中最早的是1522年的Ludovico Arrighi。其他大师也不甘落后,他们都用Chancellory Italic书体书写,但他们的风格个性仍然非常显著。例如,他们的小写字母“p”(图一,第七行)的形式和风格差异就很明显。本纳尔迪诺·卡塔尼奥(Bennardino Cataneo)堪称那个年代一流的书写大师。他大量发表书籍的能力为越来越多的人读书识字创造了条件,并增加了社会对书籍的需求。此时,Italic书体达到了顶峰。从1545年的这个例子(图一,第八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今字母形态的起源。
2.自然性(spontaneity)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这里的“自然”指的是在书写过程中自然发生的、不做作的、未经过刻意加工的意思。历史上,西方书法传统中的书写主要在于记录信息,书写艺术的自然性不是特别重要的考虑因素。有时,书法的装饰性很强,尤其是用于宣讲的文本,虽然艺术性较强,但是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非在书写中自然而成的。话虽如此,有些时候在书写过程中也是需要显著的自然性和创造力的。例如,如果出现漏写,常见的一种弥补方式是把漏写的单词或短语写在页面上的另一位置,然后画一只手指向其应当的位置。手的形式是没有一定之规的,往往由书写者自发创造。有时甚至不再是一只手。例如,近期完成的《圣约翰圣经》的书写者使用了一只鸟拉着横幅,一只蜜蜂在滑轮上工作,以及一只狐猴挂在藤蔓上的方式来指示遗漏文字的位置。
在现代西方作品中,自然性更为突出。这可能是自19世纪末以来东方书法的传统对西方书法产生了影响的结果。在下面示例中[5],拉丁字母是用一支尖头笔书写的。这些字母以非常自由的方式相互连接,而不是按照某种既定的书体书写的。背景中的文字字体较小,字母垂直排列。前景中的笔画粗壮的字母与背景中轻巧玲珑的书体相对照,为作品的整体创造了深度。再看一个示例[6],此作品以非常线性的方式书写,其中几处随机的区域使用的墨水量较多,表现出一定的自然性。文字的行与行之间没有空格,尽管字母与字母彼此接触,但与前一示例不同,它们并不重叠。然而,此作品的观感显得比前一作品更为密集,并且具有类似编织的视觉效果。
3.物像(presence of nature)
尽管自然界的事物、现象与气韵在西方的书法传统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于中国书法,但它们也是存在的,是与书写显然相关的。首先,自然图像是拉丁字母——即西方书法的主要字母体系——的历史渊源。几乎所有的印欧书写系统都是从古代中东的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而最早的象形文字就是基于自然事物的图像,尽管当今的拉丁字母与它们所源自的古老形式几乎没有视觉相似性了。例如,字母“A”源自埃及象形文字的“apis”(牛),看起来像牛的头。它被简化,然后倾斜,最终形成了Imperial Roman书体中的形式。
在近1800年以来的诸多西文手稿中,人们可以看到灵感来自自然的众多装饰元素。其中包括各种植物,尤其是藤蔓树叶、花朵和水果,以及鸟类和人。有时,这些元素非常风格化,甚至几乎达到无法识别的程度。弗拉芒(Flemish)语的《时光手册》(Book of Hours)中的一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图中有风格化的老鼠簕(acanthus)叶和带有镀金叶子的小藤蔓,而缎带上的文字从老鼠簕的枝茎中蜿蜒而过。[7]自然的图像不仅仅可以是装饰元素,而且可以成为作品的组成部分。有一些与文字特别相关的微型插图,可以在《时光手册》和《圣经》的福音部分中经常看到。有时,字母本身就是由自然图像形成的。例如,Lindisfarne福音(约公元715年至720年)中的字母“M”就是由奇幻生物组成的。[8]自然图像和文字完全融合的较早期的示例还可以在1390年的贝加莫字母表(Bergamo Alphabet)中找到,这是此时出现的许多此类的字母表之一,其中的字母本身就是由动物和人共同组成的。[9]
4.教学理念与实践
当我们向学习中国书法的学生讲授西方书法时,与其一味强调两者的差异以至于构建某种片面的、不甚真实的二元对立,我们不如建议将学生带入一个处于东西方二分框架之外的第三空间,加强介绍两个书法传统的共性。在这一教学理念的指导下,以上谈到的各点都可以直接采用为“西方书法”这节课的教学内容。尤其就风格、自然性和物象来说,教师可以直接借用第2部分中的文段为学生具体说明西方书法与中国书法在这三个方面的共通之处。
進一步就教学理念来说,首先,鼓励学生超越“此优彼劣”的简单对立的思考模式,看到中国书法与西方书法的相关性、复杂性、多样性。比如,我们可以明确地引导学生思考中国书法与西方书法是如何体现书写的艺术升华的,是哪些因素让它们都不仅仅是书面交流的工具形式,而且是体现了人们对美学理想的追求并从而实现的艺术形式。在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学生可以从最宽广的层面思考人们对美的普遍体验,思考中国与西方书法的传统是如何发挥人们共有的美学倾向的——如对平衡(balance)与风格个性(individuality)的共同偏好——又如何同时在具体的表达方式上具备各自的特点的——如对重复(repetition)、规则(neatness)、生动(vitality)的不同理解。用这样的第三空间的思维思考,学生对中国书法与西方书法的理解更丰富、更细致、更全面。
在教学实践中需要重视用更丰富的实例来说话,可以将两种传统中的相关示例并排摆放以显示它们美学原理的相通与相异之处。的确,要做到更为全面客观的学习,就要查看西方书法的历史实例,以了解其近两千年来字母形态的发展,了解它们形态的多样化,了解其视觉美学的丰富性。就此值得推荐的是Mira Calliraphiae Monumenta这部16世纪的非凡作品。它不仅包含大量书体,而且展示了书写中的各种装饰与自然绘画的细节。如此把具体的书法作品的实例呈现给学生,让他们根据看到的例子来形成自己的理解,能够支持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简单引用现有出版物中作者的观点并被动地把它们当作真理来接受,以避免继续传播以往学者的片面理解。
最后,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还主张为学生较为系统地示范西方书法书写的基本技巧,指导学生使用西方书法的工具,并参照两三种主要书体的范本来练习书写拉丁文字。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并讨论西方书法与中国书法在技巧层面上的相异与相通之处。相异之处也许不难指出,而相通之处恐需要学生对中、西书法艺术技巧有较为深入的理解。本着“第三空间”的教学理念,后面这点应当作为两者中的重点。在这点上作为教学内容的实例可以包括西方书法中的衬线(serif)与楷书中起笔收笔笔法的相通之处。衬线是西文字母中主要笔画、起笔与收笔的地方带有装饰性的凸起。比如,历史有两千多年之久的罗马字体即为一种有衬线字体。然而衬线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而是与书写的工具、材料和技巧紧密相关的。古罗马人最初使用的是软的毛笔,先将字母用毛笔蘸墨书写在石质表面上,然后才进行刻塑的,衬线的出现即是使用毛笔与墨书写的结果。这与中国书法的楷书中起笔与收笔的技巧有可比之处,因此,中文印刷体中的宋体采用了衬线是非常自然的。再例如,教师还可以启发学生思考笔顺在西方书法中的重要性,正如在中国书法中强调笔顺一样,按照笔顺书写的西文字母也往往被认为是更为规范美观的。
结语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教授西方书法的知识来促进海外大学生对中国书法的学习。传统的教学方式往往用比较与反差的方法强调中国书法与西方书法的不同,以突出中国书法相比之下的优越性。本文认为这种方式有其局限性,不利于避免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僵化理解。本文主张用“第三空间”的思维组织教学,帮助学生超越对中国书法与西方书法二元对立的理解模式,使他们不仅能了解两种艺术传统的独到之处,更能理解和欣赏它们之间的共通之处,不仅从两者中都得到丰富的滋养,更能从较高的层面上领会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与复杂性。在西方和中国书法传统之间的交叉影响越来越显著的现代,这一练习将对学生特别具有启发性与教育意义。
注释:
[1]Chiang,Y.(1973). Chinese Calligraphy: An Introduction to Its Aesthetic andTechnique.(Third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Chiang,Y.(1973). Chinese Calligraphy: An Introduction to Its Aesthetic andTechnique.(Third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Wong, F. (1999). The complete calligrapher.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4]Kramsch, C. (2011). The symbolic dimensions of the intercultural. Language Teaching, 44(3), 354–367. DOI: 10.1017/S0261444810000431
[5]Stevens,J.(n.d.). Alphabet on text [Ink on paper].见:https://www.berlinersammlung-kalligraphie.de/kgraph_stevens_e.htm
[6]Cornil, L. (1997). Illusies [Ink on paper].见:https://
www.berliner-sammlung-kalligraphie.de/kgraph_cornil_e.htm
[7]Master of Guillebert de Mets (1450-1455), et al. Book of hours. [Tempera colors, gold leaf, and ink on parchment bound between pasteboard covered with calf].见:http://www.getty.edu/art/collection/objects/1449/master-ofguillebert-de-mets-and-master-of-the-lee-hours-and-master-of-wauquelin'salexander-book-of-hours-flemish-about-1450-1455/?dz=0.5000,0.7641,0.37
[8]Lindisfarne Gospels.(700年左右).見:http://www.sunderlandminster.com/event/presentation-by-revd-john-mcmanners-wearmouth-and-jarrow-and-the-lindisfarnegospels/lindisfarne-gospels1/
[9]Grassi, Giovannino dei (1390). Bergamo alphabet.见:http://luc.devroye.org/fonts-41890.html
作者单位:
李煜 美国洛约拉玛丽蒙特大学
Marcia Watt 美国独立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