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乡土本色”篇的三大学术观点,让诗人、作家来表达会怎么样?
——说说“学术论证”与“文学书写”的区别
2021-11-02魏建宽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
◎魏建宽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
一、《乡土中国》第一章“乡土本色”的逻辑框架——一个中心论点与三大分论点
《乡土中国》全书共有十四章,第一章“乡土本色”于全书的地位,是总论性质的一章。
这一章论述的主题为“乡土本色”,篇幅不长,仅3000余字,有一个中心论点、三个重要的分论点。
中心论点(第 11自然段):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也正是基于这个核心观点,作者将他的整部书定名为“乡土中国”。
三大分论点:
(一)从中国人口数量最多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上分析,农民以“土地”为谋生手段,他们无法离开“土地”,因此“乡下人”安土重迁,以世代定居于自己所谋生的“乡土”为“常态”,“迁移是变态”。(第2~6自然段)
(二)从乡土社会的社区与社区的空间关系上分析,不同社区间人与人的关系以“孤立与隔膜”为常态,不同社区之间“人口的流动率小”,因此乡土社会中各自社区内的“生活是富有地方性的”。(第7~10自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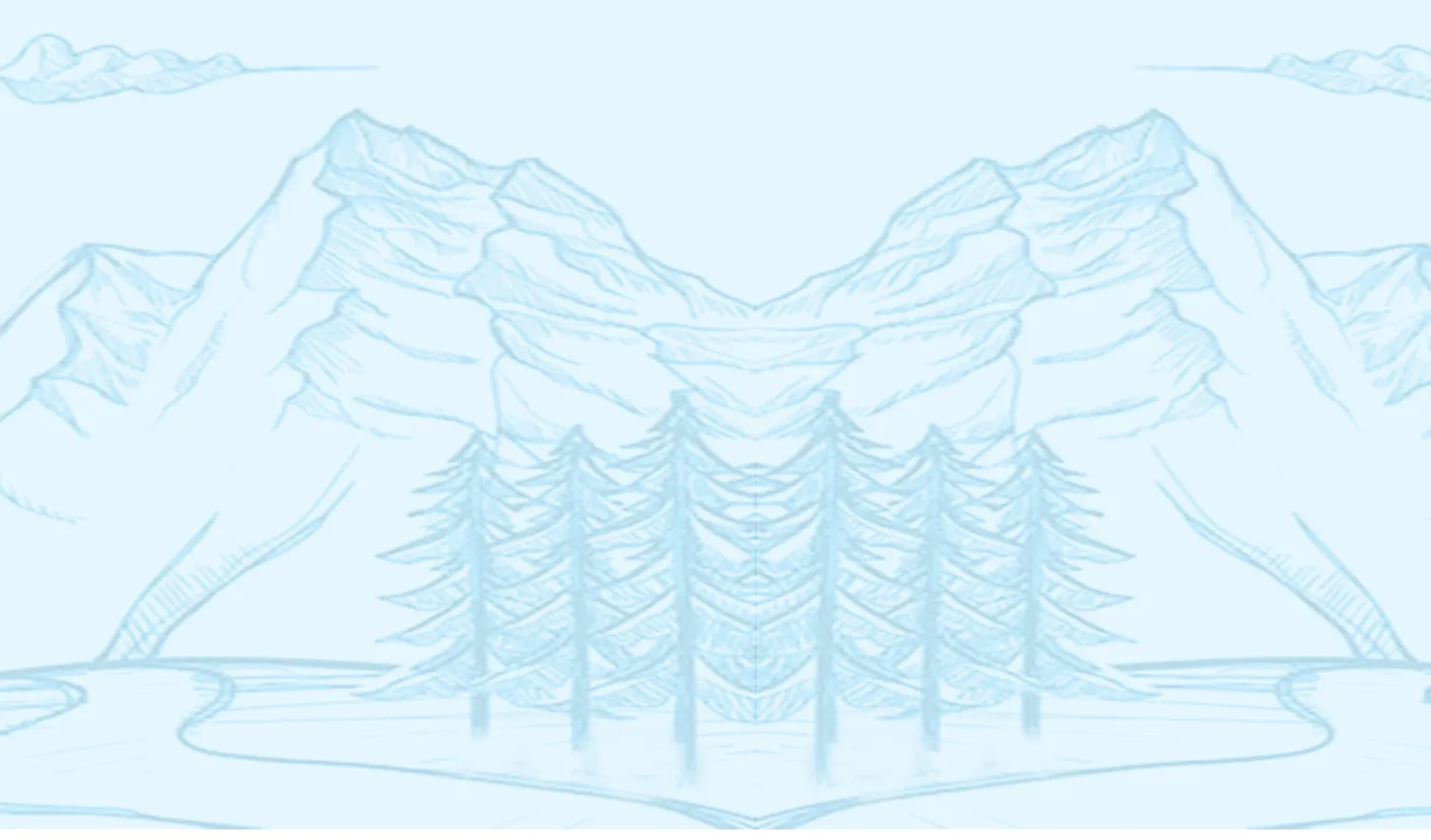
(三)从乡土社会每一个社区内部人与人的关系分析,“生于斯、死于斯”的每一个人,共同构成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个“熟人社会”主要是依靠每个人从这个“熟悉的社会”中“习”得的“礼俗”来作为“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办法”,因此,乡土社会的治理主要是依靠“礼俗”而非依靠“法理”。(第11~17自然段)
二、作者笔下“乡下人”的“土气”,如果让诗人臧克家、牛汉来表达会是怎样
作者为了得出“乡下人”身上存在视土如命、安土重迁这种“土气”特征的结论,采用的论证手法完全是一个社会学家的学术论证的手法。
作者为了论证“乡下人”视土如命、安土重迁,他密集援引了五个例子来作为论据:中原的农民迁徙至适宜放牧的草原,依旧锄地播种,不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中国的农民漂泊至西伯利亚,却不管天气适不适合耕种,仍要试着下种看看能不能长出庄稼;乡下人视土地公、土地婆为最亲近的神;奶妈偷偷塞一包灶土给即将出国留学的作者;毗邻蒙古人聚居的张北人,他们的语言从不受蒙古语影响,而且村庄几百年也只是几个姓的人聚居于固定的地域。
作者除了援引能正面支持论点的事例,当然也注重从对比的角度去援引事例,借助对比论证来增强自己观点的说服力。为了证明“以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只是变态”的观点,他举出了一个例子,即广西瑶山某些区域就存在原来聚居的地方“人口到了饱和点,过剩人口只得宣泄出外”的“迁移”现象,这些迁移的瑶人迫不得已去寻找新的土地来开垦、种植,繁衍自己的后代。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来归纳一下“学术论证”中的“以事说理”的特征——重视“事”与“理”之间的逻辑关联。“事”与“理”之间的关系,是论据与论点的关系,论述者所要做的就是努力建立“事”与“理”之间的逻辑关联,并努力使自己的论点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说服的力量。
“以事说理”,与其他说理方式相比,生动、易懂,而且人们又信奉“事实胜于雄辩”这个道理,因此“以事说理”是社会学家最常运用的“学术论证”手法。
现在,我们要谈论的另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同样谈论“乡下人”的“土性”及他们的一辈子“粘在土地上”,换作诗人会怎么表达呢?
因为只有意识到这两者的区别,我们读学术著作,才会慢慢地学会自觉地运用阅读学术著作的思维与方法去理解学术著作。
请看臧克家写于1942年的诗歌《三代》:
孩子
在土里洗澡;
爸爸
在土里流汗;
爷爷
在土里埋葬。
这首诗简洁到极致,就21字;质朴到极致,没有一个形容词,三个名词“孩子”“爸爸”“爷爷”,三个动词“洗澡”“流汗”“埋葬”,一个介词短语“在土里”重复出现。
诗歌《三代》有没有主题?当然有!臧克家想不想说出某个道理?当然想!但诗人臧克家不直接表达,这就是许多优秀诗歌所共有的艺术特征——含蓄,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优秀的诗歌必须要有“美”的品性,“理”往往隐含于诗歌的意象与借助一组组意象营造的意境背后。
“在土里洗澡”的“孩子”,未来必定重复“爸爸”的命运,即“在土里流汗”;他年老力衰之时,就是他的血汗被榨尽之时,他又将和他的父辈、祖辈一样,来自“土里”,回到“土里”,“在土里埋葬”。——这就是诗歌《三代》的一组意象背后所暗示出的“理”!
诗歌即使简洁叙事如《三代》,它诉诸读者的也必须是“情”、是“美”,而非直接呈现“理”。
再看看诗人牛汉创作的散文《绵绵土》中的片段:
半个世纪以前,地处滹沱河上游苦寒的故乡,孩子都诞生在铺着厚厚的绵绵土的炕上。我们那里把极细柔的沙土叫作绵绵土。“绵绵”是我一生中觉得最温柔的一个词,词典里查不到,即使查到也不是我说的意思。孩子必须诞生在绵绵土上的习俗是怎样形成的,祖祖辈辈的先人从没有想过,它是圣洁的领域,谁也不敢亵渎。它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活的神话。我的祖先们一定在想:人,不生在土里沙里,还能生在哪里?就像谷子是从土地里长出来一样地不可怀疑。
因此,我从母体落到人间的那一瞬间,首先接触到的是沙土,沙土在热炕上烙得暖乎乎的。我的润湿的小小的身躯因沾满金黄的沙土而闪着晶亮的光芒,就像成熟的谷穗似的。接生我的仙园老姑姑那双大而灵巧的手用绵绵土把我抚摸得干干净净,还凑到鼻子边闻了又闻,“只有土能洗掉血气”,她常常说这句话。
我们那里的老人们都说,人间是冷的,出世的婴儿当然要哭闹,但一经触到了与母体里相似的温暖的绵绵土,生命就像又回到母体里安生地睡去。我相信,老人们这些诗一样美好的话,并没有什么神秘。
今天的年轻人读到这样的文字,会作何感想?恐怕会说:这也太不卫生了吧!
这样的文字如果给妇产科的医生读到,更会摇头:这简直就是迷信!
但这样的文字就是“文学的文字”,这样的表达就是“文学的表达”!
文学的文字,文学的表达,你不能以“科学”的“求真”的眼光去打量,你要“入情”,方能感受到其中的“至理”!
牛汉说自己“半个世纪”都忘不了“苦寒的故乡”的绵绵土,因为绵绵土让他来到这个人间感受到如母体的“温暖”与“温柔”,尽管“人间是冷的”,但是在故乡、在故乡的仙园老姑姑手里与眼中、在故乡的“无法解释的活的神话”般的习俗里,诗人仍然能感受到人间的暖意。
在牛汉的笔下,接生婆仙园老姑姑、故乡的老人们,显然都被诗人诗化了;牛汉对故乡的依恋也被他用“我的祖先们一定在想”这样的揣想放大了;牛汉故乡的老人也绝对说不出如下富有诗性的文字——“人间是冷的,出世的婴儿当然要哭闹,但一经触到了与母体里相似的温暖的绵绵土,生命就像又回到母体里安生地睡去”,故乡的老人们的这些话无疑是被诗人牛汉进行了“文学美容”的文字。
不过,读诗歌,读散文,人们要的还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份诗性,这样的一份“不真实”,这样的一份“不合理”,人们还就是特别愿意接受这样的“欺骗”!
这就是文学的表达!
三、作家梁鸿与陈忠实如何书写“村落的地方性”与“熟人社会”
费孝通这样论述乡土中国的“村落的地方性”:
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而“村落的地方性”特征,在当代作家梁鸿笔下的非虚构散文集《中国在梁庄》中,却是另一番模样:
我去王家,找王家少年的一个本家婶婶了解情况。
王家,和梁家隔着一条公路,也是我们下地干活的必经之路,然而,却非常陌生,即使小时候玩耍,也很少跟他们的小孩在一起。我不知道小时候是如何有这种区分的,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接受与认同。
王家婶一听我是来问王家少年的事,非常警惕,显然,王家婶不愿意讲他的事情。我们坐下来拉家常,问王家人的生活状况,慢慢知道,原先曾经二十几户的王家人,经过二十多年的变迁,现在只剩下十来户,搬走的搬走,绝户的绝户。王家少年的事一出,王家稍微大一点的男丁,都出门打工了,哪怕出去搬砖块,也不愿意待在村里,怕人看不起。
作家梁鸿上面三段文字叙写的事件,是一个留守乡村的王姓中学生的故事。这个少年原本寡语,性格朴实,读书刻苦,村里人一度都认为这个少年会考上大学,可就是这个王姓少年杀害了梁庄的一位八十二岁的老奶奶……作家梁鸿是一位女作家,她也是一位从梁庄这个乡村出发并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女孩,她现在则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教授。梁鸿以梁庄女儿的身份,尽一切努力去接触这个王姓少年的“本家婶婶”,尝试去探究王家少年杀人这一事实背后的多重社会原因。
就在梁鸿对王家少年“本家婶婶”的叙写及她对王、梁二族关系的追述中,我们看到了今日“乡土中国”的世界,仍然存在着“村落的地方性”这一特征。打小开始,梁庄的幼年的梁鸿与仅有一路之隔的王庄的王家小孩就很少一起玩耍,人口相对较少的王庄的大人与族大人多的梁庄的大人其实也存在着费孝通所说村落与村落之间的人际“隔膜”与“疏离”。
作家梁鸿在文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不知道小时候是如何有这种区分的,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接受与认同”,但作家梁鸿只有感叹,没有对这种社会现象进行解释。即使成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梁庄的女儿梁鸿在写出上述文字时,也没能为我们提供解释,她只是叙述与描写,让读者去分析。
但社会学家却不能悬置疑问,必须给出答案,这又是“文学表达”与“学术书写”的另一个区别!
谈了“村落的地方性”,我们再说说第一章“乡土本色”中最后一个话题——“熟人社会”中的“礼俗秩序”。我想以陈忠实先生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中的一个片段为例:
白嘉轩从槽边转过身走到鹿三当面:“三哥,你看我那个小女儿灵灵心疼不心疼?”鹿三说:“心疼。”白嘉轩说:“给你认个干女儿你收不收?”鹿三惊奇地睁大了不大灵活的黑眼睛,随之微低了头,捏弄着烟锅,脑子里顿时紧张地转动起来,综合,对比,肯定,否定,一时拿不定主意。白嘉轩诚恳地说:“我们三人商量过了,想跟你结这门干亲。当然……这是两厢情愿的事,你悦意了顶好;不悦意也没啥,咱们过去怎样,日后还是怎样。你今黑间思谋思谋,明儿个给我见个回话。”说罢就走出马号去了。
鹿三捉着短管烟袋依然吸烟,烟雾飘过脸面,像一尊香火烟气笼罩着的泥塑神像。这是一个自尊自信的长工,以自己诚实的劳动取得白家两代主人的信任,心地踏实地从白家领取议定的薪俸,每年两次,麦收后领一次麦子,秋后领一次苞谷和棉花,而白家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短斤少两的事。在他看来,咱给人家干活就是为了挣人家的粮食和棉花,人家给咱粮食和棉花就是为了给人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又是简单不过的事。挣了人家生的,吃了人家熟的,不好好给人家干活,那人家雇你干什么?反过来有的财东想让长工干活还想勒扣长工的吃食和薪俸,那长工还有啥心劲给你干活?这样,财东想要雇一个本顺的长工和长工想择一家仁义的财东同样不容易。白家是仁义的。麦收时打下头场麦子,白秉德老汉就说:“鹿三取口袋去,先给你灌。你屋里事由紧,等着吃哩!一石麦子按十一斗量,刨一斗水分。”
上述《白鹿原》中“财东”白嘉轩与“长工”鹿三的这段故事,就是一则很能印证费孝通的“乡村是礼俗治理”这一观点的材料。
你看,“财东”与“长工”,虽然地位不对等,但“财东”白家两代人白秉德、白嘉轩父子都待鹿三以仁义,“长工”鹿三也以“本顺”与“踏实”回报白家。白家的上一代主人白秉德的“仁义”体现在作者对细节性事件的叙写上——麦收后立即以麦子这一薪俸物付给鹿三,而且是超额给付。而下一代主人白嘉轩这个“少东家”的“仁义”更是非同寻常,为给即将满月的宝贝女儿白灵寻个干爹,他自己虽有意寻当地有身份与地位、开着中药堂的世交冷先生做女儿的干爹,但最后还是听从了母亲白赵氏的建议,选择了他的长工鹿三,这无疑出乎鹿三的意料。正因为如此,鹿三听罢白嘉轩的请求,才会“惊奇地睁大了不大灵活的黑眼睛”,才会有小说中后面描写他的一大段的内心纠结!
长工鹿三内心大段的独白,思量的其实就是当时乡村社会的“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所依据的“礼俗秩序”。作为一名长工,他与财主东家之间,并没有按手印的契约来规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他们只是依据着一代代留传下来的稳定的秩序来行事。白嘉轩依照他爹爹白秉德对待长工的方法来对待鹿三,然后又顺从地采纳了他母亲的建议去请求鹿三做女儿的干爹。我们可以想见,白鹿原这一村落中最符合儒家文化教化下的“礼俗秩序”中的财东与长工的交往关系也都应该是这样的,这也正是作者陈忠实先生借助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所要肯定的。
至此,这一讲可以作一个总结啦!
对同一社会现象的思考,诗人、作家与社会学家表述在自己的笔下,其文字的形态是不一样的。作家重“情”,社会学家重“理”;作家重视“审美”,社会学家重视“求真”;作家重视文学手法的运用,社会学家重视逻辑分析论证。哪怕是讲同一种社会现象的故事,他们的文字风格也是迥异的!
因此,读《乡土中国》首先要学会以阅读“学术著作”的思维与方法去读,这样你才会更多地体味出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文字背后的“理趣”;其次,为了更好地读懂《乡土中国》,也可以借助已经读过的文学作品中的与《乡土中国》提及的同一类社会现象的书写,进行对比分析,这样无疑能够加深对《乡土中国》中学术论证及学术思想的理解。
总之,阅读《乡土中国》不能完全沿用高中之前阅读文学作品的思维与方法,但已经阅读过的文学作品也能有助于高中生读懂《乡土中国》。因此,从这一角度上说,《乡土中国》的学术阅读与文学经典的阅读并不是“互斥”的关系,而是存在“互补”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