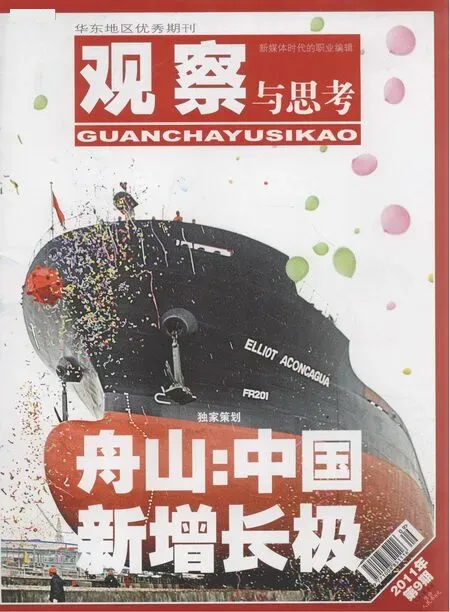马克思建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哲学背景分析*
2021-10-11陈永盛
陈 永 盛
提 要:明晰马克思建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哲学背景,是研究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重要前提。只有明晰了马克思建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哲学背景才能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观与传统哲学根本区别的核心要义,以及把握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观实现哲学革命的真精神,并有助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研究。马克思建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哲学背景可概述为:首先,传统哲学完成,黑格尔哲学是传统哲学理性主义精神的集大成;其次,传统哲学脱离现实达到了极致,形成致命的自我危机;最后,传统哲学在内外因的推动下走向瓦解,此后,哲学研究拒斥形而上学,转向生活世界。
马克思通过建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终结了传统哲学,实现了哲学革命,不仅仅使哲学研究的主体从宇宙本体转向现实的人,而且使哲学研究的对象从思维世界转向现实生活世界,还使哲学研究的范式从知识论范式转向生存论范式。这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观实现哲学革命的真精神及其与传统哲学的根本区别。通常,研究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观,主要聚焦在马克思如何建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及其理论内容和价值意义上,而往往忽视马克思建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哲学背景本身。事实上,如果缺失对马克思建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哲学背景的清晰认识,不仅不能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观与传统哲学根本区别的核心要义,甚至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观实现哲学革命的真精神。可见,梳理、分析马克思建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哲学背景,是研究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重要前提。
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不难发现,马克思建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正处于传统哲学完成且开始瓦解并向现代哲学过渡的特殊时期。这是说,传统哲学完成与瓦解是马克思建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哲学背景。因此,分析马克思建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哲学背景,关键在于要明了传统哲学的完成和传统哲学何以走向瓦解以及如何瓦解。基于此,笔者试图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梳理分析,以期实现对马克思建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哲学背景形成清晰明了的认识,从而有助于深化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研究。
一、传统哲学的完成
按照流行的见解,传统哲学是指从古希腊哲学到黑格尔哲学为止的这一阶段历史形态的哲学。这种划分并非是单纯的时间性划分,而是一种“理论性概念”的划分。因为传统哲学在追问世界的始基、本原和本质时,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为理论特征,其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黑格尔哲学是这种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它以恢宏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建构了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黑格尔之后,哲学的发展纷纷抛弃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几乎所有的哲学都对形而上学发起攻击,要求拒斥形而上学。同时,自马克思发现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症结并对其进行批判起,特别是针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进行批判,尔后的哲学运动几乎都以攻击黑格尔哲学为开端,呼吁哲学要摆脱传统哲学的思辨性和形而上性,把哲学与现实相结合,在现实中追问人的本真存在,关怀人类。可见,黑格尔哲学是传统哲学的完成,被视为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过渡的一个分水岭。对此,美国哲学家怀特指出:“几乎20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名声赫赫的19世纪的德国教授的观点开始的。……我这里指的是黑格尔。”①[美]怀特:《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杜任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7 页。
那么,我们是如何具体地界定黑格尔哲学就是传统哲学的完成?或者说黑格尔哲学在何种意义上表明了自己就是传统哲学的完成?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它以理性主义的方法,围绕本体论的“何物存在”问题和认识论的“如何认识”问题展开,并以试图找到这些超越现实生活和永无定论的形而上学问题的终极答案为自己的总体特征和研究目的。早期的传统哲学,特别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哲学所追问的形而上学问题主要是“存在是什么”。因此,形而上学在早期传统哲学中以巴门尼德排斥“非存在”的经验对象的“意见之路”而要求把“存在”作为哲学对象的“真理之路”为开端,尔后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得以形成(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②海德格尔在批判传统哲学时,指认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同时还坚决地确认马克思哲学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时起到颠覆性的作用。他在《面向思的事情》中说道:“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参见[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 页。),最后由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确定,即形而上学是一门“作为存在的存在”学问。尔后,经过启蒙运动的拯救,哲学得以从神学的樊笼中挣脱出来,并实现从此以独立化了的主观精神去探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即追问“我们能够认识什么?”这被认作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也就是哲学的重心从本体论的“何物存在”的追问转向认识论的“如何认识”的追问。
事实上,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或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其实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77 页。一方面,就这个问题的双方何者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两大不同派别,那些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属于唯心主义学派,而认为存在、自然界是第一性的则属于唯物主义学派;另一方面,这个问题本身所包含的对思维是否能认识世界本身而形成的不同回答又可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凡是做出肯定回答的都是可知论者,他们认为世界是可认识的;而凡是做出否定回答的则是不可知论者,他们否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但无论哲学就此问题演化成何样,它总是要指归到某个同一性之上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把这个同一性指归为是终点与起点同一的绝对观念。这样,全部哲学就成为绝对观念外化为自然界,再经过其自身的自否性返回到自身的,以认识论、本体论和逻辑学同一原则建构的包罗万象的形而上的体系哲学。由此,绝对观念就被宣称为绝对真理,并能通过思维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因而也就把一切矛盾消灭在绝对观念的自否性过程中,从而实现全部哲学的完成。
在黑格尔的整个学说中寻找上述的佐证,人们似乎受到马克思曾说过的一句话的影响,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现在看一看黑格尔的体系。必须从黑格尔的《现象学》即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01 页。。人们把主要的关注点都放在了《精神现象学》中。诚然,《精神现象学》无疑是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一本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性”的著作。单就其提出“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③[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年版,第12 页。这个命题就足以把哲学引向“科学”,从而完成哲学的使命,解决一切哲学问题。但如果只把注意力局限在《精神现象学》上,那意味着不仅没有对黑格尔的整个学说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甚至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所说的那句话。首先,就马克思的话而言,马克思本人也只是把《精神现象学》作为批判黑格尔体系的开始,而没有把《精神现象学》当作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并且在批判过程中虽然用了大量篇幅着墨于“现象学”,但马克思强调所有的工作在于有必要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进行批判。其次,就黑格尔的整个学说来说,《精神现象学》只不过是黑格尔建构一个思辨哲学体系的第一部分。在《精神现象学》1807年初版的封面上就印有“科学的体系,第一部分,精神现象学”等字样。同样,黑格尔在尔后完成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中把他的思辨哲学体系划分为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个部分,而精神现象学则被他压缩为精神哲学的一个环节。在此,虽然不能把《精神现象学》等同于《哲学科学全书纲要》中的“精神哲学”的一个环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反对把《精神现象学》当作黑格尔整个学说来解读。
在笔者看来,寻找黑格尔哲学作为传统哲学的完成应该到代表黑格尔整个学说体系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中去。《哲学科学全书纲要》是黑格尔亲自经手出版的四部著作之一,与其他三部,即《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法哲学原理》不同的是,《哲学科学全书纲要》历经三次修改、三次出版,而第三版出版时已经是1830年。也就是说,《哲学科学全书纲要》完全可以代表黑格尔最深思熟虑的思想。在这本著作中,黑格尔明确哲学作为科学的唯一目的和目标,即“达到自己概念的概念,并以此而达到自己的回归和满足,这甚至就是这门科学的唯一的目的、作为和目标”①[德]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30 年版),薛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7、14、17、17、15 页。。同时,黑格尔强调,一种科学的哲学思考必然是一种体系的哲学思考,因为关于绝对东西的科学本质上是体系。为了建构这样的一种体系,黑格尔首先规定哲学是对一些对象的思维着的考察。与其他哲学家将一个特殊性的对象作为思维对象,如数、空间等等不同,黑格尔把这些对象规定为是思维自身。也就是说,哲学是一种内在的同一性发展,“哲学的历史内所阐述的思维的同一发展,也会在哲学本身内得到阐述,但却是摆脱了那种历史的外在性,纯粹地在思维的原素之内”②[德]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30 年版),薛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7、14、17、17、15 页。。可见,哲学的发展作为一种自身同一性,没有历史的外在性的发展,使其自身成为自由的和真实的。黑格尔把这种自由的和真实的东西称为理念,并且是绝对的理念、绝对的东西。但在黑格尔看来,理念又是把“自己显示为完全与自身同一的思维,而这一思维同时又把自己显现为这样的活动:它为了是自为的,把自己本身同自己对立起来,并且在这一他物中只是在自己本身”③[德]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30 年版),薛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7、14、17、17、15 页。。这样,黑格尔就成功地把哲学分成了逻辑、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三个部分。④[德]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30 年版),薛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7、14、17、17、15 页。
I.逻辑,自在而自为的理念的科学。
II.作为理念在它的他在中的科学,即自然哲学。
III.精神哲学,精神在此作为从理念的他在中返回自身的理念。
但哲学的每一部分又都是一个哲学的整体,它又都是一种把自身在其自身内封合起来的圆圈,而每一个圆圈又可以突破自身作为推理进程的开始。因为“它在自身内是总体,它也是它的要素的界限,并会奠定起进一步的一个领域,因此整体把自己表现为是一些圆圈组成的一个圆圈,那些圆圈中的每一个圆圈都是一个必然的环节”⑤[德]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30 年版),薛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7、14、17、17、15 页。。在此,笔者把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绘制成如下这样一个图。

通过透视黑格尔的思辨体系不难发现,黑格尔通过概念思维的方式实现了对绝对真理的把握,不仅通过使实体等同于主体从而消解一直以来的本体论(存在论)的哲学问题之争,而且通过实体即主体的自否性实现对自身的认识,从而消解了一直以来的认识论的哲学问题之争。由此,可以确定,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无疑就是传统哲学的完成。
二、传统哲学的弊端:脱离现实
但是,随着传统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达到顶峰,特别是以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作为完成者,传统哲学自身的弊端也就完全暴露了出来,并由此孕育着深刻的危机。这种弊端表现为哲学脱离现实,成为凌驾于科学和现实生活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
事实上,传统哲学在其早期的古希腊时期就表现为脱离现实,并凌驾于科学和现实生活之上。因为它们自摆脱神话宇宙论的传统藩篱起,就试图运用理性思维在自然界的范围之内追问万事万物的根源,寻找世界万物的始基,而不关心现实生活。因此也常常为人所诟病,哲学家经常被指责能够认识天上的事物,却看不见脚下的东西。如果说这种始基的追问还是一种素朴的、自然直观的追问,那么到巴门尼德时就完全上升到了形而上学的高度。巴门尼德用“存在”这个形而上范畴代替了之前被人们认为是世界的始基的那些东西。与此同时,巴门尼德还为以后的哲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即区分开依据感官知觉的“意见之路”和强调理性思维的“真理之路”。如果说苏格拉底,这位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并提出应该把哲学的研究从深邃玄奥的自然界转向人自身,去关注正义、美德、勇敢、虔诚等与人相关的问题,那么,似乎哲学并没有脱离现实,并没有凌驾于现实生活之上。但苏格拉底的改变除了诘难人们,使人陷入矛盾,从而认识到自己没有苏格拉底那么有智慧,需要反思认识自己之外,并未给希腊城邦的现实生活带来任何改变。如果说苏格拉底最出彩的嫡传弟子柏拉图真正努力试图完成先师的使命,试图用哲学来管理城邦,建设一个哲学王的“理想国”的话;那么,这也只不过是理论思维向工程设计的僭越。这种僭越从一开始就注定“理想国”不能实施,但原因并非是其设计的方案不够好,而是“因为用理论思维只能设计出理念的国家,而理念的国家不具有工程的可实施性”①徐长福:《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15 页。。当然,“理想国”不能实施,并非就代表哲学脱离现实,或许只是表示关涉现实的失败。其实,这只不过是在为否认柏拉图“理想国”的形而上性找借口。深入细想,“理想国”的失败不正是脱离现实,没有与当时的现实状况相符合,没有真正站在人们(包括人数居多的奴隶)立场来考虑的后果吗?难道这不正是由于它纯粹是形而上的理论理念吗?如果“理想国”真的是关怀人类,从当时现实生活的社会问题出发,而不是理论思维的理想设计,它能不得以实施吗?最后,在希腊哲学衰颓的希腊化时期,哲人们都自觉地放弃沿袭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伟大思辨,转向关注人生苦难和幸福,为被剥夺政治自由的人们寻求一个内心世界的庇护所。但这一组被马克思高度赞扬的自我意识哲学,它的本质的殉道目的却不过是在于对病态灵魂的哲学治疗,“哲学看上去像是精神治疗,针对的是人的忧虑、害怕和痛苦”②[法]皮埃尔·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张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年版,第104 页。。可以说,这是在寻求在一切变故面前“不动心”的哲人境界。因此,这时期的哲学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关照,不如说是刚好与现实背道而驰。总的来说,传统哲学在早期都是一种犬儒主义式的、“不要挡住我追寻真理的阳光”的、凌驾于现实生活之上的形而上学。
当哲学从中世纪神学权威挣脱出来之后,哲学家们纷纷试图揭开世界的神秘面纱,用理性重新认识世界,探索绝对真理,建构能够终结一切的形而上学体系。在最先的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有过一段短暂的关怀人生的灿烂时光,因而也是哲学与现实最接近、最亲密的时刻。主要表现为哲学关注感性的解放,要求使人从旧式的神学禁锢中解放出来。“以丰富多彩的自然人性来反对枯槁干瘪的抽象神性,以生机盎然的现世生活来反对枯燥冷漠的天国理想,以人的正常情欲和感官享乐来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变态虚伪。”①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120 页。但这个时期的哲学并没有提出什么深刻而系统的思想,更多的只是创造一种新的文化精神氛围,并且他们的思想往往又自相矛盾或带有浓重的中世纪的陈腐气息和怪诞性。正如黑格尔所言,“在他们身上,那种想要有意识地去认识最深刻的和具体的事物的热切渴望,却被无数的幻想、怪诞念头、想求得占星术和土砂占卜术等秘密知识的那种贪念所破坏了”②[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第374 页。。
同时,随着启蒙运动的展开和深入,理性获得了如同中世纪神学教条所拥有的权威,理性成了统治的力量,特别是17世纪后理性在各个领域取得胜利。但与此同时,随着理性张力的扩张,它很快就使自己变成绝对化,并支配着一切。“人的存在被抽象化成了理性的化身,世界成了由人的理性所构建的世界。”③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6 页。事实上,近代的传统哲学正是这种理性的代言。哲学家们运用这种思辨理性或工具理性去探索普遍的、永恒的和绝对的终极真理,并且常常宣称自己找到了这种真理或至少是这种真理的一部分。由此,他们也常常用自己的哲学建构关于整个知识的体系,并宣称解决了一切问题,使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和衡量标准。
笛卡尔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开创者,他宣称找到了哲学把握绝对真理的阿基米德点和那根撬动整个哲学的杠杆,即“我思”和“普遍怀疑”。通过“普遍怀疑”,笛卡尔否弃了一切存在物,认为只有“清楚明白”的“我思”存在。正是从这种“我思”这个阿基米德点出发,笛卡尔建构了自己的理性主义的理论体系。继笛卡尔之后,斯宾诺莎把这种理性主义进一步彻底化和系统化。他认为笛卡尔的“我思”并非“清楚明白”,因为它是有前提的,即必须要经过普遍的怀疑。因此,斯宾诺莎认为,真正清楚明白的观念必须是自身自足和自明的,而具有这种特性的真观念只能是“神”的观念。正是从这个“神”的真观念出发,斯宾诺莎运用几何推理建构了他的形而上学体系。尔后,这种理性主义经过莱布尼茨的推进,最后在沃尔夫那里走向了独断论。“他(沃尔夫——笔者注)把哲学划分成一些呆板形式的学科,以学究的方式应用几何学方法把哲学演绎成一些理智规定,……把理智形而上学的独断主义捧成了普遍的基调。”④[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年版,第210 页。康德从根本上对这种独断论的唯理主义哲学体系进行了清算,他认为我们关于真理的认识并不是独断论式的“观念符合对象”,而是“对象符合观念”。这样,康德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达到了形而上学的顶端,即“人为自然立法”。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康德自己也承认理论理性的局限,因而使理性在“实践”中关怀人性,为人的道德立法。但康德在实践领域中用实践理性为道德立法所运用的是道德律令,并且要求灵魂不朽、上帝存在和意志自由,这是不争的事实。可见,其实这只不过是实践领域的形而上性的体现,并且康德的道德律令除了在形式上规定“应当这样”“应当那样”,并非与“现实”相关。黑格尔继费希特之后,把传统哲学的形而上性推到顶点。可以说,黑格尔哲学是传统哲学脱离现实的“完美代表”。因为他使一切都变成了绝对理念自身转换的一个环节,一切事物、规律和现象都从这个源泉里流出,都是它的反映,同时又都引回到这个唯一的源泉那里。“一切其他事物,自然的一切规律,生活和意识的一切现象,都只是从这源泉里流出,它们只是它的反映。”①[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第26 页。
诚然,与唯理主义相对的经验论者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哲学探索的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从经验、人和自然出发,特别是18世纪法国哲学提出了近代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哲学新思路。但无论是经验论者还是18世纪法国哲学,它们进行哲学探索的目标无不是要求达到对世界的终极解答,而非关怀人生。此外,由于他们在对主客、心物、灵肉的分裂等问题上的反驳论证中失败,使得他们口口声声的“人”要么沦落为拉美特利的“机器”,要么成为形而上学体系中的一环。最后,“人无非是体系中作为‘动物’中一个类的‘人’概念的外部表现。人的本质不是存在于人的现实存在中,而是存在于体系中的‘人’概念中”②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9 页。。正是如此,马克思在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进行剖析时发出“唯物主义变得漠视人了”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331 页。的感慨。
综上,传统哲学由于它本身的形而上特性,注定了其必然是脱离现实的,并凌驾于科学和现实生活之上。也正因为这样,它在自身中孕育了深刻的危机,并在最后从其终结处走向自我瓦解。
三、传统哲学走向自我瓦解
当传统哲学发展到黑格尔哲学的思辨体系时,传统哲学的形而上特性取得了独占的统治。当时,黑格尔哲学是国家哲学,获得全线胜利。“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渗入了各种科学,也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而普通的‘有教养的意识’就是从这些通俗读物和日报中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73、273、299 页。但在恩格斯看来,黑格尔哲学的“这一全线胜利仅仅是一种内部斗争的序幕罢了”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73、273、299 页。。事实上,在黑格尔之后,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不再是哲学家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目标。相反,哲学家们纷纷举起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帜,并且几乎都以攻击黑格尔哲学作为自己的开端,要求从抽象化的思辨体系中挣脱出来,转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关怀人类。可以说,传统哲学完成于黑格尔哲学,又瓦解于黑格尔哲学。传统哲学的瓦解既有来自自然科学进步和社会历史变迁需要等的外部原因,也有来自黑格尔体系内部斗争的原因。
首先,就外部原因而言,精确科学的发展和壮大敲响了以黑格尔哲学为集大成的传统哲学的丧钟。总的来说,18世纪末自然主义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并用它那放弃一切绝对观念性的研究方式影响着哲学的发展。由此,后人也就随着这种变迁和精确科学带来的真相揭晓逐渐对黑格尔所宣称的绝对有效性哲学体系失去了总体信任。具体地说,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的传统哲学研究方式之所以能在19世纪前占领导地位,甚至在19世纪初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主要是因为直到18世纪末,自然科学并没有取得突破性发展,它还是从既成事物开始,先研究事物,然后才研究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言,“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是从那种把非生物和生物当做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73、273、299 页。。但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生物进化论三大发现的出现,自然科学也就从之前作为搜集材料的科学变成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恩格斯认为,当我们的研究实现这种进步时,传统哲学也就走到了终点。“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99 页。因为那些原先被当作是神秘的从而只能从形而上或思辨的逻辑推理来解释的东西,现在通过整理材料的科学对事物存在的原因、发生和构成以及事物自身的联系和事物间的联系等进行科学剖析,实现了向世界进行公开呈现它们的真实本质,从而终结了传统哲学的存在必要性。可见,自然科学的进步直接造成了以黑格尔哲学为完成者的传统哲学走向瓦解。
与此同时,黑格尔主张的哲学属于它的时代的精神反映与它建构的绝对形而上体系的矛盾也日益暴露出来。后人发现,黑格尔的绝对有效性体系根本没有了他们自己所处在的时代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特别是19世纪中期欧洲各国的社会历史状况发生重大改变,社会动荡不安等已经不能在黑格尔万能的体系中找到解答和应对,也不能从这种哲学中得到关于客观世界和人类命运的正确解释。由此,面对经济危机、思想文化堕落和政治动乱等,人们开始放弃理性万能的幻想,要求从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中走出来,把哲学研究导向现实生活世界,关怀人类。
其次,就传统哲学走向瓦解的内部原因而言,主要是在黑格尔体系内形成的两个不同派别进行的斗争而引发的。其实,存在于黑格尔学派内部的纷争由来已久,只是在黑格尔死后才充分暴露出来。这种纷争主要是由那些声称自己已超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的黑格尔的学生,或那些曾经是黑格尔主义的人所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与要求力保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老年黑格尔派的对立所引发的。老年黑格尔派主要有加布勒(G·A·Gabler)、格歇尔(C·F·Goschel)、道布(K·Daub)、亨利希(Henrichs)、海宁(L·V·Henning)、埃德曼、甘斯、米希勒、霍托(Hotho)、瓦特克(Watke)、马海内克(Marheineke)等。他们是黑格尔思辨体系的拥护者,他们要求在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研究时遵循黑格尔的体系结构。不可否认,随着矛盾的分化和时代问题的突出,老年黑格尔派也逐渐认识到黑格尔体系的局限。但他们认为,“只要把一切都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15、515 页。。同时,虽然老年黑格尔派也承认观念、思想、概念等一切独立东西的意识的一切产物是人类社会的真正镣铐,现存的世界受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但他们并没有加以反对,而是认为“这种统治是合法的而加以赞扬”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15、515 页。。然而,他们对黑格尔哲学的拥护和挽救,并没有能够阻挡黑格尔哲学走向瓦解,特别是随着青年黑格尔派的崛起和壮大。
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有大卫·施特劳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卢格、科本、施蒂纳、赫斯、早年的费尔巴哈等。他们主要以“博士俱乐部”为活动中心,抓住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革命性这一生长点,反对在现实的紧迫问题中坚持黑格尔哲学那种超然态度,要求反对教会,宣传无神论和资产阶级革命。但由于当时政治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和他们自身的软弱性,他们只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宗教。因而他们以哲学的形式对黑格尔的宗教理论和基督教教条进行猛烈批判,试图以此撼动基督教的基础,间接实现对普鲁士封建专制的批判或革命。因此,与老年黑格尔派不同,他们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对现存世界的统治是一种篡夺,应该要加以反对。同时,他们认为,为了解除人们受到的来自观念、思想、概念等独立东西的意识的束缚和限制,必须“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16、516 页。。在马克思看来,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满口讲的都是些具有革命性的词句,他们却是最大的保守派。马克思指出,“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16、516 页。。
在这场斗争中,施特劳斯1835年出版的《耶稣传》被认为起到第一推动力作用。在《耶稣传》中,施特劳斯围绕福音书进行考察,并对基督教的产生以及耶稣的生平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施特劳斯发现,神奇的福音故事只不过是在宗教团体内部通过不自觉的、传统的创作神话的途径而形成的,而福音书的前后叙述也不一致,互相矛盾。而青年黑格尔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布·鲍威尔则认为,施特劳斯对福音书进行的批判所能达到的效果,只不过是肯定“实体”是在世界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但这并不足以推翻由黑格尔哲学所建构的、有坚实理论支撑的“受启宗教”,更不用说把人类引回自由了。因此,在布·鲍威尔看来,要实现从根上推翻这种“受启宗教”,从而引导人类回归自由,就必须抓住其最核心的关键点,即“自我意识”。只有把“自我意识”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体系中解救出来,归还人自己本身,成为人自己的意识力量时,人才是自由的。正当两者围绕到底是“实体”还是“自我意识”才是瓦解黑格尔“理性神学”的关键争吵得不休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恩格斯指出,“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就一下子消除了这个矛盾”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75、275、275 页。。这样,笼罩在现实世界上的“理性神学”的魔法被破除了,抽象的思辨也被自然——人本主义的“感性”所代替。“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75、275、275 页。对此,恩格斯欢呼道:“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75、275、275 页。
当然,传统哲学之所以在黑格尔体系那里走向瓦解,除了上述原因外,不能忽视哲学发展本身的内在矛盾。传统哲学发展到黑格尔那里,二元分立和理性独断已经达到了绝对化和普遍化。与此同时,这种绝对化和普遍化的弊病又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它忽视了人的非理性存在,否认了人的情感意志,因而也常常把人神秘化、抽象化。对此,以强调人的情感意志和本能冲动等非理性活动在人的整个精神和物质存在中起决定作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对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特别是黑格尔理性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其中以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和尼采的“权力意志”最为激烈。当然,哲学发展本身所引发的对传统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攻击,除了非理性主义还有很多流派,在此局限于篇幅的限制不再展开。
诚然,通过外部、内部等各方面的推动,传统哲学瓦解了。但在传统哲学瓦解过程中走出来的哲学思潮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哲学“解释世界”的研究范式。事实上,它们不是根本没有离开过黑格尔的哲学基地,或简单地把它抛在一边置之不理,就是最后又都返回到思辨理性中来寻找支撑自己论据的基点。只有马克思建构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才使哲学产生了革命性变革,使哲学研究不再仅仅致力于解释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
四、在传统哲学瓦解的哲学背景中建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
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就在于终结传统哲学,建构“改变世界”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众所周知,为人类寻找解放道路,为人类走出困境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建构理论体系和行动指南,是马克思追问哲学的本质使命所在。本质上,这就是马克思进行哲学研究所要建构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在传统哲学瓦解的哲学背景上建构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呢?
通过对传统哲学的背景分析,马克思明确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性。对此,马克思批判传统哲学,要求消灭传统哲学。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应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非宁静孤寂、孤芳自赏式的自我审视。哲学家也不是“怪人”“圣人”,哲学家就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由此,马克思要求哲学是“为历史服务的哲学”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 页。,即要求哲学去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的异化,去批判尘世、法和政治等领域。因此,马克思提出,他要建构的是要面向现实、批判“现存”并为人类全面自由发展提供行动指南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正是基于这种哲学定位,马克思首先把哲学这个批判的武器按照时代的需要转变成武器的批判。以此,马克思以这种武器的批判向“现存制度”开火,并随着他开始研究经济学,他深入到对这种“现存”的根源进行批判,也就是对私有制进行批判。正是源于对私有财产的批判,马克思初步建构了包含劳动异化理论,以及把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理解为等于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此后,通过对“德国的批判”以及费尔巴哈式的旧唯物主义进行批判,马克思从现实生活中找到“实践”这个中介,开始建构以实践为特质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尔后,随着马克思越来越把哲学指向现实生活,从参与实际活动的人们和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他建构成了以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为旨趣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即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最后,随着马克思初步建构完成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马克思把其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通过对资本逻辑进行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以此推进和发展他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
综上,通过透视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不难发现,无论是早期批判“现存”,要求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还是中后期直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甚至晚期形成的东方理论,马克思都是通过要求哲学面向现实,解答时代现实问题,为人类全面自由发展提供指南来建构他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的。换言之,马克思建构的是面向现实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是解答时代现实问题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是为人类实现全面自由发展寻求具体道路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