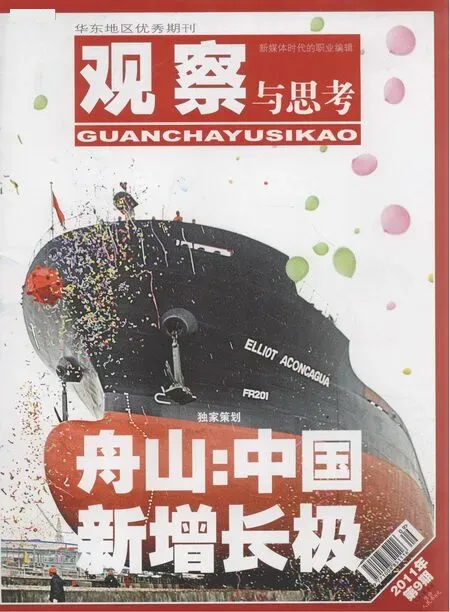本土生发与现代转向:现代国家治理的传统文化基因
2021-10-15卞学勤周佳松赵光勇
卞学勤 周佳松 赵光勇
提 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丰富复杂和多面性的,其核心是政治文化,体现为独具特色的道德政治和相应的制度体系。它既有极权专制的遗产,也有民主善治的基因。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借鉴西方治理经验和治理理论的同时,我们也要从自己的文化根源上寻找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政治智慧、“亲民惠民”的民本主义传统契合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合法性、有效性、民主性、透明性和责任性等理念,挖掘和发现其积极基因,能够为现代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提供基础知识和古老的智力资源。同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是在保有传统思想精髓的基础上,为文化注入现代自由民主、公正法治以及人权尊严的理念和新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里,“政治”和“治理”在多重意义上具有一致性。“政治”一词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古籍中就已经出现。《晏子春秋》中有“君顺怀之,政治归之”①《晏子春秋》,汤化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495 页。。“政治”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含义,便是国家的治理和政府的活动。“治理”可以说是“政治”的同义词。事实上,传统与现代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要完成现代性改造,无论对于何种文化下的人类社会理想来说,国家治理都是实现此理想的方式。毋庸置疑,现代国家治理需要体现合法性、有效性、民主性、透明性、责任性等一系列价值理念。以此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不难发现,这些要素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皆有体现,区别只是在于语境的不同。换句话说,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所寻求的治理资格或者合法性、公义公正、政府对民意的回应性、政府本位和责任性以及和谐合作等,皆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资源和证明。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质
治理理论及实践的提出,意味着公共事务寻求的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互动基础上的多元合作。治理涵盖了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一方面,政治意义上的“治理”指的是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通过此制度安排重新分配资源,建构公共责任;另一方面,管理意义上的“治理”指的是政府组织有效、高效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①参见王涛、赵光勇:《新公共管理、治理与社会管理模式创新》,《贵州社会科学》,2011 年第11 期。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迁与转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正是对此挑战的回应。它一方面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强调,另一方面是对割裂与对立的政府与公民关系的矫正。治理通过模糊国家与社会的界限来改变治者与被治者、少数与多数的对立,寻求公共事务的合作与共赢。治理实质是社会集体做出选择、分配资源以及创造共同价值的过程。②参见赵光勇:《政府改革:制度创新与参与式治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41 页。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借鉴西方治理经验和治理理论的同时,我们也要从自己的文化根源上寻找思想资源。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在于中国文化,优秀的伦理道德是我们思想的根基。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般而言,指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但更多情况下,侧重于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成果与财富。简单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一套礼乐制度、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并兼容吸收其他学派如法家、道家、墨家以及后来的佛教思想,回应农耕社会的秩序和发展需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理解,学者们有不同的观念,如:梁漱溟先生认为是理性早熟、伦理本位,③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351 页。张岱年先生认为是刚健进取、自然和谐。④参见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4 页。对于传统文化的呈现,则以诸子之学,尤其是后来的儒、道、释三家思想反映出来,因此,一定意义上而言,儒、道、释三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内核。
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方式是家庭与宗族,因此传统文化对整个社会的建构起点是家庭伦理,以忠孝仁义为社会的行为规范与道德标准,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层层递进的人格发展轨迹,而仁、义、礼、智、信则是个人品德要求的基本面向。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整合性文化。总体而言,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然而,由于传统社会的统合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政治文化,体现为独具特色的道德政治和相应的制度体系。其中,在“天人合一”哲学下,政治的泛道德化确立了政治的合法性,也在无意中为政治活动划出了伦理边界,基于政治伦理的民本主义传统成为专制“政统”下坚韧的“道统”;“天人合一”哲学基于家族伦理演化出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父权政治的“立君为民”和民本主义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了道德基础和合法性,民本主义则要求统治阶级推行仁政、善政,倾听和回应民意。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天人合一”与“天下大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代表自然界,是人类命运的主宰;人类从属于天地,是宇宙和自然系统的一部分;天能够与人类发生感应,昭示人类吉凶祸福;统治者要“顺应天命”“替天行道”,因为“天命”通过现世的“民心”来彰显。《尚书》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①《尚书》,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436 页。,便是以民意来彰显天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道德依据和人本基础。“天下大治”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追求。中国政治文化的追求是秩序和“太平”。中国在进入近代之前,尽管时期漫长,但多为历史的治乱循环,农业社会和王朝更替是数千年历史持续的特色。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社会基础。对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秩序和太平是最高的政治理想。而由于中国社会是以家族组织起来的共同体,因此,基于稳定家族的道德伦理自然弥散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文化也由家庭生活的有序和谐扩展为政治生活的和平与安宁。
第二,民本主义与道德伦理。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下,统治者的治理资格来源于“天”,“天下为公”而“立君为民”,事实上,统治者只是“奉天牧民”。天人相交,“天命”则通过“民心”予以彰显。因此,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向背影响到统治者是否能够继续执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为了君主自身的统治地位稳固,必须顺应民意,回应民意,以民为本。在现实实践中,中国社会生活的起点是家庭,基本空间是家族,家庭伦理道德扩展为社会的组织基础和合作规范。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重要功能是表率和教化。《论语》中写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②《论语·大学·中庸》,陈晓芬、徐儒宗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15、331 页。官德引领民德,为官者的道德起着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作用。道德政治对统治者和各级官员构成约束,要求统治者以德治国,各级官员的选拔标准也是道德主义的。可见,古代中国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非常注重伦理色彩,特别强调仁治、孝治和礼治等治国之道。
第三,“人治”社会与精英治理。泛道德主义的政治在实践中表现为强烈的“人治”特色。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治理通过这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士大夫阶层参与政治,二是以科举为中心的文人官僚选拔机制,三是农村社会某种程度的乡绅自治。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资格来源于对儒家经典文本的理解,而儒家经典大多是关乎道德规劝和修养身性。职业官僚制度、科举制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创举,大多数官员都要通过漫长严格的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队伍,这就保证了官僚队伍的精英色彩;然后再通过常年职业训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精英治理的专业性。
二、“天人合一”的政治智慧
现代治理是多方合作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具体而言便是国家的和谐有序、社会的良风美俗和民众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此目的,现代国家治理在结构上要求增加治理主体,要求政府和其他主体共同负责;在运作方式上,改变管控方式,以合作协商应对公共事务。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政治智慧契合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合法性、责任性、回应性及合作性等理念。
(一)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源泉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政治权威的来源是“天”。先秦道家主张人与自然的相通,《道德经》上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③《道德经》,张景、张松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1 年版,第99 页。儒家主张“天人合一”,《中庸》写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④《论语·大学·中庸》,陈晓芬、徐儒宗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15、331 页。,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①《春秋繁露》,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版,第369 页。“天人合一”思想是古代中国的宇宙观和世界观,也是古代中国人基本的思维和行为坐标。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道家说道生万物,因此,我们要“法自然”;儒家奉行“中庸之道”,凡事要不逾矩;佛教的因果轮回更是将人的命运和神秘的天意勾连了起来。“天人合一”思想投射在“天、地、人”构成的宇宙图像中,可以形象地类比为中国茶器:在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中,由盖、碗、托三件套组成的茶盏分别代表了天、人、地的和谐统一,缺一不可。在这一体系中,人类行为受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影响,政治和治理活动,自然也受到“天人合一”理念的支配。天地自然是最高的主宰,正如《吕氏春秋》所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②《吕氏春秋》,陆玖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版,第22 页。。君主的权力来自上天,君主“奉天承运”,代表上天来治理国家。由此可见,在“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下,“上天”是古代中国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的权威来源。
(二)“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的道统
《礼记》讲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③《礼记》(上),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版,第419-420 页。“大同”是中国儒家的社会理想,而“公天下”则是理想状态的权威来源和归属。“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对中国士大夫阶层影响深远,也成为中国社会的道统所在。对中国传统士人来说,他们服膺的是“天下”的“道”,服务的是黎民百姓,而非一家一姓的王侯君主。如果说皇帝专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统”,那么承载儒家“天下为公”精神的士大夫阶层则是“道统”的体现。在“公天下”的理想政治设计中,有着多中心治理的精神。
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政治权威的来源是具有神秘主义的“天命”和“道统”,“君权神授”“立君为民”将政治统治合法化。在中华文明的早期,君主是有德之人、有能力之人。正如黄宗羲在《原君》中对传统的君主专制提出大胆批判:“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④《明夷待访录·破邪论》,王珏、褚宏霞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1 年版,第28 页。神话时代的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以才能和贡献而被奉为君主;而尧舜之君,则是以其德性服务天下百姓,让天下人心服。夏商周三代以后,神秘主义的“天命”并没有从历史中消退,而与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中的人本主义结合,从道德伦理上成为对专制皇权的主要约束,且成为以民为本思想的逻辑推论,有学者认为,是否认同“立君为民”是判断是否属于民本论者的最重要的尺度。⑤参见张分田:《论“立君为民”在民本思想体系中的理论地位》,《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2 期。
(三)士大夫参与国家治理的理论依据
帝制中国的统治模式是君主专制与官僚制。君主专制体制是“家天下”,但其大一统治理模式则是对“公天下”部分回应:统治阶级向社会精英群体开放。周朝时期王室家族内部的“共和”已经带有一定的“共治”色彩。秦汉时期的丞相制度,是对君权独裁的有效制衡。西汉文帝时丞相陈平对丞相职责的理解,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①《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369 页。君权和相权的相互消长,是帝制中国的一大特点。有宋一代,士大夫自觉意识增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正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所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②《古文观止》(下),钟基、李先银、王身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708 页。由此导致宋代政治的架构被称为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权、相权、台谏之权,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三者互相限制,又互相倚恃,形成“共治”架构。③参见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6 期。
(四)和平仁爱精神的社会心理
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中国人意识到人类生活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由此认为政治和治理的领域是有限的,它们最终从属于自然伦理和社会道德。“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中国人重和谐厚生,反对掠夺自然;就社会关系而言,“天人合一”追求和平,倡导仁爱。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仁者爱人”④《孟子》,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版,第163、12、225 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⑤《论语·大学·中庸》,陈晓芬、徐儒宗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191、187 页。等主张均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和平性质,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⑥《孟子》,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版,第163、12、225 页。“杀身以成仁”⑦《论语·大学·中庸》,陈晓芬、徐儒宗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191、187 页。“舍生而取义”⑧《孟子》,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版,第163、12、225 页。等则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仁爱”追求。“天人合一”思想积淀为中国社会和平仁爱的社会文化与心理。
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哲学,弥散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沉淀于中国人的观念、意识和心理之中,代代传承,其中所蕴含的优秀政治智慧,是我们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资源。
三、“亲民惠民”的民本主义传统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建立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基础上,具有强烈的泛道德主义和伦理主义。“上天”“天道”是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来源,“立君为民”是对统治者的伦理要求,“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理想的政治架构,而和平和秩序则是中国政治追求的目标。这一整套的中国传统治理资源,在实践中体现为源远流长的民本主义传统。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以民为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⑨《尚书》,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369 页。。无论是儒家追求的“德政”“仁政”亦或“美政”,还是道家思想中的无为而治都将民众福祉放在首位。民本主义传统对“民意”的推崇同现代人民主权政治具有目的合一性。现代政治承认权力来自于人民,但和西方政治文化有所不同,中国政治更关心公共权力如何使用、为谁而使用、使用效果如何。换句话说,和现代治理理论一样,中国政治是绩效导向、结果导向。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理念和传统的民本思想、亲民惠民的政治思想具有契合性和某种程度上的继承性。
(一)民本主义思想的发展与转型
秦朝的大一统开创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自秦代到明清,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民本思想渐受压抑。但在一些开明思想家和君主的著作和政治实践中,民本思想时有回响。西汉初期杰出的政论家贾谊,提出了“民无不为本”的命题,并以此告诫统治者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实行爱民、利民、富民。贾谊对民本思想作了较为完整的表述,《新书》云:“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以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①《新书》,方向东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275 页。他提出为政治国必须以民为本、以民为命,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政治活动的核心。贾谊在认识人民的力量上,比先秦儒家又进了一步,把民众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唐太宗李世民在继承儒家传统重民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的思想,把治理民众,安定民生,视为君主的首要任务,主张帝王要施仁政,与民休息,重民畏民,并付诸政治实践。明末清初,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都对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抨击,其中以黄宗羲尤为突出。黄宗羲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重述“天下为公”“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理念,其所写的《明夷待访录》在宣传民主意识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其政治思想被认为达到“民本之极限”,是传统“民本”观念到近代“民主”思想的过渡。
(二)民本主义思想的内涵
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内涵,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心向背是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在“天人合一”哲学下,“民心”与“天意”相通,统治者要“奉天承运”,必须“应乎天而顺乎人”。如果统治者贪残暴虐无德无道而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那么民众进行政治反抗和王朝的更替,就是“替天行道”,反抗因而具有了合法性与合理性。二是重民、亲民、为民的政治伦理。民本主义是“天人合一”下“立君为民”观念的逻辑推论。由于统治者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存在,因此统治者必须重民崇德、敬德保民、勤政爱民,以国事为重,以民众为先,与民忧乐与共。统治者的言行只有符合重民、亲民、为民的政治伦理要求,才能得到百姓拥戴,巩固其统治地位。三是政策过程对民意的倾听和回应。在“天人合一”理念下,天意与民意相通,君主和各级官员在施政过程中就必须体察民情,倾听民声,从而顺应民意。无论在用人还是在处理具体政务的过程中,民本思想都要求各级统治者注意走访民间、体察民情、倾听民意、体恤民力,力行仁政从而实现恤民、养民、保民。四是政策绩效的衡量标准是民生福祉。民本主义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实现安民、富民、教民。在民本思想家看来,君主和各级官员获得统治的权利就必须尽到为民谋利、兴天下之利的责任,能否为民谋利或为民兴利除害,而非谋取一己之私利,是基本的政治评价标准,同时也是君主与各级官员须遵守的绩效标准。②参见何增科等:《城乡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年版,第4-7 页。
(三)民本主义思想的现代价值
不可否认,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是君主专制时代的遗产,带有显著的中国传统社会印记,其思想是建立在家族伦理基础上的政治道德,是父权政治的伦理要求。君主和各级官员与民众的关系犹如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君主和官员须爱民如子、为民做主、为民谋利,民众则拥戴和服从君主的统治,君主统治的权利来自为民众服务的义务,否则民众就没有服从的义务。民众和统治者之间确立了一种利益和权力的交换关系,统治者须为民众谋取利益,而作为交换,民众接受君主的统治。由此,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本位扩展为政治社会的伦理道德。同时,民本主义是父权政治的产物。国家统治者的美德和明智之处在于替天行道,他们会像保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百姓。而保护关系中,百姓的个人利益是由统治者来定义的,个人权利没有制度上的保障。民本主义很多时候只是理论上的推演,而非现实的政治实践。对民本主义理念的高调宣扬,无法掩盖政治生活的官本位实质。进一步讲,“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仰仗于统治者和各级官员的个人美德,民本主义是统治者和臣民之间缺乏强制约束力的道德约法。在这种双边约定中,只有当统治者是道德楷模的时候,被统治者才会顺从其统治。这就要求统治者必须对公众的需求做出反应。事实上,此种道德约法真实的约束力,在于以被统治阶级的“造反”和“替天行道”体现出来的异常激烈的方式重订契约。
尽管存在历史的局限,但总体而论,中国民本主义传统与现代民主思想有一定相通与契合之处。可以说,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精华的民本思想,为现代人民民主观念打下历史根基。第一,民本主义的“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理念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强调与当代中国人民民主的政治建设实践是一致的。虽然传统民本思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主权与公民权力的认识,但它至少在观念层次上肯定了“民”的价值与作用。传统民本思想认为“君以民存,亦以民亡”①《礼记》(下),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版,第1083 页。,民虽然在社会底层,但民却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中国历届领导人无不把“以民为本”作为其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②《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638 页。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历届政府努力践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践行群众路线,回应民情民意,凸显“以民为本”。第二,民本主义强调利民、富民,把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放在首位,这也与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契合。传统民本思想主张统治者应该关心人民生计,使人民生活富足、安居乐业。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一直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利民”“富民”等思想,做到“制民之产”③《孟子》,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版,第14 页。,实现民众福祉。第三,民本主义倡导为政以德、勤政爱民的政治伦理,认为君主实现治世必须做到德治和仁政,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求统治阶级以德治国,施行仁政。德治诉之于道德教化和个体道德自觉,强调德性的潜移默化,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无为而治色彩,就是说不以自己的私意治人,不以强制手段治人民,而要在自己良好影响下,鼓励人民自为。这就对各级官吏在道德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现代政府来说,就是要选贤与能,把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要求各级官员清正廉洁、勤政有为,加强自身道德修养。
四、从“善政”走向现代国家治理
当今中国正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家治理的一系列重大挑战接踵而至。面对这些挑战,现代化无疑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定位和必然选择。客观地讲,对于自身有着五千年独立文明体系的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来说,文化发展的问题本不应该成为当下中国发展的难题。然而,中国在推进现代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必然面临现代化带来的国家转型问题,即传统国家转向现代国家,这同时决定了深刻烙印在国家内核中的文化传统也要进行全面的洗涤和筛选。因此,中国在迈向现代国家治理的进程中,必须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再认识,使得中国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的文化取向更加契合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和核心价值。
(一)现代治理视角下的“善政”困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学的“天人合一”哲学造就了中国人的理性早熟,塑造了民众中道平和、追求安定与秩序的性格特点。在公共生活层面,“天人合一”哲学用神秘的“天道”约束专制统治者的独裁和暴虐,也为民众的反抗权提供了合法依据。“天人合一”哲学是“立君为民”政治观的基础,而“亲民惠民”的民本主义则是“立君为民”的逻辑推演。如果说“天人合一”哲学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契约,那么民本主义则是民众和统治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力交换关系,是一种道德契约。统治者对民众负有提供秩序、安全和福利的义务,而民众交换的是臣服和认同。当然,民本主义与社会契约论的本质区别在于:这一道德契约是不对等的,依赖于统治阶层的道德自觉,民众唯一的筹码是暴力反抗,更换统治者。由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无论是道德主义还是伦理取向,都是单向度的,全赖统治者和官僚阶层的道德素养,依赖“仁德”与“善政”。尽管传统法家批评儒家的“人治”将天下大治的希望寄托在所谓“圣贤”的身上太理想化,但法家所主张的“法治”也只是运用公共权力的手段,而非制约公共权力的规则,并非现代意义的法治。
然而,时代在变,环境在变。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中国与西方相遇,中国社会逐渐进入工业化,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主权、人民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和合法性源泉。在中国现代化的征程中,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突出体现在就业、教育、住房、看病、养老等社会民生方面,同时也体现为利益维护、社会公平、大众参与、公共危机、反腐败等政治民主诉求方面,简言之,就是体现为民主民生问题。民主民生问题,既对党委政府提出了扩大参与、分享权力的政治参与要求,又迫切要求国家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的有效与高效。因此,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便成为应对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同时增强党委政府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迫切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意味着包含民主化在内的国家现代制度建构与有效管控能力的同步推进。
在全球化、民主化的时代,传统的“以民为本”和“亲民惠民”的“善政”显然已不合时宜。传统政治文化已经无法解决现代民主社会面临的种种矛盾,在传统社会游刃有余的政治价值和伦理规范,面对现代民主民生问题时,某种程度上显然捉襟见肘。特别是在整个社会的家长制伦理下,中央集权的专制独裁妨碍了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传统社会的泛道德主义、父权政治、家族和群体取向等等,甚至成为了现代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障碍。
(二)制度建设是中国治理现代化的逻辑
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政府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而政治的现代化,核心是权力关系的制度化。实现权力关系的制度化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①参见林尚立:《权力与体制: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逻辑》,《学术月刊》,2001 年第5 期。
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通过社会交往和互动博弈所形成的规则。广义上讲,一切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都可以称为制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制度对于经济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意义重大。制度创新能够带来新的集体行动与社会合作规则与方式。换句话说,制度作为集体行动方式,一方面,有效的制度带来有效的治理;另一方面,治理的实践便是有效的制度创新。
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良性有序协调,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这个系统目标中,制度文明是基本价值维度,也是最关键的衡量指标。没有现代制度的建构,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制度文明或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又不可避免与政府为主体的社会治理结构、治理能力和治理行为联系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制度绩效与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繁荣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理念和制度的创新,通过治理手段、治理工具、治理方式的吸收与运用,优化社会治理过程,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制度涵盖了各种成文的和习惯的行为模式与行为规范,但其核心是政治活动的游戏规则和社会治理规则。因为政治是运用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的技艺和社会实践活动。政治的使命就是组织社会以进行集体行动,实现社会和个人的和谐发展。政治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以制度约束公共权力,使权力在制度的轨道上运作,这便是制度化。人类千百年来制度文化的发展凝聚了不同文明的智慧和思考,通过历史的传承和演化,成为群体共享的观念和价值系统,以及群体组织与合作的现实政治实践和社会治理规则。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而言,就是要建立现代国家制度。
(三)传统的现代转换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是在保有传统思想精髓的基础上,为文化注入现代自由民主、公正法治以及人权尊严的理念和新价值。对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立君为民”和民本主义政治理念,要在新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下,彰显和弘扬其价值意义,挖掘和发现其积极基因,使其能够成为现代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知识和智力资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明确了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目标是实现治理与善治。在语言学意义上,“治理”就是“统治”加“管理”,是旧词新用,其新意在于与“统治”的区分。“统治”和“治理”的区别,首先是公共权力中心是一元还是多元,是单中心还是多中心。其次,权力运作方式是强制还是合作。治理是多中心的,更多依靠合作和契约。再次,权力运作方向上,是自上而下还是双向互动。治理属于后者。当然,中文语境中“国家治理”并不是单纯的国际通行的多元共治的概念,同时还意味着国家在治理体系中发挥关键作用,是国家为主导进行的治理。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还是要推进政府改革,让政府做得更好,同时培育和建设多元治理主体。统治的一元结构变为治理的多元结构或者近似“多中心治理”结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使它们各自更好地发挥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强劲的生命力,历经千年,指引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政治实践以及内心世界。吴稼祥在《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中写道:“没有世界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就没有今天的人类;而没有多中心治理,就没有轴心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轴心就是多中心,就是文明的裂变。”①吴稼祥:《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326 页。吴稼祥所说的轴心时代,便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多中心,有了分权,才有了文化史上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也才有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哲学以及民本政治传统的生发。
当历史进入今日的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时代,民众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日渐高涨,改变着政府传统的管治方式,统治让位于治理。现代国家治理的兴起是全球化、新科技革命时代民主政治发展、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充分发育的结果。治理是政府与个人和组织合作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治理侧重于工具性的效能提升。在现代社会格局下,政府和社会、市场一起参与公共事务,治理要求政府更具开放性、回应性、责任性和民主性。而国家的良善治理则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和由治理所导致的社会状态。国家良善治理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对具有共同归属感、认同感和集体行动能力的共同体中,政府与社会(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共同治理。
五、结论与启示
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观察,一个社会成功的改革与转型,需要创造性地运用原有的社会文化资源。原有的文化资源的扬弃与转换,不仅能够保持历史传统的延续性,同时能够有效地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农耕时代,能够引领中国走在世界前列。在当下的国家治理转型中,也必定能够继续发挥作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古老的智力支持。
首先,传统政治伦理中的思想精粹对现代政治具有积极影响。政治要解决的是人类的集体行动,而集体合作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只有在成员之间互惠的基础上才能达成。无论何种形式的强制带来的人类结合方式都将是短命的。集体行动的互惠是一种道德要求,唯有如此,才能服务于整个共同体的利益。这种利益在西方社会,被称为“共同善”,在古代中国,则是“天道”“道统”。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是道德统率政治。政治若缺少道德的驾驭,便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权谋政治和权术技巧,便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算计,而无关乎人类公益和价值。古代中国的“民本思想”“仁德”政治和古希腊的美德政治一样,指的都是政治背后的道德逻辑。其身正,不令也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有道德才能提升一个共同体的境界,才能让我们过得更好、变得更好。有了道德的政治,然后自然有道德的社会。一个国家的安定团结、光荣与梦想,全在道德人心。而民众道德和社会风尚,又在于政治人物的道德行为和政治生活的道德伦理。从这个意识上说,官员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就是古往今来民众心目中的“天下大治”。
其次,爱民惠民、为民谋利的民本主义仍是我们的政治取向。民心认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为政治统治确立的合法性来源。政治行为和公共政策要回应民意,为民众谋利益,轻徭薄赋,仁政爱民。传统政治对民意的重视与回应在实践上将民本主义观念落到了实处。统治阶级通过多种形式体察民情、发现民意。政治与民众福祉息息相关。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政治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抽象的、空洞的。它有远大理想和具体目标,因而在正常情况下,凡事总离不开对国计民生有利的考虑。如何实现人民民主?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共产党充分掌握了“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的政治传统,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在代表民主之外,我们正在开展各种形式的协商民主,在平等协商、相互理解中寻求共识与合作。古代中国垂直谘商的民意吸纳传统启发了后来我们的政治协商制度,也为我们的协商民主提供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
再次,发挥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主导作用。现代国家治理是政治国家与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共同治理,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一治理过程要求具备合法性、有效性、透明性、正义性、责任性、回应性、参与性、稳定性等要素。同时,现代国家治理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是人民主权原则的现实体现。由此可见,现代国家治理的实现在政府之外,有发达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如此才能实现多元治理。尽管中国的政治发展未来走向也是由政府主导发展到多元参与,然而在当前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自治能力较弱的情况下,政府在治理中仍要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综观史实也可以发现,中国的现代化是政府主导和推动的结果,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变迁,现代政治发展不仅仅体现在政治民主化上,更体现在通过政治的有效作用来保障和推进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上。凡此种种,均可以看出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最后,中国的现代国家治理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国家的良善治理是“好的”治理,是治理理想状态的实现形态。治理虽是西方的“舶来品”,然而其所呈现的问题则是世界意义的。现代国家治理在中国文化中的生长和实现,必然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特殊因素互相影响。现代国家治理所具有的民主合法性、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政府行为的法治透明、政府责任性和回应性、廉洁政府、效能政府、公众参与以及自由和人权保障等等,其中很多特征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和印记。因此,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自然彰显着浓郁的中国色彩和中国个性。这一点,恰恰也是全球治理变革中中国图像所具有的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