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真性、绝望感与文学的可能性命题
2021-09-26徐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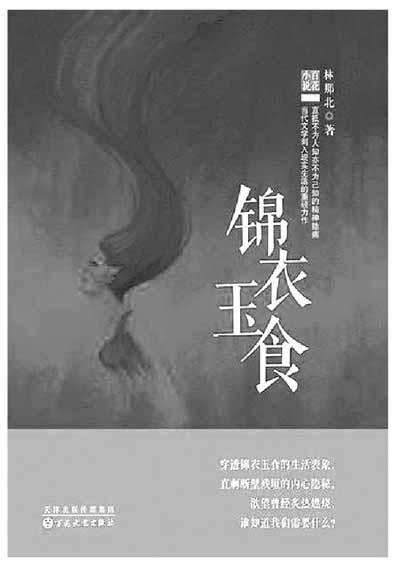
某种意义上,对林那北的任何一种解读都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当我们阅读林那北的小说时,我们会想到那个叫北北的作家,而当我们把林那北看成是小说家的时候,林那北其实又是一个博物学家,她对物的隐晦或隐秘的含义有着近乎痴迷的热情,以至于当我们认为理解了林那北时,其实是南辕北辙。这不仅仅是因为林那北有着多重身份——小说家、散文家、童话作家等——她常在多重身份间游移,还是因为林那北的作品具有一种深重的反讽性:在她作品的表面明晰的叙事下隐藏着其对人生、社会的复杂到近乎内在分裂的认知。她的作品暗藏着某种令人震惊的冷静与清醒,及其因此而散发着的绝望感。
一
诚如作者所说:“一部小说不过是某种精神疼痛或焦虑或躁动或渴求的隐秘的图,经线纬线的走向,都藤蔓一样沉默。”①真正要想揭示林那北小说中的“经线纬线的走向”,无异于探险,她的小说中布满太多的“陷阱”,稍不留神,便可能是离题万里误入歧途。长篇小说《剑问》可以看成是林那北小说创作的一个隐喻。小说情节曲折,线索明快,扣人心弦,读完后却让人疑惑重重。无数的证据都指向一点,李宗林家藏有一把价值连城的宝剑,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为了这把传说中的宝剑可谓费尽心机,耗尽心血。历经周折后,众多的赝品一一搜寻出来,都在昭示着真品的灵光,宝剑存在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但最终,经过众人不懈的艰苦卓绝的寻找,宝剑却并没有浮出水面。这不禁让人怀疑,宝剑存在吗?这是否意味着,假的宝剑不断出现,只是表明真的空无或缺失?即是说,假的宝剑背后只是一个空无,正是这真的空无和幻象才造成假的无限延宕。如此说来,真的宝剑其实就是一个无限的游移的能指,它促使人们殚精竭虑、义无反顾甚至奋不顾身,换来的却是所指的空无。这种内在空无的基底上的无望而又充满希望的徒劳寻找也就构成人的命运的隐喻性内涵。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文学的独有意义。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寻找且赋予本质缺无的生活以意义和价值。林那北无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从其取名“锦衣玉食”寄意人间烟火的吃穿二项(《锦衣玉食》)中可以得到直观的印象。但事实却是,不管你的态度如何,生活本身却是拒绝意义和方向感的。生活本身有其近乎执拗的逻辑和荒诞的内核,朝着某种宿命般的道路自顾行驶。生活有方向,但却拒绝方向感;即是说,生活具有其特定的语境上下文关系,需要结合具体语境加以把握和理解,这就需要文学赋予它形式。某种程度上,林那北的小说就是这一赋予生活以形式的表象。
这应该说是林那北小说的内核之所在。
而说生活有其方向,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生活的发展有其自身的惯性或逻辑,不以各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都是被这惯性所推动着的微不足道的个体,既不能创造历史,甚至连自身的命运也不能主宰。另一方面,虽然我们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甚至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锦衣玉食》宣传册语),但我们并非没有自己的主动性,我们仍可以有我们的选择和我们的意志。两种方向,在林那北那里,并不总是一致的,因而构成某种张力紧张关系。人的命运的反讽性也正体现在这种紧张关系中,任你怎么努力,都不能左右生活自身的惯性或历史的“诡计”。比如说老米(《老米》),本以为当上副处以后尚有可为,没想到他那个处最后却成了省里机构改革的对象。他为之奋斗而得来的副处长职位,终究成为一个所指被掏空的虚幻能指。林那北并不是要去否定目标和努力,而只是表明人生的无奈和不可把握。
林那北小说中的主人公们的生活,有其方向,但却拒绝方向感,这种看似矛盾之处,其所反映出来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对人的主动性和主体性的充分肯定。这使得她的小说主人公的命运大都呈现为意识主导下的宿命结局。其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晋安河》,木穗的人生从她母亲投河那天起就已经命定和不可更改:她的一生成为母亲命运的延续和重复,这都是在对母亲为何要投河的反复不断的追问中被设定的。林那北小说主人公们的命运,与其说是性格决定命运,毋宁说是意识决定命运,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人公们行为举止的“个体意向性”倾向。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意向状态”②。意向性并不追求意识明确,也不属意整体,它只关心它所关心的,逻辑明确而执拗单一。
虽然说,这样的主动性,在生活的方向或惯性面前常常显得微不足道,但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主动性或者说固执,生活才并不显得枯燥平庸,生活才有其质感和坚硬的属性在。这样一种固执,用作者的话说就是“精神洁癖”③,其一再显现于她的小说主人公身上,比如说木穗(《晋安河》),她的怪异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是对父亲不洁的无言批判,时刻指向母亲投河的那一天:是父亲的不洁导致了母亲的跳河自尽。再比如说王以娥(《忆秦娥》),她之所以突然不辞而别是因为丈夫秦同明失手用发号枪打死了爱子虎奔,为了推卸责任却说是虎奔自己走火所致,她不能忍受这样一种懦弱,最终只能离开。
应该看到,“精神洁癖”在林那北的主人公身上并不表现为通常意义的现实生活的逻辑,她们遵循的是精神的逻辑轨道。即是说,她们的某些行为虽看似有悖常情常理,其实自有精神上的内在理路。比如说《锦衣玉食》中锦衣感动于男友刘格拿送给她的钻石卖掉用于给父母买电视,但不能容忍他用假的钻石欺骗母亲,虽然她对母亲有各种刁钻的批评和不满;柳静能接受丈夫唐必仁出轨漂亮的女下属,但不能容忍他把漂亮的女下属献给副市长上司作为自己仕途晋升的阶梯。在她们眼里,与真有关的真实、真诚或真性情可能是最为看重的品质,其他的则可以忽略甚至被原谅。柳静的逻辑,在《床上的陈清》中俞小静那里有另一种形式的呈现。俞小静并没有因为丈夫陈清的不断出轨而离婚,虽然她也曾设想过没有嫁给陈清会是什么样的人生,但她并不后悔,她的默默忍受里有着对丈夫品性的评估:他并非虚伪之人,也无意玩弄女性或欺骗她们的感情——他的每一次出轨里都闪现着源自内心的坦荡和担当,用作者的话就是“一直到老,他都没有世故圆滑”,都“始终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单纯天性”④。
不难看出,这样一种“精神洁癖”的存在,其实就是泰勒所说的“本真性”——即“对我自己真实”⑤——的表现。林那北的小说让人明白一点,这看似至为简朴的目标,其实是对每个人的最大考验。一个能始终保持住“单纯天性”的人,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是多么的可亲、可爱和可敬。柳静们的逻辑在另一个主人公杜奇(《张飞老师》)那里有同样的显现。杜奇的生活看似没有目标且容易满足,内心其实是笃定而执着的:在他那里,慵懒的生活的另一面是对内心本真的坚守。他可以接受别人对他痴和傻的嘲讽,但不能忍受人與人之间关系的虚伪本相。因此当看到傲气聪明的杜薇同庸俗势利的常天兵之间关系暧昧的视频后,毅然辞职并离家出走,虽然这两个人一个是他所崇敬的姐姐,一个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老板。此时,杜奇的内心世界已然坍塌。这已然是一个没有了方向感的世界,漂泊因此就成为林那北的小说主人公们必须要面对的人生困局:何去何从作为一个问题凸显在他们面前。
二
“精神洁癖”的存在若隐若现,某种程度上也使得缺失和寻找构成林那北小说的隐喻式结构。这样一种缺失与寻找,在林那北的小说主人公们那里呈现一种矛盾的分裂状态。比如说木穗(《晋安河》)的坚硬和强势之下其实掩盖的是虚弱和无助,马兰花(《坐上吉普》)的决绝背后是无望,马念和牛越的执着背后是柔弱(《忆秦娥》)。缺失是林那北的小说主人公性格的背景性存在。他(她)们生活在一个布满缺失的世界,他们渴望圆满,渴望原初意义的秩序,但世界一旦“缺失了一块”(《忆秦娥》),也就意味着永远的失落:不可能找补回来了。但很多事情,恰恰就是这样。越是证明它存在,其实越加显示出它的虚无。林那北的小说显示出来的也许就是这种深刻的悖论之所在。她的主人公越加显示出对“精神洁癖”的固执,越加显示出人生的无奈: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假想中的可能或者说虚构的纯粹呢?这也使得寻找主题,在林那北那里格外显得悲壮且具有反讽意义。
寻找与缺失⑥的隐喻结构,也使得林那北的小说多有寓言的性质。比如说《有病》,堪称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的文学表现。小说中某一个小城因出现第一例艾滋病而引起的恐慌显示出来的就是“疾病的隐喻”的表征。比如说《唇红齿白》,双胞胎作为人生镜像结构的隐喻,某种程度上表明人生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结合:双胞胎姐妹都想从对方身上寻找甚或推演自己的命运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一男一女》中,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火车车厢是一个有着极强隐喻性的特定情境,在这个情境里,两个深爱着的青年男女毫无遮蔽地彼此敞开,他们之间的本性甚或人性的劣根性因而得以充分暴露,其结果他们最后走向了分手。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就具有隐喻色彩——甲哥和丙妹,这是无数个同类的无名化的象征。
大体上看,寻找与缺失的关系,在林那北那里以三種方式呈现。首先是缺失后的寻找。这种缺失,可以从实存和精神两个层面加以理解。实存层面缺失的例子,以《寻找妻子古菜花》为代表,小说中,对妻子的“‘寻找正是源于‘不在”⑦。林那北的小说更多是从精神层面的缺失入手。比如说《晋安河》中的木穗,她的人生定格在母亲跳河自杀的那一刻。母亲的跳河自杀,既是创伤体验,也是缺失,让她对人性的缺失和不纯有着近乎疯狂的怨恨,她渴望纯粹的夫妻关系,因而选择三山就成为对纯粹人性的追求和寻找的象征。但事实上,纯粹只是她的原初的假想、预设和虚构,真正的纯粹是不可能的和不存在的,三山选择她并不是出于一见钟情或所谓的爱情,而是出于经济上改变自己处境的考量。他的行为背后有着诸多出于朴素的和本能的因素,很难说脏与不脏。再比如说《天桥上的邱弟》,邱弟对花姑村的执着中,有着对人性美好的想象,而事实上,随着花姑村的改造而来的,是他父亲的官职越来越高和他父亲的本性渐渐失去。花姑村的现代化与人性的缺失构成一种奇异的对应关系。邱弟的寻找背后,是永远的缺少:现代化使得美好的东西注定只能失落。
其次,是寻找之后的空无。她的小说主人公甫一出场,就表现出积极寻找的态势:他(她)们都被某一传说中的某物所吸引、所诱惑,而去努力奋力寻找。比如说《剑问》和《镜子》。在这里,宝剑和宝镜,构成小说主人公寻找的对象,他们只是听说过有这宝物存在,他们被听说和传闻所左右。但寻找到最后,却发现,寻找的结果其实是更大的和更多的疑点,是本质上的虚无。宝剑和宝镜,某种程度成为一个空洞的闪光的能指符号,诱惑着对它进行指认和填充。寻找正是这指认过程,但填充和寻找的结果,只是更加掩盖着背后的虚无,寻找其实是对虚无的凸显。林那北通过这类小说所告诉我们的是,人们往往被表象所迷惑、所困扰和执迷不悟,表象背后有无真实存在,他们并不关心,亦无法确认。比如说《我欠了谁》,在一场酒局中,喝醉了酒的大陈说“我”欠了他5000块,虽然他并没有要“我”还的意思,但“我”深感震惊和屈辱,因为“我”没有丝毫印象,而为了证明“我”并没有欠钱,接下来“我”干出了一系列的蠢事,但有字据显示,“我”确确实实欠了大陈5000块钱,至少看起来如此。在这里,证据就成为指涉真实之存在的痕迹,循此痕迹,“那段往事一点点浮上来了”(《我欠了谁》)。但这一证据就能真正证明欠钱的事实吗?显然,林那北是把这一证据视为一个空洞的能指,并不能赋予它确切的所指——这并不能简单看成是遗忘和记忆的故事。这其实是告诉我们,在幻象的迷雾包裹下的表象世界,遗忘和堕落构成我们人生的两大情状,就连事件中的我们自己,也并不真正认识自己。我们很大程度上身处尼采意义上的颓废状态:在一个不能确认自己和不断遗忘的情境中,我们只能活在当下和表象构成的虚幻世界——距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我”有杀人吗?(《杀人嫌疑》)吕非玉结过婚吗?(《吕非玉的往事》)等等,这些都是需要重新打上引号的存在。对林那北而言,不懈的和无尽的寻找之后,是更深的困惑:“现在的问题是,向人借五千元钱都会忘记,我到底还忘了什么?”(《我欠了谁》)这里的逻辑很明显,不去寻找,我们还处于一种自我圆满的虚幻之中,寻找反而是缺失之始,寻找之旅因而构成了我们人生缺失的隐喻。
因此可以说,在林那北那里,缺失后的寻找,和寻找之后的空无,是一体两面的存在。这是一个没有初始状态的循环和宿命。林那北的主人公就深陷于这样的宿命中。她的故事,情节明朗,人物阳光,但本质上却是充满了悲观和绝望。绝望和明朗,构成林那北小说鲜明的两极和对照,看不到明朗背后的绝望感的存在,可以说是对林那北的误读。小说《峨眉》就是如此。主人公“我”生活在父亲的各种版本的故事中,“我”的生活历程实际上成为一部寻父的历史,但也正是这种种的版本所建构的父亲形象,让人产生一种深深的绝望:生活在父亲的故事中的“我”,始终见不到父亲,接触到的只是父亲的形象。那么,此时,父亲这一能指的意义,其实就变得可疑了:作为能指的父亲虽然存在(每个人都有一个父亲),但这一存在却是以作为所指的父亲的永远延宕作为前提的。这注定了寻找父亲只能是寻找父亲的形象了。这与寻找宝剑最终找到的只是一个个赝品(《剑问》)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在《剑问》中所指的延宕——一个个赝品被挖掘出来——带来的是对能指(宝剑)的疑问。
最后,是对“原初”的寻找。林那北的小说常常预设一个“原初”的存在,她和她的主人公们并不能根除对“原初”的原乡式的怀念和思想,她们要以绝望的或荒诞的抗争来表达这种“情感结构”。比如说《坐上吉普》中的马兰花,她被从原始的深山老林中带入现代都市的过程,本身就是纯粹和质朴的被玷污的过程,她的绝望从她步入现代都市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的。这也意味着,抗争注定了只能是绝望地和义无反顾地冲向悬崖与大海:她那朝向悬崖和大海的奋力一踩(油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次绝望的飞翔。再比如说《玫瑰开在我父亲怀里》,父亲的失败早已注定;这颇有点像堂吉诃德朝向风车的奋力冲杀,他们都把表象(比如风车)当成了不存在,他们寻找的是表象背后的各种可能性。
因此,对林那北而言,过程很多时候比结果更重要,比事物的存在本身(而非表象)更重要。人们既然很多时候对自己和世界,并不真正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意识,寻找过程本身显示出其意义来:其既表明结果的虚妄和难以获得,又表明对表象世界的始终如一的审视与批判。她通过小说的写作,其实是提出了过程美学的命题,个人意向性命题正是在这一点上表明其价值。这构成了对“原初”的寻找的另一种类型,即堂吉诃德式的荒诞寻找本身。
三
寻找与缺失的辩证关系,其实也是J·希利斯·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中所说的“重复”的两种形式的缠绕。比如说《一男一女》中的甲哥和丙妹,他(她)们因为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才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但这种相似和重复关系却因一次突然的置于与世隔绝的语境中而显示出他(她)们之间差异的本质来:人与人之间的相似,并不是建立异中之同的基础上,事实是相异的事物之间产生了同的因素。同因异而产生,而不是相反。即是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异构成了人的存在的本质。认识不了这点,便会对人生充满失望。但也恰恰是认识不了这点,她的小说主人公们才始终处于一种寻找的处境之中,这也可以说是林那北小说的独有贡献。她充分认识到外在世界之陌生的和异己的本相,但却绝望地和义无反顾地去追求。这可能也就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对“存在的可能性”⑧的探索吧。
这种探讨在她的《玫瑰开在我父亲怀里》中有集中呈现。父亲是一个与他的身份和处境不相吻合的不切实际的人。他是一个农民幻想家。他的想法常常具有一种浪漫的气质——热衷于造飞机、写小说,等等。没有幻想的世界,是一个让人绝望的世界,父亲的存在让叙述者“我”看到了琐碎庸俗现实的多重可能性,这或许是小说的叙述者更喜欢父亲而不是母亲的重要原因。虽然说现实与幻想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狀态,林那北想表达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可能性,现实本身是否可以容许幻想的存在?毕竟,只有幻想才能使得生活飞翔起来,幻想让人看到希望,幻想是生活之光的体现。
这种重复现象背后,不难体察林那北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世界充满着表象和幻象,世界其实处于一种永恒的循环状态中,日复一日的彼此重复着。我们被幻象所迷惑。因此对我们来说,要么生活在这种幻象中,不自知,被裹挟着向前;要么表现出一种决绝或反抗的姿态。林那北的主人公更多属于后者,这是她的主人公的主体性的表现。我们作为个体的人的主动性,就体现在人生的偏移、意向性和对自我的确认上。世界对个人的形塑作用,使得我们很多时候以一种意向性的方式表现其反应,我们很多时候并不自知。只有当我们被某个生活的裂缝所刺激从而表现出偏离或偏移的时候,才能感到并确认自己的存在,这也意味着,认识自我,源于生活中的事件及其偏移或溢出。因此,在林那北那里,事件的意义就显得尤其重要。比如说《唇红齿白》中杜凤相亲前的牙疼这一事件,成为导致其后人生一系列变轨和变故的重要象征。比如说《右手握拍》,李威妻子杜若怀孕时心脏病突现,导致前途一片大好的李威的人生陷于停顿,她的心脏病的反复发作,因而也成为李威人生的左右摇摆状态的映照关系;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个人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的故事,各种力量、各种偶然的和意外的事件,左右着人生的走向,人能否左右自己的命运呢?小说告诉读者,很多时候主动性的意念和决定,仍旧是必须的,哪怕仅仅是微不足道的一次主动选择。
从这个角度看,在林那北那里,寻找主题所涉及的其实就是自我认知的命题了。一个没有自我认知的,或自我认知不够的人,才会有寻找的必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那些浑浑噩噩的人,他们是不需要表现出寻找的“意向性”的。寻找只针对那些对现实人生或有不甘的人。比如说《唇红齿白》中的杜凤,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她对自己隐秘的欲望和思想,并不总是清楚。她后悔于当年错过了欧丰沛,因此,当欧丰沛官越做越大,她对丈夫李真诚的不满就越加明显;她想象自己是欧丰沛的妻子,却又并不想破坏家庭。当她一步步陷入欧丰沛的怀抱的时候,她的自我意识才开始慢慢复苏,她逐渐意识并表现出幡然醒悟的过程,她的自我正是这时产生;但反讽的是,在她确认自我的时候,她的人生却没有了退路可走。人生就是这样的悖论。没有自我意识的人生可能是浑浑噩噩的人生,但也可能是安全的人生。清醒的人生往往是令人痛苦的。不自知,可能才会是幸福的,比如说柳静(《唇红齿白》),她始终活在一种懵懂无知的过程中,但随着她的自我认知的逐渐清晰(伴随着对女儿的认知,女儿其实构成了柳静的镜像关系),她开始感到不安、紧张和痛苦。人的精神洁癖,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懵懂无知的象征和隐喻。是清醒使得懵懂无知变得不可能,林那北的小说,往往表现出一种清醒的痛苦感,用孟繁华的话说,这是“以一种悲悯的情怀体现着她对文学最高正义的理解”⑨。林那北的小说正是在这一点上具有“心灵史”的味道,但若仅仅把它定位在“现实生活所造成的精神迷茫和心灵上对回归的渴望”⑩的二元性上,又似显不够。
四
作家金仁顺对林那北的小说有过一段十分敏锐的直觉概括,她说:“北北的芯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的:清醒的认识,冷静的判断,精致的细节,不多也不少的伤感,对理想的坚持,对诗意的追求,以及悲悯的情怀。”11“清醒”“冷静”“悲悯”但又有似乎“不多不少的伤感”和“对理想的坚持”,这看似矛盾,其实是道出了林那北小说的内核:林那北的小说在明快的故事和节制的叙述所构成的张力关系中蕴藏着某种更为深刻的思想力量和精神指向。她的小说在如下两点上显示出其深刻之处,即对本质存在的怀疑,和对不可能之物的寻找。两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她的小说的整体氛围。这里,很难说哪一个命题在前,哪一个在后,唯一能确定的是,这是互为因果的两个命题。你很难说那把旷世珍宝的剑不存在,只能说你还没找到,甚至可能永远找不到(《剑问》);你很难说绝对纯粹之人和绝对洁净之人世界上没有,只能说你没有遇到(《晋安河》);等等。两者之间其实是一种辩证关系的体现。《请你表扬》中的杨红旗,最后强奸女大学生就表明两者的对立关系:好事(即解救女大学生)和坏事(强奸女大学生)之间往往会瞬间转换,人之为“人”其实并不纯粹。
而这,正反映出林那北的小说的某种倾向,即指向世界和自我的双重困惑及双向坚守。正是因为对世界有了困惑,才有守住“精神洁癖”的执着;而恰恰是“精神洁癖”又显示出对自我的不自信。她的小说主人公的主体性正体现在这种双重的困惑和双重的抗争之中,同样可以说,林那北小说的艺术张力也正体现在这里。
【注释】
①北北:《自序:有一条路在内心蜿蜒》,载《请你表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序言第3页。
②[美]约翰·塞尔:《人类文明的结构》,文学平、盈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26页。
③林那北:《世界是扇形的》,载《锦衣玉食》,百花文艺出版社,2014。
④林那北:《在岁月中春暖花开》,《芳草》2020年第5期。
⑤[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程炼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第57页。
⑥关于林那北小说的“缺失”内涵,另参照林秀琴:《从破碎到荒诞——试论北北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⑦林秀琴:《从破碎到荒诞——试论北北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⑧[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第59页。
⑨孟繁华:《林那北和她小说的表情》,《小说评论》2018年第2期。
⑩马季、桫椤:《重建普通人的精神谱系——谈林那北小说创作中的精神指向》,《时代文学》(上半月)2011年第3期。
11金仁顺:《北北和林那北》,《时代文学》(上半月)2011年第3期。
(徐勇,厦门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