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与探索
2021-09-26张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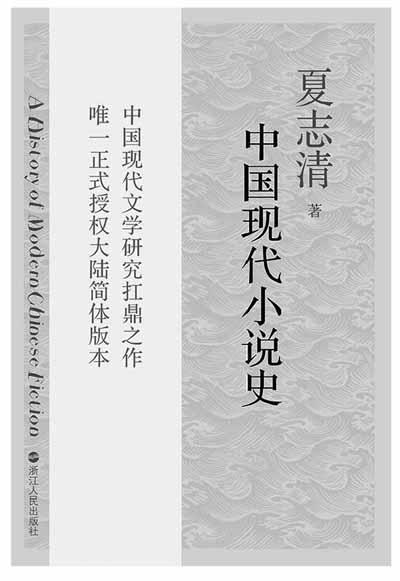
1970年代末,《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海外中译本便开始在内地“流通”,引起各种追随与批判的声浪,被认为对“重写文学史”思潮产生过影响。此书对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师陀等作家的重新发现,乃至其所谓“纯文学”批评标准所产生的延续至今的冲击,都让这部英文语境下问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至今仍不容小觑。相较于这部著作今天所受之重视与瞩目,夏志清最初的写作不无偶然因素,其过程更是筚路蓝缕,他在此书英文初版前言中就描述了写作期间饱受材料匮乏之苦,亦乏同行切磋①,应该说,这很符合彼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美国学院体制的边缘处境。这部著作得以成书,离不开夏济安、宋淇、程靖宇等寄身港台者从观点到资料上的帮助。这些,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下文简称《小说史》)1961年版前言中也提及过,只是语焉不详而已。
2015—2019年,五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渐次推出,无疑提供了从个人史视角审视《小说史》的丰富材料。《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下文简称《书信集》)收录两位重要海外汉学学者长达18年的私人通信,也跨越了冷战开启以后海外现代文学研究逐渐勃兴、并在美国学院中取得一席之地的过程。尤其重要的是,《书信集》展示了《小说史》从萌芽、写作到出版的全过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院体制与文化环境对《小说史》写作的影响,隐约浮现于夏氏兄弟书信往还文字间;夏氏兄弟对五四、对鲁迅这样的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时段与重要作家,对现代文学史观的各种讨论亦包含其中,这些观点相当程度为夏志清所消化吸收,体现为《小说史》中的具体史观与评价标准。本文借助《书信集》中与《小说史》写作有关的内容,探讨《小说史》写作缘起的历史与个人背景、夏济安对《小说史》写作的参与,以及夏志清在探索中确立的写作规划。
一、《中国现代小说史》写作的缘起
在《小说史》动笔前,夏志清现代文学的阅读量相当有限,他承认:“五四以来的文学我在中大学时没有多读。”②较之其热衷介入文化、文学与出版活动的兄长夏济安,出身纯正教会学校沪江大学英文系的高才生夏志清对英美文学的兴趣更加心无旁骛。1940年代末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夏志清以其优异的英国文学造诣,赢得赴美留学的机会,并于1951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彼时其前途似已注定,“系主任根本想不到我会在美国谋教职的:东方人,拿到了博士学位,回祖国去教授英美文学,这才是正当的出路”③。这体现了当时美国高等教育界的一般看法,但也并非仅出于美国学院体制对中国人的排斥,夏志清的前辈王际真以及较早赴美的陈世骧,都在美国的大学里立足,且各有其成就。美国的大学里,谋一个非终身教职的门槛,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也并不是多么难。问题是,以异国人身份在海外求学,纵使留在美国教书,仍很难在数百年里根深蒂固、自成门户的美国大学英文系里成就事业,《书信集》中披露的夏志清在美前10年的从教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虽然醉心英美文学,最后仍要靠教授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立足,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中国人在美国找事极难,要研究中国东西只有在大学major中国学问。”(见1959年8月19日夏志清致夏济安信)1956年上半年,密歇根大学聘期即将结束,夏志清处境艰难,甚至动了赴台湾工作的念头(见1956年2月7日夏志清致夏济安信)。在1952年5月的一封信中,他坦然承认自己的现实考虑:“两三年后我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出版,也不难在大学内找一个副教授之职。”④自博士毕业后,夏志清携妻带子,辗转于各种名声不彰的大学,教职不稳定,一段时间教教英文,既而又教教中国思想史,地位终归属于边缘。不能忽视的是,由于1950年代初铁幕开启,冷战背景下的美国区域研究渐成热门,中国现代文学因其与现代中国历史无法分割的关系,也吸收了相当的经济与人才资源。1970年代末,《小说史》中译本问世时,夏志清已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多年,遂饶有兴味地为此书撰写《原作者序》,此序包含了夏志清自述“入门”现代文学研究的“官方”回忆。他追述1951年助饶大卫编写《中国手册》之事⑤,该“手册”内容庞杂,“《文学》这一章重点却放在现代文学上,占全章篇幅三分之二”。在查阅资料时,夏志清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竟没有一部像样的书,我当时觉得非常诧异。”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第一部系统全面介绍中国新文学历史进程的著作,其上册在同年(1951年)刚刚出版,夏志清的话,不能说不对。由此,他获得灵感,在第二年写下两页“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计划书”,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过了三年(1952—1955)无拘无束、读书写作的生活”⑦。
在《小说史》第一版推出10年后,在夏志清的“官方”书写中,强调了其走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偶然性与现实性考量。不过,此时身在中国台湾的夏济安,通过与夏志清的书信交流,也在观念和视野上影响着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夏济安对《小说史》写作的介入,在該书英文第一版中体现最为显著,夏志清在1961年所写前言中特别感谢了兄长在成书最后阶段所给出的诸多建议⑧,参考《书信集》,可知这些“建议”之具体之深入,远非在成书“最后阶段”的帮助那么简单,而是始终或深或浅地参与到《小说史》写作进程中。譬如,因夏志清对彼时中国台湾地区文坛生疏,夏济安应其要求亲自撰写《台湾文坛》一文,成为该书首版唯一附录⑨。
参阅《书信集》可知,在夏志清参与《中国手册》写作前,两人书信就多有关于现代文学看法的往还,提出观点、阐发意见者多是兄长夏济安。早在1950年11月25日致夏志清信中,夏济安即大致介绍台湾文坛状况,提及柳雨生、陶亢德、袁可嘉、朱光潜、陈纪滢、谢冰莹等作家。在1951年元月7日致夏志清信中,夏济安以郑证因和宫白羽为正面例子,批评老舍小说在语言风格上的“故意卖弄”。在1月18日致夏志清的信中,夏济安正式提出对五四文学的批评,“想创导一种反五四运动,提倡古典主义,反抗五四以来的浪漫主义”⑩,夏志清在次月2日回信中,积极回应兄长的观点:“中国从五四运动到今日的情形,确需要有一个严正立场的批判……真正地把人生严明观察的文学,是‘古典文学,这种文学往往是残酷的。”11可以说,在与兄长的通信中,夏志清已经流露出对彼时自己尚不熟悉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探究兴趣,而这种兴趣的流露,与同时期他撰写《中国手册》“文学”部分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空白”的发现,共同构成了夏志清决心撰写《小说史》的思想起点。
在批评观念上,夏志清对文学风格“残酷”一面的赏识及将其用来批评中国现代文学,显然源自其长期浸淫英美文学作品与批评的阅读和理论积累。这是一种迥异于内地同期文学史写作的带有比较文学色彩的评价标准,亦延续到后来《小说史》写作中。如他对张天翼的肯定:“悉能超越宣传的层次,进一步达到讽刺人性卑贱和残忍的嘲弄效果。”12又如他认可鲁迅写于1925—1927年间的短文:“也有冷酷狠毒的幽默。”13通过《书信集》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趣,远非出于安身立命于异国他乡之现实考量,其实不乏对其出身的文化环境与现代历史的深切关怀,可以说,正是自1950年代初与兄长通信中,他开始认真地把五四、鲁迅以及白話文风格当作学术考察的对象。
此外,还需注意的是,夏志清决定着手从事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性著作写作,包括夏济安在内的港台亲友提供的文献资源也给他增添了不小的底气。他最初顾虑耶鲁大学所藏中国现代文学书籍不足,甚至有为查资料方便而迁居纽约的打算,实际上以他当时的条件也只能做到每月到哥伦比亚大学中日文系图书馆往返一次。夏志清在《小说史》“中译本序”里感谢了宋淇和程靖宇提供资料;夏济安的帮助则更加细致且深入,书中存在着许多作品版本和内容上模棱两可的地方,以及英文译本人名具体翻译的问题,这些都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夏济安在台湾亲力亲为的查找与勘校14。
二、夏济安对《中国现代小说史》
写作过程的参与
夏济安对《小说史》写作过程的参与,体现为撰写附录与资料查核,更体现为具体观点的提出和探讨。在资料的查核上,小到“棉花弹”“洋泾浜”等词汇的英译问题,大到整年文献的索取,如在1959年8月5日致夏济安信中,夏志清直接要求兄长航寄1957年全年《文艺报》,并据此重写第18章。借助《书信集》,会发现写作过程中,由于资料的匮乏,夏志清兼用了现代小说的中英文版本,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他1959年10月12日致夏济安的信中询问兄长:“有一个地主名叫Hou Tien-Kueu,究竟是侯什么(典贵?),我没有书,无法查。”
在夏志清开始《中国手册》“文学”部分撰写时,夏济安对中国现代文学关注的焦点也是基于其“秩序”和“宗旨”方面的批评,1951年一年,他先后撰写了英文文章《中国文明的未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专门反思五四运动历史影响的《1919及其后》,对中国现代文化总体持较为苛严的批评态度。在与夏济安书信探讨中,夏志清则表达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类似印象:“这文学应有的估价,当然不高,最主要的原因是一般作家不知道sin、suffering、love为何物,写出来的东西就一定浅薄。西方作家对罪恶和爱都是从耶稣教出发的,中国没有宗教传统(《红楼梦》的伟大处是在它的Buddhist philosophy of disillusion),生活的真义就很难传达了。”15在后来《小说史》的写作中,夏志清虽因阅读量扩大,对这种严厉的态度加以修正,但至少在1961年《小说史》第一版出版时,他总体批评的态度未变;直至1967年提出“感时忧国的精神”,夏志清方为现代文学的不足作出如下辩解:“国难方殷,企图自振而力不逮,同时旧社会留下的种种不人道,也还没有改掉。”16
夏济安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提供着同声相应的唱和探讨,也做出了有力支持,在得知夏志清参与《中国手册》写作后,他马上写信给出建议。批评钱锺书研究方法上“quotations很多”“很少心得”的同时,鼓励夏志清注意“秩序”和“宗旨”(见1951年6月17日致夏志清信),事实上已经是在强调历史叙述体系的建构。1952年以后,夏志清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正式开始《小说史》写作,对现代作家作品尚乏整体全面了解,此时夏济安对作家和作品选取的指点就显得尤为重要,实际牵涉《小说史》的叙述策略与板块构成。在这个意义上,1953年1月18日夏济安的来信具有特别意义,他在此信中首先认可“中国新小说有好几派”,左派“是声势顶大的一派”——在1951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后,这在当时是人所共知的观点。夏济安信中希望夏志清关注当时并未进入学者视野或难以纳入内地文学史主流论述的冷门作家与冷门作品,“little known authors,little read books里面可能有好的”。这些“鲜为人知的作者和作品”中,夏济安以自身阅读视野,特别提到了京派与海派,并对其各自风格做出基于个人印象的总结。他的实际意图是大体勾画了《小说史》一种可能的叙述版图,即“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和“左派文学”鼎立的面貌,“以免把‘左派看得太重要”。此时夏济安对五四以来文学的热情多出于个人兴趣,并无学术上深入的了解,故这里的“京派”“海派”“左派”的区分与界定较为随意而模糊。但他至少给夏志清这样三个重要的提示:其一,不受既定文学史筛选机制的影响,“一个写文学史的人多少总得有些新发现”17,多关注冷门作家与作品;其二,在文学史格局划分上,多考虑“左派”之外文学的位置与历史;其三,借助对文学刊物的回溯,返回历史现场。夏济安此信中提到“京派”与“海派”的分野,并未被夏志清直接接受,但在《小说史》第2编描述革命文学兴起后的文学史版图时,他用第5章“三十年代的左派作家和独立作家”对二三十年代文坛犬牙交错的状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提出“独立作家”的概念,以与“左派作家”相区分。这一章也相当重视以文学期刊的兴衰为线索描述文学潮流消长。在正文和附注中先后介绍了夏济安强调的《文学》《现代》,以及信中未提的《文学季刊》《大公报·星期文艺》等杂志,将现代文学历史与文学期刊史研究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小说史》所使用的现当代报刊超过60种,囊括左右,亦关注边缘。在进行作品分析时,夏志清也力求尽可能将小说单行本与其最初发表期刊加以对照,如对小说《倪焕之》的阅读,他便“觉得前后不调和”。在读到宋淇考证后,他找到了较早版本,发现此书在1949后再版时经历过删改。最后,他在《小说史》中使用的是较早版本,并在附注中对此书版本变化加以注明18。
夏济安此信虽然提示夏志清注意京海两派,不要“太看重左派作家”,又直言不讳地指出京海两派“都敌不过左派”,这与“对于人生态度是否严肃一点也有关系”,从而又模棱两可地承认了左翼文学的价值;在《小说史》附录《台湾文坛》中,他干脆直接表达了对左翼文学充满热情而直面现实的文学精神的怀念。夏志清的回信,则从夏济安信中特别摘出一段话,表示欣赏:“我认为中国近代缺乏一种‘不以society为中心,而以individual为中心的morally serious的文学。”这句话里包含了对“左派”文学与“京派”“海派”各自的批评,“左派”过于“以社会为中心”,后两派则过于看重“个人”。夏济安一方面认可左翼文学的社会价值,一方面又建议夏志清增加对左翼之外创作的發掘。《小说史》最后形成的论述格局,相对于大陆同一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事实上的确是淡化了左翼文学的存在与影响。在具体写作中,他采取了如下策略:第一,强化如钱锺书、张爱玲等非左翼作家在书中所占的比重,都给予专章篇幅;第二,与此相应的,将政治色彩较为鲜明的左翼作家直接以整章形式简单概括描述;第三,对政治上立场明显但作品艺术性较强的作家,如鲁迅、茅盾、张天翼等,则在专章论述中更多强调其作品艺术价值,淡化其政治诉求。夏志清采取的写作策略对中国现代文学复杂的格局的确有所体现,远非单纯的左右对立;与此同时,他的写作策略又在实践着夏济安“不要‘太看重左派作家”的建议。值得注意的是,在淡化左翼文学影响的同时,夏志清也对一些非左翼多有批评,如谈及京派的文学趣味时,他指出:“像周、林两氏所奉信的‘言志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建树。”19类似表述,明显与夏济安信中对京海两派作家的评价有所呼应。
三、在探索中确立的写作规划
由《书信集》来看,夏志清最初的研究计划,不限于单纯的文学研究,而是综合的近代思想研究,“用中国近代思想史作大前提,或可写成一本有重要性的书”。研究重点的摇摆不定,其原因或可归咎于“中国新文学,纯以文学眼光去批评它,当然没有什么可取处”20。如果不想写成一本枯燥的中国现代作品编年介绍,则写成一部思想史与文学史杂糅的著作,亦不失为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但以本书成书时的正文三编19章来看,夏志清仍然采用了初期(1917—1927)、成长的十年(1928—1937)、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1937—1957)这种规矩的三阶段撰写结构。按照夏志清自己在成书不久后的评价,也是“批评态度不够严肃,appreciation成分较多”(1958年12月15日致夏济安信)。这一方面是由于以思想史为背景书写的文学史,其所需的理论与资料准备,远超夏志清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更重要的是,随着阅读量的不断扩大,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看法,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改变,以至于这部著作实际成为“发现和评审”三个阶段中的“优美作品”,进而被认为是“要为中国建立现代文学的‘大传统”21。
1953年以后,夏志清在书信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苛评有所减少,在这年1月19日信中,他肯定了“叶绍钧有几篇描写都市和乡村弱小灵魂的都很不差”,还发现“落华生可说是唯一对基督教道理有同情的作家,他战后出版的中篇《玉官》,可算是篇classic”,这些观点,后来都体现在《小说史》具体章节中,如称赞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作品“是中国现代小说传统中的上等之作”,而对于《玉官》这篇不长的小说,夏志清则用了4页篇幅加以介绍和评价。在同一封信中,他还盛赞沈从文与凌叔华,特别提到后者的《绣枕》,在《小说史》里,《绣枕》亦获得了较大篇幅的评介。时年夏志清已经人过而立,在学术思想上亦已逐渐成熟。随着阅读量的积累,让他的确对中国现代文学有所发现而不无惊喜,但这种发现和惊喜是建立在既有学术积累基础上的。他批评五四以后国人的文学批评标准流于印象,“可是说到这时代作品的本身,最后的标准似乎只有‘成熟‘丰富(richness)等简单的concept”,他的雄心是在“审定文学的好和伟大,最后的标准是同一的”22,这其实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他选择与批评作品的“纯文学”导向,所谓“受了New Criticism的影响”。值得玩味的是,深刻影响了夏志清文学批评的英美新批评学派,其作品批评其实偏重于诗歌研究,除夏志清的恩师克林斯·布鲁克斯与罗伯特·潘·沃伦合编的《理解小说》外,对于小说探讨甚少,《理解小说》一书重点也在引导阅读而非文学批评,仅对海明威《杀手》与福克纳《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两篇有较为细致的分析。所以夏志清在小说分析方法方面仍需自己探索。他探索出的方法论,有两点值得特别重视:一是前文提到的比较文学取向,二是广义上的人性论,两者或可从普世主义角度合二为一来看。其对比较文学方法的使用,自己公开的解释是为了英美读者阅读便利:“将中国作家与西方作家进行对比,尤其是从塞万提斯到福克纳这样的优秀作家,后者作品往往为人们所周知。”但更深的原因则是夏志清对英美文化与人文传统的服膺。无论夏志清的初衷如何单纯,他在文化立场上不自觉地将本土反转为异域,很容易在诸种“后学”兴起后遭到基于后殖民主义视角的讨伐。周蕾在她的著作《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中将夏志清的研究作为重要考察对象,将夏志清书中讨论过的《绣枕》《沉沦》《春桃》等都一一重新点评,直言不讳地批评他“大量地运用了社会达尔文学派的优生学修辞”23。即使如此,周蕾仍然部分地认可夏志清在30年前的观察具有出于本能的敏锐性,承认夏志清对郁达夫小说的分析“与我们的讨论不谋而合”。
事实上,夏志清对作品差不多是反复阅读和挑选的,虽然“appreciation成分较多”,其评价也是更多凭借自身文学修养和阅读经验,乃至于生活经验,在具体方面并非全然依赖西方文化。他自认这是利维斯的影响:“我的moral preoccupation想是受了Leavis的影响,Leavis对诗、小说方面都严肃老实说话、不为文坛fashions所左右。”在读到师陀的《结婚》时,他曾为是否将此书纳入研究范围举棋不定,写信与兄长商榷。夏济安为此专门读了一遍这本小说,评价不高。夏志清在一个月后回信,不同意兄长对《结婚》的批评,但表示愿“再看《结婚》一遍,决定它的价值”。重读的结果是,夏志清在书中仍坚持师陀此作为杰作,“因为师陀能够在他紧凑的叙事中注入这点恐怖成分,他把《结婚》写成了一部真正出色的小说”24。不得不说,夏志清的文学品位即使不涉及任何既有的文学传统,仍然是非常诚实而敏锐的。
在与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论战中,夏志清提到自己对于“文学史家的基本任务”的看法:“评价分析某一时期主要的、代表性的作家,简要介绍导致他们成功或失败的时代状况,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切。”25由此可以看出,在经历了各种方法论与文学史观的探索后,夏志清还是在《小说史》中力图采取一种较为成熟的史家立场。而这个探索的过程,在与《书信集》的对读中,是可以得到清晰展示的。
【注释】
①⑨14T.A.Hsia”,Appendix:Taiwan”,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57,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p.viii.
②④⑩1115172022王洞主编、季进编:《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第126、166、51、52、126-127、207、195、255页。
⑤1951年6月8日,致夏济安信中,夏志清最初谈及此事:“Yale教授David Rowe得政府合同,研究中国问题,我已被他聘用。”見王洞主编、季进编《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第84页。
③⑥⑦121316192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第xxxi、xxxiv-xxxv、xxxv、181、42、459、111、399页。
⑧在1961年出版时,夏志清又以附言形式补写了对姜贵《旋风》的评论,在1970年代末中文版中,又将其扩充为附录《姜贵的两部小说》。
18在《小说史》第三章注释9中,夏志清引用宋淇观点,介绍了《倪焕之》版本大致演变过程。在《小说史》正文对该作品分析中,他使用的是1949年之前版本。
21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载《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第xv页。
23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蔡青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70页。
25夏志清:《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载《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济安、刘绍铭、李欧梵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326页。
(张涛,吉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