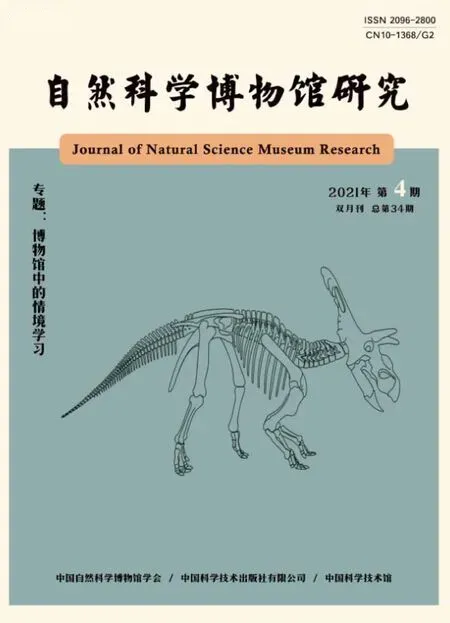女性主义叙事策略在科普展览中的应用
——以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神秘海洋”展为例
2021-09-26张娜
张 娜
科技馆界对叙事研究已不算陌生,尤其在展览研究领域,如何利用叙事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做好科普展览已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尽管性别化差异已在科技馆参观行为中有所显现(1)笔者曾基于2018年广东科学中心年度观众调查的结果,从展项研发的视角出发,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与阐释,发现成年女性观众,特别是亲子家庭观众中的母亲,是广东科学中心的核心观众,提出展项研发部门需要成年女性观众,研究与之相适应的展项设计属性,以增强成年女性观众对科技馆展项的参与度,致力于让国内科技馆行业和学界关注观众性别差异导致的参观体验的不同,针对成年女性观众这个核心观众群,开发更多面向成年女性观众的科技馆展项,增强核心观众的用户黏性,保证科技馆观众的可持续性参观体验。[1],但目前国内科技馆叙事研究尚未涉及面向不同性别观众的叙事策略。科技馆展览的男性化叙事与女性化叙事可与科幻小说中的硬科幻与软科幻相类比,前者惯于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医学等硬科学为基础、强调科学性与准确性,而后者则更倾向于采用文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视角让科技变得柔软、温暖、可及,揭示科学的人文本质。相较于疏远型的男性主义叙事,女性主义叙事是一种吸引型的叙述,适用于科学传播与普及过程中的叙事,不仅可以吸引女性观众走进科技馆、走近科学,也同样吸引着男性观众,为其提供了审视科技内容的新视角。
叙事学家将叙事作品分为“故事”和“话语”两个不同的层次,前者可以理解为作品“再现”的外部世界,属于“摹仿”层,而后者则可以理解为作品对外部世界的“表现”,属于“叙述”层。将传统的言语叙事延续并迁移至展项叙事,保留故事和话语的叙事二分法,在此基础上探索女性主义叙事策略的表征与理据,以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神秘海洋”(UnseenOceans)展览(2)“神秘海洋”展览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联合美英等国的科学家与设计师进行创意设计,展览分为导言、奇幻漂流者、神秘生物、遇见巨型生物、潜入深海、无形边界、丰饶的海洋和结语8个展区。展览带领观众从阳光普照的海洋表面到达海洋幽深之处,探索最新的海洋科学、运用最新的机器人技术及卫星技术揭开神秘海洋的面纱。展览面积达800平方米,以荧光生物模型、180度环幕、海洋地形互动沙地、科普剧场、虚拟下潜游戏、科研记录片等互动方式展示海洋科学知识。让观众在交互中探索海洋深处;在科学探索与趣味体验中,思考如何保护海洋的未来。该展览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6月在广东科学中心展出。为例,基于笔者的即身(embodied)与寄身(embedded)体验,观察、分析,思考科技馆展览女性主义叙事策略的理论与实践,分析该展览采用的女性主义叙事策略(见图1)。

图1 “神秘海洋”展览女性主义叙事策略
一、 故事: 女性母题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是重要的生命载体,孕育、滋养着世间万物。人类无意识里对水的渴望赋予水以母性。水在人类原始记忆的物质联想也使许多诗人描述水的时候将其比喻成母亲[2]。对水的母性想象与古希腊人对生命始源的思考有关。古希腊人在思考生命始源问题时,就自然而然地将水意象与母性想象联系在了一起,泰勒斯(Thales)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认为万物最开始都是由水形成的,并且万物最终都可以“还原于”水[3]。黑格尔(G. W. F. Hegel)认为水不仅是生命的始源,还是艺术家创作灵感的源泉,滋养着艺术家的灵魂[4]。水意象的母性想象可见一斑,而作为水域概念的海洋也是一种重要的女性母题,法国当代科学哲学家、文艺诗学家巴士拉(Gasiou Bachelard)认为孕育了丰富生命的海洋成为了一种“粘液”,这种“粘液”让人联想到“母乳”[5],而海洋——水——母亲的联系成为了许多诗人灵感的物质联想逻辑。
在“神秘海洋”展览中描述海洋的定语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与其孕育生命的母性特征相关,如:生命的(vital)、丰饶的(abundant)等,另一类则与其神秘莫测的女性气质相关,如:未见的(unseen)、神秘的(mysterious)、秘密的(secret)等,可见,展览中的海洋兼具母性和女性双重特质。展览开篇明义,在序厅中就交代了海洋隐喻的这种双重性,“站在沙滩上看,海洋一如既往,安详、舒缓、波光粼粼,但在海洋深处,却是另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这种阳光照耀下温柔的海面给人的温暖与人类无法抵达的、充满未知的深海带给人的不确定性构成了海洋母题的两个方面,阳性的科学技术与阴性的未知自然亦形成一对彼此对立的意象,在多重隐喻对偶和复合作用的影响下,观众积极地建构着对“海洋母亲”的想象。
二、 话语
(一) 叙述介入:翻译干涉
女性主义学者、加拿大翻译家弗洛图(Louise von Flotow)在《翻译和性别:“女性时代”的翻译》一书中归纳了女性译者常用的三种干预叙事的翻译策略: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以及劫持(hijacking)[6]。其中劫持是指译者因为质疑原文在语言和思想层面的表达,尝试改写(Appropriate)原有叙事中不具有女性意义的文本,并采用创造性的译法对文本进行重新解读,是一种对原文的操纵,使语言女性化,从而让女性的声音被听到、女性的身影被看到。法国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苏(Hélène Cixous)认为女人用“白色墨水”(乳汁)书写,从躯体到欲望,女性的文字如河流般自由流淌,说出了一切未被言说的可能性[7]。受西苏提倡的阴性书写的鼓舞,更多的女性拿起笔来书写只能被女性所感知的独特的身体体验。
在“找找我的小宝贝”匹配游戏这个展项的展台上印有如下文字:“Some plankton are baby animals—and I used to be one!To find my baby picture”,在引进展项的汉化处理后,将上述文字翻译为,“这些浮游生物里有一个和我小时候长得一样!在墙上找到我宝宝的照片”。此处将“baby picture”翻译为了“我宝宝的照片”,而原文对应的一般意义上的中文表达应为“婴儿时的照片”,可见,译者在此处进行了翻译过程中的改写,即将“我婴儿时的照片”改写为了“我宝宝的照片”。这种改写在女性主义叙事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体现了弗洛图女性主义翻译(叙事干预)中的“劫持”策略,在原本第一人称、自我中心式的祈使句中加入了“他者”(孩子)(3)在德勒兹(Gilles Deleuze)“生成他者”(becoming-other)的若干轴线中,孩童,因其非理性的行为和言语特征,也是一种“他者”(the other)。的形象,通过话语构境,在叙事中融入了对子女的孕育和抚养体验,而这种体验对于成年女性观众,特别是亲子家庭中的母亲具有独特的吸引力,能够产生认同感、激发共鸣,提升展览对该部分核心观众(4)《现代科技馆观众调查的研究与实践——以广东科学中心为例》一书中记载了2018年广东科学中心年度观众调查的结果。笔者从展项研发的视角出发,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与阐释,发现成年女性观众,特别是亲子家庭观众中的母亲,是广东科学中心的核心观众。的吸引力。
(二) 叙述距离:吸引型
女性主义叙事学领军人物、美国学者沃霍尔(Robyn Warhol)在《性别化的干预》一书中区分了“吸引型”和“疏远型”两种叙述形式。前者指叙事者的介入使读者与受述者产生认同,后者指叙事者的介入使读者与受述者产生距离。沃霍尔研究发现,吸引型叙事者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出现的频率要远远高于男性作家,而疏远型叙事者则更常见于男性作家,因此可将吸引型看作女性技巧,疏远型看作男性技巧。沃霍尔进一步指出,吸引型女性叙事策略的运用对作品的虚构性产生了淡化的作用,从而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性[8]。从某种意义上说,相较于虚构性和疏远型的男性叙事策略,女性叙事更偏向于采用现实性和吸引型策略,并运用这些女性叙事策略建构女性意识。
在“潜入深海”剧场外墙的“深海潜水员”图文板中,对海底测绘工作的科学传播是通过第一位乘坐“阿尔文”号潜水器潜水的非洲裔美国女性道恩·赖特的工作经历与体验展开的。暂且将这位双重边缘化叙事者的“他者”(5)在德勒兹“生成他者”的轴线中,少数族裔和女人均为“他者”,而少数族裔女性则是双重边缘化的“他者”。视角问题搁置一旁,聚焦叙事距离问题,可以发现在展板右下方印有这样的图文,“必要装备‘我的史努比!’”。作为世界上到过海洋最深地方的三个人的其中之一,赖特向观众讲述她下潜的必要装备是史努比毛绒公仔。严谨的科学性表述——“必要装备”与活泼的日常语言——“我的史努比”之间也形成了话语上的张力(tension),营造了一种诙谐的氛围。深不可测的海底、陌生的科学探索工具(潜水器),这些超出日常经验的未知之物给观众造成的距离感(distance)就这样被一个亲切可爱、众所周知的卡通动画形象消解了。这种现实性、吸引型的女性叙事风格不仅有利于增强女性观众的驻足力(holding power),还通过身份认同与话语构境启迪了女性观众对科学事业的追求。
(三) 叙述声音:女性叙事者
女性主义叙事学创始人、美国学者兰瑟(Susan Lanser)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区分了“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三种叙述声音模式,其中“个人型”叙述声音是“自身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即将故事的“我”和故事的主角“我”为同一人;而集体型叙述又分为三种:“某叙述者代某群体发言的‘单言’(singular)形式,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simultaneous)形式和群体中的个人轮流发言的‘轮言’(sequential)形式。”[9]女性主义叙事倾向于采用私下的“个人型”叙述声音以达到倾诉的言语效果,辅以“集体型”叙述声音以实现自我权威化,建构女性主体意识的同时也建立了女性的话语权威,让女性的声音为人信服,使女性的内心活动与生存境况得到社会更广泛的关注。
在“奇幻漂流者”(海面下200米深度区域)展区的“认识科学家”(原文为Scientist at Work,译为“工作中的科学工作者”更为准确)板块“食物链专家”展项介绍了加州莫斯兰丁的蒙特雷湾水族馆研究所的女科学家Kelly Benoit-Bird和她从事的海洋生态系统研究工作,她的工作内容的视频在展项中被投影到倾斜的圆柱形白模的剖面上。整段视频投影中都未见到这位女科学家的身影,展项图文板以“看不见,听”作为标题,颇具女性主义叙事意味。就像她所研究的大多数海洋生物一样,女科学家的身影无法为我们所见(正如光波无法穿透到海洋深处),但通过声纳/声音,我们可以探测/聆听——海洋生物/女性,即通过女性的叙述声音,我们得以在想象的空间中与这位女科学家相遇。
叙述声音由她本人,即女叙事者的个人型和集体型声音相互交织而成。个人型的“我”的声音再现了一种个性化的体验,“我最大的优势就是我的爸爸是一位机械工程师。我一直就是爸爸的小助手,很小就开始认识工具、修理东西”,这里女叙述者仍在借用父亲这一男性的刻板化印象(sterotype)建立自己的科学家形象,实则是在男性理解惯性与期待视野中的权宜之计。集体型的“我们”则讲述了她和研究团队的共同经历,“我们知道这太难了,但我们必须要做到,幸运的是,我们全做出来了”,这里女叙事者采用了“共言”形式——“我们”的集体型叙述声音替自己和研究团队发声,而并没有采用“单言”形式的“我”来代表她所在的群体发言。“共言”相较于“单言”更突出的是女性群体的共在性,建构属于女性群体的话语权威的同时,又保持了个体的差异性,使女科学家这一群体希冀被认可与尊重的女性意识得以抒发与表达。
另一处值得注意的叙述声音出现在该展览的剧场影片叙事中。影片中的叙述声音呈现了男女“轮言”式的集体型声音,在女性叙事者安详、舒缓地向观众介绍所处水层环境及其间的生物的叙述声音中偶尔掺杂着男性科学家急促的实际操作潜水器的声音:“控制中心、控制中心,生命维持系统正常,通风口安全,正在下潜,完毕”“通过200米水深,继续下潜,完毕”“我们要采集海面标本”。可以看出,男、女叙事者处于同一空间、共享同一视角,但观众却更容易与女叙事者产生身份上的认同,这是因为男叙事者在这里只是作为了孤独的机器操作者,做着机械化的陈述,而女叙事者则敞开自我,拥抱海洋与生命,以观众视角讲述着海洋生物的故事。这里女性叙述声音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接纳男性叙述声音,通过与观众的感同身受,将潜入未知海域的冰冷,转化为了与尔同行的温暖。
(四) 叙述视角:故事内叙事
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文学理论家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将叙述视角分为了全知视角、外视角和内视角三种。
全知视角又称为零视角或上帝视角,用符号表示,即叙事者>人物,指的是叙事者如上帝般全知全觉,比任何人物知道得都多,而且可以不向读者解释这一切他是如何知道的,读者只是被动地接受故事和讲述。在传统科普展览叙事,乃至目前大部分科技馆的展览叙事中,大多数都是通过这种全知视角叙述的,以此体现科学原理和操作说明的严谨性和逻辑性。叙事者是权威化的中心,观众被视为了“空瓶子”,被灌输着不容置疑的科学知识,知识由权威中心向观众进行着单向传递,观众被边缘化,与权威中心处于非平等关系,叙事者/权威中心与观众的关系与历史上的“缺失模型”对应的“公众接受科学”的早期科普形态相符,但随着公众与科学的关系由接受走向理解与参与的演变,这种全知视角的展项叙事已然无法匹配新的科技传播形态。
与全知视角相反的是外视角,即叙事者<人物。叙事者比所有人物、甚至观众知道的都少,具有一种“无知性”。理论上而言,采用外视角叙事,就如同采用全知视角一样,都会造成知识的单向流动,即外视角叙事会造成知识从观众向展项的流动,造成科学的“反向”传播。在实践中,这种逆向的传播适用于展示行动中的科学,而非形成了的科学,在自媒体时代非中心化,或中心的非确定性与情境化环境中也具有其独特的意义,此处暂不展开详述。
内视角,即“叙事者=人物”,法国结构主义学家热奈特又称之为“内聚焦叙事”,包括故事内叙事和故事外叙事两种情形。“神秘海洋”展览叙事的一大特点是大量采用了第一人称内视角的故事内叙事,叙事者讲述自己的事情,这种叙事方法本身就带有亲切感和真实感,是一种天然的吸引型叙事,既可以进行内心独白,又可以让观众借由叙事者的感觉、意识,从她(该展览的叙事者多为女性)的视觉、听觉及其他身体感受的角度去接触科学。除了第一人称内视角故事内叙事的运用,该展览叙事的另一显著特点是自由引语的大量使用。自由引语是指不加任何引导句的引语方式,是在现代小说中才出现的新模式,展现了叙事话语生成的新可能,仿佛女性叙事者直接跳脱了图文的束缚,敞开心扉、自由地对观众诉说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可见,特定的叙事形式制约着观众接受、理解与参与科学的效果,观众的反应也将影响策展人对叙事形式的选择。
三、 结语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认为每一首诗歌都像是一棵自然生长的植物,根据自身规则长成最终的“有机模式”[10]。“神秘海洋”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如水的有机美学,将水的不定性、流动性融入展览叙事中,通过解域化的故事、话语和空间构境探索主体向他者(女性、孩子、生物、环境等)的生成,重塑着主体建构的可能性,在静谧与幽暗中体验着自我的消逝与永恒的成为,为女性主义展览叙事提供了示范:在故事层面,选择了海洋这一女性母题;在话语层面,采用了翻译干涉的女性主义叙事介入、吸引型的叙事距离、女性叙事者的叙述声音、故事内叙事的叙事视角,这些叙事策略的运用建构了女性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女性观众、特别是亲子家庭中的母亲这一科技馆核心观众群对展览展项的参与度。为进一步提升女性观众对科技馆展览的参与度,乃至女性对科学事业的热忱,科技馆在今后的展览策划中需要更多地关注女性故事,从女性视角开展现象叙事,鼓励女性策展人发声,采用女性叙事者,关注女性观众群体,让女性更好地理解与参与科学,确保不同性别的公众获得适宜的科普服务,这不仅是科技馆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代科普伦理的内在需求[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