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的焦虑
2021-09-23信明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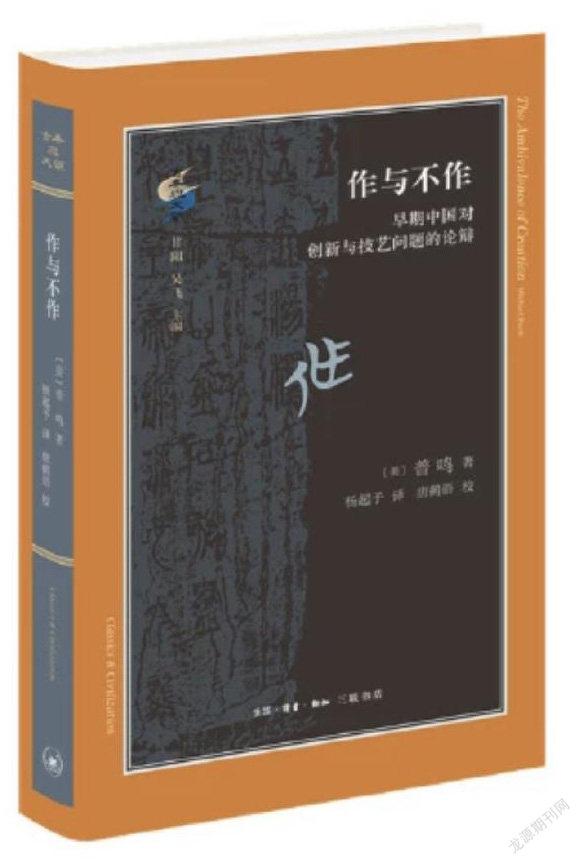
信明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孔子曾公然宣称自己“述而不作”,这引来了墨子的强烈反对,他质疑这种主张的合理性,并讥诮这种保守主义立场的食古不化。一场旷日持久的论辩由此拉開了序幕。这场论辩似乎极为低调,以至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虽然人们早已注意到与此有关的只言片语,但极少有人在乎它的全貌。普鸣以极大的兴趣对这场论辩的完整面貌进行了还原,这构成了《作与不作:早期中国对创作与技艺问题的论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一书的主要内容。
一、论辩的向度
普鸣对这场论辩的导火线,也即孔墨之间的争论给予了特别关注。他敏锐地注意到,墨子对于孔子的攻讦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在《论语》中,孔子常常以工匠造器来比喻人的教化,并认为二者的主旨都在于对物质材料和人的天生原质中所固有的文理和品格进行条理和规范,这纯粹是一个对原有属性进行修饰的过程,无需操作者自作主张在其中掺杂过多的“专断”要素。① 反之,墨子则将目光投注到这项操作的技艺层面,他认为,如果不经过技艺改造,所有原材料都无法成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技艺,才使得各种器具不断产生,人们的生活也不断改善。从本质上说,这些其实都是制器者个人“专断”的产物,因此,拒斥“专断”大可不必,只要内心持善,这种行为就无可厚非,甚至不可或缺。②
此后的论辩在孔墨所奠定的基本架构之内逐步展开。《孟子》和《乐记》遵循了与孔子相同的立场,他们将讨论范围主要限定在道德和礼乐等与教化有关的技能方面,认为这些技能都是圣人效仿自然文理和秩序的结果,以此来强调这些技能中所包含的“因循性”。③ 而《周礼·考工记》和《韩非子·五蠹》等文本则与《墨子》如出一辙,他们将实用技艺作为主要关注对象,并将这些技艺的创作权都归于圣人,以此来凸显这个“专断”过程的合理性。④ 除此之外的第三种立场则将道德礼义和实用技艺综合起来讨论,这种讨论中同样包含着两种倾向。《老子》《庄子·知北游》《鹖冠子》《淮南子·本经训》等文本一致认为世间的文化与技艺无论是出自“因循”还是“专断”,都导致了“道”的损耗以及自然的分化和失衡,因此必须全然否弃,才能回归原初的和谐。⑤《荀子》和《吕氏春秋》中的《君守》《任数》《勿躬》三篇以及《系辞》等文本则以极为曲折的方式,试图在文化与技艺生成过程的“承述”与“专断”两种倾向中取得折中与调和。⑥
与此同时,这种讨论更延伸到了“集权国家”这种更为现实的话题中。在《尚书》中的《吕刑》《尧典》《洪范》三篇以及《世本》《尸子》《管子·地数》《山海经·大荒经》等文本的叙述中,暴虐自用的“蛮民乱贼”和承天之谕的“圣人”——前者作为创作者,后者作为规范者,共同导致了刑罚和武器等与集权有关的暴力要素的诞生和确立。⑦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所附《经法》《十六经》两篇以及《大戴礼记·用兵》《管子·五行》等文本,则着力于用自然秩序对律法和暴力等集权要素的专断属性进行限定。⑧上述文本同样都旨在对集权国家创立过程中的“专断性”与“因循性”进行调和。除此之外,《墨子》和《商君书》都全然将集权要素的“创作”归于圣王,并极力推崇这种“创作”行为的正当性和必然性。唯独孟子始终坚守着恢复礼义教化的复古诉求,彻底否认这些权力要素的合法性。⑨
及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他立即向天下宣扬帝国制度的超越性,以及自己旷古绝伦的创世之功。然而秦的迅速灭亡无疑在事实上否定了这一命题。于是到汉初时,对帝国遗产的评议就出现了两种倾向。陆贾《新语·道基》与《淮南子·氾论训》等文本分别主张在《五经》秩序与自然平衡的原则下,对秦制进行扬弃吸收,他们显然默许帝国制度的某些面向。⑩与这种折中态度不同,董仲舒则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他尊孔子为素王,并以此进谏武帝因循古礼。而武帝则通过举行各种仪式,将帝国制度与自然节序,以及各种经典文本中所承载的秩序体系相嫁接,力图为这种体制赋予合法性。⑪
汉武帝的一系列举措被司马迁详细地记录在了《史记》中。对于帝国制度与汉武帝本人,司马迁的态度极为复杂。他详细叙述了历史转向之际,秦始皇、项羽、刘邦、晁错等人在道义与功能和因循与开创的夹缝中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以及汉武帝在文饰帝国属性的各种举措和仪式中所表现出的刻意和虚伪。显然,司马迁已然看透,对原有政治秩序的僭越以及与此伴随的时代裂变,是帝国无法掩饰的本质属性。但他也明白,也正是在这种突破与危机彼此交织的矛盾必然性中,历史才获得了充足的发展动力。整场论辩就在这种悖论中黯然地落下了帷幕。⑫
二、创作的维度
普鸣将这场论辩分为“文化技艺”“集权国家”与“统一帝国”三个话题依次展开,三个话题分别对应三种不同的对象范畴,它们都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那么,人们究竟是如何参与到这些范畴的生成过程的呢?围绕这个问题,各家给予了不同的“参与”限度,虽然这种限度有时会被压缩至极低,但并未被彻底剔除。即使如孔子之“不作”、老庄之“弃作”,也依然是以否定的方式,从反面为这种行为确立原则。在论辩的各个话题中,这种人类“行为要素”始终是一个中心议题。显然,各家都一致默认,人的参与是这些社会事物生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其中的争议主要在于程度,而非有无。这是他们展开论辩的共同基础,也是所有答案得以立足的前提。
因此,论辩所聚讼的关键问题并非在于人类能否“创作”,而在于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进行“创作”。然而,在具体的论辩中,并未有一套为各家所严格遵循的统一概念和术语体系。特别是对于论辩的内核,他们分别使用“作”“述”“生”“伪”“兴”等倾向不一的词来进行表述。⑬ 即使其中最常用的“作”,其意义也经历了明显的变迁。⑭显然,他们试图以概念化的方式从语义层面直接定义这种限度之必然。其实,这些词的基础语义基本一致,都是指能够导致特定现实结果的实践和行为,并且它们的主语也都共同指向人类。因此,术语的混乱也并未妨碍他们在同一论域之内彼此展开对话。而普鸣则采用最为常用的“作”来概括这种意义,显然是从最宽泛的层面来使用这个词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既有过程又有结果的人类实践,本就是一种“创作”。
除此之外,各家也尝试通过知识情境的宏观构筑,来间接确立这种限度之应然。在《论语》中,孔子将宇宙描述为一种能将世间万物都维持在永恒秩序中的静谧而沉默的存在。⑮随着论辩的推进,这种宇宙论不断被完善和发展成為一套体系严整的复杂理论。该理论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世间万物都看作是宇宙永恒秩序的产物,自然事物所蕴含的文理直接体现了这种秩序,因此,以此为模板而将其文理引入人世就成为人们“创作行为”的根本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只是虔诚的因循者,他们从未脱离这种秩序,也并未掺杂任何个体的专断因素,更未僭越宇宙的职能而在既有事物之外制造新的存在。普鸣指出,正是以这种理论为前提,孔子才拒斥任何越轨,并进而将人类所有的“创作”都描述成一种“承述”。⑯贯穿论辩所有话题层次的“因循派”,以及主张“有限因循”的“调和派”,几乎都是在这种极具理性色彩的宇宙论中展开自身立场的。
这种理论影响极为深远,从16世纪开始,包括利玛窦、白晋、莱布尼茨、孔多塞等人在内的西方学者就注意到这种独特的东方宇宙论,并将其视为与基督教文化迥异的另一种对上帝律法的领会方式。随着西方启蒙时代所带来的技术飞跃,伏尔泰和黑格尔等人则又将这种理论视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阻力。及至20世纪之后,牟复礼、杜维明、吉德炜、谢和耐、梅维恒以及张光直等西方汉学家延续了这种认识,他们都倾向于用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来探讨这种“天人合一”的有机关联宇宙论及其所带来的实际效应在人类文化的全域图景中所具有的独特性。他们都将这种宇宙论当作一种根植于中国文化血脉中的原生基因。
普鸣对这种预设提出了质疑,他从甲骨文和金文中发现了商周时期与此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更为古老的宇宙论。这些文本塑造了一个有着浓厚个性意志的人格化形象,并作为整个宇宙的代理者和掌控者,其中还有一些同样人格化的自然神灵与祖先鬼魂与之接洽并执行其命令,他们时常主动而任性地在人间制造各种福利与祸患。这种宇宙中并不存在某种能将世间万物都统摄在内的秩序,无论是自然事物还是人类,都保持着鲜明的个性,并拥有相当宽容的行为自主性。普鸣认为这些文本都或隐或显地表明了天人之际的断裂,而非合一,这与古希腊和基督教文化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格局毫无二致。⑰即使西周时期的文本中一再强调上天和祖先的典范作用,但现世的周王们也绝未因循某种秩序,而是如“偶像”所“作”的那样,以积极的姿态御疆辟土、开拓自然。这种宇宙论同样影响深远,《墨子》正是以此为理论依据,而将宇宙主宰者视为一个怀着爱人之心并“创作”了利于万物生长和人民安居的自然时节与土地空间的人格形象。圣人也以此为典范而主动“创作”各种器具,用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其他那些主张积极创作的“专断派”也几乎都是在《墨子》所建立的这种“创作论”基础上所进行的发展和延伸。
虽然两种宇宙论是彼此互异的两种知识系统,但其所描述的客观世界却是唯一的,二者的差异其实主要在于他们各自采用了不同的基础模型。如果说“理性化”宇宙论是以自然世界为模板,故而将寄身其中的人们设定为一种被动与从属的角色,那么另一种“人格化”宇宙论则是以人类社会为参照,因而为人们赋予了充分的主导性和积极性色彩。可以说,两种宇宙论各自包含了客观世界的某些真实面向,二者之间的差异绝非真伪之别,而是基于认知视角的殊异。虽然两种宇宙论在出现时间上有先后,但并无本质的差别,都是一种为特定群体所造就和持守的带有主观意向的话语。作为话语,它们并非旨在对某些为社会所默认的普遍观念和规则进行描述,而是基于这些内容的待实现。因此二者也就更不必有所谓的原生与次生之分,之前那种关联宇宙论的固有认知也就不攻自破。
当然,两种宇宙论并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思辨,在它们理论化的表象之下同样包裹着“实践”的内核,二者都是为了对人们的“创作实践”做出明确导向而人为拟构的以人类自身为基点的坐标系统。这与论辩中所出现的各种概念和语汇系统有着相同的目标和属性。只不过相比于前者,这种宇宙论似乎处于更高的维度上。正如上文所说,如果说前者试图以概念化的方式从基础层面直接定义“实践”之必然;那么后者则尝试通过对宏观知识情境的构筑,来间接确立“实践”之应然。总之,各种维度的“创作论”本质上都可以看作是基于不同立场的“实践论”。
三、文本的厚度
这场论辩最终呈现在各种文本中,这些文本无疑充当了论辩话语的“肉身”。这不但表现在那些明确携带着话语意图的论说文本中,而且对于那些貌似属性单纯的叙事文本同样适用。在早期中国神话文本的叙述结构中,葛兰言发现了某种与历时性的仪式和权力关系有关的诉求张力,在一定程度上正体现了这一点。⑱然而,这只是一种非典型的解读方式,相比之下,近现代以来的东西方学者都采取了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路径。他们一致将触手可及的神话文本,看作是对于某种遥不可及的历史原相的朦胧写照。普鸣无意指摘这种还原路径的可能性,但他指出这些神话叙述本就充满了矛盾和歧异,对它们的解读和判定首先面临一个重大难题就是取舍标准的确定,各家观点的主要破绽也正在于此。鉴于此,普鸣打算从纷乱的文本泥淖中脱身出来,转而如葛兰言那样深入分析其叙述表象下的深层张力。遗憾的是,葛氏终究未能坚持到底,他随即将这种张力指向了史前时代,由此又重新落入了主流理念皆未能幸免的陷阱之中。普鸣认为葛氏的失误正在于他脱离了文本的原初语境,如果要避免重蹈覆辙,就要重新回归这种语境。
在普鸣看来,早期中国的神话文本通常以碎片化的形态依托于其他的宏观文本而存在,这决定了它们只能作为非独立的寄生文本来参与和辅助其“宿主文本”的意义表达,因此,剥离这种语境来假设和讨论它们无迹可寻的所谓原始面貌,以及独立意义恰恰是毫无意义的。基于这一前提,普鸣将一些相关的神话文本重新回置到其原本所在的战国时期关于“集权国家”的论辩语境中,从中离析出“自然”“圣人”“臣下”“乱贼”四个角色,并围绕这些角色对于“集权国家”相关要素的“作”与“不作”,而归纳出可与该论辩话题下的“专断”“因循”“调和”三种立场相对应的三类截然不同的叙述结构。⑲简言之,这些神话叙述皆是由不同的知识群体所建构,其碎片化的形态以及彼此之间的情节矛盾正是由此而来。他们将其组织进那些立场更为明确的宏观文本之中,只是作为一种情节例证,用以印证自身的立场。
除此之外,这种特性更完整地体现在以《史记》为代表的历史文本中。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伯夷列传》中就明确指出,前代经典历史文本由于“辨是非”的意向特质所导致的对先圣形象刻画的片面和偏差。同时他更是明言自己在《史记》中对于史料的去取标准,并时常或明或暗地透露自己在其中所欲表达的价值取向。以此为前提,普鸣在《五帝本纪》中离析出了与战国神话文本大致类似的叙述结构,并指出其中所出现的蚩尤、炎帝、黄帝三个形象分别隐喻“反抗中央权力”“轻侮地方权力”以及“维护两极平衡”这三种不同的权力诉求,文本通过三者间的互动模式和胜负关系表达了明确的制度取向。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了对“帝国兴起”“楚汉战争”“削藩平叛”“武帝封禅”等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写中,相关文本以一系列张力十足的二元矛盾的叙述结构,凸显了帝国制度所面临的无解的悖论和困局,以此来隐含褒贬,寄寓主张。⑳
文本所承载的特定立场和主张,使得它们具备了与现实相互疏离的意义厚度。因此,文本并不直接对现实进行映現,而只是提供一种待实现的建构潜力,这恰恰反衬了现实的缺憾。同时,文本的组织和书写更是一种由特定知识群体所负责的“创作”,如果说文本所承载的立场反映了他们的期许和诉求,那么其所反衬的现实缺憾则指向他们的焦虑和困惑。而这些文本正好被“创作”于古代中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期。在此期间,旧有的秩序岌岌可危,全新的力量蓄势待发。新秩序的创作过程,同时也是对于旧秩序的废弃和僭越过程。两个过程之间形成了一种悖论的漩涡,现实世界也在这种漩涡的裹挟下,悬浮在一种稳定与变动彼此相持与胶着的状态之中,所有的“创作实践”也由此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困局。这使得当时的知识群体陷入了焦虑,对于现实的关切促使他们努力寻找答案,并展开针锋相对的话语角逐,这场论辩以及承载它们的文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四、结语
普鸣所揭示出来的这场关于“创作”的论辩过程,实际包含着两个层次。其一,现实的“创作”困局引发了关于“创作”的论辩,这里的“创作”是广义层面上的,其意指范围近乎“实践”。其二,论辩导致了承载各种立场和话语的文本被“创作”,这种文本的“创作”则是一般理解中的狭义的“创作”。在这两个层次之间,一个不容忽视的主导角色就是知识群体。他们直面现实的“创作困局”,而使自己陷入了“焦虑的困局”,又在这种“困局”之中“焦虑地创作”了文本。他们立足于现实之前,藏身于文本的背后,试图以一个中间者的角色通过编织各种文本,为裸露而模糊的现实世界包裹上文理清晰的话语外衣,以实现对它的重塑。总之,狭义的文本“创作”正是为了限定和重构广义的现实“创作”。随着论辩的终结,曾经弥散在其间的困惑和焦虑被一扫而清。从此,有关“创作”的原则与属性亦趋于分明和稳固,它逐渐被一套单一的话语秩序所统摄,并在这条坚不可摧的锁链束缚下,最终陷入了如履薄冰且举步维艰的境地。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⑯⑲20 普鸣:《作与不作:早期中国对创作与技艺问题的论辩》,杨起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70—73,79,83、109,109—112,91、113—118,102、123、128,150、178-182,171—177,159、164,224、235,250,295—299,72,197—198,295—299页。
⑬ 孔子将“作”与“述”加以对立,其实这两个词可以看作是同一种行为和事实的两个面向,如果说前者强调了某种行为的创新性,那么后者则强调了同一过程中必然包含的继承性。另外,荀子还用“生”“伪”等词来实现这种强调效果。其中“生”有“生育”或“生长”的意味,用以凸显这个过程的自然性,而“伪”虽然有“人之所为”之义,但荀子所取的是一种基于禀赋的自发行为。
⑭ 普鸣对“作”这个词从殷商到战国时期的语义演化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他认为这个词最初专指那些具有实用功能的技艺创作,带有明显的专断色彩,直到后来才被用于表述文化的生成,而有了“因循”的意味。
⑮ 《论语·阳货》:“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句话是对这种宇宙论最为清晰的表述。参见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6页。
⑰ 普鸣对殷商卜辞中的先王祀谱和《大雅·生民》中的祭祀场景与赫西俄德的《神谱》进行比较,发现这几种文本都显示了对于祭祀对象和神主的安抚意图,而这种操作之所以必要,就在于祭祀对象本身便不安其位。因此,与其说祭祀体现了人神之间的和谐,倒不如说预设了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在这一点上,商周和古希腊之间并无差别。参见普鸣:《成神:早期中国的宇宙论、祭祀与自我神化》,张常煊、李健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07—110页。
⑱ 参见马尔塞尔·格拉勒(葛兰言):《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李璜译述,中华书局1933年版。
(责任编辑:斯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