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可断言性”即“真”?
2021-09-23王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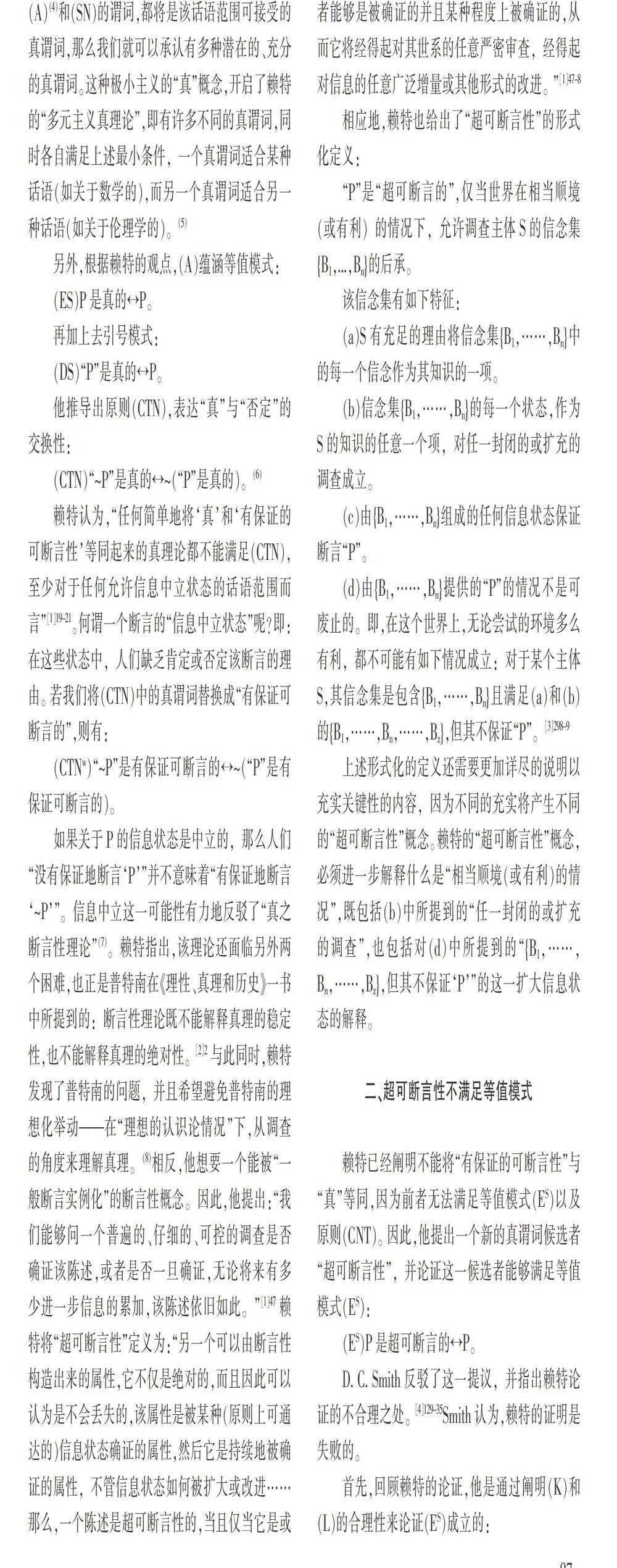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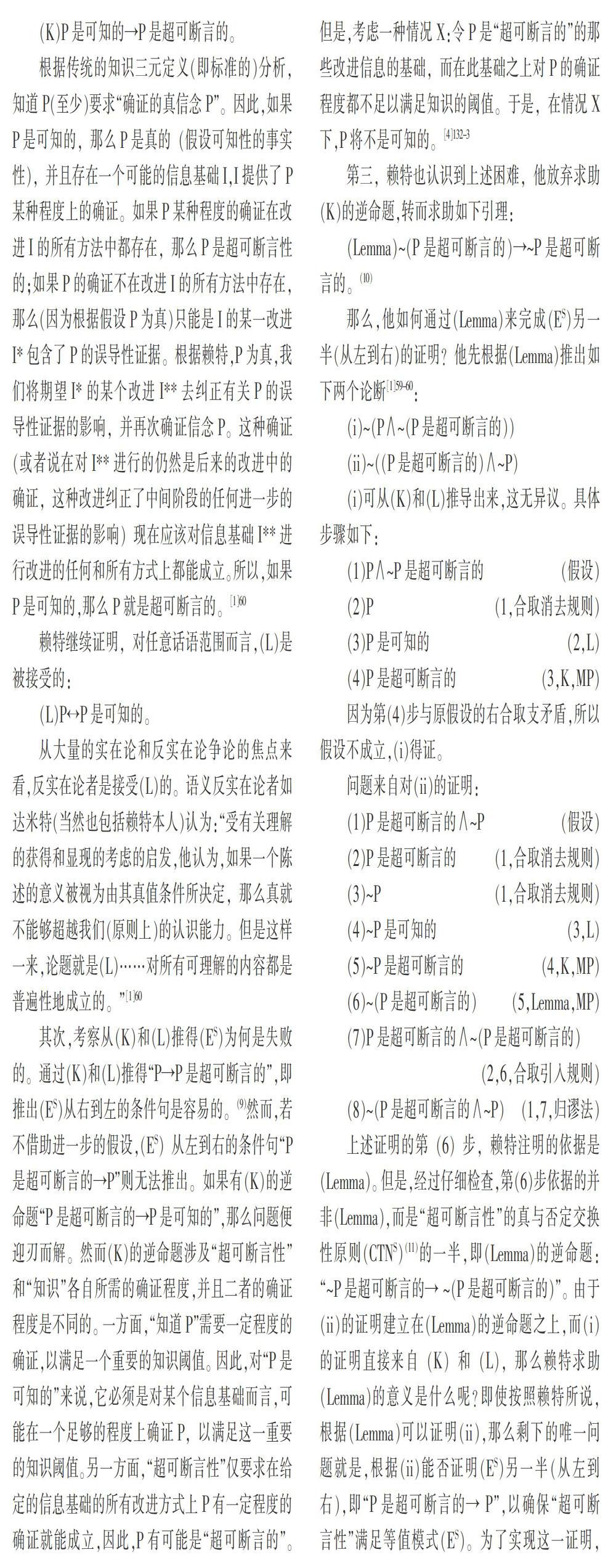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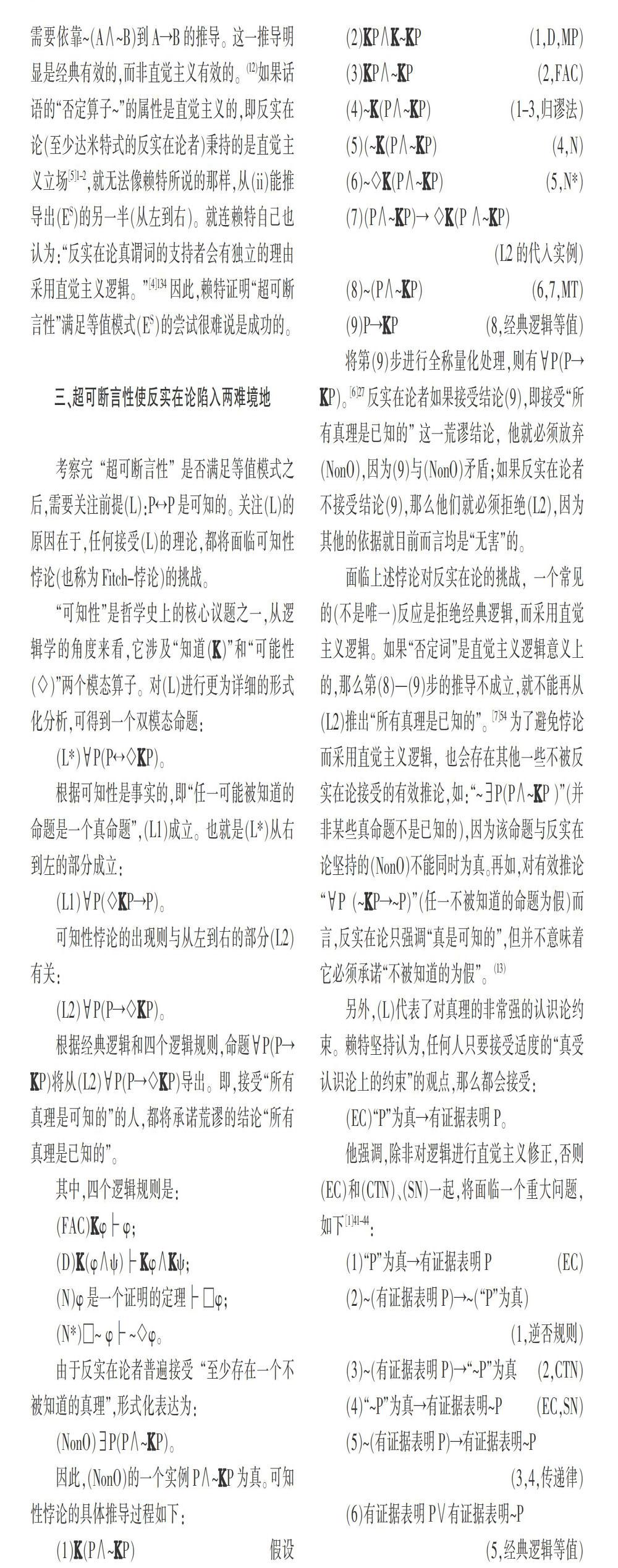
摘要:克里斯平·赖特倡导将“超可断言性”当作真谓词,进而为反实在论提供“真”概念的正面解释。他通过论证“超可断言性”可以满足等值模式(ES)“P是‘超可断言的当且仅当P”,来推动他所主张的“多元主义真理论”。赖特的这一尝试并不成功,“超可断言性”面临诸多挑战,如它实质上并不满足等值模式(ES),又使反实在论陷入两难境地,以及它具有可废止性等。如果赖特无法对这些挑战做出合理的回应,那么他将不能捍卫自己的真理论立场,同时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超可断言性”不可能成为“反实在论的真之概念”候选者。
关键词:赖特;超可断言性;真谓词;真理论;反实在论
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主要在意义理论。实在论者主张,一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它的真值条件。反实在论者则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由它的使用决定,并且任意话语都存在一个模式:“P为真→P是可知的”(1)。该模式被认为是对意义理论的约束,而且约束本身以“意义必须在使用中得以显现”为前提(2)。但这一模式并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对反实在论者而言,“真”究竟是什么。克里斯平·赖特认为,在上述模式先验地成立的任何话语中,可以将一个命题的“真”与该命题的“超可断言性”等同起来。有鉴于此,反实在论所坚持的核心观点“所有真命题是可知的”便有了充分的理由,因为“真”与“超可断言性”等同,所以,“所有真命题就是超可断言的”,这也就意味着它们都是可知的。赖特似乎给出了反实在论的“真之概念”的正面说明,然而,如果反实在论者真如赖特一样,将“超可断言性”当作一个真谓词,那么它至少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超可断言性”不满足真的老生常谈,即“等值模式”;第二,“超可断言性”使得反实在论陷入两难境地;第三,“超可断言性”具有可废止的特征。
一、 “超可断言性”的缘起及定义
克里斯平·赖特在《真理与客观性》一书中,通过指出“有保证的可断言性(warranted assertibility)”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超可断言性(supperassertibility)”这一概念,并强调后者才能够满足他所捍卫的“极小主义”真理论。
赖特认为,任何满足一组相对较小且直观的、老生常谈的谓词都构成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真谓词。[1]24就极小主义而言,这组谓词可以进一步简化为以下关键的“老生常谈”:
他强调,一旦人们认识到“真”概念本身是一个极小概念,即对一个话语范围而言,任何满足(A)(4)和(SN)的谓词,都将是该话语范围可接受的真谓词,那么我们就可以承认有多种潜在的、充分的真谓词。这种极小主义的“真”概念,开启了赖特的“多元主义真理论”,即有许多不同的真谓词,同时各自满足上述最小条件,一个真谓词适合某种话语(如关于数学的),而另一个真谓词适合另一种话语(如关于伦理学的)。(5)
如果关于P的信息状态是中立的,那么人们“没有保证地断言‘P”并不意味着“有保证地断言‘~P”。信息中立这一可能性有力地反驳了“真之断言性理论”(7)。赖特指出,该理论还面临另外两个困难,也正是普特南在《理性、真理和历史》一书中所提到的:断言性理论既不能解释真理的稳定性,也不能解释真理的绝对性。[2]2与此同时,赖特发现了普特南的问题,并且希望避免普特南的理想化举动——在“理想的认识论情况”下,从调查的角度来理解真理。(8)相反,他想要一个能被“一般断言实例化”的断言性概念。因此,他提出:“我们能够问一个普遍的、仔细的、可控的调查是否确证该陈述,或者是否一旦确证,無论将来有多少进一步信息的累加,该陈述依旧如此。”[1]47赖特将“超可断言性”定义为:“另一个可以由断言性构造出来的属性,它不仅是绝对的,而且因此可以认为是不会丢失的,该属性是被某种(原则上可通达的)信息状态确证的属性,然后它是持续地被确证的属性,不管信息状态如何被扩大或改进……那么,一个陈述是超可断言性的,当且仅当它是或者能够是被确证的并且某种程度上被确证的,从而它将经得起对其世系的任意严密审查,经得起对信息的任意广泛增量或其他形式的改进。”[1]47-8
二、超可断言性不满足等值模式
赖特已经阐明不能将“有保证的可断言性”与“真”等同,因为前者无法满足等值模式(ES)以及原则(CNT)。因此,他提出一个新的真谓词候选者“超可断言性”,并论证这一候选者能够满足等值模式(ES):
根据传统的知识三元定义(即标准的)分析,知道P(至少)要求“确证的真信念P”。因此,如果P是可知的,那么P是真的(假设可知性的事实性),并且存在一个可能的信息基础I,I提供了P某种程度上的确证。如果P某种程度的确证在改进I的所有方法中都存在,那么P是超可断言性的;如果P的确证不在改进I的所有方法中存在,那么(因为根据假设P为真)只能是I的某一改进I*包含了P的误导性证据。根据赖特,P为真,我们将期望I*的某个改进I**去纠正有关P的误导性证据的影响,并再次确证信念P。这种确证(或者说在对I**进行的仍然是后来的改进中的确证,这种改进纠正了中间阶段的任何进一步的误导性证据的影响)现在应该对信息基础I**进行改进的任何和所有方式上都能成立。所以,如果P是可知的,那么P就是超可断言的。[1]60
从大量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争论的焦点来看,反实在论者是接受(L)的。语义反实在论者如达米特(当然也包括赖特本人)认为:“受有关理解的获得和显现的考虑的启发,他认为,如果一个陈述的意义被视为由其真值条件所决定,那么真就不能够超越我们(原则上)的认识能力。但是这样一来,论题就是(L)……对所有可理解的内容都是普遍性地成立的。”[1]60
其次,考察从(K)和(L)推得(ES)为何是失败的。通过(K)和(L)推得“P→P是超可断言的”,即推出(ES)从右到左的条件句是容易的。(9)然而,若不借助进一步的假设,(ES)从左到右的条件句“P是超可断言的→P”则无法推出。如果有(K)的逆命题“P是超可断言的→P是可知的”,那么问题便迎刃而解。然而(K)的逆命题涉及“超可断言性”和“知识”各自所需的确证程度,并且二者的确证程度是不同的。一方面,“知道P”需要一定程度的确证,以满足一个重要的知识阈值。因此,对“P是可知的”来说,它必须是对某个信息基础而言,可能在一个足够的程度上确证P,以满足这一重要的知识阈值。另一方面,“超可断言性”仅要求在给定的信息基础的所有改进方式上P有一定程度的确证就能成立,因此,P有可能是“超可断言的”。但是,考虑一种情况X:令P是“超可断言的”的那些改进信息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之上对P的确证程度都不足以满足知识的阈值。于是,在情况X下,P将不是可知的。[4]132-3
上述证明的第(6)步,赖特注明的依据是(Lemma)。但是,经过仔细检查,第(6)步依据的并非(Lemma),而是“超可断言性”的真与否定交换性原则(CTNS)(11)的一半,即(Lemma)的逆命题:“~P是超可断言的→ ~(P是超可断言的)”。由于(ii)的证明建立在(Lemma)的逆命题之上,而(i)的证明直接来自(K)和(L),那么赖特求助(Lemma)的意义是什么呢?即使按照赖特所说,根据(Lemma)可以证明(ii),那么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根据(ii)能否证明(ES)另一半(从左到右),即“P是超可断言的→ P”,以确保“超可断言性”满足等值模式(ES)。为了实现这一证明,需要依靠~(A∧~B)到A→B的推导。这一推导明显是经典有效的,而非直觉主义有效的。(12)如果话语的“否定算子~”的属性是直觉主义的,即反实在论(至少达米特式的反实在论者)秉持的是直觉主义立场[5]1-2,就无法像赖特所说的那样,从(ii)能推导出(ES)的另一半(从左到右)。就连赖特自己也认为:“反实在论真谓词的支持者会有独立的理由采用直觉主义逻辑。”[4]134因此,赖特证明“超可断言性”满足等值模式(ES)的嘗试很难说是成功的。
三、超可断言性使反实在论陷入两难境地
考察完“超可断言性”是否满足等值模式之后,需要关注前提(L):P?圮P是可知的。关注(L)的原因在于,任何接受(L)的理论,都将面临可知性悖论(也称为Fitch-悖论)的挑战。
“可知性”是哲学史上的核心议题之一,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它涉及“知道(K)”和“可能性(◇)”两个模态算子。对(L)进行更为详细的形式化分析,可得到一个双模态命题:
上述论证的结论(6)表明:要么有证据证明P,要么有证据证明~P,而不可能有中立的信息状态。然而,这与大多数反实在论者所倾向的观点相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赖特建议反实在论者最好采用直觉主义逻辑,如此,就能阻止从条件句论断(5)“~(有证据表明P)→有证据表明~P”到析取式的论断(6)“有证据表明P∨有证据表明~P”的推导。但是,这又将回到上文所提到的,在采用直觉主义逻辑之后,反实在论仍会面临一些不能接受(逻辑上推理有效)的结论。
于是,支持赖特的反实在论者将陷入两难境地。如果反实在论者采用直觉主义逻辑,那么根据赖特,他们不能证明(ES)是(K)和(L)的逻辑后承,即不能证明“超可断言性”满足“等值模式”;如果反实在论者接受经典逻辑,那么他们不仅要面临可知性悖论,还必须要么拒绝“信息存在中立状态”的说法,要么拒绝(SN)或(CTN)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对真的适度认知约束(EC)连同(SN)和(CTN),使得人们在经典逻辑中推断出结论“要么有证据表明P,要么有证据表明~P”,从而排除信息中立状态的可能性。因此,支持赖特的反实在论者无论是接受经典逻辑,还是接受直觉主义逻辑,结果都会让他们自己不满意。[4]138
四、超可断言性具有可废止性
通过前文论述能够看到,赖特关于“超可断言性”是真谓词的论证存在明显缺陷。此外,还应该思考,除了论证的缺陷之外,“超可断言性是真谓词”这一说法是否还有其他的合理性?例如,赖特认为“超可断言性”能够作为真谓词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具有不可废止性。然而这一说法遭到了L. Kavanvig的反驳,她认为,“超可断言性”不能成为真谓词的根本原因与“可废止性”以及“对它的保证的敏感性(susceptibility of warrant to it)”有关。[2]15
在《理性、真理和历史》中,普特南拒绝接受“真”是“有保证的可断言性”的观点,从而提出“真”是“在认识论的理想情况下‘有保证的可断言性”。他的理由是,“有保证的可断言性”既不稳定(它有来有去,而真没有),也不绝对(保证有程度,而真没有),它无法满足真理的这两个要求。[8]89然而,赖特指出,这些要求只有对“一个命题在认识论上理想的情况下是有保证的”才能被满足,这涉及有一个“不能被任何进一步的信息挫败(否则就不会有稳定性)或改进(否则就不会有绝对性)的情况”[1]45。赖特对普特南理想化方案并不赞同,他认为:“‘有保证的可断言性是相对于信息状态的断言性。这可能会让人觉得,类似于真理的理想化的断言性似乎只有一个方向可以假设,即我们必须将相关的信息状态理想化。然后,对稳定性和绝对性的追求似乎确保了皮尔式概念将是一个结果。但这是一个疏忽。与其问一个陈述在理想的经验调查的限度是否会被确证……我们还可以问,在达到任何神话的限度之前,一个日常的、仔细控制的调查是否会确证这个陈述,以及一旦被确证,无论进一步积累多少信息,这个陈述会继续如此。”[1]47
赖特解释道,有一种方法可以建立一个断言性的类似真理的概念(a truth-like notion of asser-tibility),而不必像普特南和皮尔式那样理想化。他希望这样的概念可以从断言的“一般保证(ordinary warrant)”中建立起来。“一般保证”是在“日常仔细的、控制的调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再附加上断论:即使面对进一步的了解,它们仍将被确证。所以,这些“保证”仍然是对断言有保证的,并且一个陈述的“超可断言性”产生于“普通的可断言性”。但是,这一概念作为真谓词的基本困难在于,它既不符合“知识蕴含真”这一显而易见的真理,也不能处理普特南关于真理既稳定又绝对的要求。之所以说它不符合,是因为有些击败者是误导性的击败者,这一点在“盖蒂尔问题”中得到了很好的探讨。赖特认识到了这一困难的某些方面,他说:“我不否认,在适当的情况下,一个认知主体可能根据事实上可以被击败的信息知道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他的知识主张不因有这种击败的信息而受到破坏,那么当然需要的是,一旦获得这种信息,其负面影响本身就可以被稳定地推翻。”[1]45
赖特通过关注“一旦获得”这一特征,提出他的观点:如果d击败了S对p的有保证性,但S还是知道p,那么,如果S将学习d,则一定存在S可以学习的其他东西,从而稳定地推翻d的可废止性的影响。这是真的,但这与此例的历时性特征无关。“S有保证的被d击败,而S仍然知道p,有其内在的含义。因为如果S在有这样一个击败者的情况下仍然知道p,那么一定会有某个超越者(overrider)存在,以说明S在击败者的情况下是如何知道p的。”[2]16这种情况很常见,假设你看到你的朋友汤姆从图书馆偷了一本书,由此你知道他偷了书。这个事实并不排除击败性信息的可能性,例如,汤姆的母亲现在可能会告诉警察,偷书的不是汤姆,而是他的同卵双胞胎弟弟蒂姆。但是警察不会认真对待这个说法,原因是,汤姆有很多前科,而且大家都很清楚,过度保护他的母亲会说出任何话,试图帮他清除任何指控。因此,存在着可废止性的信息(汤姆的母亲告诉警察的),但这些信息并不会因为超越者的共同存在而破坏你的知识。(14)因此,即使有击败者的存在,认知主体的知识主张仍旧不会受到影响。
赖特将他对“真”的解释与普特南对“真”的解释相比较,获得了自己解释的独特性。这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普特南“只在调查的限度内拥有理想化的确证”,而赖特的“超可断言性”概念则以一种平凡的方式产生,它只是“普通断言性”的一种特殊情况。但就本质而言,“普通的可断言性或信念”背后的唯一的保证就是可废止性的——这正是认识论告诉我们的。赖特也指出,“一个句子的‘超可断言性并不意味着现有证据的强度,虽然这些证据是积极的,但可能是不持久的”[1]57。赖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句话会使他自己的观点变得更弱:这句话仅表明“超可断言性”所涉及的“有保证性”有程度,不同于普特南在理想化调查的极限中所产生的那种“有保证性”。如果说“有保证的可断言性”是有问题的,理由是它不能解释真理的绝对性和稳定性,那么,“超可断言性”同样也面临这一问题。普特南强调:“真应当是一陈述不可或缺的一种性质,而确证则是一陈述可以失去的性质。”[9]61因此,必须通过“理想化的认知条件下的确证”来获得这种不可或缺的特性。普特南希望通過理想化到这一极限,从而获得“不可废止的确证”,其既不能被击败,也不能被改进。赖特只是不加论证地假定他的“超可断言性”也具有同样的优点,但这与事实相反。如果赖特想要“超可断言性”是绝对的,他就必须从“不可废止的确证”来理解它,因为只有这样的确证才不会因为进一步的学习而增强力量。但是,如果用“不可废止的确证”来定义“超可断言性”,就失去了赖特的主张,因为赖特认为它只是一种特殊的,或者可从普通辩护中建构出来的确证。正如Kavanvig所说:若将真理与一个拥有“不可废止的确证”(非理想化的)的东西等同起来,那么真理将非常少;若有的话,那么底线即为:“超可断言性”根本不能成为真谓词。[2]19
五、结 语
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之间的传统争论可以被重新塑造为:相关话语是否需要一个更稳健的真谓词。赖特本人是一位基于“超可断言性”概念的真谓词的拥护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陈述是超可断言性的,当且仅当它是或者能够是被确证的并且某种程度上是被确证的,从而它将经得起对其世系(pedigree)的任意严密审查,经得起对信息的任意广泛增量或其他形式的改进”[1]48。有了这一概念,赖特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真谓词,并且在许多争论中,这个真谓词将为反实在论者喜闻乐见,因为它不仅满足“真”的老生常谈,而且将以一种极小的方式来满足。但实际上,“超可断言性”并没有达成这样的满足。问题的核心是,如果支持赖特主张的反实在论者把“超可断言性”作为真谓词,即接受赖特提出的等值模式(ES),将面临诸多困境。同时也可以看到,无论是接受经典逻辑,还是接受直觉主义方向的逻辑修正,结果都不会让支持者感到高兴。这些支持者跟赖特一样,都将“超可断言性”看作真理模型。虽然还有其他逻辑上的修正可能会被尝试,并且涉及“……是超可断言的”的相关推理原则也可能会被探索,但是这些困境(至少目前)已经表明,有更多的理由怀疑“超可断言性”能够成为反实在论的适当真理候选者。
注释:
(1)该模式也被称为可知性原则。
(2)主要指以迈克尔·达米特为代表的反实在论者。
(3)赖特通过(A)来构建“断言概念”和“‘真概念”之间的联系。
(4)或满足(A)的其他代名词(ES)或(DS)。
(5)限于篇幅,本文不对赖特的“多元主义”真理论进一步拓展。
(6)(CTN)的证明过程:根据(SN),将“~P”代入(DS)中的“P”,得:“~P”为真?圮~P。再根据(DS)的逆否命题,得:~P?圮~(“P”为真)。最后根据等值规则,(CTN)得证。
(7)这里并不主张赖特论点的合理性,旨在说明他提出“超可断言性的”的理由。
(8)普特南提出的等值模式是:(PE)“P”为真 ?圮“P”在理想的认知条件下是有保证可断言的。
(9)为了证明该条件句,假设P。根据(L)得:P是可知的。根据(K)和MP规则得:P是超可断言的。最后,解除假设P,得:P→ P是超可断言的。
(10)为了证明该条件句,假设~(P是超可断言的)。根据(K)和MP规则得:~(P是可知的)。再根据(L)得:~P。将~P代入(L),则有:~P是可知的。将~P代入(K),再根据MP规则,得:~P是超可断言的。最后,解除假设,(Lemma)得证。
(11)根据赖特的构造:(CTNS)“~P”是超可断言的 ?圮 ~(“P”是超可断言的)。
(12)因为双重否定消去规则在直觉主义逻辑中失效。
(13)参见Williamson T.Intuitionism Disproved?[J].Analysis,1982:203-207。
(14)例子来自:Keith Lehrer & Thomas D. Paxson, Jr.Knowledge:Undefeated Justified True Belief[M]// George S.Pappas and Marshall Swain,eds.Essays on Knowledge and Justification.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146-154。
参考文献:
[1]Crispin Wright. Truth and Objectivity[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2]Jonathan L. Kavanvig. Truth and Superassertibility[J].Philosophical Studie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in the Analytic Tradition,1991,93(1):1-19.
[3]Crispin Wright. Realism Meaning and Truth[M].Oxford:Blackwell,1986.
[4]Deborah C. Smith. Superassertibility and the Equivalence Schema:A Dilemma for Wrights Antirealist.[J].Synthese,2007,157(1):129-139.
[5]Michael Dummett. Victors Error[J]. Analysis,2001,(1):1-2.
[6]Jonathan L. Kavanvig. The Knowability Paradox[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7]王晶.Fitch-悖论的达米特解决方案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1):52-59.
[8]Hilary Putnam. Reason,Truth and History[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9]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M].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吴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