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拍的现代文学作品:从五位中国作家说起
2021-09-22李欧梵
李欧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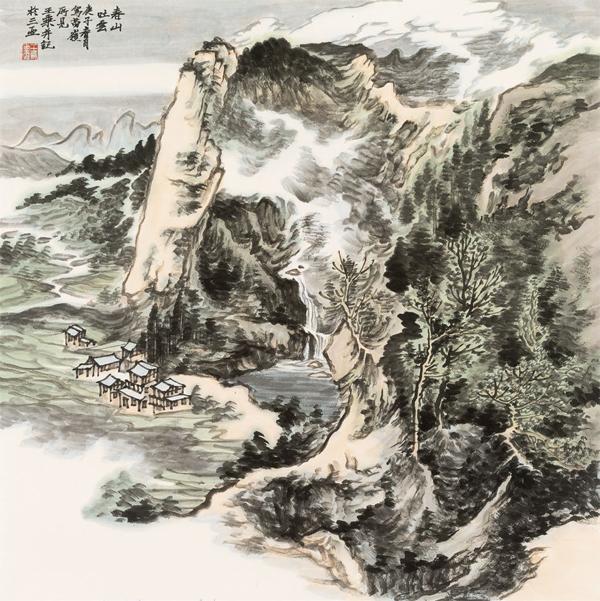
中国电影史上,改编自中外文学名著最早的影片可能是《西厢记》(1927)和《少奶奶的扇子》〔1928,源自英国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的剧本,洪深改编并导演〕,直到三十年代初期,才有改编自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1933),这些都是默片。
有声电影问世后,三十年代出现了几部备受学者研究和赞赏的经典影片,如《渔光曲》(1934)、《大路》(1934)、《桃李劫》(1934)、《马路天使》(1937)及《十字街头》(1937)等,但当中没有一部源自文学经典,当然有些影片的内容受到五四文学的影响,因为有些编剧家—如田汉和夏衍—来自新文学的左翼阵营,直接继承五四传统。然而,为什么这些名编剧家未能把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改编成第一流的经典影片?我认为原因相当吊诡:也许他们太尊重文学了,连写出来的电影剧本也非要像五四短篇小说一样。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导演—如程步高、蔡楚生、孙瑜、卜万苍等—并非文学出身,而是“匠人”背景,在文学“经典”的光环笼罩下,始终未能发挥其电影视觉所长,拍起片来像话剧一样。因此,我再次得到一个和西片相同的结论:一流的文学作品往往拍不出一流的影片;而一流的影片往往源自非一流的文学作品。
从电影中揣摩中国现代文学,实在事倍功半,吃力而不讨好,所以中外研究中国电影的学者虽然日渐增多,但研究中国文学和电影改编关系的专家却仍然凤毛麟角。我虽在此不自量力来尝试,也仅能提出一点浅见。且先举出几个实例来讨论,从几位不同作家作品谈起。
改编自鲁迅三篇小说的平庸影片
鲁迅的短篇小说,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但改编成电影的似乎不多,《祝福》(1956)、《阿Q正传》(1958)和《药》(1981)是硕果仅存的几个例子。《伤逝》也曾被搬上银幕,我以前看过,印象模糊。《狂人日记》近由作曲家郭文景编成歌剧,改名为《狼子村》,但似无电影版本。其他可以改编的如《孔乙己》《在酒楼上》《肥皂》《风波》《孤独者》等,至今好像还没有电影导演问津。
推其原因,我认为有三:第一是“光环”下的压力。第二个原因是鲁迅的小说大多是短篇,故事性不足,情节简单,却以人物、气氛和叙事技巧取胜,拍成一个多小时的影片必须“加料”,添补情节,甚至把原著中着墨不多的小人物夸大,如此则有失原著本来的面貌和精神(一般文学作品尚可随意改动,有光环的经典问题就大了)。第三个原因,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鲁迅小说的写作技巧早已超越五四以降的写实主义传统,而更带有现代主义的色彩,如心理描写、象征或表现主义的意象、语言中的嘲讽等,是一般写实电影的成规无法驾驭的,用写实的方法循规蹈矩地拍必会失败。可惜的是,偏偏所有鲁迅小说改编的影片都走这条路,大多都用绍兴的农村作背景,人物典型化,并时而作煽情式的描写,与鲁迅的冷峻和反讽笔法适得其反。
更吊诡的是,鲁迅的作品中其实含有不少视觉成分,《狂人日记》全部是由狂人的眼中看周围的现实世界,全是主观视野;《药》的电影形象更是呼之欲出,故事结尾坟前鲜花和乌鸦场面更像是电影镜头,整个故事的气氛都像是出自一部风格化的黑白片;《在酒楼上》的深冬气氛更可以从镜头中营造出来。
也许这是我的先入为主之见,所以个人对于改编成电影的鲁迅作品如《祝福》和《阿Q正传》的印象都不佳。《祝福》由名剧作家夏衍编剧,桑弧导演,白杨主演祥林嫂,演出颇为动人,但电影为什么失败呢?正因为它把原著中的知识分子叙述者的“我”取消了,整个故事变成了一种客观的写实叙事。
关于这一个删除叙述者的决定,夏衍提出他自己的理由:他把故事中的叙述者“我”误认为鲁迅自己,因此他说“鲁迅先生在影片里出场,反而会在真人真事与文艺作品的虚构之间造成混乱”。另一位名编剧家柯灵则看得较清楚:“这个‘我并不是小说中的人物,也并不完全是鲁迅”(见柯灵:《电影文学丛谈》,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页24);柯灵先生的后半句说得正中要害,但前半句是否也有理?我认为这个叙述者绝对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影片中可以作为一个角色出现,如费兹杰罗的小说和改编后的影片《伟大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74)。但叙述者也可以作为旁白的声音出现,杜鲁福的影片就曾屡见不鲜。
关于《祝福》的原著和影片的不同表现方法,柯灵认为电影中的叙述方法“完全是按照生活的规律,有顺序有层次地连续进行的……小说把实写和虚写参差运用,而虚写多于实写;电影剧本以人物的行动为主,虽然也有侧面交代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正面的描写,也就是实写”(《电影文学丛谈》,页30—31)。这种把故事连成一贯的实写手法,虽可使全片节奏流畅(但如今看来进展仍然太慢),但在形象上太过“正面”,到了片子最后,连镜头也拉到正面特写,只见祥林嫂在漫天风雪之中,衣衫褴褛,撑着拐杖,一步步走向前,仿佛要把她的“控诉”带到观众面前!也许当年观众看后感动,我却无动于衷,因为影片把原作中的反讽意味全部删除,成了一部通俗煽情片。
从剧情结构而言,夏衍和桑弧只能抓住写实叙事中的“通俗剧”成分,然而比起其他的经典影片—如1943年应云卫导演的《桃李劫》—仍然逊色一筹,因为它没有充分利用电影的影像功能,而單单把它当成一出实景舞台剧来处理。夏衍本来就是出身话剧,和不少三十年代影界左翼文人一样,而桑弧呢?在张爱玲编剧的影片(如《太太万岁》《人到中年》)中他时有佳作,但放在此片似乎被鲁迅的名声镇住了,不敢随意发挥。其实《祝福》中有不少场面都有电影“潜在”因素,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拍摄,如祥林嫂儿子被狼所食的镜头,大可拍成有图腾意义的蒙太奇效果。
乏善可陈失却“反史诗”意义
至于《阿Q正传》就更“情无可原”了,我认为此片从头到尾的写实,乏善可陈,创作人故意卖弄各种电影镜头,反而失去原著“反史诗”的反讽意义。
《阿Q正传》是鲁迅短篇小说中最长的一篇,但情节并不连贯,前半部以调侃的口气冷酷无情地描写阿Q这个小人物的衣食住行本能,甚至有点荒谬色彩,试问又怎能将之写实化?到了故事的下半部剧情才有进展,作家把阿Q放在当时的狂潮之中。但鲁迅小说中的“革命”,仍然是荒谬的,乱成一团,要处理这类既荒谬又杂乱的场面谈何容易?如果把意大利导演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请来中国做幕后指导,说不定会有点风格。其实更适合原著风格的是一部欧洲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捷克作家哈实克(Jaroslav Hasek)的《好兵帅克》(Good Soldier Schweik,1960),这部名著由一位捷克导演阿索云·安伯斯(Axel von Ambesser)拍成电影,成绩平平。然而这部小说比《阿Q正传》长得多,人物丰富,用一个弱智的“好兵”来讽刺第一次大战爆发前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社会,颇有卡夫卡式的荒谬意味。
相形之下,《阿Q正传》中的其他人物似嫌薄弱,鲁迅的用心在于讽刺当时的“国民性”,但只用一个没有灵魂和思考能力的农民阿Q,其他人物则仅是淡淡“素描”(sketch)而已,对话也不多,所以改编成电影时难度更大。影片为了弥补故事情节的不足,除了把实景放在绍兴附近小镇(因此拍出小桥流水的风光)外,也着意描写阿Q的幻想,特别是在土谷祠发梦的一段,显得很夸张,但到了最后阿Q被枪决的场面,原作中的蒙太奇效果—如围观的路人像狼一样的眼睛“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却未能发挥出来,这是故事的高潮,但放在片中却成了俗套。
近日偶然在内地买到《药》的电影版本,摄于1981年,是纪念鲁迅一百周年诞辰之作。八十年代初已是文艺界欣欣向荣的开始,但我观后觉得此版竟然“旧”得像三十年代的作品,无甚新意。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两位编剧家费尽脑汁,加添了不少次要情节,把故事中的一个次要人物—革命分子夏瑜夸大为英雄,又把夏瑜的老母的悲伤情节拖长,犹如祥林嫂再世,甚至连导演手法都处处在模仿《祝福》,只不过镜头转接稍微顺畅而已。
小说原来以老栓于太阳未出前的清晨,摸黑到砍头刑场去买血馒头为儿子小栓治肺病开始,气氛十足,但片中却把它放在结尾前的高潮,这是典型荷里活式写实片的规范,连改编鲁迅经典也不能免俗,实在令人慨叹编剧和导演想象力的局限。我还是耐心看下去,一直等到片子最后一景。果然不出所料,是郊野坟场,两个母亲为各自死去的儿子上坟祭祀。鲁迅在这个凄冷已极的场面中故意加上一个“曲笔”—在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作为支持五四运动的“呐喊”象征,然而这个较有积极意义的曲笔却被另一个意象—乌鸦—所抵消,最后瑜儿的母亲要乌鸦飞上坟头,让这位烈士显灵,但“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最后当两个母亲离去时才呀的一声大叫,“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这最后一段,是所有鲁迅读者早已耳熟能详的一段,当然研究者也为其象征意义争辩不休。在这部影片中,虽然表面上故事一切照搬,但镜头的处理完全没有任何创意,乌鸦镜头(不止一只乌鸦)瞬间即过,变成了无关紧要的背景之一,而花圈的镜头却再三出现,并以此终场,喻义十分明显,这就叫作“光明的尾巴”,原来的“曲笔”点缀也成了“正笔”和主旋律。在这种心态下拍成的鲁迅影片,又如何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也许,鲁迅小说中的思想性和象征性的文学语言太丰富了,本来就与电影的写实风格格格不入,仅仅用普通的写实手法来说一个故事,至多也不过差强人意。我认为鲁迅的作品必须用“不凡”的电影手法表现,目前似乎没有人做得到。
最出色的改编:老舍的《我这一辈子》
把中国现代文学搬上银幕的最成功作品之一,我认为是老舍的《我这一辈子》(石挥导演,1950)。这是一部中篇小说,用一种说书的方式,但却出自一个清末巡警的口中,有其主观的一致性,这是老舍小说所惯用的平民观点,而且描写的是北京(当时叫北平)中下阶层人民生活,这当然是老舍小说的特点,我觉得比他写知识分子(如《二马》)更为精彩。
《我这一辈子》的原著非但故事长短适宜,情节一波又一波地展开,而且由叙述者娓娓道来,说的是一口道地的北方话,所以由道地的北京人石挥自导自演,正好合适,几乎不作第二人想。演老舍的戏必须用纯正的北京话,还要加点土话,说起来才韵味十足,这一点石挥完全做到了。另一个要诀是表演技巧,当年的北京人说话有点像演戏,台词说得故意“油腔滑调”,但心地善良,在这个市井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坏人存在。这一切在影片中都发挥得淋漓尽致,让观众感到置身在一个极有人情味的世界,达到写实主义的真实效果。
老舍最著名的小说是《骆驼祥子》,1984年初曾拍成彩色片,凌子风导演,成绩不错,但我觉得还是没有五十年代拍摄的《我这一辈子》印象深刻,原因何在?
《骆》片领衔主演的张丰毅和斯琴高娃都是第一流的演员,北京话也说得字正腔圆;斯琴高娃演虎妞,堪称一绝,泼辣之中见人性;张丰毅演祥子,似乎太过憨直,但也称职。更难能可贵的是,老舍原著中不少俗话谚语—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都被收录于对话中,说出来很自然。可惜的是当年“老北平”的面貌在片中几乎荡然无存,仅凭几场雪景和夜景(显然受到制作条件的限制)是不够的。导演想避重就轻,从食物着手,并以此反映穷人的疾苦,如果和老舍笔下的北京市井生活—如天桥下的杂耍、天坛附近的夜市—相较的话,那种温馨又活泼的典型北平人“过日子”的生活世界,在片中还是呈现不出来。只有在这个乡土人情的世界中,祥子和虎妞的感情才有特殊意义。好在有这两个演员以演技支撑全局,而且改编后的故事也颇忠实于原著,没有变成大团圆结局(英文的第一个译本竟然让祥子和妓女小福子成婚)。
布景简陋,无法重现昔日北平风貌是全片的致命伤,这个缺隙并非本片所独有,后来陈凯歌拍的《霸王别姬》(1993)也有这个问题。也许,那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早已随风而逝,后人连“回味”也做不到了。为什么我喜欢读老舍的小说?就是因为当中有老北平的味道,友朋中“知其味”的只有胡金铨一人,可惜他已过世,只留下一本他仅有的学术著作《老舍传》。
老舍的另一部作品《茶馆》,不知是否曾被拍成电影,但至少有北京人民艺术学院演出的舞台剧纪录片,我多年前看过。“人艺”的演出精彩之至,全體演员的“北平味”十足,特别是第一幕所描写的前朝没落人物,举手投足都是戏。
《边城》中湘西乡土的想象怀旧
另一位备受学者和读者爱好的作家是沈从文,他的众多作品中似乎只有《边城》被搬上银幕;一次是香港出品的《翠翠》(1953),一次是大陆七十年代出品的《边城》,前者由林黛和严俊主演,后者的演员我记不得了。《翠翠》演技动人,但背景简陋,并非湖南实景;后者则恰好相反,背景(实地彩色摄影)颇佳,但演员则不出色。
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较老舍的老北平含义更深,名学者王德威曾在其英文专著《二十世纪中国写实小说》中特辟专章讨论沈从文小说中的“想象怀旧”,它不是真的怀旧,而是用艺术方式勾画出来的一个充满神话意味的湘西乡土;换言之,《边城》中的人物既真实也不真实。但如何体现内中的神话色彩?显然单靠实景或抒情是不够的,它需要其他视像与音乐来作烘托,例如故事中两兄弟互相比赛唱歌、向翠翠求婚的一节,就需要“音画对位”了,而深谙水性的哥哥怎会无端端地溺死?是否有神鬼在背后作祟〔犹如屈原的《九歌》或希腊史诗中的妖艳女子(sirens)〕?内中如何在银幕上表现出来?说到底仅用写实手法是不够的。可惜的是,中国现代电影中没有“诗电影”的传统,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小城之春》,但全片“读”来还像是一篇散文。
沈从文的小说世界向来兼具诗和散文的情调和含义,他把这两种不同的文体放在一个小说的架构之中,用一种他独有的文字语言表现了出来,和一般五四以降的乡土作家的风格不同,也和老舍的文体迥异。有时候沈的小说情节神秘兮兮的,而且人物有心理变态,有时又用层层相扣但又掩蔽的叙事手法,这些技巧都不容易用平铺直叙的普通写实片手法拍出来。当然,也许这又是我的偏见。
《边城》(1984)的导演也是凌子风,我对这位导演的背景毫无所知,但端看他的文艺手法,就知道他甚有涵养。然而,电影的艺术不仅在于“文学性”,更重要的是视觉形象和对于电影艺术本身的领悟。“文人”拍电影,不见得比“匠工”好,当然最好是兼二者于一身。
茅盾:五四电影改编最多的作家
据我的初步研究,五四的作家中作品改编成电影最多的是茅盾和巴金。
茅盾的作品被搬上银幕的更多,我看过的有《春蚕》(1933)、《林家铺子》(1959)、《虹》(粤语片,1960)和《腐蚀》(1950)等,桑弧的《子夜》还未看过,但以上述作品来说,成绩参差不齐。内中较受学者重视的是《春蚕》和《林家铺子》,前者虽是默片,却能表现出江南农村的小桥流水和养蚕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茅盾小说中自然主义的客观效果。然而默片的叙事手法—间或用上原著小说的部分文字—则显得笨拙。《林家铺子》是部有声片,摄于1959年,水华导演,也是夏衍编剧。电影学者陈力曾在其学术专著《电影:论中国影片与观象》中以颇大篇幅讨论此片,毁誉参半,他认为片中的所有角色(不论正反)都太“甜”,与茅盾原著精神不合,而故事中的真正主角—金钱—在片中只不过是一件临时搭配的物品而已;换言之,自然主义小说中对“物质”的重视反被片中的温情主义掩盖了(见该书,页262—263)。其他学者对此也论述甚详,此处不赘。
我个人认为另一部根据茅盾小说改编的影片《腐蚀》绝对是一部罕有的佳作,可惜我初看的复制DVD版残缺不全,最后结尾部分模糊不清,即便如此,我仍然被片中的视觉形象—特别是黑白对照的光影运用—镇住了,这种源自德国表现主义的手法,被导演黄佐临运用得恰到好处,而编剧不是别人,恰是柯灵,此片也足以证明他对电影艺术的看法:“电影所拥有的強大表现力,保证电影能够以极大的集中概括力量,来反映伟大的时代面貌。”(《电影文学丛谈》,页16)
妙的是《腐蚀》并非茅盾最好的代表作品,而且故事描写的是抗战时期汉口和重庆的特务工作,女主角本人就是一个自甘堕落的女特务。这一个题材,在茅盾作品中也罕见,是一种“反面教材”,作为一位左翼作家,茅盾在其作品中确有“矛盾”,一面歌颂抗日,一面却对一个女特务的感情生活特别关注,整个小说用她的日记形式以第一人称“我”的方式叙述,显然突出了这个女特务的“主体性”。我观后不禁想到最近李安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的名片《色·戒》,两片相隔半个世纪,但镜头运用颇有相似之处,甚至在片头都不约而同地用两条狼狗的特写开场!
张爱玲和茅盾的这两部原著,我认为皆有不足之处,张的角度太过超然,而茅盾则故意批判,但仍然掩饰不住女主角赵惠明(丹尼饰)的某种颓废吸引力,否则那位由石挥饰演的爱国青年怎会不由自拔地爱上了她?然而在中国电影的写实传统中,表现颓废并不容易,原著小说中并无色欲描写,对女主人公的身体和面部形象也着墨不多,唯电影镜头中反而表露无遗,饰演赵惠明的丹尼不是名女星,她的面部也不美—宽脸、尖颧骨、稍大的嘴,然而在黑白光影的调配下,她的颓废感特别突出,有心学者大可以此为题,写一篇类似罗兰·巴特大谈“嘉宝的脸”的美学论文。
德国的表现主义艺术产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威玛共和时期,我猜茅盾对之并不陌生,或在写作《腐蚀》时有所借用,但受到他的叙述文字所限(或者故意用温情主义的肉麻语言来表达女主人公的思绪),反而没有充分展示表现主义的颓废风格。此书写于四十年代初,不到十年,柯灵和黄佐临竟然把小说中的“潜在因素”发挥得淋漓尽致。我特别喜欢片中的几个阴暗场景:特务头目的办公室、重庆特务机关会议室和监狱,这类触目惊心的镜头,皆用明暗对照的灯光打造出来,凸显奸人的阴险奸诈个性,例如特务头目的面部特写,灯光从下面打上来,配以吸烟(片中每一个人都吸烟)的烟雾,造成一种“黑色电影”的效果和气氛,这种风格,在国片中尚属罕见。
巴金小说:粤语电影精品
茅盾的长篇小说《虹》也曾被搬上银幕,但拍的却是粤语片,李晨风导演,我在香港电影资料馆看过,觉得成绩尚可,但未能拍出小说的史诗式的架构;小说开头女主角梅行素过长江三峡的场面省略了,整个故事可以看作她—一名年轻知识分子—的感情和革命情绪成长过程的写照,然而影片中却无法表现,仅做到交代部分情节而已,比不上同一导演李晨风演绎的巴金小说《寒夜》(1955)。
无独有偶,《寒夜》的故事背景也是抗战时期的重庆,内中描写的是一个困居在这个山城的小知识分子的家庭。男女主人公本是一对有理想的恩爱夫妇,但同居后却发生婆媳冲突,妻子曾树生一怒离去,老实而软弱无能的丈夫汪文宣却在内外受罪的煎熬之下,害了肺病,在抗战胜利之日不支而死。
学者们大多认为《寒夜》是巴金生平所著最好的小说,既写实又不过于温情,而且对于战争时期重庆的日常生活细节有极为细致入微的描写。巴金自己事后回忆说:“《寒夜》中的几个人物都是虚构的。可是背景、事件等等却十分真实……整个故事就在我当时住的四周进行,在我住房的楼上,在这座大楼的大门口,在民国路和附近的几条街。人们躲警报、喝酒、吵架、生病……这一类的事每天都在发生。”这一种临场直接感,在小说中十分生动地呈现了出来,甚至小说第一章卷首有关汪文宣躲警报的场面都是巴金“在执笔前一两个小时中亲眼见到的”。(见巴金著《寒夜》,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版,2005,附录页291、292)
如何可以在事过境迁之后用电影去捕捉这种直接的临场感?这显然是原著小说对电影改编者的一大挑战,况且电影还是在香港拍摄,用粤语发音!李晨风似乎对五四文学情有独钟,甚至比内地导演更烈,尤其难得的是,他改编后的广东话并没有影响原著语言的完整。我甚至认为,李晨风改编的巴金作品—除《寒夜》外还有“激流三部曲”中的《春》—都比国语版好。我刚看过永华公司在四十年代拍的《家》,由卜万苍、徐欣夫、杨小仲及李萍倩四位导演执导,片长两个多小时,沉闷不堪,乏善可陈,比香港中联电影公司出产的《家》《春》《秋》差多了。
李晨风改编后的《寒夜》,十分尊重原著,只有在片尾最后一场—曾树生在坟前和婆婆与儿子重逢、化解怨仇的一节—妥协了,因为原著中并无这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只有树生到处找寻亡夫之墓不获,心中酸楚楚地思考是否应该离去,最后她自言自语地说:“我会有时间来决定的”,似乎有点像《乱世佳人》中史嘉莉(Scarlett)最后的那句独白“Tomorrow is another day”(明天又是另一天)的意味。但这种团圆式的结局也情有可原,可能是要照顾到当年香港观众的口味吧。
香港演员之可贵
更难能可贵的是,片中的日机轰炸镜头,剪自新闻片段,十分逼真,另片头的躲警报镜头也拍得认真,并不偷鸡摸狗,在当年(五十年代)香港的贫乏物质条件下,把炮弹落地、群众惊逃的场景处理得如此真实,并不容易。李晨风的场面调度手法不着痕迹,类似荷里活经典片的风格,在人物的刻画上更见功力。吴楚帆这位中联当家小生,在造型上十分适合演五四知识分子的角色,本片中他的演技自然而毫不造作,把巴金笔下的小人物的亲切感表现出来了。白燕演的汪太太树生也十分称职,但表现最佳的却是饰婆婆的黄曼梨,尖酸毒辣,出色之至,胜过演此类角色的所有国语片明星。为什么这几位粤语片明星能够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人物演得如此出类拔萃?我对粤语片的研究不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但至少我在这些佳片中看到一个不完全受国语话剧台词和表演方式影响的演绎传统,语言生活化,动作不夸张,正符合写实主义影片的要求。反观三十年代以降的內地电影,有时把普通话说得有南方口音,有时连坐立的姿势都像在演舞台剧。卜万苍等导演的《家》的致命伤正在于此,我实在看不下去。
粤语版的“激流三部曲”分由三位导演负责,但格调相当统一,节奏虽然颇为缓慢,但却能把原著中传统大家庭各代人物之间的烦琐复杂关系,表现得十分贴切。小说中的四川家庭,“封建气”浓,这原是巴金的本意,然而内中年轻一代的男女关系,却用一种五四的浪漫方式来描述,《家》中大哥觉新,夹在新旧之中,是主角,唯小说中他的恋情写得不够深入。然而,粤语片(吴回导演,1953)中饰演觉新的吴楚帆反而演得入木三分,他对表妹梅芬的感情十分被动,吞吞吐吐,吴楚帆演得恰如其分;张瑛饰的觉慧和紫罗莲饰女仆鸣凤的爱情,则是一种相当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放在小说中反而有点俗套。《家》毕竟是一部经典小说,为了使当年的读者对这个苦丫头同情,不惜让她自杀,我认为是有点煽情。然而在粤语片中,这段情却表现得很自然,展示出一个传统大家庭的世界,尽管少了一份狂热激进,却添加了不少人情味。
李晨风导演的第二部小说《春》(1953),主轴戏依然是较传统的大哥觉新,这一次表妹周蕙(白燕饰)对他暗恋,他竟懵然不知,但为时已晚,觉新的小儿子染病,他不敢请西医,竟使儿子白白夭折。这段戏不仅牵涉到家庭伦理,而且更表露出觉新在性格上的弱点,他的拖延和犹豫不决,如在另一个导演手下会变得无聊可鄙,但李晨风的平淡处理手法和吴楚帆的出色演技,却引起观众同情。
看完这三部影片,非但唤起我早已遗忘的巴金小说,而且令我对香港粤语片的传统刮目相看。也许,真正能够体会到五四新文学精神的人,不在于当年运动的中心—北京和上海,而在时空上都有距离的边缘—香港。
本辑责任编辑:练建安 林幼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