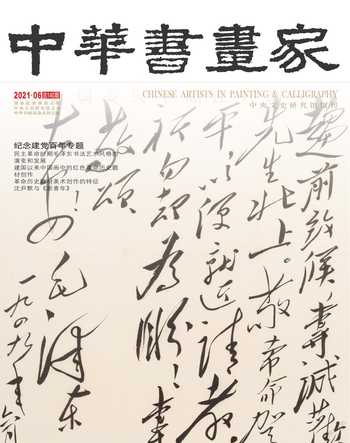沈尹默与《新青年》
2021-09-21王涛
王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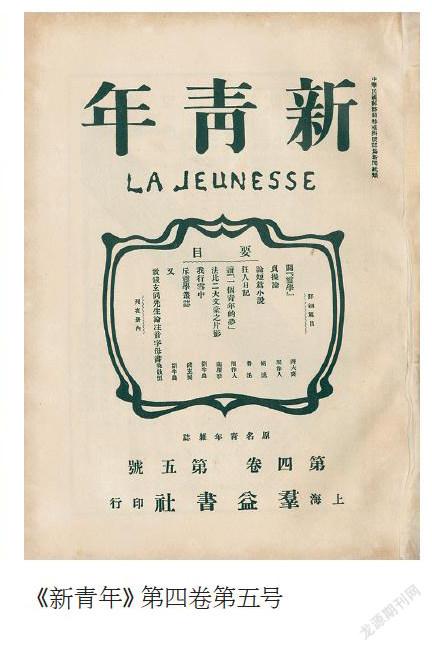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回望百年前的历史风云,体察对中国产生划时代影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感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逻辑,我们就走进了一本大写的书,走进一群大写的人。这群人中,有几位是从陕南汉阴出发,走进这段波澜壮阔历史深处的。
这本大写的书,是《新青年》。这群大写的人,就是从汉阴走出去的沈尹默昆仲以及《新青年》同人。
游学、交游与教学
沈尹默的祖父沈际清随左宗棠入陕为官,沈尹默的父亲沈祖颐历任陕西安康县知县,汉阴、砖坪、定远等厅抚民同知。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说:“我是浙江吴兴人,因父亲在陕西供职,我于1883年出生在陕西汉阴厅。”文中谈及“进北大之缘起”:“我是在1913年进北京大学教书的,到1929年离开,前后凡十六年。”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陕西选派50名本省籍学生到日本留学,沈尹默和三弟沈兼士因非陕籍,不能入选,乃自费和他们同往日本求学,受到同在日本留学的同乡许炳堃照顾。后“因家庭经济不宽裕,无力供应继续求学”,沈尹默在日本留学不满一年即归国。先居西安,后侍母移居吴兴、杭州,在杭州高等学校、幼级师范学堂、第一中学等校任教。此时,沈尹默与马幼渔、刘季平、柳亚子、章士钊、张宗祥、马一浮、苏曼殊、沈钧儒等人交往较多,常有诗词唱和。1907年,一代词宗朱孝臧见到沈尹默写的《风人松·瓶荷》词,极为赞赏,谓之“清隽欲绝”。
此时,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教书,他在同校教员刘三(季平)寓所见到沈尹默的诗,隔日即造访沈尹默。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日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作得很好,字其俗入骨”,沈尹默听后颇觉刺耳,转念又觉有理。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刺激,沈尹默从此发愤钻研书法,终成大家。因其弟沈兼士与马幼渔、周树人等都是章太炎先生门下弟子,沈尹默此时也就认识了周树人。
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沈尹默在而立之年被许炳堃推荐,到北京大学任教,始在预科教中国历史,次年开始教汉魏六朝诗文和唐诗,与随后到北大任教的其弟沈兼士和朱希祖(遏先)、马裕藻(幼渔)、钱玄同(中季)、黄侃(季刚)等章门弟子同聚北大。他们继承朴学传统,注重考据训诂,析事论理力求准确,以治学严谨著称。
作家茅盾(沈雁冰)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他在《我在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的三年》中说:“沈尹默教国文,没有讲义,他说,他只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览,在我们自己。他教我们读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韩非子的《显学》篇。他说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概况及其互相攻计之大要,读了这三篇就够了。他要我们课外精读这些子书。他又说《列子》是伪书,其中还有晋人的伪作,但《杨朱》篇却保存了早已失传的‘杨朱为我的学说。”“至于文学方面,沈老师教我们读魏文帝《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乃至近人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也教我们看看刘知几《史通》。”“沈老师说他自己也喜欢黄山谷的诗,但他不是江西诗派。”
显然,辛亥革命以后,北大的教学已不同于京师大学堂了。
“一校一刊”的结合与发力
北大初创,衙门积习深重,校长更迭如走马灯。沈尹默时在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兼课,医专校长汤尔和告诉沈尹默,当局欲请蔡元培来办北京大学,汤认为北大“内部乱糟糟,简直无从办起”,沈尹默则回答说:“如果蔡先生来办,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汤说:“那我明天就去和蔡先生讲,要他同意来办北大。”
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回忆:“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就在汤尔和与沈尹默谈话后大约第三天,尚未就任的蔡元培特意去译学馆(北大预科所在地)拜访了正在上课的沈尹默。这让沈尹默大吃一惊,颇觉意外。因为当时“社会上已轰传蔡元培将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已是中年以上的人了,阅历、世故应是很深”,却在赴任前来译学馆这个公开场所与其见面,并谈及汤尔和介绍,特来拜访。沈尹默十分感动:“心中就有个念头,北京大学应当办好,蔡先生负重名,我们应当帮助他把北大办好。”于是沈尹默在回访蔡元培校长的一次长谈中,建议他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二、成立评议会,教授治校;三、规定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并说自己的建议以成立评议会最为重要,“蔡先生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向当局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便是礼聘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此事说来真巧。有一天,沈尹默从琉璃厂经过,忽遇来北京为《新青年》组建新公司募股的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即要他暂时不要返沪,说过天去拜访。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回忆此事时写道:“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来北京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说,要他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吧。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诉独秀,他慨然应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当然,陈独秀来任北大文科学长,也与蔡元培曾是故交,且蔡元培得知陈独秀来京“即往访,与之订定”有关。
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谈到:“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蔡元培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说:“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但《新青年》搬到北京后,并未如陈独秀等人所愿,立即风行天下。
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月刊在上海问世。创办者陈独秀在第一卷第一号《敬告青年》中说:“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并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隱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之六义“明其是非,以供抉择”。《新青年》创办之初即鼓励新文学,提倡文学革命,认定“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在第二卷中公开明示“得当代名流支助”,并在此卷中发表了李大钊的《青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和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等经典之作,但刊发后在社会上反响不大,“即便能引起少数知识精英的参与,影响力主要还是局限在小众范围内”。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陈独秀、胡适等人虽口口声声倡导白话文新文学,但此前所撰写刊发的文章几乎全是文言或半文言文,这在读者看来岂不自相矛盾,更难以鲜活的形象激起读者思想和情感的强烈共鸣。已因销售不过千册赔本停刊过的《新青年》,再次“因销路不佳,于1917年8月出完第三卷后停刊”。
1917年夏天,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复辟。三年之中,两次复辟。在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旧思潮交锋,国内军阀混战,列强虎视眈眈,精英分子们痛感革新中国之艰巨复杂。民众的觉醒被视为首要,“语文一致”的白话文运动渐成知识界共识和时代洪流。蔡元培对北大的整顿改造,依靠陈独秀从文科开始大刀阔斧推进,广聘教员,整顿学风,创设学科,提倡学术,北大面貌为之一新,可谓以“兼容并包之主义”收鼎新革故之实效,变“官僚养成所”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和“完全人格”养成所。1917年11月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研究所建立,由沈兼士负责;同年12月国文门教授会成立,沈尹默当选为教授会主任。尤为重要的是,《新青年》此时迎来其实现辉煌价值的“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关键转向——由陈独秀一人主撰的“光杆司令部”,变成了力挺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大学数位文科教授轮流主编的“同人杂志”。
有了北大做大本营,又有北大同人加盟,《新青年》决定复刊,仍以月刊形式刊发,每卷六期,并正式成立编辑部。自第四卷第一号起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等“编辑部同人”每人负责一期,《新青年》“六大主编”由此得名。后因陶孟和、刘半农预备出国留学,李大钊、高一涵替其主编了第六卷各一期。《新青年》编辑部核心人物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同人皆为北京大学教授,虽然他们思想性格各异,但都以倡导新文化和救国图存为己任。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倾注心血不计报酬地承担《新青年》编辑组稿工作,同时也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
自此,《新青年》“才真正成为全国性的著名期刊,并且直接开启了以普及推广白话文写作为第一目标的新文化运动”。最早提出“文学改良”的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写道:“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两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一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名著。”
《新青年》“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也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校长蔡元培携手北大革新派师生为主体,多以白话文为《新青年》积极撰稿,内容涉及政治、道德、文学、科学、艺术、宗教、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创新。“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赞同科学和民主的,还有北大的教师高一涵、沈兼士、陈大齐、蒋梦麟、王星拱、朱希祖、杨昌济、顾孟余、刘文典、吴虞,复旦大学的易白沙等人,这些人都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文化熏陶,又是具有创见的学术界领袖人物,他们的文章不仅影响了北大的学子,也进而影响整个北京和全国的学界。”因此,北大师生校友的参与积极性迅速提升,《新青年》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日增。正是因为有了《新青年》同人编辑和主要作者为核心的革新营垒,在中国最高学府“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中,新文化运动走向高潮。
新诗与白话小说的出现
中国是诗的国度。新文化运动正是以新诗开其端,从而翻开了中国文化新的一页。
《新青年》以同人杂志复刊的首期,即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一号上,刊发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的白话新诗9首,这是后世公认的白话新诗第一次正式出现。胡适虽在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过《朋友》(即后世所称《两只蝴蝶》)等新诗,但他曾再三说自己“提倡有心,创造无力”,只是“尝试”而已。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適之外,有沈尹默、刘半农二氏,诗九首……”因此往往把四卷一号“三巨头”的诗作为中国新诗的始作。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是如此以为,而且特地作了这样的说明:“确切地说,白话诗当从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所载的诗歌算起。”
为倡导白话新诗,当时《新青年》的主要作者,“几乎都曾粉墨登场”,如李大钊、沈兼士、周作人,陈衡哲、陈独秀和周树人等,也“为刚刚诞生的新诗‘摇旗呐喊”,使得新诗坛时“红杏枝头春意闹”。但当时“真正诗才横溢且持之以恒地进行艺术探索的,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少得可怜”。周作人曾对此有过相当清醒地评价:“那时候做新诗的人实在不少,但据我看来,容我不客气地说,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一个是尹默,一个就是半农。”
沈尹默为《新青年》写的新诗,有《月夜》《鸽子》《人力车夫》等18首。从沈尹默新诗取材的内容看,“亲民”这一民本视角是其鲜明的导向,而且如胡适等人所言,沈尹默的新诗多从古乐府、旧词、曲里脱胎出来,在音韵、结构、意境、用字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这18首新诗里的《三弦》(原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1918年8月15日刊发)被公认为是新诗的代表作,曾被收入中学的国文课本。
蔡元培对沈尹默的新诗极为赞赏,他为沈尹默《秋明室诗稿》所作序称赞其诗:“独不失温柔敦厚之旨。宜乎君所为新体诗,亦复蕴偕有致,情文相生,与浅薄叫嚣者不可同日语也。”《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刊发的《月夜》,只有短短四行,却被誉为新诗史上“第一首散文诗而具有新诗美德”。废名在《谈新诗》中评价说:“与《月夜》同刊的那一些新诗,正是不能有这个散文诗的美德,乃是旧诗的余音。”沈尹默这首诗初看平淡无奇,细品则“其妙处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与沈尹默并称我国新诗开拓者的胡适,对沈尹默的新诗备极推崇。胡适在驳斥一些人把新诗视为洪水猛兽、贬得一无是处时,就列举沈尹默新诗《月夜》说:“几百年来哪有这样的好诗!”在笔者看来,这首诗似有更深的意象—可以看作是在那个特定时代,沈尹默用新诗为《新青年》同人和北大所做的一种形象宣言吧!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新青年》同人将和北大这颗“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新青年》力推的新思想新文化运动取得摧枯拉朽般的胜利,不是其第二、三卷,也不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新诗“三巨头”“粉墨登场”和第三号(1918年3月)刘半农与钱玄同演的“双簧戏”《答王敬轩书》,而是在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创造了“真文学”“活文学”和“真正国语文学”,不仅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更正式宣判了“假文学”“死文学”寿终正寝,成为“文学革命”的典范。这是鲁迅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也是作者周树人第一次起用鲁迅作笔名。它就像一声惊雷,石破天惊,横空出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成为重要标志。此后,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在《新青年》上使用“唐俟”“鲁迅”等笔名共发表54篇作品。鲁迅由此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关于《狂人日记》的诞生,鲁迅说自己因为:“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见过张勋复辟,……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就想在绍兴会馆抄古碑中“暗暗消去生命”。面对钱玄同“你可以做一点文章”的邀约,有了著名的“铁窗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答曰:“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此后接连几天,钱玄同都来拜访鲁迅,在钱玄同的催约下,鲁迅渐觉希望在于将来,确不可抹杀,便答应为《新青年》撰稿。
鲁迅思想深邃锐利、笔力沉雄犀利,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一致认可。他和弟弟周作人虽不在《新青年》同人之列,却能受邀讨论有关《新青年》重要事宜。陈独秀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对鲁迅小说表示赞赏:“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后来,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专门提到:“《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从鲁迅日记看,自《新青年》组建编辑部后,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人都在不停鼓动他创作小说、杂文及诗歌,而他们也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就这样,在一篇篇“遵命文学”中,鲁迅逐步走出了自我的“彷徨”,发出了时代的“呐喊”,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主将。
《新青年》虽从第四卷第一号始,已在刊载白话文和使用新式标点,但《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全面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排版,是从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开始的。“一代名刊”的这一做法,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报刊。《新青年》主推的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茶,促使政府颁布训令和批准有关议案,白话文和新式标点旋即在全国各类学校课本中开始普及,遂使白话文风行全国,代替文言文获得了语言的正统地位。语言和文字统一,则让更多的人通过阅读掌握文化,方便生活,使人民的思想得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解放。
而《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的轮值主编,正是沈尹默。除此期外,沈尹默还编辑了《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第六卷第六号。沈尹默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因为眼睛有病,且自付非所长”,因此轮到他编辑时,请玄同、半农帮忙代编,并说“编辑委员则仅付名义而已”。这固然不可全看作是谦辞,但也说明《新青年》同人虽是自愿组合编刊,但其相知相惜情谊深重。周树人、周作人兄弟虽不具体编刊,但二人撰稿甚多,且对办刊操心甚多,故也往往被看作《新青年》同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中称:“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和稍后进校担任国文系教授的吴虞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随后陈大齐、王星拱等一大批主力教授群体和更多的追求进步的学生群体加入作者队伍,《新青年》成为胡适所说的“代表和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杂志。“因为北京大学一批知名教授加盟,自第四卷第一号改为同人杂志,致力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发行量增至1.51.6万册。”
正因为《新青年》在中国当时思想文化界独领风骚,与其相呼应的《新潮》《每周评论》等报刊,以及后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雨丝社”等新文学社团迅速崛起,加之蔡元培校长所倡导的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歌谣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各类学术团体雨后春笋般出现,和与其相抗衡的国故派、学衡派、调和派、玄学派们,展开新旧思潮、新旧文化、新旧文学的激战。
中华新文明的创造
新文化运动在点燃五四运动之后,必将在中国酝酿出新的文明。
1919年5月4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传入北大,北京爆发“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五四运动,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这“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也被公认為是五四运动的司令部。五四运动以来,许多当事者和旁观者有大量的回忆,政学两界也大有论述。张耀杰在《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一书中所做的有关结论,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如果没有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高一酒、李大钊、周作人、周树人、刘文典、朱希祖、沈兼士、张慰慈、王星拱、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师生志同道合的风云际会,就不可能有《新青年》四至六卷的辉煌鼎盛,连同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波澜壮阔。随之而来的中国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乃至于政治史,也将会出现大不相同的另一种变局。”笔者比较认同这一观点。之所以说“比较认同”,是因为这一观点比较中肯,与蔡元培、陈独秀、毛泽东、梁漱溟等人的看法近似,但其对《新青年》同人出场先后及其影响的表述不甚精准明了,《新青年》的重要作者还有遗漏。
《新青年》深刻影响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深刻影响了《新青年》。在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李大钊就已针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为“马克思主义专号”,李大钊所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中国人系统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就在这一期和沈尹默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连续刊发。该著作在中国首次介绍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还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三大学说,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德文“共产主义的”译音),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有志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子成立收集和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著作的小组,促使马克思学说和俄国革命理论在中国得到更深入传播。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人,就是在这里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文献,坚定了自己的信仰,“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的。
作为《新青年》创办者和同人主编的核心、“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此时不仅接连写下数十篇檄文,痛斥强权政治,还决意采取“直接行动”。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亲自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陈独秀以此作为人生之信条。五四之后,《新青年》编辑部同人对办刊方向产生意见分歧。9月16日在被李大钊等友人营救出狱后,10月5日陈独秀约《新青年》同人在胡适家中开会:商定自第七卷第一号起,由陈独秀一人独自编辑《新青年》。
1920年2月,陈独秀面临再次被捕。经沈尹默昆仲设法通风报信脱险后,李大钊雇骡车陪伴掩护其返沪。高一涵后来曾著文称,就是在这路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此时陈李二人认定:国事势危,民不聊生,要“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途径,创造一种新生活”,唯有抱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牺牲精神,创建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创立新国家、创造新文明、创建新社会。
因陈独秀返沪,《新青年》自第七卷第四号(1920年3月)起,改在上海编辑出版。从第七卷第一号至第五号,《新青年》成为汇聚各种思潮的刊物,陈独秀在比较、鉴别中,由激进民主主义者成为坚定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第七卷第六号为“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8月陈独秀發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9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从第八卷第一号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新青年》学术文艺气息的淡化,引起胡适等部分同人不满,因此同人投稿大为减少。因遭查禁,《新青年》只得转入秘密编印,出版了第九卷一至五号。“《新青年》第九卷虽然政治色彩更为鲜明,但仍然刊登了北京同人的来稿,如胡适、周作人、刘半农、刘大白的诗歌,鲁迅的小说《故乡》。”1923年6月15日,在中共“三大”后,《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改为季刊出版。1924年12月被迫休刊。1925年4月后成为不定期刊出版,直至北伐战争爆发停刊。
《新青年》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至1926年7月25日出版“世界革命号”终刊,历时10年10个月零10天,共出版月刊9卷,出版季刊4期、不定期5号,共出63期。
一本杂志,一所大学,一批师生,唤醒了一个时代的青年,也唤醒了这个国家的人民,扭转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也扭转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命运。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新青年》同人编辑和五四运动前后亲历者之一,沈尹默先生曾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他还向毛泽东主席建议倡议成立了上海中国书法篆刻委员会并出任主任委员。他晚年在《回忆五四》的工笔小楷手迹中,留下这样的评语:“五四的确是旧思想与新思想,旧文化与新文化的分水岭。”并说五四运动使自己“以前像枯井似的心情,起了无限波澜”。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时,沈尹默先生又赋杂诗一首《五四运动四十年纪念日杂感》,阐述对当时一些人和事的看法:“会贤堂上闲风月,占断人间百十年。一旦赵家楼着火,星星火种便烧天。巧言惑众者谁子,庸妄名流误国家。不愿反帝反封建,却谈五鬼闹中华。当日青年色色新,打孔家店骂陈人。乌烟瘴气终须扫,但恨从来欠认真。无头学问昔曾嗤,厚古崇洋等失宜。可畏后生尤可爱,不应弟子不如师。成毁纷纭四十年,史编五四要增删。不是中国共产党,看谁重整好河山。”
今天看来,《新青年》开启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其最大历史功绩是再造了一个“青春中国”。一百年前,《新青年》所拥护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如同襁褓中的婴儿,如今已是英姿勃发;所孕育的中国共产党,已带领国人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所开启的新文化运动,被五四一辈人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如今正方兴未艾。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敬告青年》最后写道:“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克服一切困难和挑战,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现代化,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将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困境、国家困境、社会困境的彻底克服。
(作者单位:安康市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陈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