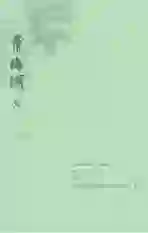我的目光注视下的二寺滩
2021-09-17牧子
不知從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父老乡亲把这片土地叫做“二寺滩”了。在我的记忆里,这里永远都生长着我的父辈们赖以维持生计的青稞和油菜,那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企盼收获的希望。
我隐约记得《祁连县志》里的记载,大致是在解放前或更早一些,这里曾坐落着两座佛教寺院,寺院的周围并不曾生长青稞和油菜,而是盛开在夏季灿烂阳光下的一片片淡蓝色的马莲花。一位曾经给这里最大的牧主做过牧役的老人,用豁齿的嘴巴一努一努地给我讲述这里的往昔时,我惊奇地发现,他的目光中并没有流露出多少苦难,布满皱纹的黝黑的脸上泛着一丝不屑的微笑,让我猜度了很长时间。
是的,父辈们从来都是把经历的苦难看得太轻,在他们饱经风霜的人生里,或许还隐藏着太多太多或美好或悲苦的记忆。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多少记忆?这些零零散散的记忆,能在你迷茫不知所措时,引领你走向豁然的去处么?
我总摆脱不了怀旧。对于这片土地,关于我所经历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不但不能消褪,反而一天天一年年清晰起来,禁不住我用怀想的目光注视她,如同注视我的母亲。
这片土地深植于祁连山南麓的腹地,在不太长的岁月里,我的父老乡亲们赋予的“二寺滩”的名字,成了一个牧区县的别称。正如张承志在《匈奴的谶歌》中所说的那样,这里“都有灿黄的油菜花,都有拦河断流的淘金客,都有黑黑的杉树林,鹅绿的夏牧场”。当时光推移到21世纪之初,灿黄的油菜花、黑黑的杉树林和鹅绿的夏牧场依然如故,只是那些脸色灰土般颠簸在手扶拖拉机里沿着沙土路西进的淘金客,犹如睡梦一般已遁入了历史。拦河断流的事会经常发生,不是为了淘得黄金,而是矗立在黑河上一座座水电站的前奏,如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赖以维持生计的青稞和油菜,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新城一样,历史在前进的历程中,也在不断地毁灭着自己,无法还原本真的面目。
我不敢妄言历史,而我和有关这片土地的一些记忆,必定会堂而皇之地走入历史的。忽然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个骇人的消息:北京肆虐的沙尘暴,与我注视的这片土地上的一条河流有关!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眼睛圆睁着,像死鱼般浑浊。张承志关注黑河,肯定比我早。他说:“弱水的上游,因为水清名叫黑河。它先制造了临泽张掖一双绿洲,又顺着走廊,北走救活了高台。居然意犹未尽,它出走廊进沙漠,在滋润了大片沙漠牧场之后,静静注入了居延海。就灌溉文明而言,它曾是一个完整和完美的流程。如果利用它的人,能把一切保留在一定限度上的话。”(张承志:《匈奴的谶歌》)
先不去管什么灌溉文明。利用这条河的人究竟有多少?整个祁连山腹地,整个河西走廊。从什么时候开始利用这条河?汉武帝在河西走廊楔入四郡时。那么,在汉武帝之前呢?不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走廊四郡”设置之前,生息在这里的匈奴、胡、羌,他们就是这黑河养大的古民族。现在,人们还在利用这条河,但能保留的究竟能保留到什么程度呢?焦渴的声音首先从北京传出,到几近干涸的居延海后,顺额尔济纳和黑河逆流而上,最终,这声音传到了我所在的这片土地。官员们开始使劲地搓着手掌来回踱步了,他们的每一次心跳都附和着这条河流的危机!
我所注视的这片土地出名了。
这里有中国最美丽的草原之一——祁连山草原,这里有瑰丽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民风民情,这里有源远流长的民族历史文化底蕴……所有这些与来自北京的一声惊呼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真正使这片土地出名的,是这条曾造就了祁连山文明或走廊灌溉文明的河流。我无心探究这条河流的往昔,而这条河流真的是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了。于是,一批又一批植树大军涌向黑河两岸开始种植树木,一批又一批农民工开始在沿河筑造堤坝,人们用法治的形式使在河滩地取沙的工场迅速消失,赶走了草场上过度啃食植被的羊群。
人们用自己认为有效的方式为一条河流正名!
然而,在这片土地的记忆深处,远不止一条黑河,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沉甸甸的历史。这段历史,使中国历史上有关西夏王朝神秘灭亡的谜团渐渐清晰起来。
位于县城以西4公里处的狼舌头,因上世纪60年代地勘人员见其形酷似狼舌头而得名。站在黑河岸边仰望那峻峭的石壁,谁能想到在它的顶端还残留着远古时代一座行宫的印记?据考古人员初步考证,这座行宫是西夏王朝末代皇帝李睨的避难之处!关于西夏王朝神秘消失的历史疑问,在我所注视的这片土地上初见端倪。公元1227年,66岁的成吉思汗亲自统率休整了19年的蒙古大军开始西征,政权势力曾一度延伸到青海湖以北祁连山一带的西夏王朝,在蒙古大军强大的攻势下土崩瓦解,西夏国第九代皇帝李睨不得不含泪西迁,在今天的狼舌头草草修筑行宫以避临头大难。但勇武的蒙古大军一路向西追讨,最终在黑河岸边的悬崖之上,使李睨命丧于蒙古刀下,他的爱妃额乃干被成吉思汗掠为己有。这位貌若天仙的王妃顷刻间将国恨家仇全部投向那位名声显赫的蒙古可汗,于同年七月的某日夜间趁行欢之机,用剪刀行刺,并掐捏成吉思汗的睾丸将其置于死地。雪恨的王妃如解除了魔咒般超然,微笑着自投黑河溺水而亡,从此,这条河流再也不叫弱水了,蒙古将士在悲痛欲绝时,把它称为“哈沱穆然”,意为污水或不洁净之水。
年轻的藏族学者索南多杰在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给这段历史找到了足以确信的印证。他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双眼充盈着不能自已的喜悦的光芒。
这段还有待于考证的历史,能否让史学家们旷日持久的困惑得以解开呢?历史在这片土地上一旦被得到确认,那么,注视这片土地的就不仅仅是我和索南多杰,这片土地将会被历史学的高尚光芒所照耀,并且名垂千秋!
我所注视的这片土地的确是母性的,她在浩浩岁月中历经了千年沧桑,最终孕育了各民族相互交融的多元民族文化,像我记忆里盛开在二寺滩灿烂阳光下的马莲花一样,一年比一年芬芳,一年比一年娇艳。
一位地质学专家曾对我谈到过,在4500万年前,这里曾是岛屿。那时候,伟大的亚欧大陆还没有形成。随着地质年代跨越式的推移,岛屿开始隆升,浩渺的大海被渐渐隆起的山脉向北推挤,直至挤入地球的最北端。当这些海水在北冰洋停留并最终影响了北半球的气候时,这片土地已经成为了这个星球上海拔最高的地方。那时候,神秘的尼安德特人开始踩着这块新隆起的大陆,从欧洲向东方或南方寻找他们自己最终的历史出口。很难想象,那些尼安德特人在这片河流纵横、峡谷遍布、雪峰林立、乱石嶙峋的新大陆上,是怎样穿越历史的。在祁连县城以南高高耸立的牛心山,就是那岁月变迁中遗留下来的一个巨大的冰斗,在冰川向四周滑动并最后以融河的形式注入大洋的过程中,给这片土地留下的除了至今仍高高耸立的山峰外,还有遍布于辽阔草原上的无数大小不一的河流故道。
4500萬年,对于我们来说的确太过遥远了。那么,再离我们近一些的有关人群迁徙的历程又会是怎样的呢?
贫苦的藏族老牧人噶·仲巴多杰夫妇世代居住在青南果洛地方,那里矗立着晶莹剔透的阿尼玛卿雪山。他们和所有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一样,把全部的精神意志都寄托给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阿尼玛卿神山。约公元723年,老夫妇唯一的聪慧的女儿长大成人,在梦中见到了阿尼玛卿山神后神奇地怀孕,并生下了一个男孩。男孩降生后,其额头上隐约印有藏文字母“阿”字,老夫妇喜出望外,为男孩取名阿柔完得智华昂秀(意为看见藏文字母“阿”)。智华昂秀长大后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但他的目光中透露着睿智的光芒,且力大无比,性情勇猛。优秀的阿柔完得智华昂秀博得了人们的赞赏,被尊崇为阿尼玛卿山神的儿子。神的儿子长大后做了部落首领,他的九个儿子长大后又形成了九个部落,再加上阿柔德芒和阿柔芒拉木部落,逐渐形成了庞大强盛的阿柔藏族部落。纵观历史,任何集团无论强大与否,都无法摆脱“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周期律。清道光年间,强大的阿柔部落出现内讧,并开始分化。各自为阵的部落千户因为在茫茫草原上承受着其他部落的劫掠而到处奔命,其中的一部分为了活命,不得不离开神山光芒笼罩下的原属草地而北迁,终于在岁月不断的淘洗中定居于祁连山腹地的阿柔贡白加隆地方。这次长达百年之久的大规模迁徙,给我所注视的这片土地带来的不仅仅是部落数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这次迁徙最终改变了这片土地上固有的文化形态。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就是曾因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讲经而奠定基础,后又由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允准建立的法名“具喜宏法洲”的阿柔大寺,也随这次大规模的迁徙而坐落在这片土地上。这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在当时就有僧侣150多人,其中活佛就有16人。由于大迁徙经历了百余年,这座寺院便不得不以帐房寺院的面目存在于世。如今,这座寺院在阿柔乡所在地以金色琉璃建筑矗立在绿草如茵的贡白加隆山下,成为这里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终日桑烟袅袅,信徒络绎不绝。而那顶硕大无比的帐房经堂,已在岁月无情的磨砺之下变得破烂不堪,静静地蜷卧在阿柔大寺金色的屋脊之下。在大经堂后侧,有一顶复制的黑牛毛帐房依然站立着,似乎在炫耀它曾经的辉煌。然而,这顶复制品,现在只供游人参观而别无用途。
让我们再把目光收缩一下,让它落于更近的历史断面上。
这片土地被尧熬尔人称为鄂金尼,这里有他们日思夜念的苏日托莱、八字墩川、乃曼额尔德尼以及夏日告图,这些如同他们生命般的地名,会时常萦绕在他们的梦中。
尧熬尔人用持续16年的时间(公元1512年至1528年),从西域阿尔金山一带向东迁移。他们穿越姆塔格沙漠,翻越阿尔金斯山,进入祁连山,然后东渡大哈勒腾河、党河、疏勒河、黑河,在完成了1500公里以上的艰难行程后,最终定居于我所注视的这片土地。这些尧熬尔人为什么要东迁呢?据尧熬尔传唱的民歌《尧熬尔来自西至哈志》中的内容,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性的判定。那时候,伊斯兰教东进,迫使撒里畏吾尔信奉伊斯兰教,而撒里畏吾尔宁死不肯抛弃自己的信仰,终于导致了战争,再加上各部落酋长和元裔割据势力的相互残杀劫掠,明王朝又因内外交困自顾不暇,置撒里畏吾尔于不顾。长期的战乱致使“狂风卷走牲畜,沙山吞没帐房,河道干涸,草原荒芜”,撒里畏吾尔处于生死交困的边缘。穷则思变,撒里畏吾尔的一支即鄂金尼部落便率先东迁,最终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随之而来的一座叫古佛寺(又称黄番寺、夹道寺、达纳贡巴、黄藏寺)的寺院,为我所注视的这片土地最终以“二寺滩”的别名烙入我的灵魂留下了历史性的伏笔。
那么,这些尧熬尔人呢?我们不妨再收缩目光,来看看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断面。
1959年,为了解决旷日持久的甘青两省草原边界纠纷,国家不得不调整行政界线。尧熬尔人在三九寒天冒着刺骨的高原寒风和漫天飞舞的大雪,赶着他们的牛羊,再次举家东迁,到他们用生命般的八字墩、托勒、友爱等居住地换来的甘肃省肃南县皇城、北滩一带定居生活。尧熬尔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不亚于热爱他们的父母。在他们流传至今的歌谣中,还有这样如泣如诉的艰辛和眷恋:
哎哟——
乃曼额尔德尼你还健在,而我就要离开你了,
我不是永远离开啊,我愿回头再来看望你;
鄂金尼草原你还健在,而我就要离开你了,
我不是永远离开啊,我愿回头再来看望你;
黑水河你还健在,而我就要离开你了,
我不是永远离开啊,我愿回头再来看望你。
哎哟——
难行着难行啊我难行,三九寒天里渡黑河,
要不是拽住牛尾巴,黑河水就会冲走我;
难行着难行啊我难行,大雪里翻越扁都口,
要不是羊皮大衣牛皮鞋,扁都口达坂冻死我;
难行着难行啊我难行,大马营滩上狼群围,
要不是点燃麦草堆,狼群就把我吃掉了。
……
尧熬尔人的两次东迁,无不充满着战乱、悲苦、艰辛和无奈。直至共和国成立后,他们才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意志实现了安定和自由。那位带着苏北淮安口音的共和国缔造者,将他对尧熬尔人富裕稳固的愿望寄托给了未来,为他们取名“裕固族”。我的尧熬尔朋友铁穆尔,每次要到这里来搜集民族历史资料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在电话里对我说:“我就要回去了!”
在同一个历史断面上,还有一次人口迁徙如这片土地上的伤痛一般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1958年,国家决定在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兴建国防核工业基地——国营221厂,达玉藏族部落1700余户牧民,为国家的国防建设甘愿牺牲自己世代居住的家园。其中,461户牧民共2183人迁往位于祁连西部最偏远的托勒(即今央隆乡)并入当时的国营牧场——托勒牧场。
达玉部落的这次搬迁是何等的艰辛!原定三年的搬迁期限突然变成了一年,后来又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完成搬迁任务。英雄的达玉人无条件地响应了国家号召,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带了必需的生活用品,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帐房都留在了原地,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园,开始了艰难的迁移。他们的搬迁是徒步进行的,在军事化管理之下,他们涉过甘子河,翻越外力哈达山口,进入默勒草原,可他们还要走,这片草原仍然不属于他们。时值初冬,空气中除了寒冷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了。无垠的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因为拾不到牛粪,他们为了吃到一口热饭,只好把仅有的木箱、奶桶、帐房杆子等一切能用来烧火的东西砸毁以充当柴火。好多人手脚都冻坏了,他们患上了雪盲症,老弱病残由于寒冷和饥饿死在了迁移的途中。在他们走过的雪地上,衣物用具抛弃了一路。
我的目光伴随着我所注视的二寺滩逐渐成熟起来。在这个连绵着无尽细雨的不太炎热的夏季,我看到了我的二寺滩像巨人般站立着,他的每一条河流、每一座雪山、每一片森林,都在岁月的变迁中保留着原初的形态,并且将继续创造着历史。我知道,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创造的新的历史,再也不会有艰涩,再也不会有悲苦,它将以新生的灵魂迎接无数岁月光明的洗礼。
作者简介:牧子,时常写作,出版文学作品集多部,系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