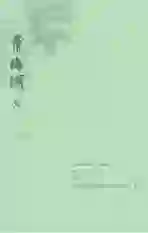祁连山下的霍去病
2021-09-17张锐强
立 功
总有一座山推动名将史册流芳,比如八公山之于谢玄;总有一位名将见证大山的辉煌伟岸,比如韩信之于太行。元狩六年(前117年),24岁的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辞世,汉武帝下令将他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形状,名将与名山彼此成全的佳话再度绑定于史册,后代传颂不衰。
人人都知道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还有几千年的武化。文化与武化互为表里。文化如同春雨,润物无声,缓慢悠长;武化如同烈火,瞬间灿烂,但很快就会熄灭。中国文化与武化其实是一体两面之事。文化冲突到极致会演变成武化,而武化结束之后漫长的伤口愈合过程,亦即隐痛期,又复原为文化。武化隐而文化显。文化长而武化短。文化武化发展多少年,民族交融也就有多少年。这个交融既有和平融合,也有厮杀血拼。而中原华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彼此武化或者试图武化数千年,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真正依靠自身力量获得完胜、将对手消灭,其实只有一次,那就是汉灭匈奴。唐灭突厥看似辉煌,但实际上靠的并非大唐的名将或者武力,而是突厥自身的内乱与衰落。与其说李世民灭了突厥,不如说他派兵收拾了突厥衰落分裂后的乱局。吐谷浑的覆灭也与之类似。
世上没有白来的捷报。胜利总是需要付出代价。这代价并非仅仅是无定河边的枯骨。汉武帝接手的是文景之治后的充盈国库,钱太多用不过来,穿铜钱的绳子纷纷朽烂。而他还没有灭掉匈奴,国库已经入不敷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车船使用税和财产税随即应运而生,当时叫算缗。起初算缗只是对在籍商人收取运输车税,十年后扩大为对全体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全部财产征收,不仅仅限于车辆。盐、铁和酒的国家垄断政策,也在此间确定。除此之外,他还发行了超大额的货币皮币。目的只有一个字,钱。或者两个字,军费。
隋炀帝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导致灭国,但时至今日运河依旧造福国人;汉武帝穷兵黩武,将富得流油的国库打空,但开疆拓土的功绩不小。事实上千百年來,中国都在享受他身负骂名换来的红利:秦统一六国后的疆域其实依旧局促。西部边境大体是从银川、兰州、成都下拉到昆明。整个国家的形状像一只手掌。只有单手的是残疾人。健全人都需要两只手。汉武帝在西北又安了一只手掌,地图连起来看,像个细腰葫芦。
黄河以西的甘肃西北直到新疆地区,合黎山(传说为古昆仑山,又名人祖山、要涂山。最高峰为大青山)与祁连山一北一南围出一条狭长的平原,可生活,可交通,所谓河西走廊,也就是这个葫芦的细腰。或者说,是条粗大的动脉血管,甚至脐带。但这只是大汉的感受。对于匈奴而言,则是其威胁中原的右臂:河西本是大月氏的栖息地。匈奴将大月氏赶走后,由浑邪王统治酒泉及其周围地区,休屠王统治武威及周围地区,控制西域各国,南与羌人相接,从西面威胁汉朝。
斩断匈奴右臂、连通大汉脐带的决策者是汉武帝刘彻,执行者是谁呢?19岁的冠军侯、骠骑将军霍去病。那是元狩二年(前121年)的事情。两年前的骠姚校尉虽然顺利建功封侯,但那时他在舅舅卫青帐下听令,所部不过八百人。而今不同,他已是骠骑将军,独立成军,独立指挥,远征万里,出师河西。19岁,今天在诸多父母眼中还是确定无疑的孩子,但两千年前的霍去病已经指挥一万士卒两万战马,麾下不知有多少胡子拉碴的宿将老兵。
当年三月,自信满满的霍去病从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出发,一人二马,翻越乌戾山(当为今甘肃白银市平川区东南的崛吴山),渡过黄河,将碰到的匈奴遫濮王斩首后,迅速渡过狐奴水(石羊河,亦称谷水。古休屠泽水系支流。河西走廊内流水系的第三大河)西进,六天转战千余里,踏破匈奴五王国。
对这些小的部落王国,霍去病既不恋战,也不像惯常那样掠夺财产子民作为战利品。并不是不需要以此报功,而是他有更加远大的目标,或曰主要目标:浑邪王与休屠王。
霍去病轻装前进,进展神速,越过焉支山(大黄山,甘肃山丹县东南)后,在皋兰山(张掖附近的合黎山,非兰州附近的皋兰山)捕捉到匈奴主力,与之展开决战。汉军虽然孤军深入,但彪悍之气不减,短兵相接,连战连捷,斩匈奴折兰王、卢侯王。浑邪王败走,其子与相国、都尉被俘。休屠部祭天的金人也被缴获。
这是一记成功的左勾拳。当年夏天,霍去病又使出右勾拳。原计划公孙敖要配合行动,但他迷失了方向,未能如期会合,霍去病毅然决定独自出征。他采用大纵深外线迂回的方式,由朔方郡(治窳浑,今内蒙古磴口县保尔浩特古城子)出发,渡过黄河后向北越过贺兰山,穿越浩瀚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抵达居延海。“居延”是匈奴语的音译,意思是“隐幽”。这是史籍中首次出现“居延”这个字眼,由此启发“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这样的名诗。当时从这里到张掖,可以行船。霍去病由此挥师向南,沿着弱水河谷推进。按照《山海经》的说法,“昆仑之北有水,其力不能胜芥,故名弱水”。此后“弱水”也泛指遥远险恶、汪洋浩荡的江水河流,此处的弱水则是黑河下游、金塔县到额济纳旗之间的别称,也就是额济纳河。黑河发源于祁连山,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沿岸水草丰茂,骑兵行军尤其方便。
抵达小月氏(未西徙的月氏人,今甘肃酒泉一带)后,霍去病再由西北转向东南,从黑河上游地区向浑邪王、休屠王的侧背发起猛攻。两次攻击路线正好形成一个圆形闭环,完全出乎匈奴人的意料。他们仓促应战,被杀得大败。三万多人被歼,五个王、五个王母被俘,另外还有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浑邪王、休屠王率残军逃走。
这两次大败让匈奴伊稚斜单于大为愤怒,有意追究浑邪王和休屠王的领导责任。怎么追究?杀头。二王为保性命,决定归降。此时他们手下尚有部众四万余人,号称十万。彼此攻杀多年,有血海深仇,匆促之间自然难以建立足够的互信。汉武帝怀疑他们有诈,随即派霍去病率领一万精锐骑兵前往接应。说是接应,和战却在转瞬之间,由霍去病临机决断。
已是秋高马肥的时节,霍去病挥师疾进。果然,受降过程并不顺利。汉军未到河西,休屠王突然变卦。浑邪王将他杀掉,收编了他的部众,但人心不稳。霍去病渡过黄河后,全军排列成威严的战斗队形前进,浑邪王也列阵迎候。其部下一些小王裨将见汉军阵容严整,心存疑惧,企图逃走,引起骚动。霍去病当机立断,立即驰入匈奴阵中与浑邪王接上头,然后指挥部队将想要逃跑的八千多人全部擒杀。局面稳定下来后,他先遣使者护送浑邪王赶到长安面君,自己则指挥部队,监视押送匈奴余众缓缓向内地行进。匈奴部众都有大量的牛羊牲畜,行进的速度快不起来。
归降的浑邪王被封为万户侯,部众分别安置在秦长城以南、黄河以北陇西、北地(治马领,今甘肃庆阳西北)、朔方等五郡,所谓五属国。作为政权的匈奴虽然最终被消灭,匈奴人的民族文化基因却成功地与汉族融和。今天的北方人跟南方人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区别,就是因为汉唐时期北方长期接纳归附的少数民族。彼此血脉交融,禀赋必有不同。
作战的第一要义并非占领地盘,而是消灭敌人。匈奴人的势力全去,河西走廊为之一空。汉武帝随即下令移民实边,在二王的地盘上相继建立武威、酒泉、张掖和敦煌四郡,而陇西、北地、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的边防部队则顺势减半。这是华夏政权首次控制河西走廊。从此以后,祁连山成为汉唐的界山,烘托丝绸之路、联通西域。
骑 射
上面这些过程基本抄自史书。尽管史书明确记载的东西不容发挥,却依旧难掩道德瑕疵。我为什么要拉拉杂杂这么多?因为必须引出这些问题:霍去病孤军深入、长途奔袭,为什么能顺利建功?匈奴人就是豆腐渣吗,那么好打?为什么年纪轻轻、素无行伍经验的霍去病,还有出身骑奴的卫青如此神勇?李广的资历比他们老、出身比他们高、名气比他们大、经验比他们多,灭掉匈奴的为什么不是他?
答案颇有些黑色幽默的意思:匈奴人并不好打。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卫青、霍去病采取了全新的战术,他们不适应。为什么灭掉匈奴的不是李广?因为他比卫、霍更精于骑马射箭,单兵素质更强。
李广的骑射技艺用炉火纯青来形容都有些俗、都嫌不够。论射箭,他可以跟匈奴箭法最准的骑士、所谓“射雕者”单挑,并在一对多的情况下,将之一一击败,射死或者俘虏;论骑马,他被俘后能突然跳上敌人的战马、将原主推开并且夺下他的弓箭,成功逃亡。具体事例可以翻看史书,《史记》对此有生动详尽的描述。反观卫青、霍去病,则没有这样的单兵素质。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因为李广是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人,自幼便生活在西北少数民族旁边,难免流风所及。关西出将,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传统一直被历史所承认尊重。直到明末,崇祯九年(1636年)还出台过这样的规定:鉴于时局危难,朝廷规定县试、乡试的第二、三场加入武经和书算内容。放榜之后,检试骑射,一共十箭。南方人必须两箭中靶,对西北人要求更高,得三箭、否则就处罚提学官。
当时人们怎么作战呢?估计不少人还是这样的印象:双方主将拍马向前,彼此通报姓名,然后挥舞兵器交战。等击败或者杀死敌手,再率领全军冲锋,锁定胜局。
这当然格外虚诞。而要为这种普遍的虚妄印象承担历史责任的,不止是民间的说书先生,还有包括司马迁、司马光在内的官方史家。他们身为文人,未经战阵,不懂甚至轻视军事,遗漏了无数的核心细节。正如费正清等海外汉学家在《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中所说的:“儒生掌握了军事历史的书写,将军事史降低到寓言和传奇的层次。”
作战是大规模的群体行为。为提高效率、发挥优势、便于指挥,只能结阵。彼此都排好阵型。最终由一个阵势对另外一个阵势,而非数千人对数千人。就像足球比赛,是一支队伍对另一支队伍,不是十一人对另外十一人。阵势摆好,进攻者开始攻击,所谓“冲锋”;攻入其阵势、所谓“陷阵”后,随即开始血拼。等对方阵型松动、战败后撤,再趁势掩杀。兵败如山倒,形容的便是阵型松动后撤时的情形。一旦打到那个时刻,局面便很难挽回。
卫青、霍去病的时代马镫尚未发明。中原王朝的骑兵因而长期担任打酱油的角色。战国时代最伟大的兵书《六韬》,给骑兵的定位不过是“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利用快速机动的优势,执行侦察任务,或者追击败军、截断补给线,“战则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一人一马的骑兵组合,作战效能甚至还不如一个步兵。为什么?骑兵还得照顾马匹。故而在卫青、霍去病之前,中原王朝一直以步兵为主。偶有骑兵,抵达战场后也要下马步战。
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特别难对付?因为他们在马上来去如风。具体到作战环节,面对中原步兵摆成的阵势,他们从不下马冲锋肉搏,而靠出色的箭法远距离杀伤:分波次骑马冲来射击,射完转身回去,换下一波。等步兵的阵势松动溃退,再持刀剑等近战兵器追击。此时已经不是公平的作战,而是单方面的屠杀。除了弓弩的远距离杀伤,中原王朝的步兵拿他们毫无办法。即便想追赶厮杀,也力不从心。而他们作战还有个特点,那就是“利则进、不利则退”。能占便宜时一哄而上视为勇敢,无便宜可占时一哄而散却不觉得耻辱,而视为天经地义。武化中间的文化决定性,由此可见一斑。
这样的对手肯定令中原王朝头疼。此前汉军并非没有名将。李广的名气一直震动匈奴。但一个人的长处往往也会成为其局限。具体到李广,他的骑射技艺超群,因而一直在努力发挥,不必也从来不会想到另辟蹊径。从史书的记载看,他几乎一直在利用骑射技艺,跟匈奴人正面作战硬碰硬。这应该也是他一直没有足够的战果、无法封侯的具体原因。毕竟他能做到,他的部下却不可能全部做到。而卫青与霍去病骑射技艺平常,顶多不过中人。既没有这样的光环,也就不会形成类似的阴影。他们之所以能在汉武帝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屡立战功,原因在于他们推行了两项创新:大规模使用骑兵;让骑兵集团冲锋。
创 新
史书有正面记载,卫、霍二人的赫赫战功,是骑兵集团冲锋战术的成果吗?当然没有。因相关史书几乎从不直接描述战争场面。大约是文人史官觉得这些细节无足轻重。但仔细爬梳史料,还是能找到足够的旁证。
比方元朔五年(前124年)春,卫青指挥汉军对匈奴发起的第四次攻击。他亲率三万骑兵,乘夜绕过外围警戒,将右贤王部包围。暗夜作战,当然无法远距离放箭。汉军肯定是手持近战兵器突然杀到,跟无法施行追逐骑射的匈奴人貼身缠斗,最终大胜。卫青由此跻身大将军行列。
如果说这还完全是推理的话,那么祁连山下的霍去病则能提供更加明确的证据。三年之后的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军对匈奴发起第七次攻击,亦即河西之战的第一阶段。这次作战的细节史书上依旧没有披露,但褒奖诏书是这样写的:
“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
“合短兵”的意思,就是贴身肉搏、白刃格斗。“杀”“斩”“诛”这三个动词也表明,使用的武器不是弓箭,而是短兵器。毫无疑问,其战术必定是冲锋陷阵、彼此肉搏。
战术的革新必然会导致兵器的改变。在此之前,骑兵的常用装备是弓箭与刀剑等短兵器。前者用于远程攻击,后者用于近身搏杀。卫青霍去病指挥的骑兵集团冲锋,很可能使用的还是短兵器,但最终必须改装步兵冲锋时的标准配置长戟。东汉的画像石中,已有不少持长戟战弓箭的内容。山东孙家村画像石上,持长戟者身穿中原骑兵常用的铠甲,从背后刺中戴着草原民族常见的尖顶帽的弓箭手;山东孝堂山画像石上的战斗场面更为宏大,也更加直观地表明,是中原骑兵利用长戟跟游牧民族作战,因其中有“胡王”字样的旁注。
艺术创造从来都不是凭空想象,都有现实的生活背景。可以肯定,东汉时代,骑兵持长戟冲锋战术已经被汉军广泛采用。而其开创者,只能是前代名将卫青与霍去病。
这个创新令匈奴人崩溃。他们原先的优势彻底消失。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愿或者不敢正面接战。李广的经历可谓旁证。
河西之战的第二阶段,霍去病当年夏天再度出兵时,原计划除了公孙敖随行,卫尉张骞和郎中令李广也同时受命出击右北平(治平冈,今辽宁凌源西南),牵制左贤王部。李广率领四千骑兵从右北平出塞后,很久未能等到张骞的一万人马,却跟左贤王的四万骑兵碰了头。兵力一比十,将士们心里不免打鼓。为安定军心,李广命令自己的儿子、校尉李敢率军冲击敌阵。李敢随即带领几十名骑兵“直贯敌骑,出其左右而还”。
几十名骑兵就可以顺利地冲破匈奴的阵势,真的像李敢对父亲的高声汇报那样,“胡虏易与尔”,匈奴人很好对付吗?当然不是。根本原因在于,匈奴骑兵不会或者不愿正面接战,无论发起冲锋还是接受敌军的冲锋,你冲锋,我就闪开。
在没有马镫的时代,骑兵冲锋肉搏几乎就是自杀式攻击。因为巨大的反作用力随时可能将你推下马去,葬身马蹄的海洋。中原王朝力行专制,帝王有生杀予夺大权,但北方游牧民族从来都不是。他们的可汗也好单于也罢,都没有这样的威严与权力,逼迫部下改用这样的作战方式。这依旧是文化在武化期间的决定性因素。
祁连山是匈奴人的称呼。汉人更习惯于称为南山。如此雄伟漫长的一座山,如何截取其形状为霍去病修墓,是个无解的历史难题。但霍去病的荣耀毋庸置疑。对手的反应感受最为客观:“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是匈奴人的哀叹。作为祁连山的支脉,焉支山今天地理标注为大黄山,和祁连一样都是匈奴语的音译:祁连为天,焉支(阏氏)为后。匈奴人不仅需要祁连山脚下的绝佳牧场繁育牲畜,还需要山上的木材制作弓箭。焉支山里应当也有生产古代化妆品的原料。如此沉重的打击,或曰如此辉煌的胜利,不仅仅依靠武力,更有创新。文化需要创新,武化更需要创新。祁连山下的霍去病,最大的贡献未必就是打通河西走廊、接通历史文化的脐带。他们发明发挥的全新的骑兵集团冲锋战术,给后世的影响虽然无人注意,但其实效应巨大。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说清,这到底是文化,还是武化。
作者简介:张锐强,河南信阳人,央视《讲武堂》栏目“名将传奇”和“书生点兵”系列讲座主讲。从军11年,30岁退役写小说。在《当代》《人民文学》《十月》发表长中短篇小说两百万字。多篇作品被《小说月報》《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以及年度小说选本转载。曾获齐鲁文学奖、全煤文学乌金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泰山文艺奖、《山花》双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