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梅洛-庞蒂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兼论与伊波利特的异质性
2021-09-17刘沛妤维罗妮卡法斯特林
刘沛妤 维罗妮卡·法斯特林
[提要]深入探讨梅洛-庞蒂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及其在何种意义上与同时代思想家发生了理论碰撞,对理解两次大战期间法国思想界的理论图景具有重要意义。梅洛-庞蒂通常被认为是在伊波利特的黑格尔译著的影响下“开启”对黑格尔哲学的人类学解读的。事实上,梅洛-庞蒂接触人类学解读早于阅读伊波利特的译注,而且,梅洛-庞蒂与伊波利特的解读方式在阐释方式、理论资源和思想母题方面具有相当的异质性。在澄清他们思想的异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别从梅洛-庞蒂本人的理论建构进程以及法国学界对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接受史两个角度考察他们产生异质性的主要原因。
探讨梅洛-庞蒂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创造性误读以及这种误读与同时代思想家产生的理论碰撞,将为我们理解两次大战期间法国的黑格尔研究提供更准确的思想史参照。梅洛-庞蒂说:“黑格尔是一个世纪以来所有伟大哲学的源头。”[1](P.83)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考贯穿于各个时期的著作、政论文章、讲稿和笔记之中,其中,较为集中的阐述则在《黑格尔的存在主义》《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和非哲学》和《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
梅洛-庞蒂对黑格尔的解读方式是在他与同时代思想家的理论碰撞中形成和发展的。20世纪50-70年代,学界大多认可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开设的黑格尔研讨班开启了梅洛-庞蒂的黑格尔研究[2][3][4];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的译著开启了梅氏人类学解读的观点逐渐受到关注,尤其是1941年出版的《精神现象学》首个法语译本,通常被认为对梅洛-庞蒂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伊波利特的影响往往被混杂在科耶夫的影响中讨论,不加以区分[5]。21世纪以来,伊波利特对梅洛-庞蒂的积极意义愈发凸显[6][7][8]。回顾文献不难发现,在梅氏的黑格尔哲学研究中,的确引用了伊波利特的译著,使用的黑格尔研究文献也大多是伊波利特所译,但并不仅限于《精神现象学》法译本。根据笔者查阅的文献,梅洛-庞蒂与伊波利特在两个不同的阶段关于黑格尔哲学发生过理论碰撞:一是1945-1948年间,二者从知觉经验与理性的关系角度对黑格尔哲学进行讨论;二是1952-1961年间,二者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新发现黑格尔哲学。在这两个阶段中,梅洛-庞蒂引用和提及伊波利特时大多表达了对其黑格尔研究的肯定,而伊波利特对于梅洛-庞蒂的态度则是经历了一个转变,他评议1946年11月23日梅洛-庞蒂在法国哲学学会上的发言时认为梅氏的理解并不令人满意①,但是在梅氏去世后撰写的三篇悼念文章中,伊波利特表达了他与梅洛-庞蒂研究的相似性。②如何理解他们之间的理论联系?梅洛-庞蒂是在何种意义上需要引用和讨论伊波利特的黑格尔研究?伊波利特所称的“具有相似性”是否意味着二人对黑格尔哲学的解读是同质的?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关于梅洛-庞蒂与伊波利特关系问题的严谨提问方式
诚然,梅洛-庞蒂研究黑格尔哲学时,或引用伊波利特的译著,或以伊波利特的研究来阐述自己的主张,我们是否就可以由此判定梅洛-庞蒂因阅读伊波利特而受其影响并开启了人类学的解读方式呢?笔者以为,若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关于这一问题的更加严谨的提问方式,反思以往研究中以“思想影响”来概括二人之间的思想碰撞过程是否合适。伊波利特对黑格尔的译介的确在当时法国知识分子间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是否可以由此认定梅氏因此“开启”了人类学解读方式?这需要参阅更多的文献资料,针对思想史中的重要史实,澄清以下两个问题: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人类学阐释是否首次出现在伊波利特的《精神现象学》法译本中?梅氏接触这种人类学阐释是否自阅读伊波利特开始?
根据笔者查阅的文献,至晚于1923-1928学年③,德·阿兰(de Alain)就在亨利四世中学的哲学课堂上对《精神现象学》进行了人类学解读。④随后,在1928-1929学年,查尔斯·安德勒(Charles Andler)在法兰西公学院(Le Collège de France)讲授黑格尔哲学,阐述了《精神现象学》的人类学维度⑤。伊波利特在译介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多次提及这一课程讲稿,并赞誉其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黑格尔在法国的复兴。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梅洛-庞蒂参加了上述课程,但是,有研究者认为,梅氏此时已经通过阅读或交流接触了上述人类学解读,尤其是查尔斯·安德勒的讲座,被视为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包括梅氏在内的法国知识分子对黑格尔进行再阐释⑥。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至晚自德·阿兰以来,法语学界解读《精神现象学》所使用的重要术语的法语翻译就已基本确定,这种译法的确容易引发人类学的解读。例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四章B节阐述主奴辩证法所使用的术语die Dialektik von Herr und Knecht被翻译成了dialectique du mai^ ter et de l’esclave,即“主人和奴隶为了价值和荣誉的生死之争”⑦。显然,这种翻译很容易让人认为主奴辩证法本身就具有人类学的意涵,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被定位在特定的人类主体中。就这样,黑格尔在认识论意义上讨论自为存在的意识与为对方而存在的意识的辩证运动,变成了人类学意义上奴隶为推翻主人统治所做的努力。梅洛-庞蒂和伊波利特都沿用了这种具有法国特色的翻译方式,他们主张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人类学解读,并不令人意外。
基于这一澄清,我们可以对梅洛-庞蒂和伊波利特的关系问题提出更加严谨的发问:既然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人类学阐释并非首次出现在伊波利特的法译本中,那么伊波利特是如何在法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强化了黑格尔的人类学面貌的?这一强化与梅洛-庞蒂的解读方式发生了何种理论碰撞?他们的思想都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本土知识分子突破传统、积极向外求索的过程,都试图以此在彼时的复杂现状和过去的丰富传统间寻求联系:梅洛-庞蒂和伊波利特最初的思想都形成于信奉新康德主义和共和-唯理论意识形态的学院之中,在20世纪30-40年代,他们感受到了法国学院哲学的危机,不满足于新康德哲学的纯粹理论性和柏格森唯灵论的过度主观性,加之面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所体现的对于历史进步的乐观观点与战争创伤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迫切需要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更有解释力的理论资源。他们的距离乍看颇为接近,并不难理解,但这是否意味着二者的解读方式是同质的?他们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是否存在异质性和原创性?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分别探究他们在早期作品和晚期作品中的相关表述。
二、伊波利特的早期解读及其与梅洛-庞蒂的异质性


针对第一点不满,梅洛-庞蒂在1946-1947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及时做出了回应和补充。首先,在《黑格尔的存在主义》一文中,他借用伊波利特对黑格尔的存在主义改造,说明作为前提的知觉经验与作为显现的理性之间的展开是如何可能的。梅氏同意伊波利特将意识的运动过程解读为揭示人类经验在其所有区域里的内在逻辑,而不是概念之间的串接,因为人在世界中存在首先就是身体存在,道德的、审美的、宗教的经验是身体在世存在的感性表达、自我给予、寻求自我理解的过程。他认为黑格尔并不是“仅仅去弄明白科学经验在怎样的条件下成为可能,而是要以一种普遍的方式搞清楚道德的、审美的、宗教的经验如何成为可能。……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人都从一种主观的‘确定性’出发,根据这种确定性的种种指示来行事,……直到主观确定性最终等同于客观真理,直到自己原来的含糊存在成为自觉存在。”[16](P.86)也就是说,梅洛-庞蒂认为,如果将黑格尔所主张的“自我意识是从感性世界和知觉世界的存在而来的反思”解读为“不同知觉经验以主体间性的辩证运动,作为前反思阶段为理性奠基”,那么,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过程就可以被用来解释知觉经验向理性的展开。因此,可以说,伊波利特发现的黑格尔哲学中的存在主义元素,帮助梅洛-庞蒂找到了理论突破口。
其次,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文中,梅洛-庞蒂进一步阐释了这种主体间性的辩证运动的驱动力问题。他将辩证法的驱动力界定为“介入某一占有自然模式、同时从中形成与他人的关系模式的人,是人的具体的交互主体性,诸存在的相续而同时的共同体”,而非“一种从我们外部给予的‘社会性自然’”“世界精神”“诸观念自身的运动”或“集体意识”[1](P.174)。这一界定意味着,“知觉经验向理性的展开过程”被梅氏进一步深化为“从原初的自然序列的感性存在去理解文化(观念和智性)的诞生过程”。在这一诞生过程中,人类的活动“置身于一种无法须臾抛开亦无法进行简化的自然的和历史的处境,知识被放到人类实践的总体性里并被后者装填”,处于关系中的主体“不再仅仅是认识论主体,也是人类主体,它凭借一种连续的辩证法,根据其处境进行思考,形成与其经验有关联的一些范畴,并通过他从这种处境和这种经验那里所发现的意义来改变它们。”[1](P.182)在这里,梅洛-庞蒂用主体间性辩证法的驱动力问题回应传统的实体形而上学的困难,即在心灵与身体、主体与客体、智性与感性、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主导下,传统形而上学将身体、客体、感性、自然视为次等的,且与心灵、主体、智性、文化相分离的,那么,如何说明知觉经验能够发展出理性的观念和文化?通过阐明主体间性辩证法的驱动力,梅氏确认了具备发展成精神性存在的物质性、兼有主体性格的客体、能发展出智性的感性、能生成文化世界的原初的自然(primordial Nature),以“辩证”这一术语来论证这些在形式逻辑中看似相互矛盾的范畴的交互关系。
通过对上述两篇文献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梅洛-庞蒂关于主体间性辩证法及其驱动力问题的论述,清晰地反映出他在阐述方式、理论资源和思想母题上与伊波利特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第一,在阐述方式上,虽然关于“原初的自然何以发展出文化(观念和智性)”的论述早在《行为的结构》和《知觉现象学》中就已出现⑨,对梅氏来说并不新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他主张以(青年)黑格尔、(青年)马克思和海德格尔进行互相阐释来进一步深化他的论证,例如,使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占用自然”(appropriate nature)这一术语来深化对原初的自然(primordial Nature)的论证[1](P.174),将马克思的“对象”(the object)概念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a mind-phenomenon)概念/“客观精神”(an objective spirit)概念进行互相阐释[1](P.178),将黑格尔的“绝对历史”(absolute history)概念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内容(in the Heideggerian sense the “metaphysical” content of Marxism)进行相互阐释。[1](P.172)该文所引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朗兹胡特和迈耶尔所编辑的《早期文选》为底本(1937年法语译本出版),本身就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因此,梅氏采取这种阐释方式并不令人意外。伊波利特《〈精神现象学〉的起源和结构》一书的英文版译者约翰·赫克曼(John Heckman)在为该书所作的引言中也指出:“法国对黑格尔哲学兴趣高涨,这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黑格尔是判断我们要走向马克思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12](P.xv)但是,伊波利特本人在该书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阐释只是偶尔提及马克思[9](P.166),并未像晚期作品中那样明显地采取对照研究的方式来进行。
第二,在理论资源上,当梅洛-庞蒂意识到知觉经验和理性的关系需要在存在的层面上来说明时,海德格尔就已经站在他的早期作品的理论背景中了。而且,梅氏指出,海德格尔此时其实已经隐约出现在伊波利特的理论中了,这也就是为何他在《黑格尔的存在主义》的结尾处指出“伊波利特还补充道,诚然,可以用另外的方式理解存在主义,这后一种提示在我们看来最为恰当……《存在与时间》的最后部分正是围绕着历史概念。”[1](P.92)但是,1946-1948年间的伊波利特尚没有完全理解梅洛-庞蒂的洞见,直到1952-1961年间,伊波利特才真正重视站在梅氏理论背景中的海德格尔,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黑格尔研究中。
第三,在思想母题上,虽然二人都将黑格尔辩证法总体的一面解读为对主体间性的强调,但也有相当的异质性。梅洛-庞蒂从知觉经验优先性的维度来论证自然史,他强调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主张的“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这一著名命题来理解主体间性辩证法。这一命题原本是针对黑格尔把人视为自我意识的外化物的观点而提出的,主张人是“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即物质本质力量的存在物”,是“社会存在物”[1](P.174),“一种为自身而生存的存在物”,从而是一种“类存在物”,通过“类生活”即自由自觉的实践而实现了人的本质。梅氏对其进行改造,认为“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实践基础”需要建立在“基于知觉经验的身体主体与其生活世界的内在统一”的基础上,因而解读出黑格尔哲学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我思”的人类学面貌。而伊波利特则是从精神的维度出发界定人的历史生成性,认为黑格尔试图解决的是如何将主体性融入到客观历史性的问题,不关注有机生命,也不关注“一般的自然的生命”[9](P.34-35)。这种将人的主体性与客观历史现实相融合的尝试,预设了主体性无法在一个自我封闭的状态下完成对外部世界确定性的探索,即传统形而上学的“我思”所面临的困境。也就是说,梅洛-庞蒂和伊波利特分别从具备发展成精神性存在的物质性和纯粹的精神性两个不同维度,向占据法国思想界统治地位的“我思”的传统形而上学设定发起了挑战,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三、伊波利特的晚期解读及其与梅洛-庞蒂的异质性
梅洛-庞蒂在其个别晚期作品(如课程笔记《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和非哲学》)中依旧引用伊波利特的黑格尔研究⑩。但是,他与伊波利特的阐释方式、理论资源和思想母题仍有明显不同,主张用强调可逆性的“好的辩证法”(bonne dialectique)/超辩证法(hyper-dialectique)来表述一种基于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关系,从而说明知觉经验的优先性何以可能,这也是梅洛-庞蒂解读黑格尔哲学最具异质性和原创性之处。具体来讲:
第一,梅洛-庞蒂和伊波利特的阐释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梅氏晚期作品(约1952-1961年间)中很少再对(青年)黑格尔、(青年)马克思和海德格尔进行互相阐释,此时他已经无意于真正理解黑格尔哲学到底说了什么,甚至不再满足于借助黑格尔的术语阐发知觉经验的优先地位,而是批判强调否定性的“坏的辩证法”(mauvaise dialectique),并提出一种强调可逆性的“好的辩证法”(bonne dialectique)/超辩证法(hyper-dialectique)。这也是梅氏针对伊波利特的第二点不满,即通过建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本体论基础来说明知觉经验何以可能,给出更加充分的论证。这一论证集中体现在他的工作笔记《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但是,梅氏此时的直接理论对手已经不是伊波利特,而是萨特。他指出,即便如萨特那样强调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维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对传统形而上学有所超越,但是,纯粹的虚无和纯粹的存在仍然是相互排斥的,这仍会使辩证运动都陷入停顿,错过了由虚无“沉入存在”这一过程所带来的对世界的真正开放。[13](P.80-81)因此,这种“坏的辩证法”(mauvaise dialectique)必须让位于一种“好的辩证法”(bonne dialectique)/超辩证法(hyper-dialectique),在后者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被比作纸上的折痕(fold)创造的“内外交织”(le chiasme)。折痕(fold)发挥一种“转折点”的作用,使纸的内外两面呈现为一种可逆性(le réversibilité),以致于难以清楚地区分谁在感知和谁被感知。这种可逆性(réversibilité)理论是对其早期作品中交互主体理论的发展。梅氏认为,要论证交互主体性的基础身体主体难以被区分,就需要为自我与他者构建起共同的本体论基础。他将一种在可逆性(le réversibilité)中不断生成的存在界定为“肉”(la chair),主张它“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不是实体……是一种具体化的原则……是存在的‘元素’。”[13](P.172)自我与他者都是“肉”的裂变,形成我的“肉”和世界的“肉”。“肉”裂变的双方用同样的东西包裹着彼此,因而无法被绝对分开,世界的“肉”作为我的“肉”的附属物或延伸,这样一来,感知者与被感知者的不同身体视角就能相互交错,不再需要通过一方克服另外一方来实现他们之间的辩证运动,不同的私人世界也就向彼此开放了。换言之,通过构建本体论基础,他揭示了“肉”裂变双方的亲缘性,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优先在肉的裂变中通过运动与知觉的交织(le chiasme)来把握意义。在梅氏看来,这有助于更好地解决传统形而上学在认识论层面通过“我思”来把握意义所带来的困难。
伊波利特晚期作品中的阐述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将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理论进行对照研究。这种做法乍看之下类似于梅洛-庞蒂早期的阐释方式,但是,笔者以为,至少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1955)和《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新角度》(1971)这两个文本中,伊波利特在阐发黑格尔哲学中关于历史的意义问题时,更多地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区别,因而阐释方式仍与梅氏早期具有异质性。伊波利特指出,尽管黑格尔哲学在法国思想界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但是,马克思和梅洛-庞蒂站在了黑格尔的对立面,因为前两者“试图维护存在的权利和人在情境中的自由,致力于一部意义模糊、没有任何绝对保障的历史,虽然这样做的风险已经被计算过了。”[14](P.v)这样的历史观“只对具体的历史情况进行分析,对人类存在的经济基础进行反思,特别是通过无产阶级对历史异化所带来的压迫进行反抗,来考察实现解放人类的必要性”[14](P.vi),明显有别于伊波利特本人试图阐明的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的同一性在现实的历史形式中展现自身”的观点。
第二,梅洛-庞蒂和伊波利特在理论资源方面更为接近。二人阐释方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受到理论资源变化的影响,相较于早期阶段而言,他们在晚期阶段都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接受了海德格尔在《人道主义书信》中的重要观点,即放弃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理解辩证法,转而主张从语言中把握存在。梅氏特别强调从语言与存在的维度进一步解释主体间性辩证法的可逆性,因为他认为语言并不仅具有表征存在意义的功能,还是一种尚未论题化的表达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前反思的沉默,因为在前反思的意义上来说,语言与存在具有同等的优先性。正如他在工作笔记《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所写:“世界存在之意义的问题是如此地难以通过词语的一个定义来解决,……语言远不是拥有世界存在的秘密,语言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存在。”[13](P.121)梅氏主张语言与存在具有同等的优先性,是为了揭示现实世界其实包含着一种未论题化的沉默世界,显然,语言的表征功能无法解释沉默世界中新意义是如何产生的,梅氏认为,真正的创造性意义产生于符号与符号之间沉默的差异之中。他用音位对立来分析符号之间沉默的差异,因为音位是潜在意义声音的起始单位,可以区分不同的符号。身体的言语器官通过对沉默世界的具身参与,在音位特征上产生了差异,故而是前反思的意义的来源。这种意义作为身体与世界的实存联系沉淀下来,为下一个创造性的音位对立作准备。在这一过程中,梅氏认为,前反思的沉默与“我思”的言语实现了可逆的辩证运动。
同样,接受了海德格尔的语言转向作为理论资源后,伊波利特对梅洛-庞蒂的态度发生了重要转变,尤其体现在梅氏1961年突然离世后,他撰写了三篇悼念文章来解释他们的思想碰撞:“思想平行”“有时吻合”“受到同样影响”“经历同样的历史悲剧”[10](P.731)。事实上,在1952年出版的《逻辑与实存》中,伊波利特就已经开始重视梅洛-庞蒂早期著作中对语言的考察。[15](P.29)在1954年发表的《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一文中,他再次表达了对话语意义的关注,并指出海德格尔从本体论层面考察现象学,可以用作研究黑格尔哲学的重要理论资源。[16](P.308)在1961年发表的悼文《梅洛-庞蒂哲学中的存在与辩证法》《梅洛-庞蒂思想的演变》和《梅洛-庞蒂哲学中的意义与存在》中,伊波利特指出了法国思想家能够为阐发黑格尔哲学中关于历史的意义问题所做的工作,积极评价了梅氏的贡献,并对其进行补充。此时他意识到,梅氏自《行为的结构》一书开始便将人的行为视为意义的表达,伴随着黑格尔辩证法所揭示的人的历史性生成过程,人的行为的意义表达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直至死亡那一刻仍在追寻的。但是,他认为应当对梅洛-庞蒂的意义表达进行区分,指出sens和signification的区别:sens用来表述知觉经验中产生的前反思的意义(实存的意义),而signification用来表述理性支配下的“我思”的意义,从sens到signification的生成过程即为《精神现象学》中所暗含的追寻历史意义的过程。然而,梅氏本人在《知觉现象学》中对“能表达的言语”(parole parlante)和“被表达的言语”(parole parlée)的区分,以及晚期对不可见的和可见的区分,却被伊波利特忽视了。此外,通过参与《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的写作,伊波利特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对人的历史生成性的考察确有必要进入本体论层面,因为“他者的实存是我自身实存的本体论条件”[14](P.162)。这种本体论条件也不是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二元本体论,而是在生存论意义上参与到世界之中。
第三,梅洛-庞蒂和伊波利特仍各自延续早期的思想母题。伊波利特的晚期作品从语言维度入手重新发现黑格尔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早期的人类学解读完全放弃,而是以本体论基础补充论述他第一阶段的思想母题,即人的实存的历史生成性。这一思想母题的精神性维度,显然与梅洛-庞蒂所主张的具备发展成精神性存在的物质性维度——肉(la chair),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也就是说,即便伊波利特对梅氏理论的态度发生转变,也不意味着二人在这一阶段对黑格尔哲学的解读是同质的,因为他们第二阶段的理论推进或转向不过是对第一阶段思想母题的补充和完善,从根本上来讲,侧重点仍然是不同质的。
四、产生异质性的原因
通过本文第二和第三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说,梅洛-庞蒂和伊波利特对黑格尔哲学的解读都具有明显的法国特色,是一种人类学的创造性误读,但是,他们在阐释方式、理论资源和思想母题方面具有相当的异质性。那么,我们需要继续追问: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异质性?
一方面,我们要把这种异质性放在梅氏本人理论建构的进程中去考察。当1946年梅氏首次集中阐述黑格尔哲学时,他自己的理论建构正处在早期现象学研究和晚期本体论建构的中间过渡阶段。此时他早期的代表作《知觉现象学》刚刚出版,但正如梅氏自己所言,此时他已经意识到了法国学院哲学框架的局限[17](P.10),尤其是笛卡尔传统下“身体”概念的难点,不得不寻找新的突破口。黑格尔哲学给他的理论构建带来了巨大的灵感。在他看来,黑格尔“首开先河,尝试对非理性进行探索并将之融入一种更加开阔的理性”[1](P.83),因此可以被视为“揭示了人类经验的先验逻辑”[1](P.86)。这正与梅洛-庞蒂本人此时的理论诉求不谋而合,即批判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的共性问题“言语必须以思维为前提”[17](P.231)[1](P.115),论证“前意识的知觉本身孕育着意义”[17](P.239)[1](P.118)。这也是该篇论文被收录在名为《意义与无意义》的论文集中的原因:他认为,知觉的过程有着不可避免的偶然性,理性和秩序无法保证消除偶然性,为了阐明意义的真正来源,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意识的运动过程为他解释“人从混沌走向绝对的过程”提供了灵感(P.。于是,人类学解读的黑格尔哲学成为他首选的理论资源,伊波利特的译介恰逢其时,符合梅氏自身理论建构的需要,可以作为合适的切入点,因此被称为“标志着法国的黑格尔研究迈出的关键性一步”[1](P.83)。但是,在20世纪50-60年代,梅洛-庞蒂筹划着下一步的写作计划,即“准确描述从知觉信念到明确真理的过渡”[1](P.126)。尽管这一写作计划数度更改,并由于梅氏英年早逝而仅仅呈现为未竟的手稿《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但是,梅氏始终在尝试论证一个具有总体意味的“意义的本体”(P.。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梅洛-庞蒂对黑格尔哲学的解读呈现如此这般的面貌是基于他自身理论建构的需要。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把这种异质性放在法国思想界对海德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接受史中去考察。在1946-1948年间,梅洛-庞蒂和伊波利特都从知觉经验与理性的关系角度对黑格尔哲学进行讨论。此时的梅洛-庞蒂已经初步意识到需要建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本体论基础来说明这个问题,海德格尔就已经站在他的理论背景中了,而他此时的理论困难需要在黑格尔哲学中寻找灵感,伊波利特的译介和研究恰好帮助梅洛-庞蒂找到了突破口。但是,此时的伊波利特并未充分认识到建构本体论基础的必要性,或者说,海德格尔并未以《人本主义书信》发表之后的面貌出现在此时伊波利特的理论建构中,因而他认为梅氏的发言并不令人满意。他们此时理论的异质性,究其根源,是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在他们理论建构中的出场顺序不同。此外,法国思想界几乎同时接受了(青年)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这种理论接受的时间契机为对其进行相互阐释/对照研究提供了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被梅洛-庞蒂和伊波利特作为理论资源之一的(青年)马克思的文本,是收录于《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文选》中的《国民经济学与哲学·论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和市民活动的关系(1844年)》[1](P.173)[14](P.90),仅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三笔记本”的部分内容,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第1部分第3卷(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和第二版第3卷的底本)在编排顺序和文本结构上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虽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2014年中文版单行本的底本)中的写作顺序版更为接近,但却缺失了“第一笔记本”和“第二笔记本”,因此,他们难以在使用这一理论资源时注意鉴别如下问题: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的“地租”部分就已经对黑格尔哲学的“神秘主义”(即绝对精神的神秘性)进行了批判,“第三笔记本”中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是作为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而出现的,而且并没有最终完成,在被分割为三个片段的论述中,体现着马克思此时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一直在发生变化。梅洛-庞蒂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伊波利特虽然意识到新文本出现所提供的新的理论灵感[14](P.vi),但受时代局限,二人都没能超出《早期文选》去看待这个问题。时至今日,学界有必要意识到,我们考察两次大战期间法国的黑格尔研究时,要区别作为理论资源的马克思、青年马克思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同版本中的马克思。
结语
虽然梅洛-庞蒂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受到了伊波利特的影响,但是,事实上,他接触人类学解读早于阅读伊波利特的译著,而且二人对黑格尔哲学的解读显然在阐释方式、理论资源和思想母题方面具有相当的异质性。产生异质性的原因应当从梅洛-庞蒂本人的理论建构进程以及法国思想界对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接受史这两个角度去考察。
注释:
①梅洛-庞蒂的报告和他与伊波利特的讨论最初发表于《法国哲学学会学报》第41卷1947年10-12月第4期,后收录于《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一书中,详见:[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王东亮译. 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M]. 三联书店, 2002: 1-74.
②这3篇悼念文章包括《梅洛-庞蒂哲学中的存在与辩证法》(Existence et dialectiqu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Merleau-Ponty)、《梅洛-庞蒂思想的演变》(L’évolution de la pensée de Merleau-Ponty)、《梅洛-庞蒂哲学中的意义与存在》(Sens et existenc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la Maurice Merleau-Ponty),收录于《Figures de la pensée philosophique : écrits de Jean Hyppolite (1931-1968)》第2卷中,详见:Hyppolite, J., Figures de la pensée philosophique: écrits de Jean Hyppolite (1931-1968),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1, pp. 685-7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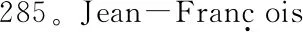
④de Alain的讲稿于1932年出版,详见:de Alain, Idées.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Platon, Descartes, Hegel, Comte, Paris, Hermann, 1932, pp. 259。
⑤Charles Andler的讲稿于1931年出版,详见:Andler, C., Le fondement du savoir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l’esprit” de Hegel,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1931, 38(3), pp. 317-340。
⑥Bruce Baugh在《French Hegel: From Surrealism to Postmodernism》一书中指出,梅洛-庞蒂的黑格尔研究受到de Alain的影响,详见:Baugh, B., French Hegel: From Surrealism to Postmoderni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14。
⑦法语文本为Combat à la vie et à la mort. L’un et l’autre posent leur vie “comme une chose sans valeur”. Le fait n’est pas douteux; nos plus cruels combats ne sont pas pour l’existence, mais bien pour l’honneur,摘录自de Alain, 1932: 259。
⑧类似的观点可以参阅:夏莹:《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黑格尔入径——以伊波利特为例的思想史考察》,《求索》2020年第5期。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起源与结构》,还应分析伊波利特1946-1948年间的其它文献,以及1952-1961年间伊波利特的变化。
⑨梅洛-庞蒂在《行为的结构》和《知觉现象学》中对原初的自然(primordial Nature)的说明,旨在强调一个前客观/前反思的感性领域,详见1.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杨大春、张尧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48页;2.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73页。
⑩《Philosophy and Non-Philosophy since Hegel》是梅洛-庞蒂1960-1961年间为在法兰西公学院(Le Collège de France)开设课程所做的详细笔记,在其去世后由文稿执行人克劳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整理出版,详见:Lefort, C., & Char, R., 1982,目前尚无中文版,英文版见:Hugh J. Silverman, 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