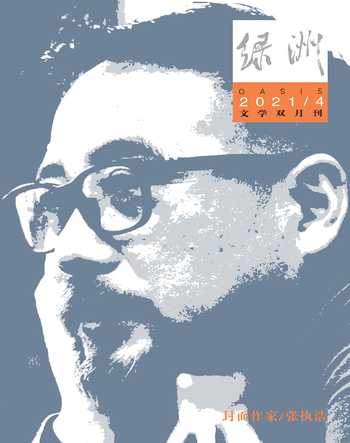几瓣元素 一个核心
2021-09-13虹影
虹影
报纸
我永远忘记不了那一天,放学后没回家,背着书包,在弹子石街上闲逛。理发店里坐着一个中年女人,戴着眼镜,双手握着一张报纸,理发师正在给她剪发。我看到一张大照片,是讣告,是总理的讣告。8日,他走了。
我眼泪掉下来。那女人回头看到我。她的眼睛是红的,把手伸给我,紧紧握着。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是我的老师。她一向看不起我,态度非常凶。可是这一天因为失去我们崇敬的人,她对我出乎意料地好,以后也对我很是关心。
那是1976年1月9日,我十四岁,在山城重庆。
我父亲因为眼疾在家,母亲出外做苦力。父亲病休后,回家当家庭妇男,订了重庆日报。每天他坐在六号院子的堂屋抽一个叶子烟,读重庆日报。在完全眼盲前,父亲是我们那几条街,最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过年时,看过的旧报纸,都被他弄来糊房间。邻居们也来要报纸,一年的报纸够糊好多房间。那些年久未修的老房,因为有了报纸,变得像样子,也有了年味。院子里的孩子,因为有这些报纸,识字都早。从六号院子走出的泼妇,骂街时也会骂出文化。
表姨与小舅
为了缓解我是非婚生的孩子而总被邻里欺负的问题,六岁时母亲将我送到她的忠县乡下,跟好多亲戚住在一起,他们对我很好。
在丰都的表姨有天来接我,她生得白净,不像风吹日晒的农妇,头发在脑后绾得整整齐齐,穿得也干净,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她与母亲不沾亲,但带故。早年听说母亲逃童养媳婚约到重庆,她是追随者。她到重庆后,找到我的母亲,两人成为好朋友。后来她认识了在船上工作的现任丈夫,两口子住在一号桥一带,未有孩子,在孤儿院领养了一个男孩。男孩聪慧,生得周正,他们极爱,生怕扔掉孩子的人后悔,便在孩子上初中时全家回到乡下老家。表姨、姨夫待我如亲生,儿子有的,我也有。她自己饿肚子,却从未让我饿过肚子,受过凉,生过病。
在乡下待了一年,母亲终于想起我,让小姨来表姨家,带我回重庆上小学。走时我与表姨都哭了。
表姨在一号桥一带住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母亲总说她,模样儿生得俏,又能干,针线活做饭样样顶尖,还遇到一个爱她的男人。经过一号桥时,母亲说想她,说一号桥的事,很多时候都是在说表姨,说她的儿子对她有孝心,不过成年后,有点儿怪表姨带他离开了重庆,不然他成绩好,肯定读大学,做学问,而不是在田里劳作。我六岁在乡下,却发现表姨另一个秘密,她有一个亲生儿子,却不敢相认,是当时生产队在批斗的一个人。那儿子是她逃离重庆前生的,而且孩子的父亲是地主少爺,是被他强暴或是自己爱上,不得知。也许她要回到乡下,也有思念这个孩子的原因。表姨去世得很早,是我二姐告诉我。但对我来说,她没有走,她永远是三十多岁的样子,干干净净,美丽的一张脸。写到一号桥时,她好像就在我眼前,站在自家石头房前,对爬在树上我说,话包子,下来吧,下来我给你做地瓜饼。
在重庆不说一句话的我,在她面前成了“话包子”,这就是她改变我产生的奇迹。这么多年过去,除了《前世今生:孔雀的叫喊》,我写到她,我的《月光武士》题献给她,一个在我生命历程中护送我一段,最重要的人之一。
母亲的亲弟弟,住在一号桥往黄花园方向之间的临江半山坡,母亲经常去看他。为节省公共汽车票,我们会从临江门公交车站转盘走下去。小舅是倒插门,舅妈是独女,在印章厂做雕刻工,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工人。他们住在山坡的吊脚楼,要下好多歪歪扭扭窄窄的石阶。
小舅家墙上有好多照片,有母亲年轻时美丽的倩影。小小的我到他家,会看墙上的照片,弄不懂母亲这么美丽的人为什么在家里常常对我冷暴力,甚至出言伤我。
小舅的家下面有座小石桥,从那儿可以到江边。这一带居民的工作,大都跟江和船相关,也跟我小时长大的南岸贫民窟差不离,每家都有几本书的故事。小舅当年知道姐姐在重庆城,就一个人沿江走几天几夜的路来重庆,我在《饥饿的女儿》一书写了他。
混血姐姐
母亲在白沙陀的造船厂的搬运队工作,同事都是成分有问题的人。有一天春节陪母亲加班,我坐在造船厂的沙滩上,看母亲像一个男人一样,和另一个阿姨一起抬氧气瓶。下午五点半收工,我们没搭上顺路船。回南岸野猫溪家的路上,有一位日本混血的蒋姑娘,她对母亲很好,对我很好。我们走山路回家。我太小,她背我回家。
母亲经常讲起这家的悲情故事,石梯上走着日本母亲,下面追着的人是三个女孩和父亲。这幅画面,打我几岁时邻居都在说,现在蒋姑娘就在眼前,对一个孩子来说,神秘莫测,仿佛都是故事书里的人。母亲说,蒋姑娘的爸爸是个翻译官,手握手杖,身着西服,走在街上,真是一表人才,引来好多女人爱慕的眼光。母亲在1952年搬到南岸来就认识他,也认识他的夫人,蒋姑娘的母亲。母亲的话点点滴滴融入我的心,朝夕起伏,随风荡漾开来,她是这一带最美的女人。我小时走在街上,就在看谁是最美的女人。
也是那一次走山路回家,蒋姑娘说,六六,你妈妈是我认识的最美的人,最美的人在用她的肩膀和力气养活你们一家。她当时眼睛就红了。小时我不懂,现在我写到这儿,你读到了,你会懂的。
解放碑
解放碑,属于重庆长江南岸之北,在半岛之上,是重庆商业中心地带,中心的中心,有一座中国唯一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碑,1950年国庆,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题写碑名“人民解放纪念碑”,八角形八层,设有旋梯达于碑顶,碑顶向街口的四面装有自鸣钟,朝着每个方向,一到整点,便报时,碑台周围为花圃。
我们那群写诗的人,约会常在碑下,听着顶上的时钟响,灵感倍出,长诗哗哗涌出,忘记指责晚到人,而是兴奋地当街朗读。
解放碑周围有重庆吴抄手、国泰影院、群林市场、交电大楼和美术公司,边上就是好吃街,80年代,五一路上曾经摆有长长地国外旧货服装,重庆姑娘小伙子穿得很摩登,后来被管制,所有旧货衣服被放在长江珊瑚坝上烧毁。
解放碑周围还有两个公共汽车中转站,一个是较场口,一个是临江门,从这两个地方可以去西区动物园或是江北红旗河沟、机场、戴笠公馆、红岩村、沙坪坝、渣滓洞、白公馆、北碚。
对我们重庆人来说,对住在南岸贫民窟的人来说,到一次解放碑,就等于乡下人进一次城。过年也要去解放碑走一次,在人山人海里,人挤人,互相打望,才算过年。
在我心目中,解放碑最有名的西餐馆是西西咖啡馆,这个餐馆最早是从母亲的嘴里听到的。她告诉我餐馆里面的陈设,如何华丽,侍者如何有礼貌,菜品如何好,孔二小姐如何在那儿教训重庆警局头子。等到有一天我可以进去时,发现这儿全然不是母亲说的那样,里面陈设普通、侍者也不鞠躬,菜品也不惊艳。我去的时候已是80年代,怎么比?不过母亲喜欢这儿不为怪,一是母亲是热爱美食之人,二是母亲见过世面。大姐说,母亲与她的生父,袍哥头子,是那儿的常客。他经常不带银子,结账时,手一招,便有人走上买单。
朝天门码头
朝天门码头隔江正对着我从小长大的六号院子。但院子里不是每个房间可以看到这码头,比如我家,必须爬上阁楼的天窗,站在瓦片上才能看到。跑到院子下面的八号院子前的空地,两江三岸一清二楚。最喜欢看大轮船驶入。最喜欢国庆、春节放焰火,天空耀眼得像是在梦境里。
这儿是大码头,经常会有棒棒拿着扁担和绳子找活,也有各种小贩在此。重庆有了出租车,也像甲壳虫一样铺满这儿的沙滩,这儿沙滩有岩石,也是洗衣妇喜欢的地方,主要是当长江变黄时,嘉陵江的水还清绿着,好洗衣服。这儿大小好多趸船,一般走长江下游武汉、宜昌、上海的轮船都停在此。嘉陵江边上货轮停得也多。
最喜欢听轮船调度室的调度员与轮船上的驾驶吵架,全是重庆脏话,生动、诙谐,太重庆了,不止我,好多江边人都喜欢当相声听。
这个码头是人生悲喜剧的舞台,联系着重庆人好几代的命运。常在江边看到裸露脊背的纤夫,喊着整齐的号子。同是重庆人的音乐家郭文景说,坚韧强悍的纤夫、凄凉高亢的山歌、强烈刺激的川剧锣鼓以及长江流域气息对他的音乐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每回回重庆,我走在这码头,淡忘的情景会陡现眼前:母亲抱着小小的我,与生父生离死别,一个人踩着沙滩,走向渡轮。生父走上朝天门的石阶,他不停地回头。1980年我离开家,在这儿停下。离家多年,在1989年,我返回南岸六号院子,得知生父离世。清晨,我乘渡轮过江,一心要去北京,下轮渡,走完长长的跳板,一步一个脚印走在沙滩上,站在码头的石阶上,回望南岸,一幕又一幕,挥也挥不掉,脸上全是眼泪。
叫醒我们的力量
1976年以一个女孩被几个少年欺凌开始。《月光武士》里那个女孩可以说是我,上小学时,我在学校外墙下被他们打,按在地上,要我学动物叫。其实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不仅我,别的女孩也遭遇同样的欺凌。那些年,个人的事,国家的事,统统沉淀在心里。
1980年我发现身世之谜,见到了亲生父亲,之后每年都在惊天动地地变化。我的生活在出走,在路上,在卡车、火车、飞机,越洋,在地球的另一半,1976年看不清了,便转身,背对。
1999年,我的父亲走了。2006年,我的母亲走了。周围的邻居,认识的人,也渐渐走去另一个世界。2020年,我只能停在伦敦,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巨变,隔离的生活,时空交替,每天窗外的救护车尖叫,与死亡频频擦肩而过,不时在网上参加葬礼。
生命很卑微,我的生命連“卑微”两字都不能触及,是“卑贱”。我站在长江边,看到轮船翻了,江水里沉浮的生命,无能为力,那一艘艘往江下游驶去的大轮船,是那样强大,充满诱惑,我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在里面,远远离开这儿。
时间的流逝,丰富我,掠夺我,构造我。重庆这座山城,当你心静气定,环视四周,你会看到山外有山,群山连绵。
是的,重庆一直在那儿,当我朝它转过身来,它就在对我说话。这几十年,虽然我一直用别的城市代替重庆,我有意转移注视点,我书写武汉、北京、香港、布拉格、罗马、伦敦、纽约和瓦拉纳西。写别的城市,我是在写,可重庆,我发现,我害怕,我心疼。
我的二姐在去年用手机做了家里的相册。我看到很多旧重庆,很多从前的人,那些消失的身影,跟1976年相连,那些淡掉的形象渐渐呈现,渐渐清晰。瞧瞧,这是表姨的儿子,表姨不在我的世界了,可我想念她。再瞧瞧,我在一张集体照片里,看到张妈领养的儿子,可是张妈,也走了,我也想念她。大厨房最后一个灶前的张妈,一样的瓜子脸,她不像院子其他邻居敌视我,而对我温柔关照。她被男人家暴,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止,小小的我看着,那是权力,那是不可置疑的威严,有时并非是强者,而是弱者,弱者对弱者的暴力。如果一个人的记忆从婴儿时就有了这种担忧,重叠着这种碎片,一次次组合,五六岁植入,就难拔掉身上这根刺了。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就在那儿,不停地在叫醒我沉睡的记忆。
回忆是一座座山,翻越它们,需要勇气,也需要契机,命运的安排,记忆才能在这样的巧遇中通过文字的记录存在下来。
重庆的呼吸,重庆的心跳,重庆的沉沦和新生,我不必写,这座城是长在我心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出生就看见了它,它一点点进入我的眼睛:这是江水,这是船,这是沙滩,这是礁石,这是山,这是石阶,这是担担面,这是辣椒,重庆人的命,阴暗的天,打雷如炮弹在轰炸,满天飞舞的鸽群。我跟着母亲过江,上朝天门码头,乘车到解放碑,到临江门走下长长的马路,走到一号桥,母亲在那儿说表姨,她说着表姨:“白素瑶在重庆时,跟我最要好了,她长得好好看,她在乡下也最喜欢你了,是不是呀?”我点点头。我们朝小舅的家走去,这好几站的路,那时对一个小女孩来说,差不多要走一个小时吧。母亲怎么走得那么有耐心,可惜我现在才感觉到。
责任编辑惠靖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