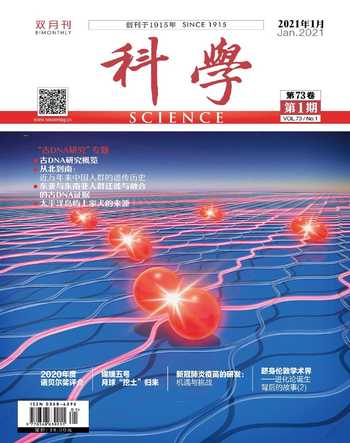古DNA研究概览
2021-09-10刘雅琳
刘雅琳
DNA是绝大多数生物的遗传信息载体,能从分子层面反映生物个体之间的差异。通过深度挖掘古代材料中的DNA信息,可以了解生物群体的历史演变情况,也能探究生物类群之间的系统进化关系。但由于古DNA难以长久保存,内源DNA含量低(获得的DNA绝大部分是外源的微生物DNA),且容易受到污染(主要指出土后现在生活人的接触造成的污染),所以从化石中获取属于研究对象的内源古DNA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非常困难。但也存在极个别由于保存环境理想,样本可能保留了微量内源DNA的情况,这些材料给研究古DNA提供了机会。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提高,科学家已能从这些保存良好的材料中获取极微量的古DNA片段。再利用生物信息学技术,将高度破碎化的DNA片段信息进行拼接,从而获得古代样本中的遗传信息,使我们能够回溯到样本生存的年代,以更广阔的视角来分析人、动植物,甚至于微生物的遗传历史。
古DNA研究简史
分子克隆技术、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相继诞生之后,很快被引入古DNA研究中,许多学者试图从博物馆样本、洞穴沉积物和永久冻土保存的古代动植物,以及古人类材料中获取DNA。1984年,希古奇(R. Higuchi)等获取了已灭绝动物斑驴的线粒体DNA序列片段,这是国际公认的古DNA研究开端[1]。然而,由于当时的技术和对古DNA特征认识的不足,早期研究中获得的古DNA大多是来自外界的污染,且大部分结果不可重复。探索过程中,科学家逐渐积累了经验,不断改进实验技术,为后来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开始意识到,对于高度降解的古DNA来说,规范的实验标准十分重要,否则实验结果将由于污染而不可重复。随着古DNA提取方法的改进,以及研究标准的建立和完善,古DNA研究正式进入可重复的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对象侧重于含量相对丰富的线粒体DNA片段或者少量核基因序列。越来越多的实验室开始进行相关方面的尝试,推动了这一新兴研究方向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PCR技术很难正确扩增含量极低的内源DNA片段,导致部分古DNA实验结果仍然不可重复,所以针对人类的古DNA研究方法在该阶段依旧受到极大的质疑[2]。
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诞生,古DNA研究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代。由于二代测序技术能够得到极短的DNA片段信息(这与古DNA的特征相似),所以实验人员可以进行测序,并通过生物信息技术进行拼接,来获得可靠的古DNA数据。实验方法也在这一阶段不断被革新,2010年拉斯马森(M. Rasmussen)等报道了4000多年前的爱斯基摩人基因组[2],格林(R. E.Green)等依据3个尼安德特人样品绘制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草图[2]。随后,越来越多的古人类基因组被公布出来,如丹尼索瓦人、早期现代人(包括田园洞人、Ust’-Ishim和Oase 1)等[3],研究也逐渐深入化和多元化。这些研究共同推动了古人类DNA研究不断前进,为古人类迁徙路线及人群间基因交流的探索提供了遗传学支持。
古DNA研究难点
获取合适的材料是开展古DNA研究的第一个难点。古代材料由于距今年代久远,绝大部分已经完全降解,保存良好的样品十分稀少。例如,在中国南方温暖潮湿的气候条件下,很难发现保存良好的样本。
其次,古样本中内源DNA含量极低,获取它们十分困难。内源DNA与环境中的微生物DNA混杂在一起,由于提取出的总DNA中,大部分是外源杂质DNA,内源DNA的比例非常低。即便是质量相对较好的样品,也难以提取出足量的DNA,所以,有时候需要反复实验才能得到足够用于分析的DNA信息。研究人员需要在混杂的DNA中,将含量极少的内源DNA分离出来,并进行研究。例如,第一个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草图是通过1%—5%的内源DNA重建的[4]。因此,科学家一直关注如何更好地将外源与内源DNA分离开来,如何降低外源杂质的影响等问题。
再次,古DNA还容易在获取时遭受到出土后现在生活人的接触造成的污染。任何形式的接触都可能将操作人员的DNA带入样品中,进而对内源DNA造成污染。因此,古DNA的提取要在古DNA超净实验室中进行,实验人员需全身防护。但即便是在超净室内、防护设备齐全与操作规范的前提下,也不能完全避免实验中的污染,所以这就要求研究人员在每一步都要建立空白对照,最终获得数据进行相关的污染评估。

另外,DNA损伤也是古DNA研究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DNA损伤是一种正常的生命现象,时刻在生物体内发生,生物对其也有一套完善的修复机制,但是这种机制随着生物的死亡而停止工作。DNA损伤程度与时间、温度、酸碱度、湿度等因素有关,在寒冷干燥环境中保存的DNA损伤程度会小一些。生物死后的DNA损伤会导致DNA高度碎片化,且会带来编码错误,直接影响DNA测序的质量。
为了克服以上困难,研究人员提出了许多在实验环节中的优化方案,比如在发掘和实验过程中严格遵守操作流程,使用特殊的酶对古DNA片段进行损伤修复等。新的古DNA捕获技术是其中一项关键技术,该技术大致分以下几步:诱饵设计(能够特异性识别古DNA的探针与磁珠相连形成诱饵)、总DNA获取、文库制备、杂交捕获、杂质DNA片段清除、高通量测序[5]。我们利用这一技术,将4万年前田园洞人的内源DNA含量,从捕获前的不足0.03%提高到捕获后的46.8%[6]。同时,新古DNA捕获技术也可用于对内源DNA含量极低的样本开展研究。除此以外,古DNA单链文库的构建同样是关键技术之一。采用新型的古DNA单链文库技术,能够获取古样品中单链DNA片段的信息,极大地提高古DNA片段的来源。针对古DNA特点开发的提取、文库构建、古DNA捕获和测序等技术,推动了古DNA研究的高速发展。
古DNA技術的重要意义
古DNA技术在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帮助我们回答了以下问题:绘制了已灭绝的古老型人类(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基因草图,并说明古老型人类与非洲以外现代人之间存在基因上的相互影响[3];现代人祖先走出非洲并非只有一条迁徙路线[7];中国南北方古人群早在9500年前已经分化,至少在8300年前,南北人群融合与文化交流的进程即已开始,4800年前出现强化趋势,至今仍在延续[8]。
古DNA研究不仅能够为我们回答以上人类基因交流和迁徙的问题,还在人类健康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古人类基因贡献对现代人在适应环境和健康方面产生影响:现代人基因组中含有大量源自尼安德特人的能影响角蛋白合成的基因,从而能较快地适应欧亚大陆较冷的环境;帮助藏族人适应极高海拔环境的EPAS1基因,很有可能与丹尼索瓦人有关[3]。除了对人类自身DNA研究外,对古人类牙结石中保留的微生物DNA的研究,也能从进化角度揭示了饮食变化对人类健康状况造成的影响[9]。另外,古DNA研究已经成功应用于考古遗址出土沉积物中的生物古DNA信息的获取,最近发表的有关白石崖溶洞遗址的沉积物DNA分析,为丹尼索瓦人在此长期生存的推断提供了重要证据[10]。
结 语
随着技术的发展,古DNA研究实现了从片段到基因组的突破。而针对那些古DNA特有的难题,科学家们又推出了一系列对策,如控制污染、建立文库、基因捕获、鉴别内源DNA等。
随着古DNA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希望未来能够从更大时间与空间尺度的样本中获取古DNA,如特别古老的样本、炎热环境中保存较差的样本、外源污染多的样本与各类环境沉积物样本等。古DNA研究集中了考古学、遗传学和生物信息学等多个研究领域的优势,致力于各学科合作还原重大事件的源起,同时古DNA研究的发展也推动了各学科自身的进步。
[1]Higuchi R, Bowman B, Freiberger M, et al. DNA sequences from the quagga, an extinct member of the horse family. Nature, 1984, 312(5991): 282-284.
[2]盛桂莲, 赖旭龙, 袁俊霞, 等. 古DNA研究35年回顾与展望.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2016, 12: 14-28.
[3]张明, 付巧妹. 史前古人类之间的基因交流及对当今现代人的影响. 人类学学报, 2018, 37(2): 206-218.
[4]Green R E, Krause J, Briggs A W, et al. A draft sequence of the Neandertal genome. Science, 2010, 328(5979): 710-722.
[5]王恬怡, 赵东月, 张明, 等. 古DNA捕获新技术与中国南方早期人群遗传研究新格局. 人类学学报, 2020, 39(4): 1-15.
[6]Fu Q, Meyer M, Gao X, et al. DNA analysis of an early modern human from Tianyuan Cave, China.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3, 110(6): 2223-2227.
[7]Fu Q, Li H, Moorjani P, et al. Genome sequence of a 45,000-yearold modern human from western Siberia. Nature, 2014, 514(7523): 445-449.
[8]Yang M A, Fan X, Sun B, et al. Ancient DNA indicates human population shifts and admixture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 Science, 2020, 369(6501): 282-288.
[9]Adler C J, Dobney K, Weyrich L S, et al. Sequencing ancient calcified dental plaque shows changes in oral microbiota with dietary shifts of the Neolithic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s. Nat Genet, 2013, 45(4): 450-455.
[10]Zhang D, Xia H, Chen F, et al. Denisovan DNA in Late Pleistocene sediments from Baishiya Karst Cav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Science, 2020, 370(6516): 584-587.
關键词:古DNA技术 研究历史 研究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