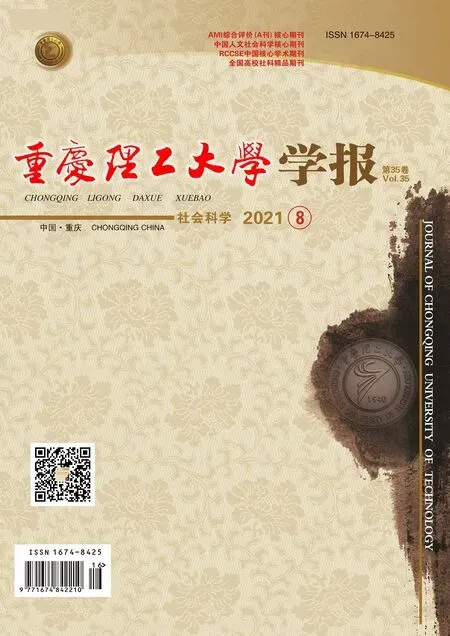世行《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在美国反倾销程序中的适用合理性研究
2021-09-10陈文清
陈文清
(复旦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438)
一、引言:从改革指引到反倾销认定——《营商环境报告》数据适用的多维化趋势
营商环境,是指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1)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营商环境,是指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世界银行Doing Business小组于2003年开始发布《营商环境报告》,这份重量级文件自此诞生。2019年10月24日,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该报告显示我国在所有经济体中表现不凡,连续两年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最近,“营商环境”一词频繁进入公众视角,《营商环境报告》与我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指引与衡量改革的重要指标。《营商环境报告》的最主要功能为“评价”,评价的核心是营商的便利性、效率、成本和市场环境的公平性。而随着时间发展,《营商环境报告》数据与指标的作用早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评价,而是已经作为国内改革指引、国内法治化建设指引、国际性的投资指引等被世界各国予以研究、加以利用。由此可见,一方面,《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的适用层面与广度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各国对《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的使用大多是作为参考或指引的间接使用,很少出现直接使用的情形。目前,有关这份报告的研究和使用尚不深入,其功能和价值依然有待探索。然而,在近年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中,出现了直接适用《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的情形,主要表现为《营商环境报告》数据被美国商务部直接运用到对外(主要表现为对华)反倾销行政程序之中,作为非市场经济主体替代价值核算的数据源——在美国反倾销实践中,当反倾销调查程序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时,美国商务部一般通过评估替代国的生产要素来确定正常价值(normal value),实为一种“替代价值”[1]。《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在美国反倾销行政程序中的适用尽管备受争议,但已然形成“行政惯例”甚至被美国商务部“奉为圭臬”。这一做法具有开创性,也展现了《营商环境报告》数据适用的多维化趋势。
《美国法典》第19编第1677节a条(c)(1)(B)项要求美国商务部根据市场经济国家中关于这些因素价值的最佳可用信息(the best available information),对非市场经济主体的生产要素进行估价(2)参见 Downhole Pipe & Equipment,L.P.v.United States,No.15-1233(Ct.Int’l Trade 2015).。因而,美国商务部在反倾销程序中适用《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的前提是证明该数据最佳可用。对于最佳可用信息的确定,一般通过检查和比较使用某些数据与其他数据的优缺点(3)参见 Dorbest Ltd.v.United States,30 CIT 1671,1675,462 F.Supp.2d 1262,1268(2006).;且并不要求客观上的最佳可用,只要求一种主观上较为合理的结论即可(4)参见Zhejiang DunAn Hetian Metal Co.v.United States,652 F.3d 1333,1341(Fed.Cir.2011).。自2012年的东莞朝阳诉美国联邦政府案起,我国海外企业不断就美国商务部适用《营商环境报告》数据作为反倾销替代数据的做法提出抗议,广州Since硬件公司、佛山顺德公司、杭州盈清公司、上海惠利公司等曾一次或多次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USCIT)就这一问题提请司法审查。在上述案件中,美国商务部对其行为的自我论证主要从《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的属性层面展开,申言之,美国商务部认为《营商环境报告》数据所具备的特殊属性足以表明其可以作为最佳的替代数据源。而这些属性也均被USCIT予以认可,在判例法的传统下确认为实质上的“法律属性”。然而问题在于,《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即便在法律属性层面具有被作为替代价值核算数据源的可行性,但由于该数据在获取方式和指标设计上的特殊性,必须通过间接使用、比较使用、补充使用等特定的适用方法对数据的重大缺陷予以消解。基于此,本文将以《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在美国对华反倾销行政程序中的适用问题为视角,对这一行政裁量行为的合理性予以重新审视,并尝试提出应对策略。
二、《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在美国反倾销行政程序中的法律属性
美国商务部将《营商环境报告》数据视为具有“代表性”“相对准确性”“可依赖性”的优质数据源运用于反倾销行政程序中,更在一系列的司法判例中得到了USCIT的全盘认可。基于此,《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在美国反倾销行政程序中的上述法律属性被予以确立。
(一)《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具有代表性
《美国法典》第19编第1677节b条(C)(1)项,指示美国商务部在选择最佳可用的生产要素信息时,应选择产品特有的、代表着一个广泛的市场平均水平的、公开可得的信息。美国商务部在相关的对华反倾销案件中,认为世行《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具有法规所指示的代表性,且得到了USCIT的支持。
1.同期性
同期性(contemporaneous)是指使用的数据与反倾销调查同期,同期性是代表性的表现之一。由于《营商环境报告》在发布后保持每年一次更新的频率,具有实时性,因此美国商务部可以选择该审查时段的同期报告数据进行替代价值核算。在2013年美国对华地板等反倾销案(广州Since案)中,美国商务部选用了《201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的印度数据作为广州since五金公司(简称广州Since)经纪和处理(Brokerage & Handling,以下简称B&H)成本替代价值认定的基础(5)参见 Since Hardware(Guangzhou) Co.v.United States,No.09-00123(Ct.Int’l Trade 2013).。美国商务部指出,来自世界银行的印度数据反映了许多该国不同公司的经验,而这些公司都为公开上市公司,所涉具体问题的成本代表一个广阔的市场平均值,并且这些数据与审查期间(POR)同期。由此可见,同期性被美国商务部作为数据代表性衡量的一个重要标准。由于美国反倾销调查通常需进行几轮甚至十几轮,因此在先前审查程序中适用的数据往往会因为不具有实时性被美国商务部或者被利害关系方要求更换调整,而《营商环境报告》数据一旦被美国商务部认定为可使用替代价值核算数据,就只需在此后审查中更新同期数据。
2.一般性
一般性与特定性含义相反,在美国反倾销语境下,特定性指的是商务部在替代价值核算时适用某一具体替代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往来中形成的商业数据,包括报价单、货运单据、财务报表等。而一般性可以理解为“代表广泛市场平均值”(represent a broad market average),是一种非特定数据,反映市场中经济个体的一般或者说普遍状态。一般性数据与特定性数据都可能具有代表性,个案适用的关键在于美国商务部的行政自由裁量。例如在抚顺金利案中,美国商务部指出“关于商业价值的代表性,除倾向于公开的、税收专属的数据之外,还必须考虑主要替代生产要素价值的代表性”(6)参见 Fushun Jinly Petrochemical Carbon Co.v.United States,No.14-00287(Ct.Int’l Trade 2016).。由此可见,某一数据是否具有代表性并不绝对,美国商务部依然需要通过衡量该数据在个案中适用的合理性,即该数据是否与被调查企业生产、销售相关,是否反映其生产、销售经验加以判断。
然而,在对《营商环境报告》这一一般性数据进行评价时,美国商务部似乎已偏离了其审查标准,以一般性取代了经验性要求,直接设定了《营商环境报告》代表某一经济体的广泛市场平均值,因而具有代表性这一因果关系。例如佛山顺德案中,原告认为,美国商务部不应依赖世界银行数据,而应使用印度货运代理公司Samsara和HapagLloyd的数据,世界银行数据根本不反映任何印度生产商的经验,而只是基于当地货运代理、航运公司完成的一项调查。然而,美国商务部表示世行数据是否反映了佛山顺德的特定经验(line-by-line experience)并不重要,关键是世界银行的数据是否是B&H成本的可靠来源。佛山顺德的数据并不代表比世界银行报告更广泛的数据,也无法说明这些报价是如何得到的,或者它们是否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自行选择(7)参见 Foshan Shunde Yongjian Housewares & Hardware Co.,Ltd.v.United States,No.10-00059(Ct.Int’l Trade 2016).。再比如微山宏达案中,美国商务部选择使用南非国际绿色组织Oceana发布的《奥西安纳报告》(OceanaReport)计算替代财务比率,并认为相比原告提出的两家公司的财务报表而言,该报告数据更具有代表性与合理性(8)参见 Weishan Hongda Aquatic Food Co.v.United States,273 F.Supp.3d 1279,1293(Ct.Int’l Trade 2017).。由此可见,美国商务部已经放弃了对《营商环境报告》数据适用合理性或者相关性的个案审查(经验性要求),单单基于其“一般性”法律属性,认为世行数据具有代表性,能够成为合理的替代价值核算基础。进一步发现,在一般性数据可发挥功能的诸如B&H成本项目下,美国商务部已经明显表现出对于一般性数据的青睐,相比之下,特定性数据的广泛性欠缺、来源存疑,难以超出一般性数据所具有的代表性高度。
(二)《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具有相对准确性
正如前文中美国商务部所说,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是基于专业而广泛的调查而得出的。美国商务部进一步指出,正是这些调查使得世行数据是多家企业真实贸易经验的反映。杭州盈清案中,美国商务部明确表示“《营商环境报告》基于多种来源及公司的实际或者真实(actual)经验”,因此倾向于使用世界银行数据,而不是原告提议的数据作为钢丝衣架的合理替代数据源(9)参见 Hangzhou Yingqing Material Co.v.United States,No.14-00133(Ct.Int’l Trade 2016)。。对于美国商务部的观点,质疑之声四起:有被调查企业指出“世行报告中使用的是报价(quote price),而非真实价格”“该报告中的价格并不包含本企业实际发生的费用”……其中最为有力的论点之一是直接指出报告数据与实践经验之间的差异;东莞朝阳案中原告方声称“《营商环境报告》使用20英尺集装箱的成本,而本企业使用40英尺的集装箱,因此商务部认为两种集装箱的每立方英尺成本相同的假设不成立,替代价值计算不准确(accurate)”(10)参见Dongguan Sunrise Furniture Co.,Ltd.v.United States,No.10-00254(Ct.Int’l Trade 2012)。。尽管美国商务部的部分解释较为敷衍与模糊,但国际贸易法院法官在判决书中的一段表述足以表明美国反倾销司法对于《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的态度——法院认为,无论如何原告所述都不足以使其将替代价值核算相关结论发回美国商务部重审或要求美国商务部重新计算,因为美国商务部并不需要为每个被调查企业计算“确切”(exact)的替代价值(11)参见 Nation Ford Chem.Co.v.United States,166 F.3d 1373,1377(Fed.Cir.1999),该案得出了“替代价值计算过程困难且必然不精确”的结论。。换言之,USCIT同意原告所说的美国商务部依据世行报告数据所计算的替代价值并非确切(exact)数值。但根据美国商务部审查,该数据已经足以保证最终计算结果是一个相对准确、真实(actual)的数值,而且基于过往判例,法院也不要求美国商务部必须计算出一个准确无误(accurate)的数据。
由此可见,美国商务部及USCIT均认为《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尽管不能确切地与被调查企业贸易实践完全匹配,但具有相对的准确性,是该国对外贸易领域营商环境的平均表现,不存在较大的数据缺陷与偏差。《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的相对准确性(actual)也因此被司法判例所肯定。
(三)《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具有可依赖性
1.基于对编制组织信誉的绝对信任
在广州Since案中,原告方认为美国商务部不合理地使用了世界银行报告,因为它完全基于曼谷一个城市的成本数据。对于这一有关数据来源的基础性缺陷,世行也在报告中直接予以承认。然而,美国商务部选择直接无视该问题,并基于对编制组织——世界银行的绝对信任,认为《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必然具有绝对的可依赖性。正如该案中,美国商务部指出世界银行的数据是一个信誉良好(reputable)的信息来源,这些数据是由独立组织编制,并基于对大量生产商的调查,完全可用于评估B&H成本。
2.基于对公开发布行为的附带考虑
在东莞朝阳案中,美国商务部表明:“世界银行数据具有可靠性,因为这些数据是公开发布的(published publicly)。 而相比之下,原告方提出的计算经纪成本的数据并未公开公布,其中包括一张发票和两份报价,这些数据所代表的数据范围并不比世界银行报告更广泛,美国商务部无法判断报价是如何征求的,也无法判断报价是否是从更广泛的报价中自行选择的。”②由此可见,相比于特定公司财务报表、单据等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内部性的财务数据,世行《营商环境报告》在全球范围内公开发布,任何国家、组织、个人都可以直接获取并加以利用。
3.基于对代表性法律属性的衍生判断
东莞朝阳案中,美国商务部还指出,“代表性”这一法律属性本身也增加了世界银行数据的可依赖性。美国商务部认为:“除了公开发布这一因素外,世界银行数据的可靠性还在于这些数据(《营商环境报告》数据)是基于六处来源,而且这些数据是同一时期的。”(12)参见 Dongguan Sunrise Furniture Co.,Ltd.v.United States,No.10-00254(Ct.Int’l Trade 2012)。由此可见,《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反映广泛市场平均值,具有同期性的代表性法律属性内涵也加强了其可依赖性。
4.基于对过往判决的完全尊重
目前,在涉及《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中,审理法官似乎已经放弃了继续从其他方面对《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的可依赖性予以说明,而是直接援引过往判例,表明其对于《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反倾销适用的态度始终具有一致性。在近期发生的一起美国对华钢丝衣架反倾销案件(2017年上海惠利案)中,USCIT通过援引杭州盈清案、佛山顺德案等过往判决,指出其一再肯定美国商务部视世界银行数据为衡量B&H成本的可靠和准确来源的做法,并在此再次予以肯定(13)参见 Shanghai Wells Hanger Co.,Ltd.v.United States,No.15-00103(Ct.Int’l Trade 2017).。
三、《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在美国反倾销行政程序中的适用缘起
(一)问题起因——美国对华反倾销程序中替代价值核算的困难性
对于我国企业产品,美国商务部需要另行寻找合理可用数据对被调查企业某一生产要素下的成本、费用等项目进行替代价值计算,作为倾销认定的一部分。尽管自行寻找可用信息并进行替代价值核算给予了美国商务部自由裁量的广泛空间,然而现实中寻找一个能够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选择一个能够反映中国企业真实贸易经验的替代数据源是非常困难的。正如鄄城康泰案中,美国商务部指出:“由于没有一个潜在的替代国具有与中国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包含对所有生产要素进行估值的数据。”(14)参见 Juancheng Kangtai Chem.Co.v.United States,No.14-00056(Ct.Int’l Trade 2017)。这也使得美国商务部在对华反倾销程序中寻找“特定数据”的这一可用路径逐渐成为一种不可能。事实上,目前所有适用《营商环境报告》数据作为替代价值核算基础的案件,都是将中国企业作为被调查企业。可以理解为,《营商环境报告》其实是美国商务部“特意”为中国企业寻找的数据。
(二)直接原因——《营商环境报告》数据适用的可行性
在面临上述困难局面后,美国商务部开始从全球寻找对华反倾销替代价值核算的数据源,而最终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数据被商务部锁定。
《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区分市场(国家或地区),具有一般性(代表广泛市场平均值),公开发布(任何国家、组织、个人都可以获得并加以利用),并设置了11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执行合同”“跨境贸易”“办理破产”“劳动力市场监管”,而正是“跨境贸易”项下的二级指标为美国商务部反倾销替代价值核算提供了相应的基础数据。上文提到的美国商务部对经纪和处理成本的替代价值核算,主要就是依据“跨境贸易”项下的成本项目(包括边界合规和单证合规)。如表1和表2所示(15)参见世行营商环境官网.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2019-11-25)。

表1 当前“跨境贸易”项下的二级指标体系

表2 进出口时间和成本指标(16)成本指标是对一个约6.1米(20英尺)的集装箱所征收的费用,参见文献[2]。 所包含内容
近年来,《营商环境报告》的指标体系与所涉经济体数量一直处于变动与扩张状态[3],这意味着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国家或地区参与至《营商环境报告》的指标评估。《营商环境报告》的评估体系(主要是具体评估内容)也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跨境贸易指标下也有可能会产生更多项目可用于美国商务部反倾销核算。不仅如此,《营商环境报告》本身由世界银行这一权威组织制定,是世界金融领域公认的国际最高标准之一。因此,理论上,《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完全可以被用作替代价值核算的基础数据。
(三)附带因素——避免诉辩矛盾复杂化,提高行政调查简易性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对华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频率逐步提升[4],不仅有反倾销、反补贴,还出现反规避、337调查、301调查,以及动用201条款限制产品进入等[5],我国政府与企业也相应地实施了一系列的贸易反制措施。贸易反制措施可以理解为出口国用于反制进口国贸易保护措施、防止进口国不合理的贸易保护措施损害出口国企业利益的行为,主要包含3个维度:(1)出口国行政措施;(2)国际组织司法审查措施;(3)进口国司法审查措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属于进口国司法审查措施,由被施加行政制裁的出口国企业提起,相比行政措施而言适用更加直接也较为频繁,因而在贸易反制措施中占有重要地位[6]。近年,由我国企业直接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案件,胜诉率已接近50%——2017年,USCIT发布了173件受理案件,中国大陆企业为原告或共同原告的有49件,胜诉23件;2018年,USCIT发布了182件受理案件,中国大陆企业为原告或共同原告的有41件,胜诉19件(17)参见 United States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https://www.cit.uscourts.gov/slip-opinions-year,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0月8日。。尽管胜诉不等同于免于承担反倾销税,但有效防止了美国商务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美国方面面对逐渐增加的案件数量与愈发复杂的案情调查,再加上数轮甚至数十轮的行政复审,也面临着行政、司法资源紧张的问题。而美国司法权在历史上就有过基于节省行政资源、提高行政便利性的考量而向行政权让步的做法,最典型的就是美国行政法中的“谢弗朗强尊重”,要求司法解释让位于行政解释[7]。因此,在现实困境与历史传统的双重作用下,美国商务部选择《营商环境报告》数据作为最佳可用信息,且USCIT对这一做法予以全盘肯定也便不难理解了。
目前看来,美国商务部在对华反倾销中适用《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的做法从过去的两步简化为一步,即免去了替代国酌选后的重要步骤——美国商务部无需进一步寻找该替代国的可用一般数据或特定数据,只需确定哪一国家或地区的世行数据可用即可,这对于加强美国商务部的行政便捷性或简易性大有裨益。而对于法院而言,认可《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在维护本国行政机关、提高其行政效率的同时,也可以有效避免诉辩矛盾的复杂化——原被告双方无需就某一具体数据适用的合理性展开深入调查并进行长篇辩论,法院也免去了相应的事实与法律审查。
(四)根本原因——替代国制度及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认定的不合理性
《美国联邦法典》第19编第1677节b条(C)(1)项适用的前提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向美国出口产品。此时,如果商务部根据已经获得的信息仍不能决定其正常价值,将根据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价格来确定替代价值,包括综合费用、利润、容器和包装的费用等其他费用支出。在美国反倾销法中,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因此美国商务部需要选择合适的替代国,再进一步选择可适用的数据以确定来自中国的被调查商品的正常价值。
从美国反倾销实践来看,当前美国商务部选择替代国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亚洲国家,例如印度、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此外还出现过南非、哥伦比亚、保加利亚、厄瓜多尔等国。一般而言,美国商务部认为这些国家与中国具有经济可比性,是潜在的替代国[8]。但是事实上,这些国家的出口产品在生产工艺、技术、类型、成本、价格等方面很难与中国企业产品有可比性或相似性。例如,微山宏达案中的被调查商品“淡水小龙虾尾肉”,就极少有国家出口;常州天合案中的“光伏产品”也少有国家掌握相关生产技术。由此可见,美国商务部很难寻找到能够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替代国,也很难寻找到能够与我国企业生产经验相似的替代国企业,以印度、泰国等作为替代国其实只是相对“可行”之策。实际上,上文中美国商务部所感叹的那句“没有一个潜在的替代国具有与中国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正反映了替代国规则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认定的不合理性。
目前看来,学界关于美国反倾销法中替代国规则与我国非市场经济地位认定问题的相关讨论颇多,关于这一规定的不合理之处不再赘述[9]。笔者强调的是,实际上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为我国企业带来了替代价值、单独税率等制度负担,也为美国行政机关带来了实践层面的操作难题,对于双方而言均具有不利性。
四、《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在反倾销行政程序中适用的合理性症结
综上所述,《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在反倾销行政程序中的引入既提高了行政调查的效率,又加大了反倾销税收幅度,因而备受美国商务部的青睐。同时,美国商务部又从《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的属性层面阐述了将其作为最佳可用信息的合理性且得到了USCIT的认可,因此单就美国法的角度来看,美国商务部的这一行为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不合法性甚至不合理性。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商务部仅从法律属性角度证明了《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的可适用性,却忽略了该数据本身的局限性以及为克服该缺陷所必须遵从的方法论限度,并与之相悖。
(一)《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的客观局限性
1.标准化案例情境与假设
在标准化案例情境方面,世行数据存在3点局限:第一,世行所设定的标准化案例情形中的规则不能给出对环境的全面描述;第二,标准案例情景所描述的交易指的是某一具体问题,无法代表企业遇到的各类问题;第三,使用标准化案例情境,导致数据范围缩小,只能对所评估领域进行系统化跟进。此外,《营商环境报告》的指标依赖两个假设:第一,所涉企业通常是有限责任公司或同等的法律实体;第二,企业家了解并遵守所适用的规定[10]15。《营商环境报告》承认,《营商环境报告》依法提供的数据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基于事实的洞察之间存在差异[10]16。因此,标准化案例情境与假设所存在的缺陷是《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局限性最为主要的来源之一。美国商务部对于成本等要素的替代价值核算则大量依赖于标准化案例情形。
2.对于“法律”的依赖
《营商环境报告》的数据来源主要是相关法律法规,《营商环境报告》所包含的数据大约有2/3是基于对法律的解读[10]17。尽管法律法规解读的过程中也有受访者的加入,但主要是提供、帮助《营商环境报告》团队发现并了解相关法律法规。而《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对法律法规的依赖存在着一个重大风险,即经济体内如果无法长期、完全、一贯地遵守法律,那么数据的准确性也会受到影响。
3.“实际做法”的个人判断
尽管世行doing business团队与多个参与者进行广泛咨询,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其余数据的评估错误,然而其中许多基于“实际做法”而非文本上的法律所形成的数据会受到受访专家对“实际做法”的个人判断的影响。此时,如果受访者之间存在分歧,《营商环境报告》则将采取“中位值”的方法进行解决。而实际做法中最主要的指标来自费用指标和时间指标,这两项指标都是“跨境贸易”项目下涵盖的二级指标,尤其是时间指标对受访专家个人判断的依赖度极高。
4.对于“时间”的衡量误差
在对于时间的衡量中,《营商环境报告》的方法论假设是企业知晓必要的信息且在办完手续后没有浪费时间进行下一步工作。但事实上,可能存在企业缺乏信息或未能及时跟进的情况,也可能存在企业不理会繁琐的手续从而不及时反馈的情形。因此,对于“时间”的衡量上,从企业方面收回的数据极有可能存在误差。
5.选取城市的非代表性
《营商环境报告》数据侧重于经济体内规模最大的商业城市(对于2013年前人口规模超过1亿的经济体,选取了第一、第二大商业城市),这一做法的主要目的是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因为在大城市开展调查能够更加有效地收集数据,也便于管理。然而,与此同时也导致了数据的代表性降低,这是因为部分经济体内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规模最大的城市难以代表该经济体的整体水平。
6.企业组织形式与规模的非代表性
《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的焦点常常放在具体的企业组织形式上——通常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实体。这一做法一方面是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另一方面,规模较大的企业组织所提供的数据也更为准确详实。因此,《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对于其他的企业比如独资企业、小企业再比如国有企业而言不具有代表性。
(二)《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反倾销适用的方法论悖逆
《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存在以上6个方面的局限性,使其在对外适用上必须遵循特定方法,即应严格限制在“补充性”“比较性”“间接性”使用3种方式之内,从而对数据的重大缺陷予以消解和克服。因此,美国商务部将《营商环境报告》数据适用于反倾销行政程序的做法已然与之相悖。
1.对补充性使用方式的悖逆
《营商环境报告》在数据用途中强调,《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由于范围的局限性,应通过其他信息来源予以补充[10]12。此外,营商环境报告还指出,有17个不同的项目或指数采用《营商环境报告》作为其数据来源,而这些指数的得出通常是将《营商环境报告》数据与来自其他来源的数据进行整合,以便在竞争力等某一特定的总体维度方面对经济体进行评估[10]20。可见,《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的使用最好与其他数据相结合,单一使用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具有片面性,补充性使用才能得出更为全面、正确的结论。因此,美国商务部在需要高度准确性的倾销认定方面,完全依赖《营商环境报告》数据进行替代价值核算的做法显然极其不妥当。
2.对比较性使用方式的悖逆
《营商环境报告》已经指明其数据收集的最终目的是形成指标,并通过横纵向对比帮助评价各个经济体相比于过去的改革状况以及相比于其他经济体的发展状况,从而形成一份具有意义和价值的报告。《营商环境报告》每年发布24 120项指标,为了形成这些指标,《营商环境报告》团队衡量了逾118 000个数据点。《营商环境报告》数据说明的方法论部分指出,《营商环境报告》数据运用标准方法进行采集,这一做法的目的是确保各经济体之间及不同时段的可比性,而这一点正是其方法论的优势所在[10]20。《营商环境报告》提供的定量指标,可将每个经济体的结果与其他189个经济体的结果进行比较[10]22。换言之,这一评估方法之所以合理,是因为世行在各个经济体内使用的数据收集方式是一致的,因此完全可用于相互之间的比较,而如果将各个经济体的数据单独提取出来,其实并不具有绝对的准确性。正如经济学家通过设定统一标准、随机抽取样本的方式进行实验的目的是借助比较的方式验证或得出某一结论,但并不会将其实验中的数据单独抽取直接加以利用。比较性使用,也使得《营商环境报告》数据本身的缺陷被填补,比如,选择规模最大的商业城市如北京、上海、曼谷等尽管无法代表整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但这些代表性城市都是该经济体的最大城市,数据间便具有了可比性,从而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与泰国等其他国家间的营商环境对比。再有,世行指出尽管标准化案例情形存在固有缺陷,然而可比性依然可以确保,将其用作比较性使用可以得出准确结论。因此,该报告是比较视阈下的“评估”,而不是对单一经济体的评价,只有对《营商环境报告》团队收集的数据进行比较性使用,才能得出合理结论。美国商务部单独抽取使用“单个经济体数据”、单独攫取标准化案例情形中的数据用于替代价值核算的做法与世行所强调的数据使用的方法论要求相悖逆,有违该报告的方法论精神。
3.对间接性使用方式的悖逆
世行指明在创立该报告时主要考虑了两种类型的用户: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10]72。因此,对世行《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的实际利用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1)参考与指导。《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的用途:首先是为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和指导。各国政府以其作为国内市场监管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社会改革等的指引与改革成果评价指标。例如为了确保政府机构间的协调,哥伦比亚等国成立了监管改革委员会,将《营商环境报告》指标作为其商业环境改善计划的信息来源。其次是为金融机构与个人的投资活动提供参考与指导。金融机构及个人以《营商环境报告》数据、指标作为各个经济体监管水平、法律制度完备程度、公民履约意识等的反映,从而评估该经济体的投资环境等,作为对外投资等金融活动的依据。(2)理论性研究。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Kristalina Georgieva提出,《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已成为大量科研工作的数据来源,从《营商环境报告》发布时始,使用《营商环境报告》数据撰写的学术论文超过 3 000篇,工作论文数量达7 000篇。此外,大量权威的研究机构将《营商环境报告》数据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础与理论验证的依据。例如,世界经济论坛在全球竞争力指数中采用《营商环境报告》数据来证明竞争力如何成为经济增长的全球性驱动因素。因此,严格意义上,《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的可依赖性理应限缩在参考与指导或理论研究层面。尽管《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具有权威性、可利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doing business小组以特定目标城市为样本、通过随机调查得来的数据,能够被美国商务部直接适用于某一特定企业的某一具体成本项目的替代价值核算。申言之,在如此微小的环节进行数据适用将与企业实际贸易状态间产生较大的偏差。
五、《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在反倾销程序中适用的多维应对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尽管《营商环境报告》数据作为反倾销中替代价值核算基础已经在美国反倾销行政与司法中达成基本共识,但是这一做法存在严重的不合理性。2003年4月,美国经济学家Bruce A.Blonigen发表《美国反倾销自由裁量权惯例的演变》,文中通过经济性分析方法得出了“美国反倾销行政机关过多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是导致倾销幅度上升的主要原因”的结论(18)参见Bruce A.Blonigen,Evolving Discretionary Practices of U.S.A.Antidumping Activity,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April 2003,p.20.。而本文指出《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的适用实际上正是美国商务部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对于这一问题,应当及时关注并积极应对。
(一)微观:转换海外企业的反倾销应诉思路
我国海外企业是美国商务部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直接受害者,应作为第一层面的基础力量,在权利受到不合理侵害时以美国调查机关或美国政府为被告,通过提起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方式,借助美国的相关司法审查制度对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进行控制。这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尽管这一方式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USCIT基于对本国行政部门的维护与对本国贸易的保护,会尽力维持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但从当前司法实践看来,对于较为不合理的行政行为,USCIT大多判决会发回并要求重新作出。
从以往案件来看,对于《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在美国反倾销行政程序中适用的问题,目前所有的海外企业在提请司法审查时都是从这一数据本身的获取方法、专业性、可适用性角度提出质疑,使得美国商务部及USCIT不断通过强调该数据的“代表性”“准确性”“可依赖性”,而一一否决。可见,对于关键性的不合理之处——美国商务部对《营商环境报告》数据适用方法的悖逆,我国海外企业还尚未发现。向USCIT提起司法审查的举措固然值得称赞,但仅就该数据本身提出质疑只能徒劳无功,以败诉收场。因此,海外企业应当及时转变应诉思路,尝试从适用方式角度切入,通过论证《营商环境报告》数据适用的方法论限度,指出美国商务部依赖性、单独性、直接性地使用该数据的严重不合理性。为了强化论述的专业度与严谨度,海外企业还可以寻求《营商环境报告》数据专家的技术支持以形成相关证据,或者请求其作为专家证人直接参与诉讼。
(二)中观:强化美国对华反倾销行政裁量权滥用问题的政府应对
尽管中国在美国法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导致了替代数据问题的出现,但从USCIT的司法判决来看,美方所创设的不合理制度也为自己的法律实施带来了负担,这一制度不具有单方不利性。因此,目前更应关注和警惕的是如何避免美方因为自身的不利性,在实务层面“创制”更多的已突破合理性界限的所谓自由裁量行为。对于美国商务部反倾销行政程序中的自由裁量权控制,我国政府可以从两个层面应对:
第一,政府间谈判与磋商层面。我国政府可以就美国商务部在反倾销程序中的自由裁量权滥用情况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与磋商,以个案为例列举美国商务部的不合理行政行为,而《营商环境报告》数据作为替代数据的不合理适用就可以作为相关例证。这一做法除了应对《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在美国对华反倾销中广泛适用的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要求美国政府关注其行政机关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问题并加强控制。
第二,WTO体制下的争端解决层面。WTO体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DSM),是根据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DSU)专门建立的用于解决世贸组织争端的司法审查制度。当WTO某成员方从事国际经济贸易活动的当事人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WTO另一或多个成员方的行政行为侵害时,既可以选择直接启动国内救济程序也可以选择通过该国政府间接启动DSM。两种程序是相互独立的,相互之间并无层级或隶属关系[11]。目前,WTO争端解决机构(DSB)的审查范围包含法律,以及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抽象行政行为[12],还包括成员国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对于美国商务部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我国政府还可以通过将争端提交至DSB的方式予以审查。
(三)宏观:促进与替代国的跨境贸易以实现营商环境协同发展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建立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目标。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强调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13]。2019年10月23日,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公布,我国的营商环境法治化逐步进展。姜明安教授率先总结了法治政府建设与营商环境改善的8个方面[14]。我国政府对于“营商环境”的重视度逐年提升,优化营商环境已经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经济发展新方略。然而,我国对于世行报告的利用主要是借助其“评价”功能改革我国国内营商环境,而对于《营商环境报告》的关注点则更多地落在指标排名的提升上,是一种“同比”分析,即通过与过去进行对比达到评估改革成效、发掘不足之处的发展目的。
基于《营商环境报告》被美国商务部用于对华反倾销中的这一现实,在注重纵向的国内改革发展的同时,还应横向关注被美国商务部认定为中国的“替代国”的相关改革进程与发展水平,包括印度、泰国、菲律宾、南非、哥伦比亚等国家,以实现“跨境贸易”领域营商环境的协调发展。主要原因在于,替代国在“跨境贸易”领域的营商环境水平的提高,会降低该国企业的平均出口成本(包括边界和单证合规),使得该国的《营商环境报告》成本数据下降。如果美国商务部运用这一数据核算替代成本值,将会降低被调查产品的成本额从而减少倾销幅度认定,这对于我国企业无疑是有利的。
实际上,“营商环境”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提出以及《营商环境报告》这份重量级文件对于“跨境贸易”指标的逐项计分,都将激发各国的主动改良行为(参见表3、表4)。因此,实现跨境贸易领域营商环境的协同发展,本质上还是扩大、加强与这些替代国的贸易交往,组建“经济交往圈”。这一路径也与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总体思路相契合。

表3 我国与“替代国”近两年跨境贸易指标排名与得分变动情况

表4 2020年我国与“替代国”(19)笔者挑选了与中国排名相近的4个国家进行二级指标比较。 跨境贸易下二级指标得分
六、结语
在对非市场经济主体实施的替代国制度之下,美国商务部尽管被赋予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其所选择的替代数据仍应受到“最佳可用”的严格限制。在以往案件中,美国商务部不断强调《营商环境报告》数据具有代表性、准确性、可依赖性,然而实际上,该数据在反倾销程序中并不可用。世行数据并非想象中的完美无缺,而是存在很多的客观缺陷。为此,必须通过比较性使用、补充性使用与间接性使用的方法予以克服。美国商务部截取部分数据直接用于替代价值核算的做法已然与《营商环境报告》数据的方法论精神相悖,是对其自由裁量权的不当滥用。在认识到这一问题之后,需要由浅入深,从企业到政府做好应对,并及时关注这一做法背后的“滥权”警报,防止美国商务部等行政机关出于提高执法效率、化解执法困境的目的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以执行“替代国制度”等美方创设的不公平、不合理的贸易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