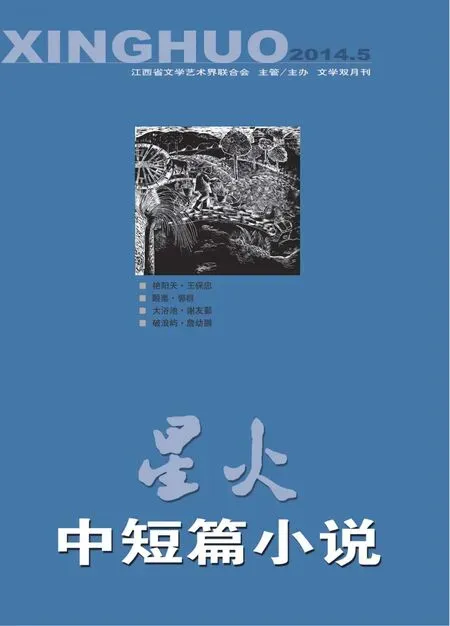我们去稻田收割什么?
2021-09-07范晓波
○ 范晓波
我们在济美牌楼边的水田插秧时,村民们表情喜乐地聚在路边围观,一位大娘笑得合不拢嘴,身子像风中的秧苗一样前俯后仰。
当地驿友说,大娘在给我们笨拙的手艺打分。
在后来的采风中,我意识到村民的好奇可能还有别的缘由—此地很久没人以如此古老的方式栽田了。奉新县是优质大米产地,不少地方已普及机插,无条件租用机械的农户,也基本都以抛秧取代了插秧。
参与AA合种的16人部分是从未下过水田的新手,插秧1.5亩用了近两小时,随后以抛秧的方式对付一块面积稍小的水田,只花了二十来分钟就完工。根部结好泥坨子的秧苗飞镖一样画着优美的弧线一簇簇从空中射落,在倒映着云彩的水田溅起无数欢笑。
在奉新大米育秧基地,一位戴鸭舌帽穿蓝色工装的姑娘讲述“一株水稻的一生”后,熟练地介绍拖拉机、插秧机、烘干机和喷药无人机的效能。起初还以为她是县里安排的专职讲解员,见她亲手操作这些神器后,才反应过来,这位名叫吉兰的80后其实是它们的主人,她靠这些设备,耕种了两万亩稻田。
在当晚的篝火文艺沙龙上,一位来自鄱阳湖平原的60后驿友回忆年轻时种田的艰苦。那时,手握锄头在烈日下面对铺展到天际的农田,心里常冒出这样的感叹:劳动是光荣的,劳动也令人绝望。
吉兰常穿着皮鞋走向田野,有时还会在裤兜里揣瓶三两三,歇息时坐在田头望着潦河上的浮云喝两口思考人生。
现代科技不仅提升了农业的效率,也改变了农人的生活方式。
吉兰的皮肤比大多数公务员和企业白领还白皙,她农忙时开着机器下田干活,农闲时去省城谈单,其他时间在网上收单发货。她还订阅了《星火》杂志加入星火奉新驿,情绪飞扬时也会写点似诗似散文的句子。
吉兰说,她认识的一些外省年轻同道,也是穿着皮鞋种田的。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城市积蓄能量后又回到生养过自己的农村,从前辈手里接过土地,以全新的方式流转经营。他们是新时代的农民,生活情趣和城市里的年轻人并无多大差别。
第三届稻田写诗农耕体验活动,改变了作家们对农业及农民的固有印象,也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的希望。能留住青春养活梦想的土地,才是真正有希望的乡村。
我们用手工栽种收割水稻的做法,在逃离了农耕之苦的人看来更像一种仪式,甚至,会有人觉得它是一种秀。不管他人观感如何,每位参与者都能在当年的星火文学年吃上自己种出的米,从口腔延伸到胸腔的感动带给不谙农事的作家们长久的自豪。我们在稻田里收获的,却远不止这些。
只要星火驿站还在,稻田写诗活动大概率还会一年年举办下去。农业的生产方式在革新,作家对新农村的认知在跟进,我们对土地的敬重对粮食的感恩却不应衰减。
这是人与土地的基本伦理关系,也是乡土文学不变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