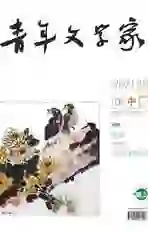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突围
2021-09-05李媛媛
李媛媛
从古至今,女性问题一直是我们社会关注的焦点。因为,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恩格斯说过:“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或社会的妇女解放程度。”旧时的中国封建落后,女性常被看作男性的“附属品”“所有物”,以及传宗接代的工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丝毫没有尊严和话语权可言。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女性更是为了迎合男性的审美标准,残忍地进行“裹足”,强迫自己裹小脚,忍着剧痛也要坚持缠脚,甚至以裹足为荣,裹得越好,意味着将嫁得越好。裹住的虽是脚其实缠住的是女性的思想,没了思想就没有了尊严。如果说,女性的解放从放脚开始,那么真正女性的觉醒,是意识到经济的独立和思想上的“释足”。庐隐对女性进行了新的定义:“不仅做女人,还要做人。”这句话简单而深刻。女性只有有了思想上的独立,才能摆脱封建礼教影响下旧的生活和思维模式。女性解放先驱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的问世,也揭示了女性独立的真谛:“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屋子”和“钱”都是一种隐喻,也就是说女性只有有了独立的空间,有了物质基础,才可以谈及精神独立。物质上的独立,是独立意识产生的先决条件,两者缺一不可。
在庐隐、丁玲、萧红等左翼女性作家笔下先后塑造出许多新女性形象,她们带着女性小说家理想化的审美意识,成为五四时期女性作家女性价值观的载体。如莎菲、梦柯、杜晚香等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新女性强烈的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她们既有才华和智慧,又有对思想解放的强烈向往。她们希望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体现自我价值,作品中传统女性的柔弱、顺从、自卑被新女性的自尊、自爱、自强,充满进取的精神所代替。从安于命运、埋怨命运到改变命运,从逆来顺受的传统女性到自立自强的新女性。但现实终归是残酷的,女性想要真正打破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缚任重而道远。因此,丁玲笔下的诸多女主人公,或多或少经历着思想“释足”艰难的历程。
《莎菲女士的日记》描述的莎菲是一位都市资产阶级新女性。文本中从一开篇对主人公居住的地方展开了一段描述:“对着‘白垩的天花板,感到寂靜可怕。”“屋子”“墙壁”和“天花板”这些空间描写体现出沉重的压抑感。结合空间的描述我们可以联想下现场的情景,这种压抑感不言而喻,而这种压抑感我想正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象征意义的写作手法,是另一种隐喻。大的社会环境是压抑的,那么一定有一部分人会选择无奈、压抑自己,而另一部分人会在压抑环境中选择去“突围”。文本中的莎菲就是这样一个受“五四”影响的新女性,她极其痛恨封建礼教的束缚,她渴望男女平等,追求爱情自由。因此,她不停地更换住所,感情上在凌吉士和苇弟之间犹豫不决,这些都体现出“五四”新女性在爱情、欲望中的徘徊和挣扎。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中评论莎菲时写道:“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绝叫者。莎菲女士是一位旧礼教的叛逆者,她热爱着又蔑视着她怯弱矛盾的灰色求爱者,在游戏式的恋爱过程中,她终于从腼腆拘束的心理摆脱,从被动到主动,在吻了富有‘魅力的红唇后,她就一脚踢开那不值得恋爱,离开了爱虚伪的青年。这种大胆的描写,至少在当时中国女性作家中写作手法是大胆的。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矛盾心理的代表者。”丁玲笔下塑造的女主人公形象有着共同特点: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梦坷》《阿毛姑娘》中梦坷、阿毛姑娘,看似不一样的女性角色,但其思想追求是一致的。她们有自己的追求和欲望,虽在实际生活中总是处处碰壁,但并不影响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阿毛姑娘不是“知识女性”,随着自己眼界的打开思想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她开始对生活有了新的“想法”,对想要的生活有了追求,开始在旧生活中展望,开始对新生活憧憬。她不再甘愿听从于丈夫,不再甘心平庸的生活,她渴望尊重和新生。“也许早就不是从前的阿毛了,这是她唯一的损失。她懂得了是什么东西把同样的人分成了许多阶级”“她对于每天逛山的男人,细心去辨认,看是属于哪一类的男人,而对于那穿着阔气的,气宇轩昂的则加以无限的崇敬”。她大胆地梦想着能有个体贴她、爱她、又不侮辱她的男人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她甚至宁可忍受丈夫施加给她的皮肉之苦也要去国立艺术院当模特。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其结果必然是悲剧性的。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阿毛姑娘这种大胆的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实中只会让她身心陷入更加痛苦的境地。但阿毛姑娘始终和残酷的现实抗衡最终以死来“反抗”。她活得真实而通透:要真爱、要温暖、要自由,这也是新女性的墓志铭。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不仅打造出新女性形象,而且作者从女性的视角、女性的心理、女性的笔触来感受“释足”过程中强烈的爱与沉重的叹息,是美也是悲。像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 :“女人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在痛苦和骄傲中去放弃传统。”文本中在描写女主渴望见到凌吉士时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我要那样东西,我还不愿去取得,我务必想方设法让他自己送来。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地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吻呢。我简直癫了,反反复复只想着我要施行手段的步骤,我简直癫了。”连续两个“癫”字的运用,将女性对于爱的渴望大胆地揭示出来,这种大胆、直白的自我剖析,展现了女子强烈渴望追爱的心理。摒弃以男性的目光去审视女性的传统叙事模式,将女性从“被述者”转变为“自述者”,从“被塑”的传统形象转变为“自塑”的独立形象。从男性传统的视角看,女性形象是被扭曲的、消极的、片面化的。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做的一次轰动性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将“娜拉出走”的问题与五四运动后中国新女性的问题相联系。“娜拉”是《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生活在美满家庭里的娜拉,有着可爱的孩子和可靠的丈夫,只是有一天她竟忽然醒悟:她觉得自己是丈夫的玩偶,孩子们又是她的玩偶,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她的个人价值在哪里?为了找寻答案她毅然地决定离家出走。这像罗生门事件一样没有结局和答案,人们不禁会想娜拉走后会怎么样呢?她离开丈夫的庇护该如何生存?过着怎样的生活?靠什么生活?对于娜拉走后的结局,鲁迅认为: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对于“出走”和“堕落”,我想“出走”是娜拉想靠自己独立地生活,找回属于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鲁迅先生所说的“堕落”则是指娜拉迫于生计,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女性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很难独立生活,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种断言,对女性来说不免有些消极和片面。而丁玲笔下,则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发现女性新的命运历程。莎菲敢于袒露自己对男性的爱和对性爱的幻想,在日记中真实记录自己的想法:“假使有那么一日,能获得骑士一般的人儿温柔的抚摸,随便他的手尖触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牺牲一切,我也肯。”这段描述可以看出莎菲愿意为了爱赴汤蹈火,在爱情中,她追求的是灵与肉的统一,这体现出“五四”新女性对爱情最朴素的愿望。随着莎菲与凌吉士相处的深入,她逐渐发觉凌吉士美丽的外表之下有着一个低俗的灵魂,她的心里产生了剧烈的思想斗争。虽然莎菲内心里鄙视凌吉士,厌恶凌吉士腐败的生活作风和享乐主义,但实际生活中她又接受着凌吉士的挑逗与戏弄,这也确实让莎菲感受到甜蜜。莎菲虽沉寂在幸福中,但她并没有完全迷失自己。莎菲一直在感情与理智中徘徊。在日记中她反问自己:“真的单凭一种骑士般的风度,就能使我堕落到如此地步吗?”此后一次次心理矛盾却总是无法抑制自己爱的欲望,因凌吉士的到来而雀跃,但随后的失落感越来越强烈。感情和理性的来回拉扯,最终让她回归理智。我想女性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心理,根本在于对自尊心的维护对自我的保护,可以内在柔弱但外在必须刚强。
从梦坷、莎菲、阿毛姑娘一直到贞贞,她们虽然具有各自的人格特点,但也有着共同点,那就是:无论外界环境如何,无论她们何种身份,她们都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女性最珍贵的品质莫过于精神上的自立与自强,敢于做自己。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一文中自析到“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作者从女性的视角描写着笔下的人物,用女性的心灵感受着小说的人物,用女性的笔触描写着主人公。像一只滴血的鸟,为了模糊而又确实存在的幸福不惜遍体鳞伤,甚至死亡。那么,女性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 在《杜晚香》中隐约找到了答案。杜晚香,在后母的白眼中长大,却像“一枝红杏”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对墙外世界的好奇心。来到北大荒后,她强烈体会到生活的激情、工作的快乐和被人需要的幸福,让她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从女性视角看,杜晚香的故事更像是“冬天里的一抹阳光”。每个女性都有着自己的追求,无论结果圆满与否,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个人思想的独立,都是女性思想上的进步,这种顽强抗争的精神更是女性身上难能可贵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