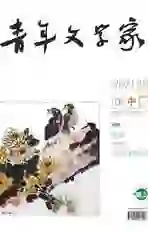从《秋颂》看济慈的消极感受力
2021-09-05贺婷婷
贺婷婷
济慈是英国诗坛上鲜有的天才诗人,其诗歌、诗论亦如璀璨的明星在天宇中熠熠生辉。他创作的诗篇《恩底弥翁》《秋颂》《夜莺颂》《拉弥亚》等篇篇誉满人间;同时,他又是一个十分重视传统的人,一直吸收着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等人身上的英国诗歌传统。他的诗论散见于他给亲朋好友的书信中。其中,最为著名而影响深远的诗论是他的“消极感受力”(国内有多种版本的翻译:周珏良将之译作“天然接受力”和“反面感受力”,梁实秋先生译作“否定的才能”,袁可嘉先生翻译为“消极的才能”,等等。本文所采用的是王若昕翻译的“消极感受力”)。他认为一个诗人要想有所成就,成为一个像莎士比亚那样伟大的诗人,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要有“消极感受力”。作为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这是一种独特而迥异于其他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理论。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比较注重情感的表达,对个人思想和风格的表达几乎成为一种风尚,而济慈却认为真正的诗人是无个性的,诗人的状态是一种无我的状态,是一种与客观事物平等相处、和谐沟通的状态,而不是诗人作为主体高高在上、主宰一切的强势。济慈这种超然的“消极感受力”在他的著名颂诗《秋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济慈的消极感受力
“消极感受力”是济慈在1817年12月28日写给其兄弟乔治和托马斯的书信中提出的,直接的表述只有短短的一段。王若昕将其译为:“一些事情开始在我的思想上对号入座,立刻使我想到是什么品质造就了一个有成就的人,特别是在文学方面。莎士比亚如此多地拥有这种品质—我指的是消极感受力。即是说,一个人能够经受不安、迷惘、疑惑,而不是烦躁地务求事实和原因—对于一个大诗人来说,对美的感觉压倒了一切其他的考虑,或者更确切地说,置其他一切考虑于不顾。”这一观点道出了一种超然的品质,也阐述了一种状态和境界,这种状态我们可以不确切地称之为“一知半解”的困顿状态。事实上,对这一诗论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进行探析。
一方面,这里的“消极”是一种积极心态、情绪的对应物。狂欢与消沉可以说是两种极端的情绪。欢快、愉悦等美好的情感能够让人记忆深刻,失意、困顿等消沉的情绪亦会令人铭记于心。不同的是,快乐的记忆因美好而让人永远珍藏,消沉的情绪却因痛苦而让人心刻下伤痕,人们往往习惯选择遗忘。前者让人感受到幸福的美感,后者却令人苦不堪言,美感荡然无存。难道消沉、痛苦注定毫无美感可言吗?并非如此,事实上消沉、困顿的境遇更易于氤氲一种特殊的美感,只是这种美感常常因为人们的理性和世俗需求而遭到忽略。济慈所赞赏的“消极感受力”是一种特殊的感知能力,这种能力能够让人撇开世俗理性的生存与需求欲望,而去感受事物本身,感受它的真与美。另一方面,这种不安的、迷惘的、疑惑的“消极感受力”并不是我们平时意义上“积极”的对立面,而是一种有别于用理性和逻辑性的思维方式去对待诗歌创作的主体介入的方式。在对待诗歌创作中的客体时,他不赞成用理智去分析、去判断,急于探究事物的原因和本质。这是一种更加全面、更加科学,甚至包含前一方面的解说,无论怎样,这两者都透射与“消极感受力”的相关项,亦即与“人”相对应的客观对象(这里的“人”一般意义上,我们称之为“主体”,与之相对应的“客观事物”习惯称之为“客体”)。因此,要想达到“一知半解”的困顿状态,首先我们应学会处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消极感受力中体现的主客体的关系与传统不同。传统方法把世界万物看成是与人处于彼此外在的关系之中,并且以我为主(体),以他人他物为客(体),主体凭着认识事物(客体)的本质、规律性以征服客体,使客体为我所用,消极感受力恰恰反对“征服客体,使客体为我所用”的方式,而强调尊重客体。这里的“消极”也可以理解为相较于传统主客体关系中,主体作为征服者的“积极”而言,济慈将主体的积极性消解,一再强调不要急于求真务实,便是为了使主体和客体处于平衡状态,处于平等地位,这样主体和客体才能平等对话,才能进入一知半解的状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即可领略到真正的美感,还需要作为主体的人与客体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这种“心理距离”不宜过远或过近,过远感知则成了一种漠视,过近则会产生不自然的压迫感,只有创作主体与对象保持一种“最佳心理距离”时,创作主体与客体才会处于平等的地位,处于无功利的审美状态。达到这一审美状态后,想象力就要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想象力才能破除理性思维的枷锁,将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存在的或不存在的一切事物联系起来,實现对创作客体的创造整合,使创作客体可以打破常规达到自由的状态。诗人的品质在于“感受”,接受并尊重与对象交流时的种种体验,而后通过情感的方式呈现出来。由此可见,济慈视情感为连接创作主体和客体的桥梁。如果没有情感的催化,审美主体和客体还只是互相尊重的状态,只有通过情感的融合才能达到物我不分的审美状态,才能实现物我交融,达到“真即是美,美即是真”,美感压倒一切的境界。因此,基于济慈个人对消极感受力的阐释及众多学者的解读,我们可以知道,消极感受力涉及主体、客体、想象力与情感等多方面交融的共同作用。
二、从《秋颂》看济慈的消极感受力
《秋颂》是济慈深受世人喜爱的著名诗作之一。每当秋收季节,夜幕开始降临,农人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落日的余晖里,田间的草丛开始响起了夜幕的赞歌。每当这个时候,人们总会想起济慈,想起那个美的化身,想起他的《蝈蝈与蛐蛐》,更想起他的《秋颂》。它不仅给人一种纯美的享受,更体现了诗人淡化创作主体色彩的消极感受力的诗学理念。
消极感受力是一种诗人应具备的珍贵品质,获得这种特殊能力的前提是处理好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应打破传统理性思维下的征服、奴役客体并使之为自我服务的惯性模式,给予客体足够的尊重和自由,与之保持和谐的平等关系,并与之保持一定距离,这种距离不能远到主体漠视客体,也不能近到主体对客体构成压迫感,而是找到二者的平衡点使之达到“最佳心理距离”。在《秋颂》这首诗中,诗人赋予他的描写对象以绝对的主体性。第一节中“……你和成熟的太阳成为友伴/你们密谋用累累的珠球/缀满屋檐下的葡萄藤蔓……”,此时“秋”像一位强大的谋略者俏皮地与太阳“密谋”,用自己神奇的力量,装扮着人间大地:透明的珠球缀满葡萄藤,苹果树压弯了腰,葫芦胀大了肚皮,晚开的花为蜜蜂绽开了笑颜。第二节中“秋”化身为一位漫游的女神。谷仓、田野里到处都是她的身影,她时而坐在打麦场上,时而倒卧在田垄,时而歇在花旁,她会让发丝随风轻扬,会为罂粟花香沉迷,会耐心地瞧着徐徐滴下的酒浆。第三节中,到了傍晚,世界开始奏响属于她的乐章,小飞虫、蟋蟀、知更鸟、群羊、燕子,都在为女神的到来引吭高歌。整个过程中“秋”都是主动地在展示她的风情与韵味,诗人给予了客体足够的主动权,这就是主体与客体保持适当“心理距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