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虫三章
2021-09-02王玲花
王玲花
季节入夏,草木并秀,万物丰满。鸟虫们在盛大的铺排里,气象万千。
立夏·蝼蛄
立,虽是一个慢动作,不会给你旗帜鲜明的提醒,但突然有那么一天,你猛一抬头,树上已挂起了一串串槐花,你会感到,那浓稠的叶片里,正在蓄谋一场起义。
我所在的故乡,暑气还在路上,但夏的火爆脾气已露端倪,摆下了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孟夏之初,天地始交,草木并秀,虫鸣蝶飞,万物见了风地长,它们都将向着丰满富饶挺进。
最先憋不住的是蝼蛄和蚯蚓。你看,寂寂夜晚,朗朗月下,蝼蛄清嗓亮喉,唱起了歌谣;茫茫田野,炎炎热里,蚯蚓弓腰曲身,走起了舞步。连《逸周书·时讯解》都说:“立夏之日,蝼蝈鸣。又五日,蚯蚓出。”那又五日呢,王瓜的藤蔓就要蹭蹭蹭,往上爬了。
蝼蛄,经历了漫长的冬眠,在春风里迅速长,立夏时,已至芳华。饱满的荷尔蒙在雄蝼蛄的心里汹涌、翻滚、蔓延,实在憋不住了,就清清嗓子,“咕咕——咕咕——”地唱起了情歌。雌蝼蛄就会含羞带娇地爬出来,偎在雄蝼蛄身旁,一场情事在阔达的土地上生动展开。亲热缠绵的结果,是繁衍了后代,延续了香火。
这下,蝼蛄们高兴了,但庄稼不高兴,爷爷就更不高兴了。
月下小院,爷爷在乘凉。屋子背后的田野,有黑和寂静做了背景,那些蝼蛄的叫声格外地清冽明亮。在声声起伏里,爷爷猛吸一口旱烟,脸上的愁苦在火星里,一道一道,肆意成流,然后,就是一声长长的叹息,然后,就说“听蝲蝲蛄叫,就不种庄稼啦——”那个“啦”字拖了好长好长的尾音。
看我不解,爷爷说,这满地的蝼蛄,种了也白种。爷爷虽这么说,但总没有让一块地闲着。地是爷爷的命根子,让它繁盛延续是爷爷一辈子在做的功课。
有经验给爷爷撑腰,爷爷自有法子对付它们。比如施肥翻地,比如大水灌溉,再比如爷爷锄地的时候,看到拱起来弯弯曲曲的蝼蛄隧道,便挥起大锄砍下。一锄下去,洞毁穴塌,蝼蛄们魂飞魄散,如惊弓之鸟,四下里逃窜。爷爷迅速抓起它们,放入随身带着的瓶里。晚饭时,我就有美味入口了,那脆脆的咀嚼,喷喷的香,对很少能尝到肉星子的童年无疑是一份慰藉。每每想起,那香味隔着久远的时光还能飘过来。
夏的底子,永远是盛大隆重的铺排。夏的序幕一开,天看着一日胜似一日地热了,胃口淡下去了,可聪明的人们总会变着法子,让能吃的不能吃的,瞬间变成美味。我在一条小吃街上,遇到蝼蛄,是三十年后的事了。它们已被码放在油锅旁,标本一样地,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成为串,油锅里一炸,黄灿灿的,有着琥珀一样的成色。不必说那浩大浓稠的高蛋白,也不必说那入骨入髓的香了,单是那晶莹剔透的色,就会让人垂涎欲滴,不吃都不行了。
这蝼蛄该吃,谁让它是害虫呢?就连危害的手段都不是谦谦君子做派,你看,蝗虫光天化日之下不惧不窘,理直气壮地吃叶啃茎。而蝼蛄呢,躲在暗中,钻到地表下,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只咬植物根部,即使块茎植物也都不放过,又毒辣又猖狂。植物还没来得及喘息就死了,死都不知是怎么死的呢。
蝼蛄,家乡人也叫蝲蝲蛄,土狗。这种小昆虫灰头土脸,其貌不扬:头小而锥,身粗而短,一块甲片扣在头与背之间,翅从甲片里伸出,贴在背上。六足两须两尾,前足似铲,后足发达,中足短小,尾须细短,有小刺排列,似两把小刷。背部茶褐色,腹部灰黄色。那样子一点也不亮眼。
李时珍曾有记录∶蝼蛄穴土而居,有短翅四足。雄者善鸣而飞,雌者腹大羽小,不善飞翔。
蝼蛄有翅,按说能飞。可从小陪着庄稼长大的我,从不曾见过飞着的蝼蛄。爷爷说,蝼蛄一生,只有两次飞翔,都为搬家。炎炎夏日,潮湿润泽之地,池塘沟渠附近,都备受它青睐,家安下来,心也就落地了。冬天一来了,它就迫不及待在找干燥之地,安营扎寨。春暖花开之时,它又恋念那些湿润之地了。这中间的搬来移去,都要靠着飞翔。其余时候,那翅膀,就成了装饰或者摆设。
蝼蛄其貌不扬,还迫害庄稼,难怪在唐诗宋词里遭排斥。它只能躲在地底下,看燕舞、听莺歌,羡那青草池塘处处蛙,慕那点水蜻蜓款款飞。也就《古诗十九首》里,让它露了一下脸:“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还把它写得凄凄惨惨,悲鸣不断,还不能让它当主角,只做凛冽的背景来陪衬、渲染和烘托。
齐白石老先生倒是喜欢它。画作里,它虽不像虾那样霸气,倒也频频亮相。无论《蝼蛄茨草》《蝼蛄栀子》,还是《红蓼蝼蛄》,都是硕大茂盛的植物下,一只小而单薄的蝼蛄,贴服在地面。我不知道在这鲜明而凛冽的比对里,齐老先生在隐喻什么?只是觉得,那些盈满纸张的茂盛,瞬间就会枯萎。
我记住了一个传说,我记住不是因为传说的主人公身份的显赫,而是因这小而不起眼的蝼蛄,它无意间的一个举动,改写了历史。显赫的人物身上,总是有传说营造出的神秘和传奇。当年,王莽追赶刘秀,刘秀跑了好久,又困又饿,体力不支,在荒草中隐藏。实在太累了,迷迷糊糊睡着了。睡意正酣,突然,感觉身子底下有东西在动。他随手一摸,是一个虫子,他很生气,把它撕成两截,扔一边。一抬头,就看到了远处的追兵。好险呀!好险!那一瞬,感激和愧疚同时涌上了刘秀的心头。他迅疾找了一段狗尾草节,把折断的虫子连接在一起。它对虫子说,等我做了皇帝,我封你每块地拱三垄。可这虫子偏偏听错,把拱三垄听为遍地拱了。从此后,虫子就开始遍地拱。这虫子,就是蝼蛄。
记起这个故事时,我仿佛又看到了那月色,旱烟袋,又听到了蝼蛄的欢鸣,爷爷的悲叹。时光正像这蝼蛄,即使躲在深处,总也能让人清晰记起它的样子。记起它的时候,我又闻到了烤蝼蛄的味道,夏的味道。
当下,这夏就要漫上来了,我会遇到小吃街上的蝼蛄。中年了,口味渐渐淡了下来,我想,遇到时,还是不吃了吧。
小暑·飞蛾
夜幕落下,月亮清亮亮地挂在中天,热气像个玩累了的孩子,坐在那里轻微地喘气。屋檐下,一盏电灯贴墙而挂,像黑暗里举起的火炬,傲娇地发出魅惑的光芒。
这时候,屋子热得待不下去,人不安,是要到院子里,爷爷是要借着月光和蒲扇,在一杯又一杯的茶水里,等夜色凉下来。我呢,在灯光下,看着飞蛾扑火,全然忘记了热。
一只飞蛾,扑闪着翅膀,唱着快乐的歌,向着明亮的诱惑,扑上去,奋不顾身,毅然决绝。然后,翅膀折断,仓皇而落。又一只,扑上去,然后落下。生命被灯撞出耀眼的火花,那瞬间的怒放,绚烂、惊艳、辉煌。
没过多久,地上密密一层,像飘散的落叶,干枯、悲凉。也像璀璨的烟花,落地无声,转瞬即逝。小小飞蛾,芳华的生命,就此冻结。小暑的天气,任凭用怎样的热烈,也喊不回已走远的生命。凉下来的暑气中,昂扬一首悲壮的歌。我不由可怜起这些小飞蛾。
每天早晨,爷爷都会收拾昨晚飞蛾扑火后的狼藉战场,直到整个夏季结束。
明明知道陷阱重重,却要跳,义无反顾地跳。明明看到同类倒下,还要前仆后继。真傻,也真蠢!可是,如果没有了光和热,世界该将会多冷漠?小小飞蛾,粉身碎骨,可是为了血色理想?决裂壮举,可是为了涅槃重生?
其实不然,飞蛾扑火,本意不是要去扑火,是把灯光或者火光,错当月光了。飞蛾夜间飞行,月亮就是指引它飞行路径的灯塔。可它呢,偏偏眼睛又不好使,又记不清月亮的样子,是不是月亮,都认为是月亮,结果,折了翅膀,丢了命。
一时错念,断送了卿卿性命。本想怒放,怎奈凋零,本觉那里是幸福的巅峰,却原来,是寒森森的无底深渊。
飞蛾是蝴蝶的姊妹,可命运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你看,它长得小小矮矮,瘦瘦弱弱,一件枯叶一样的羽衣,老气横秋,暮气袭了一重又一重。既没有蝴蝶璀璨华丽的羽衣,也没有蝴蝶端庄优雅的长相,在气质上,更要矮下去一大截。
像蝶,却不恋花。毕竟不是蝶,没有美丽的貌和绚丽的衣,娇艳的花怎会喜欢?
蝴蝶是太阳的宠儿,飞蛾却不是月亮的最爱。这长相连月亮也看不上,所以,它要去追,不停地追,循着那一丝丝光明,追啊追。因为缺少,所以渴求;因为爱,所以醉。哪怕是死呢,也要怒放一次。
它跟蚕一样要作茧自缚,化茧成蝶,可哪里有蚕的待遇?蚕一直被赞誉之声高高抬举,它呢,却处处遭人嫌弃,让人厌。它要么标本一样地黏在墙上,要么枯叶一般地沾在姑姑晾晒的衣服上,还留下一层黏糊糊的粉末。姑姑看到,就会厌恶地拍打,嘴里不停地说,快点离开!讨厌的家伙!有时,我想,如果是蝴蝶落在姑姑晾晒的衣服上,姑姑又会怎样呢?那一定是又惊又喜,又爱又恋了。
它又蠢又丑,还懒。它从来不筑巢,把卵随便产在树枝、叶片,甚至是枯草上,即使是过冬,也要寄宿,一生都在寄宿。长大后的飞蛾,成天忙于繁殖,寿命很短,根本没空筑巢,也懒得筑,反正有地方宿就可。
阔大的昆虫领域,种类繁多,琳琅满目,这不起眼的飞蛾,太容易让人忽略了。人们记住它,大多是因为“飞蛾扑火”这个成语,《辞源》把其喻为自投死地。《梁书》上说:“如飞蛾之赴火,岂焚身之可郄。”这飞蛾不会曲折,不善婉,一条道要走到黑,真正是又蠢又憨。
“飞蛾爱灯非恶灯,奋翼扑明甘自陨。”它要去奔赴,谁又能拿它怎么样?
都说是爱情一来,就会晕头,就会醉。张爱玲,出身名门,风华绝代,才情横溢,本该仰起头来活着才对。可自从遇到那个到处拈花惹草的胡兰成,就晕头,就醉,不惜把自己低到尘埃里,说什么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心里是欢喜的。到头来,折断翅膀,伤了心,让自己的爱情袍子上爬满了蚤子。不是试过,怎么会知艳阳高照后,还有暴风骤雨,可试过后,你还是原来的那个你吗?那决绝和凛冽里,有着飞蛾的秉性和气息。
谁说痴情是女人的专属?金岳霖,堂堂七尺儿郎,林徽因一个笑声就把他点亮。四月天啊,那么明媚,那么美,白白的牙齿,浅浅的笑,还有指尖那淡淡的味道,秘而不宣的含蓄,骨子里开出的罂粟花。他痴,他迷,她走到哪里,他便到哪里,哪怕是隔着云端,哪怕是终身不娶,你若安好,我便晴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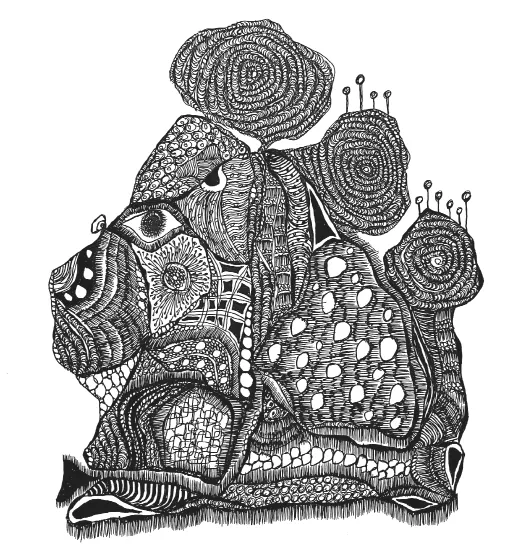
林徽因去世后,他还为她过生日,并拿出照片,说,今天是徽因生日。
得不到,不怨不恨,终身不娶,孤抱晚年,认了。金岳霖是飞蛾,却要一棵树上吊死,吊死,也甘心。
弘一法师,是飞蛾。气象万千的烟火不要,浓稠甜蜜的爱情不要,骨血牵扯的亲情不要,就要佛门。孤独清苦,粗茶陋室,又算得了什么?皈依,皈依,向着心中的佛光,走下去,一直走下去。面对妻儿的苦苦挽留,头也不回,不回了。
曾有人问我,你写作劳心费神,耗时折寿,还不赚钱,为了什么?我苦苦一笑,算是作答。心想,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又一想,自己何尝不是飞蛾一只,向着那光,一意孤行地扑上去,又执拗又凛冽。
想来,这飞蛾,就是雪花一朵,也是流星一颗,怎可抵挡这凄凉薄情的世间和漫漫冷酷的黑夜,冷艳素雅中,总有转瞬即逝的些许悲凉。凋零了,化作一滴清泪,化作烟尘,化作灰。明天,太阳又照样升起,天还会黑下来。
这暑气,这热天,给飞蛾搭建了涅槃重生的背景,飞蛾破茧化蝶,迎来了它生命的辉煌。可同样是这热和光,给了它一意孤行的决绝,璀璨的怒放,还有生命的凋零。
可,它会生生不息。明年的暑天,又会在老院的灯下,奋翼扑火,陨落,呼啦啦铺满地。那地上,总也有一种精神在发出光芒。
大暑·萤火虫
大暑天,夜色升起来,热的火爆脾性也降了不少。
屋子里还是热,人待不住,爷爷撮条马扎,坐在院子里的月影里,摇把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全家人闲谈。蚊虫开始肆虐,父亲抱来麦秸秆,燃起一堆火驱蚊。
这个时候,对我诱惑最大的就是屋后的池塘。那里有天空陨落的星星,也盛放着我好多亮烈的萤事。
池塘,不长荷,只长水草野花之类。青蛙鱼儿之类倒是不少。天一黑,蛙声虫声就从荷塘里、草叶上四下里漫开、飞扬,像开一场音乐会。在盛大的背景里,萤火虫提着灯盏,和着节拍,亦步亦舞,登场了。
家乡人把萤火虫叫亮亮虫。
黑暗里、池塘上,萤火点点、萤星盏盏,流萤舞步缓慢,似乎带了醉意,看上去,像荧光棒,也像小灯笼,但我觉得,它们更像是夏夜的眼睛。
南朝萧泽说萤火虫是“腾空类星陨,拂树若生花。”也说是“屏疑神火照,帘似夜珠明。”暗夜里,萤火虫类星陨,若生花。神火照,夜珠明,这若隐若现,忽明忽暗,让夏夜摇曳生姿的,这小小萤火虫算是其一。
《诗经》里记载:“町疃鹿场,熠耀宵行”,宵行,就是萤火虫,这叫法,形象,像夜行的归人。身心疲惫的征夫,听到呦呦鹿鸣,看到闪闪萤火虫,思乡恋家之情瞬间膨胀,漫漫黑夜,漆漆征途,那闪闪萤火虫,可是家中伊人期待的眼睛?
三奶说,天上的星星就是地上的亮亮虫变的,亮亮虫就是天上落下的星星。我对此曾深信不疑,站在池边,看一眼曼舞的萤火虫,看一眼闪烁着的星星,然后,就摇头,就否定。还是不变来变去的好,星星是天空的眼睛,萤火虫是大地的眼睛,哪个少了,都不好。那时,心里装满童话。装满好,见不得一点瑕疵和残缺。星星也罢,萤火虫也罢,只要发自己的光,散自己的热,天上地下的,除了位置的区别,没有什么两样。
萤火虫的光并不亮,但如果是许多光聚集到一起呢?我想,应该像灯盏,似火光,不然,晋之车胤在家贫,不得油的情况下,就不会捉了萤,囊起来当灯,夜读了。
当然,我们的兴趣更在捉萤火虫。这是乡下孩子的特长,汗衫一脱,拿在手中,慢慢靠近萤火虫,然后,猛一甩,汗衫像展开的小旗。再猛一收,萤火虫便被兜在汗衫里,成了囊中之物。已有女孩子拿了卷成桶圈的草叶来,小小萤火虫,一闪一闪,绿草叶瞬间镀了光。我们捧在手里,像捧着灯盏,也像捧着光明和希望。
或者把萤火虫装到一只瓶子里,暗夜里,它们一闪一闪,小星星一般,玩腻了,就把瓶盖打开,禁锢久了的萤火虫,“哗啦”一下飞出来,像一条流动的光带,又耀眼又明媚。有时,把装有萤火虫的瓶子放到家中当油灯,我们睡了,它还醒着。等猛然记起瓶中的萤火虫,天已大亮,萤火虫早没了气息。
“银烛秋光冷华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是宫女在玩萤火虫。黑漆漆的夜里,她望穿秋水,不见归人,却望见了这闪闪萤火虫,她轻启莲步,随手拿起小扇去扑。这轻扑,是雅了不少,却也让一颗童心瞬间复活,那些怨愁也暂时忘却。
那隋炀帝玩萤火虫,才叫壮观。成千上万只萤火虫,放于山谷,天上繁星闪闪,谷中萤火盏盏,交相辉映,黑暗里,忽明忽暗,何等奇观。他站着,痴痴而观,静静来赏,萤火虫绕着他飞来又飞去。堂堂帝王,如果不是痴爱,又怎会有如此举动?难怪李商隐曾用“至今腐草无萤火”来嘲讽他。
小小萤火虫,长得小巧又可爱。黑衣,红头,修长身。六足、两须,半圆眼。后翅,不飞时折叠于翅下,飞时如扇打开。腹部有发光器,里面有荧光素和荧光酶,荧光器上有小孔,空气由小孔进入,发生氧化作用,就发光。那黄绿色的光,在黑夜里一闪一闪,幽灵一般。
我曾问三奶,萤火虫为什么只在夜晚发光?三奶说,夜晚适合谈情说爱。三奶看我疑惑,说,你长大了,自然就会明白。
我明白了的时候,已经恋爱了。夏夜是最易发生爱情的时间,雄性的萤火虫使出浑身解数,使自己明亮,以引起异性的注意。雌性的萤火虫看到,如中意,就用光做出爱的回应。就这样,它们以光的名义占据对方的心,一束光引着一束光,走进幸福的殿堂。
当然,它们白天并不是就不谈情说爱,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萤火虫从孩提到成年,化蛹成蝶,要经历十个月,而成虫也只有二十几天的时间。这青春太过短暂,岂能只选择黑夜绽放?
这样一想,大暑的夏夜,亮着的何止是眼睛,更是热辣辣的爱情。
恋爱的年龄,如火的夏季,这不能不说是大自然的有意安排。
三奶还说,萤火虫发光,除了求偶,还御敌。萤火虫的天敌们,看到光,就不敢靠近。据说,萤火虫化蛹成蝶,变成成虫后,就只吃露水、蜜露,或花粉、花蜜。肚子里吃下去的都是花啊,蜜啊,水呀,难怪,在热烈的夏天,心里藏着花一样的爱、蜜一样的情。
萤火虫,夜幕下的精灵,靠着光影,靠着舞蹈,来抒情。
后来,屋后头的池塘干枯了,即使在大暑的夜晚,也见不到萤火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