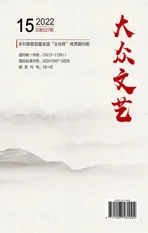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电影的接受分析
2021-08-28黄可佳朱剑卿
黄可佳 朱剑卿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广东广州 510925)
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在1994年《橄榄树下的情人》获第47届金棕榈奖提名,并于1997年凭《樱桃的滋味》斩获金棕榈大奖之后,其电影逐渐广泛进入到国际视野。伊朗作为东方电影国家的新起之秀,20世纪九十年代一经露面,便在国外立即形成了以法国为主的阿巴斯电影研究热潮。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大家或对阿巴斯的某部杰出作品作单一分析,或对其某一类题材电影作研究,对阿巴斯电影作整体研究的也有不少,但多是针对电影文本自身,缺乏将观影系统的另一维——观众的接受纳入研究范围。电影的价值是通过作品与观众在相互交流的作用下形成的接受结果,笔者力图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以新的角度更进一步探寻到导演的创作动机、影片的风格特征和接受效果。
一
阿巴斯无疑是一位深谙接受美学的电影导演。阿巴斯导演非常尊重电影观众,认为衡量一部电影好坏的标准就在于观众能多大程度上参与到电影当中。他想要创造一种非展示、非表达的“半成品电影”,“在这种电影里,是观众的想象力决定了有多少东西可供参观,而非用我们的讲述和展示来超越他们的想象力。”在阿巴斯的心中,“隐含的读者”应该是聪明的、富有想象力的,他们能够从自己的电影中有感而发,在自己的脑海里构建出符合自己审美取向的电影。因此他在自己的影片中使用大量的长镜头和大远景、启用非职业演员、营造现场感十足的场景,以及采用逼真的声音处理,将自己的思想理念糅合在纪实性的美学风格之中,并大量使用极富隐喻性的意象以及不确定性的结局,通过“明确与暗隐”“展现与隐伏”之间的相互作用,召唤观众与之进行互动。
观看阿巴斯的影片,一定不能忽视的便是其电影中反复出现的道路意象。纵观阿巴斯的电影作品,片中的人物总是在路上奔走寻找:《何处是我朋友家》里阿默德四处奔跑寻找同桌的家,《生生长流》中地震后导演沿路去探望曾经的小演员,《樱桃的滋味》里巴迪开着车到处寻找能够帮助掩埋自己的人,《橄榄树下的情人》中侯赛因在路上疾奔去追寻爱情,《随风而逝》里工程师仿佛去山坡上接莫名的电话,《ABC在非洲》里一群人也是在行走中敏锐地捕捉细节……影片中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受阻的、前途未知的,“路”成了阿巴斯电影中极富隐喻性的象征物。阿巴斯在其DV作品《基亚罗斯塔米的道路》中对“路”的集中出现作出了解释:“这些道路承载着记忆。它们象征人类未经记载的寻觅,对生命的寻觅。也许是感伤的,也许只为一口食粮,道路上就画下了杂乱的线条。”在“路”上,当地的自然景观和社会风貌徐徐展开,人们在“路”上寻找的是爱情的美满、是生活的希望、是生命的价值……随着一路前行,寻找的结果却是不确定的:导演是不是找到了小演员、侯赛因是不是获得了美丽的爱情、巴迪是不是放弃了生命、工程师到底来村庄干什么,影片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观众只能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做出猜测。但最终“所有的路都能到达某个地方”,阿巴斯通过明确的过程展现以及暗隐的寻找结局,呼唤人们体验生活的经历、享受生命的过程。
小学教育的瓶颈、地震后的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成人世界的多疑和叽喳、灰尘仆仆中被淹没的人的身影、碎石机上影子的晃动不安、医院里因病逝去的小生命……这些固然让人心生感慨,但阿巴斯的影片并没有满足于展现生活的疮痍,而是要让观众主动去“发现”山间清晨明媚的阳光和嘹亮的口号、崎岖的路边散发香气的小花、地震后生机勃勃的草地树林、光秃的山包上葱郁独立的大树、痩石嶙峋中乌龟尽力地翻身、草地上欢脱的狗和等待的羊群、妇女和儿童的欢歌笑语……阿巴斯的电影在展现生活的疮痍背后隐伏着大量象征生命顽强和生活之美的意象,让观众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产生了情感的“共鸣”,并实现了心灵的“净化”。
他的电影安静朴实,他用纪实的影像来昭示生活本来的面目,他没有用任何刻意的矫饰来蒙蔽观众的眼睛。他就是要让观众去“发现”、去探寻,让大家为自己寻得一丝隐秘而沾沾自喜。
二
阿巴斯电影因其独特的视角和纪实美学风格、诗意悠远的画面、深刻的政治和哲学寓言、深切的人文关怀在国际范围内广受称赞。但阿巴斯仍被认为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导演。其争议性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由个人不同的审美倾向出发的商业和艺术之争,二是总体而言国际盛誉和国内冷落之别。前者因为涉及个人的审美趣味,不便作过多评论分析,因此这里主要讨论国内外的不同接受效果。
获得过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他,其作品在本土却因各种原因长期处于“地下”状态。据2005年阿巴斯在伊斯坦布尔电影节上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政府在过去的十年间没有放映过任何一部他的影片。
近年来伊朗电影逐渐广为人知,但伊朗本身并非电影大国,且伊朗当局对电影的发行进行了严密的掌控,因此伊朗的电影创作多是“戴着镣铐跳舞”。尽管阿巴斯的电影作品采取了一种“疏离政治”的态度,但影片中的一花一草均来自伊朗这片土地,那么诸多属于伊朗的社会问题还是或隐或显地反映在了他的影片当中:《特写》中的失业问题、穷人和富人悬殊的社会地位,《家庭作业》中对教育问题的探求,《何处是我朋友家》中儿童与成人世界的对立,《生生长流》中对宗教教义的怀疑,《橄榄树下的情人》中灾后政府的无为、知识分子和农民的阶级隔阂……任何一种都不是敏感的政教合一的伊朗当局所喜闻乐见的。就如同张艺谋、贾樟柯的电影被认为是拿中国的愚昧和落后去取悦西方,阿巴斯的电影一迈出国门,其透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就像是在世人眼前扯下了伊朗的“遮羞布”,让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宗教对个人价值的压抑都无所遁形,政府当然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其进行压制。
伊朗的普通民众并不像政府一样抱有政治立场,所以伊朗民众并不排斥阿巴斯的电影。他的电影在国内禁放期间,许多人都通过盗版DVD或是地下放映来观看。后来阿巴斯的电影在国内上映,售票厅前甚至排起了长队。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电影的主人公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电影主人公的生活经历跟观众自己的别无二致,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去银幕上看自己的人生。这样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奇特的观影体验,再加上阿巴斯对人们生活和命运的深刻理解,都深深捕获了伊朗民众的心。但不能忽视的是,伊朗政府对电影发行和放映的控制,深刻影响着伊朗民众的观影态度。禁放期间,尽管有人通过其他方式观看阿巴斯的电影,但这些人毕竟占少数,大部分人是没有这种观影主动性的。观众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只能在国内允许放映的影片中有限度地进行自主选择。
三
“任何一个读者,在其阅读任何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之前,都已处在一种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的状态。没有这种先在理解与先在知识,任何新东西都不可能为经验所接受。”但是这种期待视野既使阅读理解成为可能,又对其产生限制。因此阿巴斯的电影能享誉国际,获得其他国家观众的认同,但国内观众的接受效果则异常复杂。
如今的观众审美态度更加开放,常常能够随着观看影片的进程打破自己的惯常思维方式、调整自己的视界结构。阿巴斯的电影走出国门,大家能够从其影片中体察到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对生命意义的探索——或是随着电影进入到童真的世界,感受到诗意优美的镜头语言。这使得国际认同成为可能。同时,影片也向世界展现着东方神秘的国家——伊朗——人文和艺术的一面,这与很多西方人眼中落后、贫穷、脏乱的伊朗形象相背离,观众在阿巴斯的影片中不断满足着对神秘国度的好奇,又不断修正自己的“先在理解”。观众在观看阿巴斯电影时会对自己“发现”导演某个有隐喻意味的意象而暗自得意,且影片的不确定性结局也能充分调动观众的能动作用。其电影使观众在观影时充分实现了自我的价值,让观众产生一股欣悦和满足感,在扩大了观众的期待视野的同时,也帮助观众形成了新的审美经验。
相较于国际视野的开放,伊朗由于长期的封闭和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文化形态,从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公共期待视野。而这一相对稳定的公共期待视野,对观影和接受起着选择、求同和定向的作用。阿巴斯的电影之所以在国内长时间无法公映,就是因为其影片中的伊朗形象背离了公共期待视野。公共期待视野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权者的控制,对个人期待视野产生影响的同时,还影响着当下文学接受的深广度。就电影而言,观影这种精神消费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伊朗政府贯彻着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掌握着伊朗电影市场的话语权,他们希望民众看到的电影是维护伊斯兰宗教和伊朗政府的,推崇与阿巴斯电影完全相反的电影形式——通俗剧,并将不符合者排斥在外,这使得阿巴斯的电影享誉国际却在国内备受冷眼。国内观众所接受到的影片质量和影片类型都受到严格限制,所以他们的感受力长期处于稳定的水平,无法向上跃升。伊朗民众长期观看通俗剧一类的影片,个人的期待视野没有拓宽,便很少有人会主动选择在阿巴斯电影禁放期间去寻找途径观看其影片。更遑论说电影只是人们生活的调味剂,并不是生活必需品。任何一部再伟大的电影,人们不会因为无法看到它而产生紧迫感。
结语
任何一部真正有价值的电影绝不会因为短暂的或地域的不认同而消失在世人的视线当中,反而会随着世界的变迁、人们生活体验的丰富和文化水平的提升、时代精神的发展而历久弥新。尽管阿巴斯的电影作品有良有莠,但这位用艺术的方式看待现实生活,敢于去发现、质疑,并将观众置于与自己平等的位置的电影导演,值得我们尊重。其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纵然在目前还无法受到商业的青睐、国内的认同,但随着观众审美品位的提升,阿巴斯必将穿越时空站在观众的面前,与之平等地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