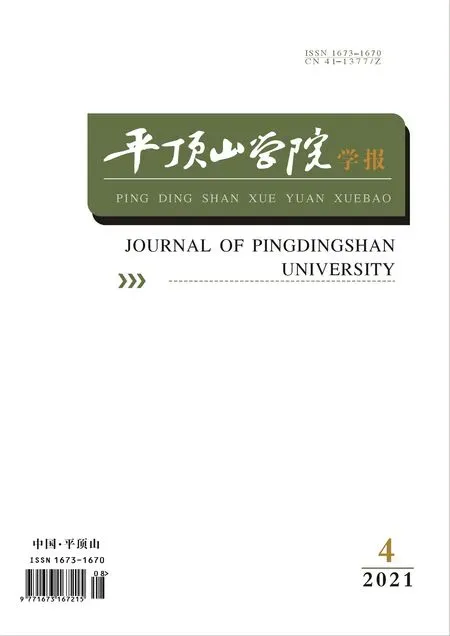汉画像西王母图像近三十年研究综述
2021-08-27谢伟
谢 伟
(深圳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2 )
一、汉画像西王母图像三十年研究概述与评价
1989年至2020年这三十年是汉画像西王母图像研究历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众多的研究成果,成绩斐然。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根据图像构图内容、方式进行分类的研究;(二)西王母形象与艺术表现形式的发展演变研究;(三)考古辨伪研究;(四)附属物研究;(五)和其他神话人物的比较研究;(六)其他研究。
(一)根据图像构图内容、方式进行分类的研究
对汉画像构图范式的研究一直是汉画像研究的重点,在有关西王母画像的研究中,很多学者根据构图内容、方式的不同对西王母汉画像进行分类。李锦山、曾琳、顾森等学者根据构图内容不同对西王母汉画像提出三种分法。第一,将其分为六类:(1)西王母+侍奉仙人,(2)西王母+灵禽瑞兽,(3)西王母+侍奉仙人+灵禽瑞兽,(4)东王公+西王母,(5)西王母+得道仙人,(6)其他。第二,将其分为五类:神魔型、神人型、神圣型、神仙型、神巫型。第三,将西王母图像分为繁式、简式和象征式三种。繁式:西王母及其侍属。简式: 西王母坐于几上或龙虎座上。象征式:“胜”形纹。
黄雅峰、姜生、方艳、李浥等学者根据构图方式不同对西王母汉画像提出四种分法。第一,将西王母汉画像图示分为自由图式和平衡图示两种。第二,根据西王母组合序列,分为三种形态:(1)从子路+西王母,(2)风伯(即箕星)+西王母,(3)东王公+西王母。第三,在构图方式所传达的人物关系演变上看,将其分为周穆王+西王母、东王公+西王母、凡夫+神女三类型。第四,偶像型与情节型构图。
这些学者对西王母汉画像内容和构图方式进行分类,让我们看到西王母汉画像组成的基本范式,有利于学术界了解并解读汉画像。然而略显缺憾的是,仅根据构图内容、构图方式的不同对汉画像西王母进行范式分类,未能考虑不在区域性内的汉画像。对于很多不能用构图内容、方式简单归类的西王母汉画像, 学者似无暇顾及。这是今后西王母研究需要加强的地方,至于组合变迁的具体历史过程及驱动这种变迁的思想背景信仰结构仍待进一步揭示。此外,这种构图方式的变化涉及重要的一点,即不管根据构图内容分类还是根据构图模式分类,学者都关注到汉画像中西王母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可惜以上数篇论文没有具体论证西王母形象与构图形式的发展演变的过程。
(二)西王母形象与表现形式的演变研究
关于汉画像西王母艺术表现形式在汉画像石中的具体发展过程,学界提出不同的看法,主要研究有两个方面:西王母形象的嬗变研究与西王母图像系统的演变阶段研究。
汉画像西王母形象发展有一个演变过程。郑先兴提出其发展经过了“长寿之偶像(汉初到哀帝)”“神的救赎(西汉哀帝到东汉中期、山东模式)”“神的创世(东汉中期到末年、四川模式)”三个阶段[1]。包兆会从图像学、文献学研究先秦两汉的西王母形象流变[2],可惜内容与汉画像图像结合不够。刘婵、尹钊等学者认为西王母形象由原始到完善,由简到繁[3],从《山海经》到汉画像西王母呈现了凶猛怪物到雍容的中年妇人的转变[4]。贾雪枫则认为西王母形象经历了巫到神的嬗变[5]。
事实上,汉代社会在西王母信仰流传的不同时期,反映在汉画像上的构图特征是不同的,而不同阶段的不同构图特征应是学界划分西王母发展阶段最有说服力的依据。信立祥的《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有专节讨论西王母图像的演变。从他的描述中可以归纳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和郑先兴的时代分类一致,不同的是他以东王公的出现为标志作为主要划分依据。这种较少存在争议的特征指标在学界很具有说服力,循着这个线索,汪小洋在《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中心的形成与宗教意义》[6]一文中也以东王公的出现为标志,将西王母图像系统的演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东汉中期以前,西王母与仙界的出现是形成阶段;第二阶段为东汉中期到末年,东王公出现并进入西王母神仙世界,这是西王母至上神的努力阶段。
东王公成为与西王母配对的对偶神表现了汉代社会对西王母图像系统的进一步改造,东王公的出现也是汉代人阴阳平衡观念在汉画像上的反映。由东王公的出现,学者关注到汉画像中所体现的阴阳五行观念。美国汉学家巫鸿直接指出西王母作为阴的象征,东王公作为阳的象征[7]。王倩、高莉芬、张利静等学者也关注到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东王公的出现是由于阴阳和合观念发展,也与五行系统有关,具有特殊的空间功能及象征意义。
(三)考古辨伪研究
对西王母汉画像的考古辨伪通常分为两类:第一,对汉画像西王母图像是否出自汉代进行辨伪;第二,对所谓的西王母图像人物身份究竟是西王母还是女墓主进行辨伪。
1982年1月,黄明兰在《中原文物》上发表《穆天子会见西王母汉画像石考释》一文,作者认为此汉画像石是1949年以前洛阳古玩商马氏所遗,并将其年代考证为东汉。作者从画像石下层—中层—上层对画像进行描绘,然后考据文献确认西王母的身份是我国西部处于母系社会以虎豹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酋长。黄文发表后的第二年,《中原文物》于第五期发表了雷鸣夏的《“穆天子会见西王母”画像石质疑》一文,作者不仅质疑黄明兰在文中所提马氏所遗的东汉画像石“穆天子会见西王母”的真伪和定名问题,并且认为汉画像中女性人物身份也值得商榷。雷文主要从构图格式以及具体物象考释证明:(1)马氏石构图不太符合汉画像石的格式,马氏石一个画面中掺和了画像石三类图像,即墓主生前场景、神怪祥瑞题材、历史故事题材,而事实上汉画像中这三类图几乎不混刻在一起。(2)图中出现的楼阁中的柱以及台阶并非汉代所有;而且马氏石中的主车不符合汉代的车制结构原理,而是以清代冯云鹏所编的《石索》为底本翻刻而成。(3)论文从西王母范式特点出发,认为图中人物并不具备西王母的身份特点,并推测图中人物为女墓主。
雷鸣夏的这篇考释文章为后来西王母汉画像的辨伪考证提供了借鉴。尤其在汉画像涉及女性人物身份的辨认上,雷文所提出的依照西王母范式定身份的做法有一定的可取性,然而在整个东汉,除常见的有构图范式的地域性汉画像外,还有一些地方出土的汉画像可能无构图范式,如何看待跨区域无构图范式的西王母图像,这涉及更多的判断依据。此外,有时考古工作人员在撰写报告时对图像的命名、判定会影响接下来的研究。学者将报告与原石进行核对时会出现最初命名不一定准确的情况,因此在确定图像类别、阐释画面时需更多的辩证分析。
在江苏徐州沛县栖山一毫石椁墓中,在中椁东壁画像内侧房屋内有一戴胜女子端坐,有不少学者对该女子身份进行论证。刘辉撰《沛县栖山石椁墓中的“西王母”画像管见》[8]64-68一文,主张首先按照墓葬均秉持为墓主服务的原则出发,认为此幅画像楼阁内描绘的是男墓主的日常活动,而这座墓属于夫妻合葬墓,所以墓葬画像中应有女主人的存在,因此作者推测这是女墓主。这篇文章一出,引起其他学者质疑。石红艳、牛天伟两位学者与刘辉商榷后撰文认为刘文并未明了西王母与女墓主的辨识问题。该文从东西壁画像中男女人物的对应关系、西壁画像房屋内女子的形象特征及其所处环境以及西王母图像志的典型特征三方面进行论证,最后得出石椁上的女子并非女墓主,而是西王母无疑的结论[9]。
石、牛两位学者的论文指出刘文的最大失误是将墓室和棺椁、单身墓和夫妻合葬墓的差异性混淆。因为在汉代社会,西汉早期的木椁土坑墓与后来普遍使用的夫妻合葬墓不同,整个墓葬都属于墓主,与妻子无关,所以夫妻二人的肖像或共同生活的场景不需要同时出现在画像中。显而易见,刘文中所列举的实例均不能作为作者推论的证据。
但值得注意的是,刘文实际上提出了汉画像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注意点,即“任何一个画像石墓中的画面都不是孤立、零散的,有着它们内在的联系,应该把整个墓葬画像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联系起来去研究其中的每一幅画像”[8]64。这种研究方法有利于我们解决汉画像石存在的不少特殊问题。对西王母画像的考证辨伪是一项十分考验学者功力而又非常艰苦的工作, 从当前的进展来看还略显迟缓。从这个角度加强对西王母的辨伪, 必将推动西王母乃至整个汉画像的研究进程。
(四)附属物研究
由对西王母身份的辨识涉及西王母研究的核心问题,即身份确定的附属物研究。关于对西王母附属物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方面:第一,对附属物的整体研究,这类文章对关于西王母的诸多附属物如胜、三足乌、九尾狐、龙、鹿、麒麟、青鸟、玉兔、蟾蜍、龙虎座、凤鸟、羽人等进行具体描绘。第二,对某一附属物的专门研究:(1)对龙虎座的研究,(2)对西王母持纴器的研究,(3)戴胜的研究,(4)蟾蜍研究。
在这些对西王母某一附属物的专门研究中,学者尤其对龙虎座给予很多关注。王苏琦对四川出土汉代西王母图像中的“龙虎座” 进行考察,可惜由于资料不够丰富,导致在研究中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线索来研究地区差异和变化的方向。仝涛、邹芙与郑先兴都追溯西王母龙虎座的起源,前者认为西王母龙虎座造型和我国北方发现的某些神兽座有共同的渊源,后者认为西王母龙虎座造型可以追溯到濮阳西水坡所发现的蚌壳龙虎塑像。事实上有关龙虎座所涉及的西王母汉画像都出自四川,通过分析四川有关西王母的汉画像石,我们发现画像中的西王母都正面端坐在龙虎尊上,彰显出很强的神性色彩。龙虎座在四川盛行“应该和古代巴蜀文明对于龙虎的信仰和崇拜有一定的关联……巴文化以崇虎而著称”[10],正是因为巴蜀还是把西王母当成神,所以才把龙虎放在汉画像中,只要有西王母的汉画像都有龙虎座。对西王母附属物的研究文章近年在逐渐增加, 且研究的视角也逐渐加细, 但个别文章的论述深度则显得较浅。
(五)和其他人物的比较研究
有不少学者将西王母与其他人物进行比较研究,主要有两大类:第一,将西王母图像与伏羲女娲神结合起来研究;第二,将西王母图像与西方人物进行对比研究。
汪小洋在《汉壁画墓中西王母、女娲图像的辨析与意义》[11]中对西王母图像与伏羲女娲的存在问题进行探索,并对图像信仰进行辨析。作者认为壁画墓中的西王母、女娲图像的不同说明两者不仅在墓葬绘画的表现形式上存在不同,而且在长生信仰上也存在着区别。陈金文在《东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与伏羲、女娲共同构图的解读》[12]一文中从山东省微山县两城镇与滕州市桑村镇出土的汉画像西王母、伏羲、女娲图入手,将西王母与伏羲女娲神结合起来研究,这种对比研究有利于考察不同主神的不同构图方式,以及在长生信仰上存在的区别。高继习曾发表《白色的西王母——西王母与雅典娜神话的比较研究》[13]一文,作者发现西王母从外观形象、所处环境到神职等全部要素,都与古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女神有密切关联。然而作者主观臆断比较强,不能作为严谨的学术论述。
(六)其他研究
在西王母图像的其他研究上,有不少文章用西方理论解读汉画像西王母图像的美学隐喻象征。朱存明、朱婷的《汉画像西王母的图文互释研究》[14]一文利用文字与图像互补,认为西王母汉画像美学意义的根源是符号性的隐喻象征。略显缺憾的是, 在用文艺美学解读汉画像时,学者未能用西方文艺学理论深入解读汉画像叙事与寓意,大多时候显得牵强,不能浑然天成进行论证。对西王母图像的起源问题,学界集中在受佛教艺术影响说、中亚双马神影响说和中原传入说、源于本地说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郑先兴、黄诗棨、孟青也等学者对西王母图像进行民俗文化学研究,郑先兴在《汉画像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中以婚姻为切入点对汉画像做社会学的研究,不仅追溯了西王母神话,还对西王母的附属物背后的寓意进行探索。然而略显缺憾的是,作者侧重于先民生殖崇拜,多为主观臆测,不少观点缺少逻辑论证。
综上所述,这三十年间汉画像西王母图像的研究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关于西王母构图分类问题上,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看法,但是就这一问题,现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这势必会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明朗化;在西王母身份辨认上,学术界也提出了范式对照以及联系墓葬整体分析的方法;在西王母形象发展演变以及阶段划分问题上,各家抓住不同时间段西王母的不同表现形式,提出不少新的观点;在附属物研究问题上,学界对西王母诸多附属物都进行整体或专门的研究;在将西王母与其他人物进行比较研究、联系西方理论解读汉画像等方面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
就目前西王母汉画像研究的情况来看, 笔者认为存在如下三个不足:(1)学者对西王母汉画像是否存在过度解读的状况。众所周知,汉代制作汉画像石、画像砖的匠人几乎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知识素养不足。他们在制作汉画像时接触到关于西王母寓意的信息不能和当今的我们相提并论,而且目前我们接受的大部分西王母信息还有很多是在汉代以后发展完善的。(2)学者就西王母汉画像的构图内容、构图方式进行范式归类,但在整个东汉,除常见的有构图范式的地域性汉画像外,还有一些地方出土的汉画像可能无构图范式,如何看待跨区域无构图范式的西王母图像,这涉及汉画像人物的身份判断。(3)如何看待汉画像辨伪情况,或者说如何看待西王母与墓主人身份重叠情况,有些被认定为西王母的图像有学者质疑为墓主人,或是否还可能存在是普通女性的情况?结合西王母当时的社会寓意,匠人很有可能在画像中加入西王母的构图因素,以此带有祝福逝者永生的美好寓意。而这种既是西王母又是逝者的双重形象如何更好地客观理解,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汉画像其他人物形象中是否也含有双重寓意的存在亦是汉画像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汉画像西王母图像研究新趋势的探寻
基于目前这种状况,今后汉画像西王母图像研究将有怎样的发展可能呢?根据前文汉画像西王母图像研究在这三十年的发展特点来看,其发展新趋势可能有以下几点:(一)学者都注意到西王母在汉代构图模式的变化,但是鲜少注意到西王母在构图发展中呈现俗化的过程,西王母画像在汉代的俗化演变过程值得我们再深入思考;(二)在西王母俗化过程中,西王母面部表情愈加清晰,这是古人自尸、像祭祀发展后,人物肖像有了进一步表现方式,对比同时期的文学叙事还未出现对面部的特写,这值得我们思考在汉代图像叙事是否超过同时期的文学叙事;(三)秦汉传世文献涉及西王母的主要有《山海经》《淮南子》《穆天子传》,从传世文献与图像学两方面共同考察先秦两汉西王母形象是不少学者在论文中都谈到的问题,然而如何深入比较文本、图像中的西王母之异同还需更多的努力。
(一)西王母图像在汉代的俗化演变过程
李凇在《从永元模式到永和模式——陕北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图像分期研究》[15]中研究陕北有关西王母的汉代画像石在东汉永元年间和永和年间图像存在差异,作者将其定义为永元模式和永和模式。在永元模式中,西王母像基本为正面,戴胜,有玉兔或羽人跪侍,有独角兽,有玄武,有日、月轮,没有华盖。而在永和模式中,西王母图像三分之二侧面,不戴胜,无玉兔或羽人,无独角兽、日月轮、玄武,且伴有庄园建筑图。可见东汉中期到东汉后期,西王母的神圣性下降, 由浪漫转向现实, 墓主的重要性得以强调。作者认为两种图像模式所反映出来的内涵差异与东汉中期到东汉末年的社会文化变迁一致。这引起笔者注意,现在发现的西王母图像大部分出自东汉时期,主要分布在山东、苏北、河南、四川、陕北等地区。是否其他地域的西王母图像也如陕北有同样的内涵折射?是否其他区域的西王母也逐渐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俗化?下面我们试从苏北、河南、山东、四川等几个汉画像石盛产地入手,考察不同地域的西王母图像在西汉到东汉的俗化演变过程。
《中国汉画像石全集·山东画像石》所录有关山东西王母画像三十余幅,从图中可知,山东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常戴胜端坐,她一般端坐于画面顶层的正中间。西王母图像很少有侧面的,多以正面端坐示人,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有翼,神性色彩很强。而四川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都有龙虎座,一直神性色彩强烈。道教最先起源于这两地,与西王母崇拜结合起来,因此在这两地西王母有极高的地位。
河南出土的西王母画像不同于山东、四川两地,在河南出土的西王母汉画像石中,经常可见西王母手持纺织工具在劳作,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可见其俗化程度之深。郑州新野县樊集吊窑第28号墓墓门画像砖有一幅西王母图像,此图西王母既没有坐在彰显身份的龙虎座上,也没有端坐的姿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西王母的坐姿已经完全不是神人端坐的姿态,而是像汉代妇女跪着劳作,西王母侧身拿着两个对置的三角形物件。关于这两个三角形物件,学界认为此为用来纺织的绕线板。此图西王母头上戴的胜被加长,学界认为“胜”是织布机上用来卷经线的横轴上的“滕”。 这表明西王母与养蚕纺织有紧密关系。南阳市茹楼端庄出土一汉画像石,画面左面刻西王母侧面而坐,画中刻有一羽人手植仙草面向西王母,画右侧有一玉兔在捣药,西王母身着汉代普通妇女服装。
苏北出土的西王母画像与日常生活结合得也十分紧密,与东王公对坐或相拥。徐州铜山白集出土一座东汉末期的汉画像石墓和石祠,石祠的东西两壁上有东王公和西王母的画像,时间出自东汉中期。该画像整个画面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西王母在最上层,没有戴胜。后方玉兔、蟾蜍在捣药,侍女端庄地站立,羽人在起舞。这里西王母与东王公相拥在一起,都以侧面姿态呈现。在此画像上,东王公与西王母都身着普通汉代人的服饰,没有神性。苏北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东王公多与当时的社会联系在一起,褪去了不可冒犯的神性色彩,且画面中多出现六博、鼓舞场面。
综上可见,河南出土的西王母画像经常可见西王母手持纺织工具在劳作,苏北出土的西王母画像与日常生活结合紧密,与东王公对坐或相拥。在这两地出土的西王母图像上我们看到了人物图像的俗化过程。
(二)尸、像到汉画像面部表情的演变彰显图像叙事的进步
《仪礼·士虞礼》郑玄注:“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16]上古在祭祀过程中, 经常出现用活人代替死者接受祭祀的情况,这就是尸祭。通常担任“尸”的人是同一宗族的子孙,他穿戴祖先的衣冠,将看不见的神灵形象化,或是采用装扮神灵的形式再现祖灵形象,严肃端坐在神的特定位置上接受大家的歆飨和膜拜。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时代尸祭开始衰落,而战国就已经逐渐消失了。而在战国兴起的是“像事”。顾炎武《日知录·像设》引用宋玉的《招魂》时曰:“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17]这表明了“像事”兴起在战国之时,是古代以“尸”祭祀的历史代换。“像事”指的是“以祷告代替了表演,以图像、牌位代替了活人”。可见肖像的兴起源于“尸礼”,自“尸礼”废除之后,人们以画像或塑像假之祭拜。
在秦汉的造型艺术中存在不少写实的作品,但少见有关真正刻或画的肖像。邢义田曾指出:“基本上来说, 汉代画像有大量需要显示身份的人物, 可是当时的石匠似乎无意就人物作惟妙惟肖的个性刻画, 使人一望即知所刻画的是某一特定人物,他们通常借助榜题、衣饰特征(如子路)或其他布局上格套化的安排(如二桃杀三士)。”[18]事实上邢义田忽视了西王母这个典型的人物形象在构图发展过程中面部表情的变化,前文我们梳理了西王母的构图,可以发现西王母在构图发展中呈现俗化的过程,并且在西王母俗化过程中,西王母面部表情愈加清晰,这是古人自尸、像祭祀发展后,人物肖像有了进一步表现方式,这也意味着图像叙事的进步。肖像表现人物,涵盖相当深刻的文学形象表现的深刻变革。
一直到汉代末期,乐府诗《陌上桑》中言秦罗敷“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也只是借服饰来表现人物形象,而非对人物五官的刻画。这里可以得出清晰的一点,即图像叙事的发展或早于文学叙事,这值得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
(三)文本、图像中的西王母之异同
秦汉传世文献涉及西王母的主要有《穆天子传》《山海经》《淮南子》,从传世文献与图像学两方面共同考察先秦两汉西王母形象是不少学者在论文中都谈到的问题,形象在文字与图画中都可以生成,将图像和文献结合,可以更加全面地建构某一历史时期的西王母形象。学者的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出现以下两个问题:(1)学界更多的是将文本中的西王母形象与图像中的西王母形象割裂开来研究,单独论证文献中的西王母形象在先秦两汉的发展流变,再辅之简谈画像中的西王母演变过程。或将重点放在画像中的西王母演变过程,再辅之简谈文献中的西王母流变。这种研究未能清晰地论证文献与图像在同时期表现西王母形象时的异同。(2)不少研究抓住文献中对西王母形象的描绘生搬硬套到汉画像中的西王母形象中去,忽视画像西王母的地域性以及个性特点。没有辨别出哪些特征在文献中不存在而属于西王母图像所特有,更没有区分出不同地域的西王母有地域特征,这种地域特征亦非文献所能展示。
如何深入比较文本、图像中的西王母之异同,学界还需投入更多的关注。而辨认出神话文献与图像文献的联系与差异是我们在研究汉画像人物形象或故事文本传播演变时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