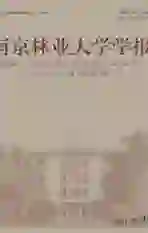生态批判与图景重构:高兹“生态危机论”的逻辑进路
2021-08-24李培鑫
李培鑫
摘 要:对于生态危机的思考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一大元问题。在西方生态危机理论谱系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围绕生态危机问题而阐发的“生态危机论”内涵丰富,意蕴深远。经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高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危机受市场经济的刺激不断强化,并伴随着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而达到极峰;随后高兹转入对人类文明现代性的思考与对旧社会主义模式的生态批判,否定了生态原教旨主义的理论主张与旧社会主义模式中的生态治理,重申了社会主义愿景背后所蕴含的生态启迪;最终提出了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三个维度超越资本主义的生态重建思想,搭建了生态社会主义整体模型。不难发现,高兹在界定生态危机性状、挖掘生态危机根源和谋求生态危机治理时,充分吸取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智慧,其“生态危机论”的阐发亦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通过梳理高兹“生态危机论”的逻辑进路,可以为当今我国生态危机治理提供思路启示和路径启示。
关键词:高兹;生态危机;经济理性;生态社会主义;人与自然和谐
DOI:10.16397/j.cnki.1671-1165.20210306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自人类社会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问题日益成为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改善生态环境,克服生态危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哲学维度的再思考,是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必需。关于生态问题的思考贯穿于高兹全部理论体系之中,国内学者对高兹生态思想的研读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以小见大”,以高兹的生态理论为锚地,从不同切入角度对高兹生态思想进行剖析。有学者对高兹资本主义科技观进行研究,提出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会导致劳动的异化、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1];有学者对高兹资本主义消费观加以研读,指出异化消费会引发超额生产、奢侈消费和巨大浪费,并由此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2];有学者从高兹资本主义劳动观入手,提出从破除异化劳动、解放非物质劳动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解放路径。[3]这种研读路径由表及里,可以由研究剖面纵向窥视高兹生态思想深度,但其视角局限存在认知片面化的问题。二是“把握线索”,抓住高兹生态思想中的核心线索,宏观把握其思想的构思、运作逻辑。有学者以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4]或生态社会主义[5]理论为线索,揭示了高兹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和对未来社会构想的完整思路和乌托邦性特征。这种研读路径横向连绵,可以展现其理论的内在逻辑脉络,但因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就是涵盖要素较多的要素集,所以研究中存在指向宽泛化、因果不匹配、推理有跳跃的问题。本文沿用第二种研读路径,尝试以高兹关于生态危机的论述为线索来串联高兹理论中的相关元素,有机整合高兹资本主义批判视角。高兹对生态危机的直接感知与分析,是高兹生态思想的起点,也是贯穿其全部理论的隐性脉络,更能凸显高兹生态思想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发掘高兹乌托邦精神的真实根基和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旨趣。那么高兹“生态危机论”因何阐发,内涵如何,指向何处,有何价值呢?
一、高兹“生态危机论”的逻辑起点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作为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智慧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高兹追随马克思的思想轨迹,着眼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狂飙突进、工业化进程迅猛增速的现实维度进一步开拓了生态危机理论视野。高兹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制度、经济模式、科学技术的反生态辨析,是高兹“生态危机论”的逻辑起点。
(一)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
高兹从社会制度层面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予以揭露和批判,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马克思曾有过从社会制度层面思考生态问题的尝试,他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破坏的内在耦合关系,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结论是要求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第二,高兹发现生态危机的地理空间分布是有规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问题最为严峻显著,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又具有同构性。因此,高兹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态问题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并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进行深刻辨析。
首先,高兹发觉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人的主体因素、主观情感全部被抹杀,利润至上、“利润挂帅”成为生产的常态。他从哲学层面上对生产者盲目追求利润的动机进行界定,指出这种动机实质上是一种“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一项行动如果以投入种种要素赚取最大产出为目的就是经济理性行为”[6]48。经济理性是工具理性的一种,工具理性所追求的是效用的最大化,经济理性追求的是经济效益最大化。理性本是人类主体性的确证,但资本主义制度使理性走向了人的对立面,纯粹的经济理性迫使人从理性的主体沦为了理性的奴隶。基于经济理性的生产动机必然会打破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劣質的产品、严重超标的工业废弃物。生产活动在破坏自然的同时,也破坏了人的生存条件,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7]776。其次,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干预经济十分有限,其制度设计缺乏生态视角,政府部门因其利益博弈困局难以做出实质性生态调控举措,公共政策体系缺乏对可持续发展的考量。而唯经济效益至上的发展理念只会使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再次落后,甚至从根本上威胁国家的运转和维系。最后,高兹指出“最令人恐惧和失望的根源”并非是生态问题本身,而是一个社会对生态破坏的无视和冷漠。利润“传达出强迫、固执、暴政的资本信息,除了‘更多、更大、更快外别无其他”[8]106,经济理性塑造了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类不断贪婪地向自然索取资源,劫掠大自然来满足自身无穷无尽的逐利欲望,最终导致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难以兼容甚至是尖锐对抗。
(二)生态危机的强化:市场经济带来异化消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异化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从异化劳动到异化消费的内容转向,异化消费的反生态意蕴也愈发凸显。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斥着“那些特殊的社会利益集团为了压制个人而加之于个人之上的需要”[9],这本质上是一种虚假的需要。异化消费就是由虚假需要所引起的、人们盲目顺从而难以自制的消费行为。高兹进一步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辨析资本通过引导消费而获益的本质,从中明确指出市场经济模式本身就缺乏生态考量,这体现了高兹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断由制度形态批判转向经济学批判。在生产端,资本主义生产服从“要么积累,要么死亡(accumulate or die)”这一法则。为了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而盲目竞争,所有生产者都变成市场经济语境下的“经济人”,生存的意义丧失了,道德的视野褪色了。谵妄焦躁的生产者只关心自己产品完成“惊险的跳跃”,只有“企业意识”而无“社会意识”,早已主观排除了对产品有用性、质量、道德因素的权衡,“从经济推理中得出伦理是不可能的”[8]24。在消费端,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商品的飞速积累要求匹配足额的消费,为了规避产品滞销就需要不断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包装、广告、样式翻新便是常用手段。在瞬息之间就能完成产品更新迭代的市场里,破旧的物品不仅在物理层面上“过时”了,而且在经济理性塑造下成为“贫穷的标志”,在道德层面上也“过时”了。[8]106也就是说,人为制造“稀缺性”成为必需,攀比、求异和从众的消费模式成为必要,“消费带来安全感”的认知模式成为必然,资源有限性和欲望无穷性的尖锐对立成为必定。总之,无限度生产导致自然资源枯竭,无限度消费必然带来浪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然承载力趋于崩坏。
(三)生态危机的极峰: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
长久以来,在浩瀚无垠的自然界中,人类显得无比渺小,掌握科学技术使人类得以揭开晦涩神秘自然界的面纱,世人热情讴歌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通过科学技术来控制自然、驾驭自然的能力成为判断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高兹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审视中,却发现了这一现象:医药技术进步,人的体质却下降,在某种意义上,药物成为“病因”;车辆方便出行,拥堵却在增加,出行工具反而造成出行困难;自然本是人生存的前提,生态灾难却造成人类伤亡——随着科技的发展,似乎人的生存因素全部变成了人的灭亡因素。不可否认,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人们在进行科技研发、使用和推广的过程中,也造就了如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不断激化人与自然的矛盾,科技的发展使现代性过程中出现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二元悖论。高兹指出,发展科技本就是资本逻辑运作的关键一环,“资本主义只发展那些与其逻辑相对应并与其持续统治相适应的技术”[8]28,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科技的占有也就意味着对利润的占有,因此科技在使用中无疑会打上经济理性烙印。随着社会发展,科学技术从一种附着性的生产要素逐渐转变为一种独立性的生产要素。科学技术作为独立性生产要素并非不偏不倚地伫立于民众与资本家之间,而是存在靠拢于资本家的倾向,成为压迫人的工具;生产劳动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中介,科學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固然就存在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马克思曾使用“裂痕”概念来揭示由工农业生产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在物质变换上的断裂与疏离。高兹认为,当科学技术由被经济理性塑造了的人的主观意志来操控与使用,这种人与自然的疏离进一步嬗变为人对自然的压迫,科技成为压迫自然的工具。在诸多科学技术中,核技术尤其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威权本性。这种威权以对自然的倾轧为标志。在现实中,由于受到经济和政治因素的驱使与裹挟,对科学技术的生态批判往往被遮蔽或无视了。“科学技术”成为现代性话语体系中绝对正确的概念,“科技即好”成为人们新的精神枷锁。因而,与被经济理性塑造的生产和消费相比,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更强、危害更深,会使生态危机问题成几何倍数增长,引发生态危机极峰。
二、高兹“生态危机论”的逻辑演进
经由对资本主义一系列的准生态批判,高兹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危机爆发的必然性、人与自然关系冲突的尖锐性和生态破坏的不可逆性。同时,高兹也认为,不能仅局限于批判,更应该积极构想一种能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主体,以开创“一个使经济服务于社会最高目标而非迫使社会服务于经济的社会”[6]4。而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以人类发展的现代性为坐标,是选择“退一步”,放弃发展以求生存,还是“进一步”,依靠发展来解决问题?
(一)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退一步还是进一步?
在应该以倒退还是前进的方式去激活崭新“历史主体”的迷思中,高兹首先否定了以生态原教旨主义为代表的“退一步”观点,并以富有历史穿透力的论据对此展开批驳。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文,揭示了人类面临着严峻的资源枯竭、能源危机与环境污染等生存困境,戳穿了人类沉溺于破坏自然而又妄求永续发展的美梦,同时也促使许多对人类前途命运持有悲观态度的研究流派和社会团体纷纷涌现,其中以生态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力最为广泛。生态原教旨主义所倡导的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彻底取消工业技术,通过建立“小而稳定”的社会秩序,实现以生存为目的的自我生产,破除大量生产、过度消费和大量废弃。高兹态度鲜明地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南北两极分化严重,世界经济格局愈发动荡不安,这种所谓的“小而稳定”并不现实,为了生态问题而让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贫困国家放弃工业化,是置其于死地之举。“放弃工业化”的构想本质上是“崇尚大自然善心”的“准宗教信仰”,是对“茹毛饮血”时代的回归,而丢失了社会发展的现实维度,其结论必然是无比荒谬的。在前工业化时期,自然是完全异己、与人无涉的自然,虽然生态问题远不如今日严峻,但此时的“社会有机体尚未体悟到自身的主体性,面对强大的自然界,社会有机体展现更多的是敬畏姿态”[10]。高兹认为,人类应以共生共荣、协同进化的态度面对大自然,工业引发的问题要靠工业增长来解决——烟雾过滤和污水处理装置、以遗传学和优生学为代表的生物工程、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等等,均对人与自然协调共进起着积极作用。随着科技的发展,工业甚至已经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并因此是自由的资源和条件”[8]13。人类应在工业化的成果之上,去寻求不以破坏经济的发展能力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引导经济发展走生态之路,而非为了保护环境去放弃经济发展。这也体现了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念,将再生产自然界纳入人的生产过程以实现“物我两旺”。需要指出的是,高兹强调发展科技的观点并没有陷入偏执的“技术乐观主义”,他始终坚持用辩证法的原则看待科技,支持发展具有生态效用的科技,而对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一直持有坚定的批判态度。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参照:社会主义愿景
想要谋求发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找准参照物——参照物可以帮助人们判断发展的速率与效益。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审视生态问题,可以得出:当一种社会制度阻碍了人与自然和谐,那么这种社会制度就丧失了历史必然性,必然要被可以促成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制度所代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生态和谐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 因此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社会。[11]在高兹看来,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经典描述——“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7]185,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已自我定义为反对资本主义发展范式的社会形态,“放弃以社会主义为参照意味着我们将同时放弃超越资本主义”[7]4。社会主义美好愿景实质上就含有破除资本逻辑和经济理性的意蕴,可以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变革提供方向指引。
对以苏联为代表的旧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反思,是20世纪末以来社会主义理论学者必须直面的问题。高兹也积极从生态视角对旧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审视和反思,并指出旧社会主义模式并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超越资本主义发展范式的参照主体绝非是旧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政府在决策时往往对经济发展和技术发展采取无条件肯定的态度,兴建了大批的钢铁冶炼厂、石油化工厂等重化工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了工业增长奇迹。其造成的生态危机问题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如乌克兰地区的核电泄露,咸海、贝加尔湖、波罗的海的水污染等等。高兹认为,这其中固然有社会和政治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旧社会主义模式中,环境信息无法自由流动,即在政府纵向的组织架构中、在中央与基层之间、在计划经济的供与求之间缺乏有效的“民主反馈”。一旦缺乏“民主反馈”的提醒,政府极易走入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去扩大生产规模的歧路。铺天盖地的核能建设和重工业铺建就是最鲜明的例子。在旧社会主义模式中,能源生产和分配高度集中化,经济政策强制化,政府运作方式单向化,一切经济活动都要服从中央的指令性计划,而无法根据实际经济情况和生态需求作出实时反馈和调整。因此,与资本主义相比,旧社会主义模式同样缺乏生态考量,甚至对生态的威权性占有和破坏更为强烈。在这种社会模式中,社会组织和民众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认知与实践,是源于政府强制性、政治性胁迫,而非发自内心的生态保护自觉。
由此,高兹认为,虽然旧社会主义模式背离了社会主义愿景,但社会主义愿景的光辉仍在闪耀。需要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定义——以批判资本主义反生态性为契合点,将现代生态科学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式。
三、高兹“生态危机论”的逻辑归宿
生态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资本逻辑及其发展范式的根本颠覆,“资本主义文明的所有价值都需要重新审视”[8]101。高兹主要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三個维度去探索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现实路径,搭建了生态社会主义整体模型。至此,高兹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准生态批判转入了对未来社会形态的构想,也就意味着高兹开始从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上构筑“绿色乌托邦”。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构想与不切实际的空想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一)生产方式上,对社会进行“生态重建”
“生态重建”的含义是依据生态化的指标变革整个工业社会体系,按照生态标准来评估发展效益、生产水平、消费水平与科技使用情况等等。在高兹看来,想要达到这一目标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方面,必须要限制经济理性的辐射。高兹并不否定经济理性的存在意义,经济理性可以存在于生产、发展和交换过程中,而关键在于明晰经济理性蔓延的界限(即经济理性自由表达的范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理性功能边界无止境的恶性膨胀,资本只会狂热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生态平衡的破坏并不会增加企业的财富负担”[8]12。限制经济理性并非是像生态原教旨主义那样在宏观上彻底否定经济和工业化发展,也并非在微观上取消商品流通或者限制企业的收益,而是要限制市场主体对收益和盈利的盲目追逐行为,使社会中的纯粹经济理性不至于压倒其他层面的考虑。这样经济理性才能服从于社会发展的整体目标,避免经济理性主导全部社会生活,尤其是在生态、政治、伦理、健康、人际关系、价值体系等非经济的领域内。
另一方面,要将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生态理性是一种价值理性,从“人之为人”的层面说,生态理性是比经济理性更为高级的理性。价值理性侧重对非物质的探求与人生意义的实现,生态理性意味着以一种长远的目光来考察发展的可持续性,无法用“计算与核算”的相关话语表达。与功能边界不断畸形膨胀的经济理性相比,生态理性自带“限制和维持”意味,其内涵是指投入可回收可循环的原材料资源,采取环保型的生产方式,以提高产品的耐用性、可维修性为重点,并且注重产品的社会效用。因此,这是一种“使生活更好”而“劳动和消费更少”的发展理念,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节约资源、避免浪费。高兹认为,生态理性不仅是规制资本主义经济理性肆意蔓延的隐喻,而且会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制度下盲目追逐利润、盲目扩大生产规模的动机,真正开创“一个不再由效率、盈利和竞争等经济价值主导一切的社会”[7]4。一旦经济活动以生态理性为基底,社会就可以实现生态化转型,催生出以太阳能节能产品、氢气发动机、绿色农药为代表的“生态-商业”、“生态-工业”绿色发展思路。
(二)生活方式上,改造国家权力关系
以布克钦为代表的生态学者认为,生态问题根源于“社会支配”,即人对自然的压迫来源于政治统治中人对人的压迫。高兹也指出,资本主义下的经济理性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经济理性在政治领域内也塑造了以发展速度为政绩考核标准的“官僚-工业机器”,“庞大的官僚-工业机器及其领导地位也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理性扩张的表达”[7]87。要想将经济理性纳入生态理性之下,尤其需要在缺乏生态考量的公共政策体系中拓展民众的选择权等民主权利,保障民众的政治生活与政治参与,以实现“使经济和技术沿着深思熟虑与民主辩论的模式与方向发展”[6]10。
“计划—反馈机制”是高兹在政治生活层面解决生态问题的设想,其含义是:政府主体事先制定发展计划,以确定宏观上的发展方向,排除结构性变化;公民主体通过政治参与程序(甚至是非程序性的抗议和社会运动)以反馈发展结果,促使政府主体调整发展计划,进而重塑和引导下一阶段的发展。“计划—反馈机制”是一个闭合的线路,其中公民对于发展结果的反馈会作为信息影响下一步的决策活动,由此形成反复循环。该机制的最大特点是可以将政府决策和人们的切身愿望与需求建立“返回式联系(Ruckbindung)”,用规范的机制来代替决策者直观判断,使决策更加体现公众的真实愿望与切身利益,而非屈服于资本发展的要求。“计划-反馈机制”体现了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和民主參与,是一种基层民主,有助于使人们从长期性的视野出发看待问题,缓解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人们只顾短期利益而忽略长远发展所导致的生态问题。基于民众意愿、彰显环保理念政策的落实,又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可以实现制度的功能性与每个人的目标相吻合,这种民主决策模式突破了以往的专家决策模式,形成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上下贯通、去中心化的决策闭环,在高兹看来,只有工人、农民、技术人员等劳动者才能明确感受到自身生产行为对生态的实际影响,而非高居“庙堂之上”的官僚与专家。
高兹不断探索生态问题背后的政治根源,并由此创立了跨学科性质的“政治生态学”,成为当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构成。但是在现实中,由于政治地位的位差,公众的生态诉求仍有被官僚政客忽略的隐患;而且,官僚政客为了中饱私囊和获取政治筹码,往往会鼓吹重经济而轻生态的举措。这些煽动带有很强的欺骗性与蒙蔽性,底层民众难以辨别。这些现象引起了高兹进一步的思考,他开始寻觅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心理和认识根源。
(三)思维方式上,重塑个体价值观
马克思的自然观指明,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具有自觉意识,人的实践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因此人类要对维护生态平衡负首要道义责任。也就是说,“生态问题的本质及其影响首先是人的问题”[12]。受马克思的自然观和滥觞于古希腊的西方人文精神的熏染,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注重在生态危机中日益凸显的“人的问题”。威廉·莱斯将伦理和道德视为调控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因素,主张依靠人的伦理自觉与道德进步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萨拉·萨卡认为要利用自然伦理观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从而培养具有环保意识的“新人”。作为“人本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高兹的理论构想中也有浓厚的人文关怀。他认为,要想实现社会宏大叙事中的“生态重建”,需要从公众的认知根源入手,使每个人在心理层面上对经济理性深恶痛绝,让生态理性真正“发于思,止于行”,落实在公众的日常生活中。与其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高兹发现现实中普通民众对生态环境的认知愈发薄弱,应对生态破坏的手段较为单一,所以他更加注重依托于外部力量对人的价值观进行生态化改造,如以“削减工时-工会教育”为手段来重塑公众下班后的文化生活,从而培养公众正确的生态行为,使公众掌握正确的生态知识,提升公众的环境保护自觉。与对人的素质有较高要求且见效较慢的“伦理约束”和“道德进步”相比,高兹的观点无疑是更富有成效的。
高兹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公众的日常行为习惯,并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现象:工人、雇员劳动时间漫长,导致其下班后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所剩无几,为缓解疲劳和满足欲望,这部分时间大多用来去消费,“快乐地投入精力进行消费”的人们缺少独立思考、审视生活的时间。在这种状态下,人们被禁锢在物质、消费、科技编织的“理性铁笼”之中,作为“人的精神的无机界”的自然界与人渐行渐远。“蓝天、白云、碧水、净土”等田园牧歌式的意象成为被时代所抛弃的苍白幻想,人们缺失自然界对精神的滋养,失去了对生命底色与自然本真的探寻。人类精神的源泉日益枯竭——仅仅将工作视为谋生手段,发放工资后立刻通过消费获取自我满足感,而对自身消费、浪费所造成的自然环境负担浑然不觉。
以这种“虚假的满足,空虚的生活”为靶,高兹探索出“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理性的消费”完整逻辑链。“更少的生产”是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使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企业可以借助电脑程序和自动化系统来取代人力劳动,工人完成生产任务的时间得以大大缩短,因此,企业可以对工人的工作时长进行削减,“如果要减少商品消费(这对保护环境而言必不可少),同时让每个人最大限度获得主导生活的自主权,则时间政策是最好的杠杆”[6]105。工人完成既定工作后就可以下班休息,企业为保证自身盈利,可以在剩余时间内雇用临时工继续劳动,这样在不损失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还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和失业情况。“更好的生活,理性的消费”是指提前下班后,工人将会获得个人生活的主导权,这部分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去使用,“或学习充电,或更换工作,或体验另一种生活或职业生活之外的‘第二生命”[6]92。在工人的“第二生命”里,工会要发挥生态教育功能,如马克思所言“而实际上工人也是重视‘踏踏实实的教育的,只要这种教育不掺杂资产阶级牟取私利的伎俩”[7]130,公众可以有组织地在工会里集体思考、公开讨论特定环境议题,去辨析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既丰富了自身的环境知识储备,又可以使劳动者用生态理性的观点审视自己的职业生活,培育节约、环保的价值取向,重新建立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思维和对生命本真意义的探求,反省由生态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精神缺损,最终摆脱金钱关系和经济理性的束缚,实现个人对消费的自我设限和对自然的亲近。
四、高兹“生态危机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路启示
在成功夺取全面小康伟大胜利的今天,人们的物质财富积累达到了历史新高度,但环境污染现象和奢侈浪费之风仍然存在,加之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生态危机呈现出全球性蔓延态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遭遇了瓶颈与生态治理赤字。高兹“生态危机论”中所呈现的环境保护思想,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破解日益突出的生态治理“进路”难题、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秉持绿色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生态主导型的现代化发展
“我们应如何发展?”是现代性向人类提出的永恒问题。高兹在理论构建中始终在追求一种人与自然之间适度的张力与动态的平衡,例如他要求限制经济理性,而非根除经济理性;要求限制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而非彻底取缔科学技术。这体现了高兹肯定现代性的发展方向,经济的复苏、科技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无不依赖于现代性,他的尖锐批判所指向的是现代性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效应。我们要看到,中国目前正处在浩浩荡荡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是中国当下尤为迫切的任务。然而,国际上高呼“碳排放正义”的西方生态霸权话语极力钳制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并与国内的极端环境保护组织、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思潮里应外合、愈演愈烈,妄求以环境问题为砝码剥夺中国的现代化资格。同时要看到,将表现为货币形态的经济发展总值作为衡量发展水平的唯一指标也是不可取的。曾盛行于国内的传统发展观认为,只要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整治思路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这种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方式打破了自然界的内在循环机制,对大自然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破坏。因此,寻找一条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各要素有机整合、协调发展的道路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着精辟洞见,“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3]316,准确把握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而突破了工业化时代下对于人与自然关系机械的认知方式,以生态化、整体化、可持续化的视角来辩证性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扬弃了人与自然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基于此,我们应明确建设工业文明、实现工业现代化与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双重任务,正确认识和理解现代化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并行不悖、相互融合的耦合性关系,赋予我国現代化发展以新的生态内涵与指向。具体地说,在农业方面,要加强研发优质化肥产品,搭建循环利用畜禽粪便、秸秆、农药包装物的产业闭环,以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为抓手提升、优化、打造农产品的品种、品质、品牌;在工业方面,摒弃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为基础的粗放型工业模式,发展以低耗能、低排放、高质量为特点的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工业发展过程中,以最低生态代价谋求满足当代人需要,并造福子孙后代的永续发展。
(二)聚合科技要素,赋能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并非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高兹对市场和科技的存在合理性持肯定态度,但他指出必须将市场限定于某些契合经济理性的领域内,限制市场与经济理性边界的畸形膨胀,发展具有生态效用的技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对于资本的接纳也带来了诸如填湖造景、私挖滥采、占用耕地等掠夺自然、破坏环境的现象。逐利的本性使资本纷纷向低成本、高利润、回报周期短的行业涌动,反观以高成本、回报周期长为特点的环保行业,其生态科技、生态生产力和生态资本的有效供给明显不足。要逐步解决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从两处着手:
一是坚持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资本主义妄求使用“技术的魔杖”来减缓经济增长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但无数事实已经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辅助资本主义劫掠自然的帮凶。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切实需要,“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13]362,科学技术才得以成为人与自然互利共进的助推器。国家要继续引导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利好民众和利好自然作为科技研发与创新的重要指标,消除科技研发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以牺牲人体健康为代价的陈旧观念,扶持研发更多优质、精良的绿色科技产品和服务。
二是完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国外自由市场经济对于经济理性的无限度放任和纵容,已然造成能源枯竭、物种灭绝和全球性生态灾难等攸关人类存亡的危机,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血淋淋的负面素材。只有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发挥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作用,才能约束和抑制资本的贪婪本性,才能防止追求不断增殖的资本合理化和制度化,才能驾驭和利用资本助力于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改善;而“生态”二字赋予了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以更高层次的含义,有利于根治市场经济下资源利用不充分、配置效率低下、短期逐利决策行为密集等生态市场顽疾和体制桎梏,从而在经济体制层面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坚持以人为本,以生态教育为手段培育生态意识
人类是作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而存在。人的存在,不仅要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而且要对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转负责,生态危机实质上也反映出人们价值观念的失准与偏颇。高兹聚焦于马克思笔下“现实的人”,指出生态危机的解决最终取决于对个人价值观的生态化改造,即通过生态教育来培育人的生态意识。生态意识,内化为人类尊重自然、亲近自然的道德修养和价值观念,外化为污染整治、生态修复等具体的环境保护实践。“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14],生态文明的产生、建设与固守,都需要“现实的人”来承载。根据我国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公共生态意识与行为已有所提升,但仍存在着明显的“高认知度,低践行度”现象,人们呵护自然的责任感与道德感亟待加强。究其原因,这与我国目前生态教育在总体上的滞后性不无关系,具体表现为生态教育体系不完备、生态教育内容不深入、生态教育主体不专业、生态教育方法不健全、理论教育与生态实践不连贯等等。基于此,我们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建构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相承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相整合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革新生态文明教育内容话语,促进生态文明教育内容既“转时态”又“转语态”,建立科学的生态文明教育督导机制,对生态文明教育工作的实效进行考察与评估,借助新媒体技术的传播途径多元化、传播渠道扁平化优势,扩大生态文明教育覆盖面,以期在社会层面平衡“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厚植公众环境伦理道德,呼唤人们心中向往“枕山臂江”“天人合一”的本真良知和勤俭节约的质朴美德,使每个社会成员真正践行生态理性指导下“够了就行”“知足而乐”的可持续性消费观,超越经济理性指导下“多多益善”“越多越好”的不可持续性消费观。
五、结语
高兹的生态思想一直遭到诸多质疑。学界普遍认为,高兹要求限制经济理性、打破资本主义发展范式的构想具有鲜明的乌托邦色彩,有悖于现实实际。然而,当我们转变固有的对高兹生态思想的解读视角与理解范式——将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纳入“生态危机论”中进行审视和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高兹的生态思想始终贯彻了对生态危机问题的关切这一逻辑主线。他提出的“生态-商业”和“生态-工业”发展思路、在制度设计中增加生态视角、发挥社团的生态教育功能等“应然”思想,无不在现实中存有积极的“实然”要素,彰显了其思想滋生于社会现实土壤之上的现实关切。他本人也曾说,“重要的不是要定义一种新的、一致的政治方案,而是要提出一种新的、有想象力的态度,这种态度将是激进和颠覆性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改变我们发展的逻辑”[8]83,并且由此尝试去寻找一种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体,求解“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难以兼容的悖论。因此,我们正确的态度不是苛责前人,而是审慎思考,吸收借鉴其思想中的精华来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参考文献:
[1] 冯旺舟.技术的异化与国家的转变——论安德烈·高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J].山东社会科学,2019(7):21-27.
[2] 吴宁.消费异化·生态危机·制度批判——高兹的消费社会理论析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4):122-129,160.
[3] 王磊峰,陈永森,刘伟伟.论析高兹生态社会主义的劳动观[J].江西社会科学,2013(7):13-18.
[4] 庄立峰,叶海涛.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考察[J].思想理论教育,2014(4):49-53.
[5] 包庆德,贾敏.宁少但好: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构想[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8(5):106-111.
[6] 安德烈·高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迷失与方向[M].彭姝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7]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 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 [M].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
[9]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6.
[10] 李全喜.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政治哲学意蕴的存在前提[J].学习论坛,2019(6):70-75.
[11] 陈培永,刘怀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构架[J].南京社会科学,2010(2):50-57.
[12] 余谋昌.生态文明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2.
[1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3.
(责任编辑 朱 凯 李 亮)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ecological crises is a major meta?problem in the overseas Marxist ideological trend. In the western ecological crisis theory pedigree, the “ecological crisis theory” expounded by André Gorz, an ecological Marxist, is profound in meaning and rich in connotation. Through the ecological criticism o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Gorz believed that the capitalist system is the root cause of ecological crises. The ecological crise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vere with the stimula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reach the peak with the capitalized 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rz then reflected on the modernity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made an ecological criticism on the old socialist model, negating the claims of ecological fundamentalism and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in the old socialist model and reaffirming the ecological enlightenment behind the socialist vision. Finally, he proposed the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thought that would surpass capitalism from the dimensions of production mode, life style and thinking mode, and thus set up the overall model of ecological socialism. It can be found that Gorz fully absorbed the wisdom of Marxism view of nature when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crises, digging for the root cause and seeking for the treatment of ecological crises. His exposi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theory” showed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ism. Sorting out the logical approach of Gorzs “ecological crisis theory” can provide enlightenment of thought and path for Chinas ecological crisis management.
Key words: Gorz; ecological crisis; Economic Rationality; ecological socialism;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