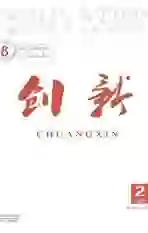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之审美
2021-08-16韦蕊
[摘 要]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之韵味,是中国人在演唱艺术中所追求的深远意味,是民族声乐艺术魅力之所在,更是中华民族整体精神风貌的体现,其美学标准建立在中国戏曲、曲艺、地方民歌等传统和民间的音乐艺术审美追求基础之上。中国民族声乐中气息技巧、吐字行腔和抒情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审美特点——韵味,可从气韵、声韵和情韵三方面进行解读,其蕴含的声学、美学、哲学知识丰富,对当今流行音乐的发展仍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 民族声乐艺术;审美;韵味
[中图分类号] J6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21)02-0092-09
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从广义上来讲,主要包括传统的戏曲演唱、曲艺说唱和民族民间歌曲的演唱三大类民族演唱艺术,也包括新民歌、新歌剧的演唱和西洋唱法民族化的演唱等”[1]。回顾中国声乐艺术发展的数千年历史,从远古时期先民唱的“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的弹歌,到梨园、戏台、剧场的演唱,中国声乐艺术经过了历朝历代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国家,具有民族特色的声乐艺术审美特色——韵味。这些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味”,是民族声乐艺术的魅力之核心,更是中华民族整体精神风貌的体现。
一、韵味在声乐艺术中的美学解释
韵味作为中国传统的美学概念,最初是广泛运用在诗词、山水画等文艺创作中,指的是艺术作品必须达到某种审美风貌和意境[2]257,是美学的中心。后来“韵味”这个词也被大量运用于由文人参与的中国戏曲、曲艺的创作中,意指曲文既讲究文辞、格律,又讲究音韵和意境。而在传统的戏曲表演艺术中,“味”的解释是“剧种旋律、戏曲化的发声(行当音色、表现音色)、吐字(喷口力度、字音反切)、乐汇音型语音化(上、下滑音)、音符群(大、小颤音,上、下颤音,装饰音)以及喉阻音(虚阻音与实阻音)、立音等多种多样的用嗓技巧”[3]90-91。如果用记谱的方法将美妙动听的戏曲唱腔中的声音滑动进行记录,再机械地照谱宣唱,唱出来必然是缺乏生气、呆板没味儿的。几百年来,民族声腔艺术口传心授、代代繁衍的特点,使得这种韵味蕴藏在旋律的语音化中,蕴藏在用嗓、行腔、发声吐字的艺术技巧中。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和历代文艺家们的总结提炼下,积累并形成了一整套民族传统声乐有关咬字行腔的美学原则和方法技巧,韵味从中得以窥见一斑。从各种戏曲、曲艺、民歌唱法的用腔来看,各种调整字音声韵、带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润腔,以及为表现人物性格特色而进行的力度和表情处理,都对词曲和谐畅达、曲情表现的完美统一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在民族声乐艺术中,韵味是一种从内外部技巧到情感体验创造都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审美的要求;在吐字、行腔、用声和抒情方面,都表现出了约定俗成的美学原则的艺术效果。这是评判声乐艺术作品是否具有审美价值的重要标准,更是中国民族声乐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毕生追求的美学理想。
二、中国民族声乐艺术韵味的解读
(一)气韵
在中华民族传统审美经验中,“气韵”是中国古代艺术美学领域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也是历代艺术家和批评家评价艺术品的重要话语。“气韵”原不是一个词语,最早“气”是在古代生命哲学中为中国古代哲人所重视。古代先哲认为生命现象产生于气,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气韵”作为一个词出现在艺术美学理论的范畴,最早是在绘画领域,魏晋南北朝的谢赫在《古画品录》论“六法”中提出,“氣韵生动”居于“六法”的首位[4]7。其中,“气韵”指的是绘画表现出的人物的人性气质、精神风度,是对顾恺之的“传神论”观点的发展和升华,“气韵生动,乃顾恺之的所谓传神的更明确的叙述,凡当时(指魏晋时期)人伦鉴识中的所谓精神、风神、神气、神情、风情,都是传神这一观念的源泉、根据,也是形成‘气韵生动一语的源泉、根据”[5]。五代画家荆浩继其后提出,“山水画的‘六要(气、韵、思、景、笔、墨),其核心是强调要在‘形似的基础上表达出自然对象的生命”,“认为外在的形似并不等于真实,真实就是要表达出内在的气质韵味”[2]279,“气韵”被认为是艺术作品的灵魂,此后也成为整个中国画的美学特色,被作为中国绘画艺术所追求的最高标准。而在书法艺术中,同样也非常重视艺术作品的神采风韵。唐代书法家张怀瓘云:“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6]宋代书法家蔡襄在《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三十四论书道:“学书之要,惟取精神为佳。若摹象体势,随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之所为耳。”[7]从战国时期《列子·汤问》中钟子期对伯牙琴声的评价“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8]到明代朱权在《善歌之士》中对歌者演唱的评价“一声唱到融神处,毛骨萧然六月寒”[9]可以得知,不管是在绘画和书法艺术领域,还是在音乐艺术领域,气质和神韵都是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品评音乐作品的重要标准。只有抓住表现对象的气质神韵的音乐作品,才能使作者和听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与西方的写实主义不同,中国人更注重把握艺术作品的精神灵魂。“在中国古代美学体系中,‘气韵生动的命题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说,不把握‘气韵生动就不可能把握中国古典美学体系。”[10]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中的“气韵”,气为韵之本,韵为声之魂。在声乐艺术中,没有气就没有声,更没有所要表现的一切事物的精神风韵。气是声乐表演艺术的基础,气息的运用是声乐表演艺术家必须掌握的基本技术,而唯有灵活掌握气息,赋予气息以作品的思想和情感,才能产生韵味,使声乐作品生动和鲜活起来。在古代声乐论著中,气息技巧作为发声技巧的基础,地位无可替代。唐代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说:“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间出,至喉乃噫其词,即分抗坠之音,既得其术。即可致遏云响谷之妙也。”[11]294清代陈彦衡在《说谭》中说:“夫气者音之帅也,气粗则音浮,气弱则音薄,气浊则音滞,气散则音弱。”[12]气主宰着音和韵,决定了作品的格调。
元代燕南芝庵在《唱论》中谈及歌之格调:“抑扬顿挫;顶叠垛换;萦纡牵结;敦拖呜咽;推题丸转;捶欠遏透。”[13]16其格调无不是运用气息技巧所致。不同的气息技巧会产生不一样的艺术效果。例如,表现水面或草原的宽广,山川或河流的蜿蜒起伏,气息是一贯到底、连绵不绝的萦纡,如长调风格的蒙古族民歌《牧歌》和反映赫哲族人民劳动生活的《乌苏里船歌》的引子部分,就是通过控制腹肌的力量,使气息平稳均匀地支持声音,来营造一种舒展宽广、安静宁谧的画面和烟波浩渺的韵味。例如,表现悲愤激烈或高昂激扬的情绪,气息是喷薄而出,依靠腹肌的爆发力、有力收腹的顶气,从而使气息力量集中支持声音奔涌而出,造成一种如虹的气势,如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最后一句“泪飞顿作倾盆雨”[4]28,在短暂休止后的“倾”字与前面“作”的音构成了八度的大跳音程,喷气的技巧非常有感染力地表达痛失亲人,犹如五雷轰顶般痛彻心扉的感情。还有表现欢欣鼓舞的气氛、活泼热烈的情绪情感时,气息的支持是饱满积极富有弹性的,在乐曲速度较快、乐句较长的情况下,还要使用偷气、抢气等技巧来获得响遏行云、高亢婉转的声音,从而营造出欢快热烈的气氛。
在声乐艺术中,“气韵生动”一方面指演唱者运用不同的气息技巧产生不一样的艺术效果,另一方面指“反映客体作品和表演主体的生命活力的气势”[14],即演唱者在诠释声乐作品时所赋予作品的气质和生命力。例如,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演唱歌曲《梅花引》时,对首句“一枝梅花踏雪来”[15]的“踏雪”二字间做声断气不断的十六分休止的处理,赋予了梅花灵气和生命力,把梅花似仙子一样踏雪而来,傲然挺立在白雪天地间的形象鲜活地表现出来。又如,男高音歌唱家郭颂的经历使得他的歌声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都是歌唱家本身的审美喜好和二度创作所给予音乐作品的气质。因此,声乐作品的气韵不能脱离演唱者而单独存在,它深受演唱者自身的气质风度和艺术追求的影响。
(二)声韵
最早记录我国音乐美学思想的著作《乐记》中有言:“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6]语言是歌唱抒发情感的载体。我国民族声乐艺术中的语言,以声(五音)、韵(四呼)、调(四声)为特点的汉语语音体系为主。汉语的这些特点形成了我国民族声乐讲究咬字吐字的传统,形成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特有的民族韵味。
1.声之韵,在于字头腹尾之运化
在声乐艺术中,“词”是“情”的主导。吐字艺术是韵味的构成因素,在以声传情的艺术实践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明代魏良辅在《曲律》中提出:“曲有三绝:字清为一绝;腔纯为二绝;板正为三绝。”[11]495他将“字清”作为声乐艺术审美的首要标准。清代的王德晖、徐沅澂在《顾误录》中说:“唯腔与板两工,唱得出字真,行腔圆,归韵清,收音准,节奏细体乎曲情,清浊立判于字面,久之娴熟,则四声不召而自来,七音启口而即是,洗尽世俗之陋,传出古人之神,方为上乘。”[17]用“真、圆、清、准”几个字点出了传统声乐美学中对字、腔、音、韵的审美追求。传统声乐理论把歌唱的吐字归纳为“出字”“引长”“收声”的过程。清代著名的戏曲家、小说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声音韵味的奥妙就体现在字头腹尾的处理上,他认为吐字最难的、又必不可少的是要把握“出口”和“收音”两个诀窍,唱一个字要把握三个部分,字头“以备出口之用”,字尾“以备收音之用”,“又有一字为余音,以备煞板之用”,但是字头、字尾和余音又不能太刻意,必须自然而然,浑然天成,“字头、字尾及余音,皆须隐而不现,使听者闻之,但有其音,并无其字,始称善用头尾者”[13]144。
(1)字头韵
中国民族声乐中歌唱发声的字头指的是字的声母。即使是没有声母的字,也很重视从静止到韵母的发声过程。在传统民族声乐理论中,字头对表现歌曲的情绪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声母发音的准确、有力、夸张能更深刻地表达歌曲的情感。戏谚:“咬字千斤重,听者自动容。”[3]112唇、舌、齿、牙、喉“五音”,其發音部位不同,声母阻气与出字破阻之间摩擦发出的音,就形成了塞音、擦音、塞擦音、边音、鼻音等不同的声音效果,既增强了歌曲的表现力,也给歌曲带来了不一样的韵味。
20世纪80年代家喻户晓的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因其富含人生哲理的歌词、通俗易唱的旋律以及富有民族韵味的演唱,一直传唱了30多年而经久不衰,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这首歌最初由张暴默演唱,但她唱的版本太抒情和柔美,导演认为不大符合整部剧给人的形象感受,于是最后换成了蒋大为的民族男高音版本。歌唱家蒋大为在谈对这首歌曲的二度创作时,一直强调要顺应语言的味道去唱歌,他认为把握语言就是歌唱成功的第一关键因素。他说,在拿到这首歌曲时,他反复地朗读歌词,到唱歌时,自然而然地加入了一些处理,使得歌唱更富有韵味。比如,他在“一番番”和“一场场”的字头上加入了下滑音的处理。下滑音的运用使字头更有力量,增长和强调了“番”字头在唇与齿和“场”字头在舌与齿部位间摩擦的时值。这样的处理使字头更带劲儿,充分表现出了奋进中饱含的辛酸,使得歌曲在高亢中又带着苍凉,让人不禁联想到取经路途的艰难和唐僧师徒4人百折不回的精神,从而受到鼓舞。
(2)字腹韵
咬住字头,紧接着要向韵母过渡。韵母又有头、腹、尾三个成分。其中,字腹是韵母的主要母音,在歌唱中有吐字引长的作用。因此,在民族声乐理论中又把字腹称为“引长”。无论是单韵母还是复韵母,对字腹的演唱要求是在音值引长延伸时,字不变形,并且要根据歌曲情感表达的需要调节气息的强弱和共鸣腔的空间大小。“橄榄腔”是我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昆曲中非常重要的演唱技巧,这个技巧的运用使情感表达更含蓄、更细腻。它的要领主要是在一个字的字腹上用功。通过控制气息,使字腹的音量由轻而重,再由重转轻,像橄榄一样两头小中间大,从而使歌声听起来深情动人,情感细腻深邃,如临帖一样笔笔勾勒,字字讲究,耐人寻味。例如,昆曲《牡丹亭·游园·醉扶归》的旋律有一字多音的特点,橄榄腔的技法就把昆曲在一个字上迂回婉转用功的细腻讲究的“水磨调”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如“袅晴丝吹来闲庭院”[18]9的“闲”字,出字后要在韵母“i”音上拖完三拍,在1、2、3三个音上分别做橄榄腔后,在最后一拍的后半拍才归韵到“an”,不急不躁,稳稳地唱好每个音,才能准确地表现出杜丽娘端庄持重、挪步暗生香的闺秀气质。又如由汉乐府诗中的《上邪》改编而成的艺术歌曲《长相知》,表现了一位女子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态度。许多歌唱家在演唱这首歌曲时,在“上邪”的“邪”和“我欲与君长相知”[19]的“知”字等一字多音的韵母上都做了橄榄腔的演唱处理,充分表现了古代女子表白时内心的情感由羞涩到渴望,转而压抑控制的“由收到放再收”的含蓄的内心变化过程。橄榄腔的字腹韵腔处理,也表现出我们较之西方,在表达激情的习惯、方式上不同的含蓄的民族性格特点。
(3)字尾韵
传统民族声乐理论中非常重视字的收音。如果字尾收音不分明或不准确,就会影响词义的表达。字尾的收音又称为“归韵”。传统声乐艺术演唱的归韵,按照相同或相近的韵母分类为“十三辙”。合辙押韵后就会产生不同的韵味特点。如“-n”和“-ng”二者虽然都是收归鼻子音韵尾,但前者是收前鼻音,后者收后鼻音,若归韵不准确,不仅韵味受影响,意思的表达也会受影响。南宋张炎在《词源·讴曲旨要》中道出了以字成韵的奥秘:“腔平字侧莫参商,先须道字后还腔。字少声多难过去,助以余音始绕梁。”[20]他指出,遇到歌词少、拖腔长的情况,如果在出字后运用归韵和装饰音的方法进行处理,就能使声腔更婉转,形成余音绕梁的效果。
20世纪40年代后,我国出现了一大批民族声乐艺术家,如王昆、郭兰英、常香玉、李谷一等,她们的演唱技艺构筑在中国传统曲艺、戏曲、民歌的基础之上,她们有的以传统戏曲为基底并向民歌学习,有的根植于民歌的土壤再借鉴戏曲的唱功。在民族声乐艺术领域,她们对韵味的追求和创造一刻也没有停止。曾被《人民日报》评价为“为我国声乐艺术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并载入我国音乐艺术发展的史册”的歌唱家李谷一,她的声音中有着“一种得益于传统戏曲和曲艺的熟稔”[21]。她演唱的《乡恋》,因富有个性的声音和独特的民族韵味而曾风靡了整个中国。开头几句“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她对切分节奏进行了换气处理,在“你”与“的”、“永”与“远”、“我”与“的”之间造成了一种停顿的感觉,又把“身影”“歌声”“印在”“心中”的“身”“歌”“印”“心”四字的韵母,分别是“en”“e”“in”和“in”,都在其小節最后一拍的两个余音上做了韵尾归韵的韵腔处理。这个处理非常巧妙,漫不经心地听会觉得与众不同,细细品味则感到意蕴生动、余音绕梁,不仅突出了“身影歌声印在心中”的歌曲主题思想,也把歌曲的艺术形象展现得惟妙惟肖。带有京韵大鼓风格的歌曲《故乡是北京》,如果严格按照谱子唱,很难体现出京韵的味道。而李谷一在演唱时,对旋律进行了特殊处理,在字尾的归韵上大做文章。例如,“静静地想一想”的第二个“想”字,她巧妙地加入了休止,把“想”字的字头和字尾归韵分开,出字即停,转而用后鼻音韵母“ang”在两个音上强调并延长,不仅表现出了人在沉思时的状态,也把以鼻腔归韵为主的京韵特点瞬间凸显出来。
2.声之味,在于丰富多彩的润腔技巧
“润腔”是情感表达的民族化、艺术化,是声音在歌唱抒情技巧里的艺术升华,是使没有生命的音符变得生动传神,从而使声乐艺术作品透过表象,成功实现意象的表达的重要技巧。在我国传统声乐艺术和民族民间音乐中,韵味常藏于润腔之中。不论是传统戏曲,还是民族民间歌曲,在传统民族声乐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都积累了丰富的润腔装饰技巧。这些腔调大多与所唱字音的四声调值密切相关,又或者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变迁发展过程中的民族文化和情感的印记。
(1)为顺应字音的四声调值而用的润腔
为顺应字音的四声调值而使用的润腔,不是旋律结构中的音,而是演唱者结合了所唱的字的四声阴阳的调值,对歌曲旋律所做的增加音符的特殊处理。昆曲中常用的润腔装饰细分起来有16种之多,几乎都是为了调整腔与字音之间的关系而存在的。例如:在一些音调向上的旋律中,对于歌词中的某些字音来说,中间相差一个音,这时候为避免曲调不顺,就在中间添加一个音,这个音就是“垫腔”,如《牡丹亭·游园·皂罗袍》中“谁家院”[18]11的“谁”字,腔格为“[62] ”,在这两个音中间加了一个“l”音,这个“l”音就是“垫腔”。“垫腔”这种润腔技巧更适用于缠绵悱恻的曲词,它的运用可以使曲子更婉转多情。歌唱家在对一首民族风格的歌曲进行演唱的二度创作时,通常先对歌曲的一字一句进行认真分析,在歌曲旋律与字音不是非常贴合的情况下,会在不贴合字音的旋律音上加入前倚音或后倚音等装饰音,使旋律更符合字的音调。加入装饰音也是润腔技巧的一种。例如:歌曲《十五的月亮》,“十”在普通话中的音调是阳平,调值是由中升到高,旋律中只有一个音“5”就立即过渡到“五”字上了,如果按照谱子的旋律唱,唱出来就是“失”的阴平调,听起来字义会有误。因此,歌唱家演唱这首歌时,会在“十”字的“5”音上加入一个下方小二度的前倚音“#4”,使字更符合由中升到高的音调特点,听起来更朗朗上口,亲切动人。
(2)镌刻着民族文化和情感印记的润腔
这种润腔方式大多存在于民间歌手的演唱中,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生存环境息息相关。例如,生活在高原、高山等地区的民族民间歌手所唱的民歌中,会较多的存在拖腔和滑音等润腔装饰。苗族民歌手在唱“飞歌”时,句内的滑音和句尾的甩音是他们惯用的润腔方式,这既充分表现了他们所生活的大山地势险峻的特点,也表现了苗族人民性格中的豪放张扬。又如,瑶族、京族、纳西族等在生活方式上有迁徙或游牧特点的民族歌手,其歌声中自带有“颤音”这种独具特色的润腔方式。用声乐理论来分析,“颤音是在一种‘气与‘力的配合中产生的,是在气息的冲击下,声带在向下拉紧和向上放松之间快速变换,使喉头呈现纵向颤动的结果。”[22]这种带有技术难度的颤音,听起来像是民间歌手刻意追求的艺术表现手段,但当问及他们为什么这么唱时,瑶族人民回答“习惯用这种声音”[23]。这种润腔方式是迁徙民族艰难迁徙历程的印记,能让人感受到这个民族在长期迁徙历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与磨难。
这些镌刻着民族文化和情感印记的润腔,能穿越时空,直抵人心,不仅让人陶醉于声音中所蕴含的自然与人文情态、民族情怀,更让人惊叹中华多民族文化的多彩魅力。
3.声之妙,在于顿挫得法、抑扬有道
“顿挫”一词出自《后汉书·孔融传赞》,以评价声调的抑扬和停顿转折。诗文和绘画、书法艺术中以“笔法顿挫”来形容内容的跌宕起伏、回旋转折。戏曲昆腔中有“顿挫腔”一说,意思是在第一个音符出口后稍停顿一下,之后再用虚声唱出另一音符,用虚声唱的音符称为“挫”,前后顿挫的两个音则呈现出实虚的音色对比之美。清代声乐理论家徐大椿认为:“唱曲之妙,全在顿挫,必一唱而形神毕出,隔垣听之,其人之装束形容,颜色气象,及举止瞻顾,宛然如见,方是曲之尽境。”[11]618“顿挫”的用声技巧出神入化地表现了曲子的神韵和情感,“顿挫得款,则其中之神理自出,如喜悦之处,一顿挫而和乐出;伤感之处,一顿挫而悲恨出;风月之场,一顿挫而艳情出;威武之人,一顿挫而英气出;此曲情之所最重也”[11]618。如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在《谁说女子不如男》唱段末句“这女子们,哪一点儿不如儿男?”中“男”字的拖腔后运用了顿挫技法,把花木兰的巾帼英气生动地展现了出来。在戏曲声情艺术实践经验里,有一句话叫作“轻、重、抑、扬出感情”[3]120。这句话正是对顿挫技法的补充说明。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对字的抑扬顿挫之道也有所总结,他认为:“曲文之中,有正字,有衬字。每遇正字,必声高而气长,若遇衬字,则声低气短而疾忙带过。”[13]158演唱中的抑扬顿挫能使音乐这种听觉艺术呈现出明暗虚实对比的视觉效果,给人无限的遐想,同时也展现了中国传统艺术注重虚实结合、起伏跌宕的线条美的审美特点。
(三)情韵
声为情之形,情为声之本。无论是将激情蕴含于旋律意境,用含蓄的方式表现在板路腔调上的昆曲、京剧艺术,还是将激情形之于声音旋律,以更生活化接地气的音乐形象来感人的评剧、豫剧等地方戏曲和民间小调,情韵始终是声乐艺术作品表现追求的终极目标。我国民族声乐艺术自古以来都注重声情结合,以情动人。正是因为有了情韵,它的音乐语言才成为人民的音乐语言,它的激情才能动人,含蓄而富有魅力。
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声情并茂。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有终日唱此曲,终年唱此曲,甚至一生唱此曲,而不知此曲所言何事,所指何人,口唱而心不唱,口中有曲而面上身上无曲;此所谓无情之曲,与蒙童背书,同一勉强而非自然者也。虽腔板极正,喉舌齿牙极清,终是第二第三等词曲,非登峰造极之技也。”[11]593歌者必须先用心感悟曲中之情,心有所感,有感而发,歌声才能牵动听者的心。歌者的声情要与曲情相合,曲情与心意相通,情与景相融。只有心口同唱,声情并茂,歌唱技艺才能登峰造极。晋代张华的《博物志》中记载了春秋时期一个名叫韩娥的民间女歌手,她的歌声极富感染力,人们能从她的歌声中感受到她的情绪,并被其深深打动,因她的歌声欢快而开心、悲愁而泣涕。她要到齐国(今山东省大部)去,因为没有旅费,便转往雍门(今陕西咸阳)借歌唱谋食。她住在旅店中,有人用言語羞辱她,她便曼声哀哭,用歌声尽情表达她的悲伤。当地的人们听了,便整日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不能自拔,只能请她改用柔婉的声调再唱首欢乐的歌,人们这才从悲伤的情绪中解脱出来,被她的歌声感染而又欢欣鼓舞[13]2。由此,足见感情浓郁的歌声有着多么神妙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一位歌者,其演唱的歌声必须发自真心,真情流露,才能将歌中之情传达出来,与听众产生共鸣。任半塘在《唐声诗》中讲道:“歌者不可轻于启喉,必待自己之真情既发,而后再有声辞之吐;能先触发自己之真情者,自能宣达声与辞中之歌情,以度予听者。”[24]我国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在回忆自己演唱歌剧《白毛女》时说,当时她是一个字一个动作地去揣摩人物的内心,务必要做到真实。青年歌唱家雷佳在回忆复排歌剧《白毛女》的经历时说,郭兰英老师在指导她演唱和表演时一直强调要真实。让她最为感动的是郭老师在示范喜儿哭爹那场戏时,完全不顾90岁的高龄,亲身示范,毫无保留。郭老师当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让所有人都惊到了,一声“爹”更是瞬间把大家的眼泪给喊出来了。剧情和曲情中的情韵就是通过歌者的真诚感悟,饱含在歌曲的一字一句中,使听者动容。
情之韵味,既宣达于词与声中,又蕴含于心中之真情,只有设身处地,力求将曲中之意形之于声音,才能使声音技巧与情感表达合二为一,达到声情并茂的最高艺术境界。
三、结语
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博大精深,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其中蕴含的声学、美学、哲学知识丰富,对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仍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流行音乐界被奉为传奇的女歌手王菲曾说她的歌唱风格深受邓丽君的影响,而被誉为“国际天王巨星”的邓丽君自幼受到大家闺秀的母亲的影响,爱听黄梅戏、评戏等地方戏曲,耳濡目染,戏曲功底为她辉煌的流行歌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根基,使她歌唱的音色、咬字、气息的运用都具有独特的民族韵味。邓丽君的歌声牵动着海内外华人,至今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音乐人,这也正是民族声乐艺术中所蕴含的气韵、声韵和情韵的深厚艺术魅力之体现。无独有偶,曾深受老百姓喜欢的流行歌手屠洪刚是京剧演员出身;著名流行歌手韩红一直都从民族声乐中汲取养分,并在流行音乐界将其发挥到极致。这都是民族声乐艺术之韵味赋予他们歌唱技艺不一样的艺术魅力。曾经培养了韩红、雷佳、龚琳娜、吴碧霞等当代著名歌唱家的民族声乐教育家邹文琴,在她几十年的声乐教育生涯中,最注重的就是继承民族声乐的优秀传统。她认为要发展民族声乐,既要借鉴西方演唱技法,更要从民族传统中汲取养分。曾任天津音乐学院院长的音乐教育家石惟正,在《人民音乐》发表的文章中高度评价了邹文琴在中西传统声乐的优势契合上所做的努力。谈到继承传统的重要性,他说:“我国20世纪初到现在的专业歌唱史就是一部继承民族传统和借鉴西方的中西碰撞、交流和优势契合、出新的历史。”[25]演唱者只有深深根植于民族的土壤,将民族的演唱技巧和表现方式,融会贯通地运用于自己的演唱创作,才能使演唱富有深厚的底蕴和魅力,质朴中透出感人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李晓贰.民族声乐演唱艺术[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1.
[2] 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3] 陈幼韩.戏曲表演美学探索[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
[4] 王夏.声乐表演艺术中的“气”与“韵”[D].杭州:杭州师范大学,2009.
[5] 徐复观.中国古代艺术精神[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134.
[6] 张彦远.法书要录[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152.
[7] 水赉佑.蔡襄书法史料集[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8.
[8] 列子[M].殷敬顺,陈景元,释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55-156.
[9] 朱权,姚品文.太和正音谱笺评[M].北京:中华书局,2010:151.
[10] 叶朗.中国美学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0.
[11] 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12] 陈彦衡.说谭·总论[J].中国戏剧,1995(11):56.
[13] 周贻白.戏曲演唱论著辑释[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
[14] 杨易禾.音乐表演艺术原理与应用[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259.
[15] 蔡世贤.中国艺术歌曲选(1996—2003)下册[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239.
[16] 礼记[M].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760.
[17] 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M].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159.
[18] 张卫东.张卫东演唱说戏牡丹亭[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0.
[19] 杨曙光.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赏析与演唱[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8:66.
[20] 张炎,沈义父.词源注 乐府指迷笺释[M].夏承焘,校注.蔡嵩云,笺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4-15.
[21] 李诗原.李谷一声音的个性、魅力与价值[J].人民音乐,2020(3):4-11.
[22] 韦蕊.瑶族民歌唱腔特色及其文化内涵探究[J].百色学院学报,2018(5):82-90.
[23] 毛殊凡.瑶族历史文化与现代化[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62.
[24] 任半塘.唐声诗: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95.
[25] 石惟正.邹文琴教学随想[J].人民音乐,2010(1):58-59.
[責任编辑:丁浩芮]
The Charm of Music: Artistic Aesthetics of Chinese National Vocal Music
Wei Rui
Abstract: The charm of Chinese national vocal music is what Chinese people pursue in the art of singing and is the reason why national vocal music is so appealing. It also reflects the overall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s aesthetic standards are based on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folk songs such as Chinese operas, folk art forms and local folk songs. The charm of Chinese national vocal music as shown in breath technique, enunciation and lyricism can be interpreted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breath, sound and lyricism. It contains rich knowledge of acoustics, aesthetics and philosophy and still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pop music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national vocal music; aesthetics; ch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