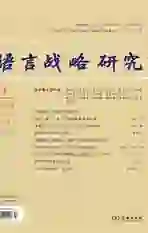缅甸华语传承模式研究
2021-08-09李春风

提 要 缅甸华语传承模式有4个发展阶段,南北两条传承链。缅北为:顺外传内-完全传承→顺外传内-传承受阻→顺外传内-传承复苏;缅南为:顺外传内-完全传承→顺外弃内-传承中断→顺外拾内-传承复苏→顺外传内-传承复苏。缅甸华语传承模式、华人与主体民族的语势和语言-文化适应关系构成的三要素变迁系统,其发展趋势是:“顺外传内-传承复苏”模式是缅甸华语传承的历史选择,“外势大于内势”是缅甸华语语势的客观趋势,同化是华-缅族语言文化关系的发展走向。国家语言政策对跨境移民群体语言文化有制衡作用,甚至对其走向起决定作用;经济价值是永恒的变量,是激发新生代华人传承华语的最主要动力;跨境移民群体语言文化被同化是不可避免的,要及时抢救挖掘海外华语资源;华人处理好语言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能为中缅搭起互信互助的桥梁。
关键词 华语传承;模式;变迁;语势;同化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21)04-0019-10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402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various models of Huayu inheritance among overseas Chinese and different factors underlying these model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model of Huayu inheritance in Myanmar,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four development stages and two inheritance chains. Three elements constitute the changing system of Huayu inheritance model in Myanmar: the model of Huayu inheritance, the vitality of Burmese versus Chinese inside and outside Chinese families, and the lingua-cultural adaptation relationship. As far as its development trend is concerned, the model of “outward adaptation to the majority language and inward maintenance of the minority language” is the historical choice; the vitality of Burmese outweighing that of Chinese is the trend, and the lingua-cultural development trend between Chinese and Burmese cultures is towards assimilation. The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has a check and balance effect on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cross-border immigrants, and it even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ir development trend. In addition, the economic value of Huayu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new Chinese descendants to inherit Huayu. It is suggested that Chinese descendants shoul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language identity,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us building a bridge of mutual trust and assistance between China and Myanmar.
Key words Huayu inheritance; model; changes; language vitality; assimilation
一、華语传承及传承模式
语言传承指族群语言在不同代际间的传承。我国语言传承研究领域中的“华语传承”“祖语传承”,是能将国内外华人语言传承研究联系起来的重要术语(李春风2019),可用于所有社会主体语言之外的族群语言,现阶段多用于海外华人的语言文化传承研究。
关于华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很多学者已做过探讨(李宇明2017;周明朗2017;陆俭明2019;等等)。郭熙(2004,2006)认为,海外华人社会的“华语”不是汉语的任何一种方言,它建立在方言之上,同时又是超方言的,是一种标准语。他把华语看作“祖语”(郭熙2015)。祝晓宏、周同燕(2017)也认同华语是指向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华人共同语。郭熙(2017)的祖语阐释中,则包括方言等。基于缅甸的实际,本文采用更广义的华语概念,把汉语方言等也包括进来。
郭熙(2017)从代际传承角度将祖语传承分为完全传承、传承中断、完全隔绝3类。完全传承,即除了完整习得母语之外,还有机会接受系统的祖语教育;传承中断,分为新移民后代和史上华裔两种情况,总的来说是缺乏或者难以持续下去的祖语教育;完全隔绝,即下一代完全没有接触祖语,即使他们所处的祖语家庭或者社区或多或少地给了他们一定程度的接触机会。
周庆生(2018)从跨境移民群体语言文化适应性角度,将语言传承模式分为顺外弃内、顺外传内和隔外存内3类。顺外弃内,指顺应并转用主流强势语言,放弃本民族语言,达到语言融入或同化的结果;顺外传内,指既顺应主流强势语言,也保留本民族语言,兼通本族语和主流语言;隔外存内,指與主流强势语言保持一定隔阂,只在封闭的本民族语言圈内生活。
周文揭示了跨境移民群体与当地主体民族语言文化的强弱关系,郭文则是对祖语传承过程及结果进行定性。二者皆适用于华语传承研究,我们将其整合为“关系-结果”的语义结构,构建缅甸华语传承模式,即在描述缅甸华语现实传承状态的基础上为其定性。
二、研究路线、研究方法
缅甸华人华侨约250万,主要分布在仰光、曼德勒、勃生、毛淡棉等主要城市,一般从地域上划分为缅南地区(以仰光为中心的仰光、内比都等地)和缅北地区(曼德勒及以北的腊戍、木姐、八莫、东枝等地)。从祖籍地看,滇(云南)籍最多,闽(福建)籍次之,粤(广东)籍位居第三,还有海南、四川、广西籍等。闽、粤籍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南部地区,缅北地区则以滇籍为主。
缅甸华语传承情况比较复杂:从迁徙源看,滇籍与闽、粤等籍差异明显;从地缘看,缅南、缅北地域差异明显。20世纪60年代开始,缅甸实施非常严厉的遏制华文教育发展的语言政策,直至90年代才有所松动。这一语言政策对缅甸华语传承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又使之产生了明显的代际差异。因此,20世纪60年代成为当代影响缅甸华人语言传承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据此我们将缅甸华人划分出华语能力差异显著的4个年龄段:老年段(60岁以上,生于1960年以前)、壮年段(30~59岁,生于1961~1990年)、青年段(20~29岁,生于1991~2000年)、少年段(6~19岁,生于2001~2014年)。
本文探讨的对象为缅甸华语传承模式。研究路线上,我们以历时时间为纵轴,共时地域为横轴,结合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在“关系-结果”内梳理华语传承模式下缅甸华人与缅甸主体民族的语势(语言势力的强弱)、语言-文化适应关系,构建缅甸华语传承模式系统,探析缅甸不同代际华人华语传承模式变迁及其成因,客观认识流动性社会中,华语传承的特点、走向。
本文研究方法有:(1)问卷调查法。对缅甸曼德勒、毛淡棉、仰光、掸邦(东枝、果敢、腊戍、景栋)、八莫、密支那等地华人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66份。其中缅北华人137份,缅南华人29份;老年段22人,壮年段20人,青年段45人,少年段79人。学历从小学至博士,职业有学生、律师、教师、商人、政府公务员、公司职员及自由职业者等,其中以学生、华文教师为主。问卷内容包括个人信息(年龄、性别、祖籍、出生地、现居住地等)、语言生活(家庭、社区等)、语言(文化)态度(对母语、缅语、祖籍国文化的认同等)、语言规划等。(2)访谈、观察法。对近30人进行访谈,并现场观察。(3)个案调查法。对一些华人进行家庭个案调查,直观展现华语传承代际差异。(4)资料法。部分访谈内容、材料来自戴庆厦等(2019)的《缅甸的民族及其语言》[ 本文中关于曼德勒、东枝等缅北地区的材料均取于该书。笔者为该书作者之一,材料属于集体成果,特向调查团队致谢。]。
三、缅甸华语传承模式变迁及成因
缅甸华语传承模式表现出鲜明的历史时段特征和地域特征。以历史标志性事件为界点,分为4个发展阶段,结合地域特征,形成南北两条传承链。缅北为:顺外传内-完全传承→顺外传内-传承受阻→顺外传内-传承复苏;缅南为:顺外传内-完全传承→顺外弃内-传承中断→顺外拾内-传承复苏→顺外传内-传承复苏,其中“内”为华语,“外”为缅语。下面以时间为纵轴具体讨论。
(一)第一阶段:全缅“顺外传内-完全传承”
1960年以前,缅甸华人华语传承模式为“顺外传内-完全传承”。华人为了生存,融入缅甸社会,接受当地语言文化,但同时坚定地保留中华民族传统语言文化;华人社会完全传承华语。在华人社区华语是强势语言,使用范围比缅语大,即内势大于外势。华语与缅语是共生关系。
这一时期华语传承模式的形成,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起到积极作用。我们调查的22名老人,全部同时会说华语、缅语,大部分水平都很高。22人全部在家里学会华语,其中18人在儿童时期学会,4人是在青少年时期。22人在家中与长辈、同辈全部使用华语交流,与晚辈也多用华语;交际场合中,一般只有对方为非华人时才用缅语。一些访谈对象告诉我们,缅甸这个年龄以上的华人都不同程度地会讲华语(以方言为主),大部分达到熟练程度,有的老人还在华文学校学会了普通话。但出生地在中国的华人,有些是不会缅语的。华人很团结,一般多在迁居地聚居,所以即使不会缅语也没关系,用云南话、广东话(粤方言)、福建话(闽南话、客家话等)、海南话交流就可以了。
1960年以前的缅甸华文教育从无到有、从起步到兴盛,是华语在离开祖籍国后也得以顺利传承的重要保障。仰光东方语言与商业中心董事长曾圆香女士(76岁)说:“大概在晚清时期1902年左右,有一些华侨移居到缅甸,他们认为要想和家乡的亲人保持联系就要会写汉字,想了解世界也要有文化知识,所以他们纷纷办起了华文学校。20世纪四五十年代,缅甸共有300多所华文学校。我是福建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我的母校有140多年的历史,华侨中学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那时候缅甸的华文学校很红火,整个东南亚的华侨子弟都来缅甸学中文。那时的华文学校都是三语学校,教中文、缅文和英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2年。像我们这些60岁以上的人当时都受过华文教育。”
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是这一时期华语传承的深刻根源。绝大多数移居缅甸的第一代华人至死只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心心念念要落叶归根。很多华二代从小深受家庭、父母的影响,也对祖籍国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仰光华文教师郑瑞发(69岁)出生于缅甸,是二代华人。他在接受访谈时说:“我们那一代人的传统观念还是很强的,我们受到来自老家的老一辈的言传身教。还记得小时候,我爷爷总是说‘我要回老家,我要回老家,可一年又一年,一拖再拖,始终没有再回去过。他们没有回去,并不是乐不思蜀,而是条件所迫。他在这里勤勤恳恳劳作,得到的收入全部寄回老家,自己不留分文。”临别时,郑老师说:“能够相遇并交流,这是难得的缘分,再相见不知何年何月了。我们这一代人,看到中国人就当是自己人。”
(二)第二阶段:缅北“顺外传内-传承受阻”,缅南“顺外弃内-传承中断”
1960~1990年代,华文政策的指挥大棒几令缅南华语传承中断,缅北也是苦苦支撑,华语传承遭到重创。20世纪60年代缅甸军人执政后,强制实施民族化政策,规定华校只能利用课余时间加授华文,每天不得超过1小时英文授课时间,必须授足缅文课程。1965年4月,《私立学校国有化条例》颁布,政府将全国所有私立中小学收归国有。1965~1966年,政府将全缅几百所华校收归国有。1967年,《私立学校登记条例修改草案》颁布,规定除单科补习学校外,不准开办任何形式的私立学校。华文教育从正规教育转为非正规教育,以“华文补习班或家庭补习班”形式存在。1967年“6·26”排华事件后,政府规定“缅甸教育由国家承办,不允许私人办学,任何补习班不得超过19人”,连家庭补习班也被禁止。从此,缅甸国内一律不允许教授华文。奈温政府期间(1962~1988年)出生的华人,华语水平整体大幅下降。缅北、缅南出现两种华语传承模式。
1.缅北——“顺外传内-传承受阻”
缅北各地华语传承模式以“顺外传内-传承受阻”为主。华人能够接受缅甸主体民族语言文化,融合加速。同时,受国家严厉的华文教育政策影响而传承受阻,华语艰难地保持。缅语逐渐成为强势语言,华语与缅语形成竞争局面。
1965年,缅甸华文学校全部被收为国有,华裔小孩只能穿纱笼、学缅文、说缅语。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缅北地区一些华语教师冒着危险,偷偷为华人子女开设家庭补习班,一些家庭坚持让孩子以各种形式学习华语。这个情况持续了二三十年。1981年后,缅北华校在讲授佛经的名义下,变相地恢复起来,但也只是遮遮掩掩、苟延残喘地维持华文教育的火种而已。这是如今四五十岁的缅甸华人不会说华语或华语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以缅北曼德勒市55位华人调查数据为例。30~59岁的华人36名,有5人不会华语,11人略懂,20人熟练;缅语则100%熟练。而16位60岁以上的华人,15位华语熟练,缅语全部熟练。相比之下,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华人,华语水平出现明显下降。
东枝也是如此。为不使民族文化失传、子孙后代忘记母语,东枝有老师坚持开办补习班,学生东躲西藏地艰难补习。很多年轻人受不了这种压力,最终放弃学习。这一时期的华文教育几近瘫痪,直接导致华人后裔缅化速度加快,造成今日东枝地区很多40岁以下的闽、粤籍华裔不会说华语,出现华语传承受阻。华语一般只在家庭内部或熟人间才敢使用,緬语使用场合越来越多,逐渐成为强势语言。
2.缅南——“顺外弃内-传承中断”
缅南华语传承模式为“顺外弃内-传承中断”。华人被迫放弃本民族语言文化,被迫融入缅甸主体民族,逐渐被同化。华文教育在学校、家庭几近灭绝,华语出现传承中断。缅语成为华人日常生活用语,是强势语言。
1967年发生“6·26”排华事件,为了人身安全,华人不敢承认身份,很多华人在家里都改说缅语,更不敢教下一代说华语。缅南尤其是仰光的华文教育出现断层,消失近30年。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华人几乎都不会说汉语,对中华文化一无所知,很多人连自己的祖籍地和汉语姓名都不知道。据曾圆香女士说:“排华事件时,市场附近有个教师联合会,30多位教师被砍死了。我们都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只能说是缅甸人,不敢讲中文,每天穿纱笼。我们初中毕业后就没有机会上高中了,只能靠家庭补习的方式学习汉语。”郑瑞发老师感慨道:“仰光的中文教育已经出现断层了,我这把年龄是正规华校最后一届小学毕业生,再小一点的就完全没有受过华文教育了。”
这一时期的华文教育在缅甸几乎灭绝,既有外因又有内因:外因是缅政府实行民族主义政策,华人华侨经济遭受重创,华文教育失去了经济和政策支持,无以为继;内因是许多华人生活困窘,无暇顾及,人们觉得学习华文没有用处,加之第二、三代华人逐渐被缅化,逐渐接受了“华文无用论”的说法。
形成南北传承模式差异的原因有两点。
一是南北地理位置差异带来的政治迫害程度不同,华文教育发展状况不同。
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实则消灭了华语学习途径。“6·26”事件给缅南华人带来巨大的心理阴影,人们对华语和华文教育采取了极其谨慎小心的态度,能让下一代继续学习华语的家庭极少。缅南华教在学校和家庭都受到严格监控,导致缅南华语传承中断。曾圆香女士说:“缅南地区家庭补习方式受众面极小,很多华人为了自身安全,干脆放弃华语。这导致下一代华人对自己的语言文化没有感情,华语传承中断则是必然。”
缅北华文教育事业也受到重创。但缅北多为山区少数民族联邦地区,离政治中心较远,其政治影响辐射减弱,且缅北华人也被视为少数民族,受迫害程度相对小些,华人可在政策夹缝中求生存。如1960年中缅划定边界时,被划为缅甸的果敢居民(多是杨姓滇胞)成为缅甸少数民族之一,腊戍、果敢中学成为缅甸境内唯一获得政府认可的华文学校,用“果文”(实为华文)进行母语教育。缅北其他地区有人冒险开办10人以下的家庭补习班。有的华人则从缅南逃离到缅北教授华文,如缅甸东方语言与商业中心的黄校长,就和先生一起逃到缅北租牛棚、稻草棚,在背面搭建简易教室教授华语。虽然条件极其艰苦恶劣,但老一辈华文教育者正是凭借一腔爱国热忱,用青春、热血和信念保护民族语言文化传承的火种。
二是缅南华人籍贯复杂,方言差距大,传承难度相对较大;缅北滇籍华人居多,方言差距小,传承难度相对较小。
早期来缅甸定居的闽、粤籍华人多居于仰光等南部地区,后逐渐迁居曼德勒。这些华人说粤方言、闽南话、海南话等,彼此之间不能通话,华语使用范围非常有限,只能用于家庭、同乡之间。政治环境使华语不易传播和代际传承,而有的方言与普通话差异大,也不利于华语教学传承。
而早期多从云南入缅的华人,还有从云南边界进入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在缅远征军等,都居于缅北地区。果敢地区的果敢族从前就是汉族华人。滇籍华人和果敢民族都要求自己的青少年保持华语。云南方言成为缅北地区重要交际用语之一,且与普通话差异小,有利于华语教学传承。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缅北以学习佛经的名义,比较早而广泛地开展了佛堂佛经式华文教育。
(三)第三阶段:缅北“顺外传内-传承复苏”,缅南“顺外拾内-传承复苏”
1990~2000年的十年间,缅南和缅北华文教育事业得到不同程度发展,华语传承出现复苏。
1984年,缅甸默许语言补习班合法。1988年后,可在寺庙里采用“佛学教科书”教授中文。缅甸华文教育事业遇到新契机。缅北凭地缘优势、经济优势及族群意识,积极兴办华文教育,华语传承模式为“顺外传内-传承复苏”。缅北地区主要是滇籍汉人,省籍单一,人口较集中,办学正规,教师队伍较稳定,学生毕业时颁发正式毕业证书。20世纪90年代缅甸对外开放后,缅北华人通过开展中缅边贸等方式先富起来,为华文教育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缅北华人在继续融入缅甸主体民族社会的同时,凭借华文教育的薪火相传而得以传承中华语言文化,使一度受阻的华语传承出现复苏。
缅南历史遗留问题较为复杂,很多华人对排华事件带来的心理创伤还心有余悸,对重拾华文教育顾虑重重,家长不让孩子接触中文,都想把孩子送到西方国家去,因此都很重视学习英文。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受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华人意识到中文的重要性,缅南地区出现一些营利性质的华文补习学校,重拾中断了近30年的华文教育,其华语传承模式为“顺外拾内-传承复苏”。但缅南华文教育发展迟缓,新生华人缅化程度非常高,语言认同、民族认同与先辈大相径庭,华语传承受到的重击不可逆转,只是形式上的复苏。
整体来看,这一时期出生的华人,华语水平最低,民族认同度低,缅语水平很高,对緬甸国家认同度高。华语学习主要依赖华文学校,缅南华人家庭已经很少使用华语,华语使用空间非常小。如调查的45名青年段华裔中,38人在学校学会华语,达到熟练程度的仅22人,且日常用语以缅语为主。被问到“为什么学习华语”时,他们大多选择“父母要求或自己感兴趣”,只有2人选择“因为长辈是华人”。华人被缅甸主体民族语言文化同化是大势所趋,缅语是缅甸的国家通用语言,是地区和族群内的强势语言。
(四)第四阶段:全缅“顺外传内-传承复苏”
2000年1月,缅甸政府特别表示要汲取周边国家教育发展经验,这为华文教育创造了发展空间。受经济利益及其激发的民族自豪感驱动,缅甸华人学习华语的热情空前高涨,全缅华文教育事业快速发展。这一时期出生的华裔青少年华语学习明显低龄化、家庭化。受调查的少年段(79人)中,81%在儿童时期学习华语,青年段(45人)则只有35.6%;少年段40.5%在家中学习华语,青年段则只有11.2%。少年段母语认同、民族认同感较青年段有显著提高。此阶段南北华语传承模式都为“顺外传内-传承复苏”。
缅甸对中文的需求不断增大,以华语为第二语言的新兴华文学校越来越多。缅北这一时期的华文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佛经学校、果敢语文等名义开设的华校、语言与电脑学校在各地创办,形式多样,如幼儿教育班、会话班、补习班、家教等。至2012年,缅甸已有161所华文学校。其中,缅北138所,规模较大、学生千人以上的有40~50所,学生共计68 107人;缅南23所,学生总数约3800人。[ 本部分数据来源于邹丽冰(2012)。]这对缅甸华语传承有一定积极作用,但缅语仍是强势语言,华人语言文化的趋势仍
是被同化。
四、华语传承模式系统发展趋势
如上文所述,缅甸华语传承模式、华人与主体民族的语势和语言-文化适应关系在4个发展阶段也有所变化,这三者构成缅甸华语传承模式变迁系统,该系统内部各要素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如表1所示。
表1中,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变迁主要受缅甸国内政治环境、语言政策的制约和影响;第三阶段的“传承复苏”,是受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缅甸政府调整国内外语言政策,为华文教育提供发展空间;第四阶段的“传承复苏”,根本原因是受经济利益驱动,全缅对华语人才需求激增,缅甸政府放松华文教育政策,并积极配合开展国际中文教育。这3个系统要素总体发展趋势如下。
(一)“顺外传内-传承复苏”模式是缅甸华语传承的历史选择
华语传播一直是一种非排他性传播(郭熙,李春风2016),即使是在经济上占一定优势时,缅甸华人仍然以尊重当地文化、努力融入当地社会为目标,积极“顺外”。华人对华语都有较强的认同感,认为华语是他们的根,很多老年华人受访时都语重心长地说“根不能断,载体不能丢失”。即使在排华时期,有些家庭仍想方设法让小孩学习华语,很多华文教师冒着生命危险教授华语,坚持“传内”。但受语势(缅语是强势语言)和语言-文化适应关系(同化)现状制约,华语出现的传承复苏,很难从质和量上恢复至盛景时期,华族语言文化销蚀非常严重,只能说华人学习华语的意愿有所恢复,学习人数有所增加,华语水平有所提高。受经济利益驱动,年轻华人让下一代学习华语的越来越多了。“顺外传内-传承复苏”是最符合当前缅甸华人华语传承发展的模式,是历史的选择。
(二)“外势大于内势”是缅甸华语语势的客观趋势
缅甸国家通用语言缅语是强势语言,华语为弱势语言。虽然华语学习者数量不断增加,华人华语水平有所提高,但华语在缅甸的使用范围未见扩大,尤其对年轻华人来说,华语多是华人祖语传承的工具或者谋生工具,很少用于日常生活交流,缅语仍是华人族群的强势语言。
缅北一些有老人居住的华人家庭或社区才使用华语,年轻人在社交场合大多愿意使用缅语。缅北克钦邦八莫一个29岁的年轻人说:“爷爷奶奶那一辈只会汉语,不会说缅语。父母都是在缅甸出生的,会讲汉语和缅语(汉语好于缅语)。到我们这一辈,会讲缅语和汉语(缅语好于汉语)。再下一辈,像我哥哥的孩子基本只会说缅语了。我在家跟父母一般讲汉语,跟兄弟姐妹们讲缅语较多。年轻人被缅化得越来越严重。”一位曼德勒滇籍华人研究生说,她的家庭用语是云南方言,她曾试过在家说缅语,遭到父母制止,因为爷爷奶奶那一代人会很生气。但是她跟4个哥哥都说缅语。缅北很多华人会说云南方言,但年轻人使用的很少。掸邦东枝一位华校校长说:“大部分年轻人积极去缅校、学缅文,即便是在华文传承最好的果敢地区,果敢人也普遍认识到缅语的重要作用。”缅南日常生活中使用华语的场合更少。可见,缅语在缅南、缅北都是强势语言,其缅甸国家通用语言地位非常稳固,“外势大于内势”是缅甸华语语势的客观趋势。
(三)同化是华-缅族语言文化关系的发展走向
族群青年人对本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的态度,往往决定该族语言文化的发展走向。缅甸华裔青年在以下三方面表现出了同化的趋势。
对缅化现状非常包容。华裔青年都认为缅语歌很好听,缅甸传统服装很美。访谈中问及华人缅化问题,很多年轻华人表示:“家庭教育比较传统的,怕孩子被缅化,反应很强烈,但现在年轻人越来越能接受这些了,可能(缅化)速度要加快了吧。”东枝一位21岁的华文女教师说:“我在东枝出生,是第三代。我妈妈是缅族。我户口本上民族写缅族和汉族两种,不过我更倾向于写缅族。”对此,年长者很无奈,但已无法改变。
对缅语的认同高于华语。如反对“家人不会说或不肯说缅语”的分别占66.5%、62.5%,而反对“家人不会说或不肯说汉语”的分别是27.5%、37.5%。一位25岁的华人研究生说:“我不会感到不高兴。但爷爷奶奶那一代应该不会接受,父母一代应该可以接受得了。”一位果敢学生郑重地说:“自己是缅甸国民,应该学习自己国家的语言,学会了缅语就便于果敢人融入缅甸社会。”这说明缅甸华裔青少年在保持华族特征的同时,已逐渐融入所在国文化生活,找到社会归属感。
能够接受族际婚姻。老一代华人很难接受族际通婚,但多数年轻人表示可以接受。他们说:“爷爷奶奶那一代是肯定不会接受了。爸妈都还是比较传统的,我们家亲戚都比较排斥与外族人结婚。我们这一代倒觉得没关系。”
五、几点启示
海外华语传承是动态变化的,与社会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因此,缅甸华语传承模式研究具有普遍意义,能为我们认识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各国、不同时代的华语传承特点提供参考和指导。纵观缅甸百年华语传承模式变迁系统中各要素的变化,有些是客观规律在起作用,如移民群体与住在国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化关系的发展规律;有些是要素间相互制衡的结果,如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国家政治政策、经济政策的关系,住在国与祖籍国的邦交关系对跨境群体生存地位的影响,等等。这些都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一)国家语言政策对跨境移民群体语言文化有制衡作用,甚至对其走向起决定作用
本研究表明,缅甸的国家语言政策对缅甸华人语言文化传承有着根本性的影响。该国语言政策对移民群体语言传承具有制衡作用:如果有民族主义语言政策干涉,则相融同化过程加速;如果没有这类政策,则是一个自然融合同化的过程。从缅甸华语传承模式成因看:缅南,客观外因即缅甸国家语言政策影响非常大,且在历史跨度中,外因影响主观内因,影响了少数民族的语言认同;缅北,客观外因与主观内因共同作用,形成阶段共峙、同化,仍影响语言认同。跨境移民群体语言文化与国家主体民族语言文化相融、同化是大势所趋。即便政策再放松,受某个契机或者因素驱动,母语传承或许会出现复苏,但复苏程度各有不同,语言文化传承已出现销蚀。
(二)经济价值是永恒的变量,是激发新生代华人传承华语的最主要动力
在华语传播动机中,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华语的传承和维护(郭熙2013)。20世纪60年代以前,华人经济优势较明显,华文教育事业兴盛,华人语言文化传承顺畅。当华人被政策打压,经济、安全状况无法保障时,华文教育事业难以为继,华语传承则中断、受阻。而当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乘着缅甸国内语言政策环境放松的东风,缅甸华文教育事业再度兴起,激发了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华语不但是民族传承语,更被赋予了经济价值,刺激华语传承复苏。
新生代华人对华语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由困惑到明晰,他们清楚自己的华人身份,更认同自己是缅甸公民,华语传承的第一要素則是经济因素。诚如年轻受访者所说:“华裔学汉语当然有民族感情的因素在里边,但近些年来考虑到实用的因素会更多点。”一位华文教师说:“开始的时候华人并不支持(学华语),我们去当家教的时候要说服家长让孩子学中文。现在祖国富强了,学习汉语的热潮遍布全球。”缅甸华校提出的学习宗旨由“中国人必学中文”转变为“人人学华语”,[ 《缅甸华文教学融入社会主流》,华声报,2003年12月11日,https://news.sina.com.cn/o/2003-12-11/09591315368s.shtml。]本质上也是弱化华语的民族传承属性,凸显华语的社会经济价值。华语的这一重要经济属性,能够解决华语传承复苏与华人融入缅甸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还能弥合华人社会与缅甸主体民族、与缅甸政府的关系,更好地为缅甸社会发展服务,形成民族团结局面。
(三)跨境移民群体语言文化被同化是不可避免的,要及时抢救挖掘海外华语资源
缅甸华语传承的变迁涉及华人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几代华文教育者的奋斗史、辛酸史,很多华人为此做出巨大牺牲和奉献。但跨境移民群体被不同程度同化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同化程度加深,华人族群特征被逐渐销蚀,年轻人缅化速度会越来越快。
海外华语资源是全球华人共享的社会资源,其资源属性体现在经济、文化、社会及个人等多方面、多层次(郭熙,刘慧,李计伟2020)。缅甸一代又一代的华语传承者,在华语传承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在传承实践中的经验、认识、过程,同样是宝贵的财富。对华语传承调查研究,挖掘整理不同时代华人社会文化特征,与时间赛跑,尽早尽快记录华人尤其是老一代华人时代背后发生的故事,是我们海外华语研究者应尽的责任。
(四)华人处理好语言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可为中缅搭起互信互助的桥梁
语言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看似属于不同层级领域,实则相互牵动延展(李春风2021)。越来越多的缅甸华人既承认自己的华人身份,又明确表示祖籍国与住在国不同,认为中国是祖籍国,缅甸是祖国,对缅甸的国家认同度更高。一位28岁的年轻人说:“华人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这种认同感逐渐淡薄。祖辈会100%认可,父辈可能只有80%认可,而到了我们这年轻一代,可能只有50%了,华人被缅化的程度越来越深,民族认同感越来越淡,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缅甸人,缅甸是自己的祖国。”
在缅甸出生的新生代华裔,自觉、积极地融入主体社会,接受缅化。他们兼用缅语、华语,给自己带来了经济利益;承认自己的华人身份,有民族认同,也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发展;正视中国与缅甸在华人心中的地位和关系,认同祖籍国中国,认同祖国缅甸,疏通中缅文化差异,为中缅两国搭起一座互信互助的桥梁。曼德勒福庆语言电脑培训学校李祖清校长说:“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华文教育这种民间外交来促进住在国缅甸跟祖籍国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对我们这些华人来说,中国跟缅甸的关系就像娘家和婆家的关系,娘家跟婆家的关系好了,我们才会好。”
当今缅甸华语不但对华裔后代有吸引力,很多缅族子弟也投身到中文学习中。这让缅族人有了更多接触、了解华人历史文化的机会,将加深缅族与华人间的信任和融合。2021年2月,缅甸军方宣布接管政府,冲突不断升级,局势愈加复杂,在缅华人受到一定冲击。未来,缅甸华文教育的发展值得进一步关注。
参考文献
戴庆厦,等 2019 《缅甸的民族及其语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郭 熙 2004 《论“华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第2期。
郭 熙 2006 《論华语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郭 熙 2013 《华语传播和传承:现状和困境》,《世界华文教育》第1期。
郭 熙 2015 《论汉语教学的三大分野》,《中国语文》第5期。
郭 熙 2017 《论祖语与祖语传承》,《语言战略研究》第3期。
郭 熙,李春风 2016 《东南亚华人的语言使用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双语教育研究》第2期。
郭 熙,刘 慧,李计伟 2020 《论海外华语资源的抢救性整理和保护》,《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李春风 2019 《国内语言传承研究综述》,《海外华文教育》第1期。
李春风 2021 《缅甸华人母语认同代际差异及成因》,《八桂侨刊》第1期。
李宇明 2017 《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陆俭明 2019 《树立并确认“大华语”概念》,《世界华文教学》第1期。
周明朗 2017 《全球华语大同?》,《语言战略研究》第1期。
周庆生 2018 《语言适应-传承模式:以东干族为例》,《语言战略研究》第4期。
祝晓宏,周同燕 2017 《全球华语国内研究综述》,《语言战略研究》第1期。
邹丽冰 2012 《缅甸汉语传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责任编辑:韩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