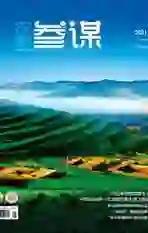乡村吆喝声
2021-08-03王太广
王太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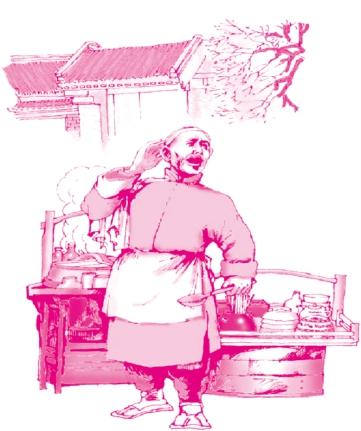
每当我夜晚散步时,总能听到一位妇女用小喇叭放出的录音“烙馍豆腐串、白糖粽子——”一下子就唤起了我对儿时农村走村串巷叫卖的吆喝声的回忆。
俗话说:“卖啥吆喝啥。”小时候的村庄里,经常看到挑担的货郎,他们进村后先是摇动拨浪鼓,接着是或长或短的叫卖聲:“大针洋线桃木梳——”这是针对村妇的;“糖豆帽卡玻璃球——”这是吸引孩子的。货郎的挑子是一座移动的百货商店,东西又多又有趣,装在玻璃瓶里的糖球五颜六色,仿佛聚集了整个世界的甜,而我却难得有钱买上两粒。
还有接连不断的吆喝声““打——豆腐”“补锅钉盆喽——”“磨剪子来,戗菜刀——”“卖馓子——”……
每年开春,村庄里就响起“赊小鸡哎赊小鸡”的吆喝声。那人挑着大而扁的箩筐,里面是“叽叽”叫的小鸡娃。卖鸡人进庄后找个空地放下挑子,撒一把浸泡过的小米,小鸡娃立刻活跃起来,叫得更欢,拥挤着抢食吃。买鸡娃的妇女们,立马围拢上来,边看边议论颜色的好坏、鸡娃的肥瘦,商量着买不买、买多少,然后讨论还价。一番成交后,卖鸡的便把小鸡娃如数过给买方,在小本子上记账后又去招揽下一个买家。所谓赊小鸡,就是用先欠后还的方式买刚孵好的鸡娃,卖家是游贩,挑着担子走村串户。你赊多少鸡娃,他记在小本子上,到了秋天他再来,没钱者可用鸡蛋顶账。当时,我问大人:“要是赊他鸡娃的人搬家了,或那个小本子丢了咋办呢?那人岂不成了冤大头?”大人回答得干脆:“不用担心,这是老几辈的规矩,春天赊,等到秋后鸡长大了,分辨出公母时再付钱!”
吆喝声像细细的线,在记忆里悠荡,钩挂的是一些人的音容,寻常而又难忘的旧事。我记得那个叫王连敬的补锅匠,一个操着北方口音的汉子,头上有不少白发,个子不高但很健壮,门牙少了两颗,说话总不关风。他面前堆放着有洞眼和裂纹的锅、盆。每到钻眼时,会涌出细细的粉末,发出“吱吱”的响声,有的洞需双面补上铁皮,有的用锡涂平就好了。每当补好后,他便说一句“补好了”,然后敲一敲锅盆,交给对方。补好后锅或盆发出的声音是“噼噼啦啦”的,那是一种由铁片、铆钉、伤痕组成的不再浑圆的混响。
当时,水屯大队九队的郭进禄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一进村就开始打车铃,车把上插着一根带有红缨子的铁丝,车架旁系着小板凳和一个工具包,这是乡间宰猪匠的标志。他宰一头猪不到两分钟,而且刀口小、流血少。有人问他手艺为啥这么高?他毫不掩饰地说,宰猪这小手艺也得靠功夫。既要眼力好,又要刀功好。老郭宰猪的手艺在驻马店以东的农村名气很大。
还有一位姓韩的杀狗人,面孔油亮,身材粗壮。如果他只带了一根棍子,就会吆喝:“打狗——”;如果他挎一个篮子来就会吆喝:“狗肉——”。他是个粗心大意又不识字的人,有人赊狗肉的时候,只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记下赊欠斤两,却不写姓名,到了他收账时难以查找。还好,那时的农村人实在,大都给他狗肉钱。
吆喝声是让人愉快的,在商业不太发达的年代,它带来的是浅浅的喧哗,但不含疯狂的成分,像似熨帖的平民化声乐。“青菜啦青菜,绿油油的青菜”“谁买杏,谁买杏先尝后买,不甜不要钱。”这种叫卖声时常萦绕我的耳边。还有一位卖布的:“经拉经拽经蹬经踹,冬暖夏凉不结实不要钱!”字字用力确实契合了农家纺织土布的特征和品格。
走村串户的吆喝声是一门艺术,是一种纯粹的民间创作,虽然如今逐渐淡出,但吆喝声给予我的那份亲情,却浓在心头,化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