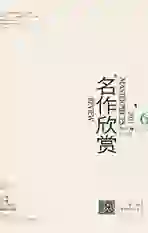《石羊里的西夏》的叙事艺术
2021-08-03王晓哲
摘 要:当代军旅作家党益民创作的历史小说《石羊里的西夏》,对叙述历史的第一人称“我”进行了独特的处理。运用“本我”“自我”“超我”的心理学名词对小说进行分析,会看到“自我”意识下的叙事主线贯穿全书。小说通过梦境的穿越、梦境与幻觉环环相扣、追忆与预言相结合、用史书还原场景等手法,在“自我”意识中穿插大量“超我”意识,使历史场景画面呈现出扑朔迷离又一以贯之的整体感。“本我”“自我”“超我”协调统一于作者的历史感觉和历史感情,在“自我”与“超我”之间自由穿越,在迷离虚幻而又真切自如的场景中转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往事的追忆思索过程,形成了独特鲜明的叙事艺术。
关键词:“自我” “超我” 叙事
弗洛伊德在1923年的《自我与本我》中提出“本我”“自我”“超我”的心理学名词,以解释意识和潜意识的形成和相互关系。“本我”由本能欲望组成,是人格中的原始部分;“自我”负责处理现实世界的事情,是“本我”与“超我”的仲裁者,既能监督“本我”,又能满足“超我”;“超我”是良知或内在的道德判断,是从“自我”中分化出来的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的道德控制的部分。严格意义上讲,“本我”“自我”“超我”三者属于人格结构范畴,这三个基本概念的提出,把笼统的人格分析概念一分为三,更加具体,更加生动,也为形成人格的心理活动提供了新的思考。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人格是人的心理活动长期作用的结果,人格的形成和人的心理活动具有重要的联系?那么,在人平时的心理活动中,是否也存在着“本我”“自我”“超我”的思想意识活动?
借用“本我”“自我”“超我”这几个名词,有助于我们分析一些文学作品表现的思想意识活动,尤其是对“我”这个第一人称的分析。有些小说借助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转换,切换叙事的场景和方式,使叙事过程呈现出迷离多变的虚幻场景,但每个场景又给人真切温暖的感受,虽不真实但自然,属于独特的“那一个”,从而创造了一种文学上的典型。当代军旅作家党益民创作的历史小说《石羊里的西夏》,是一种新奇而大胆的尝试。 在大多数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作者是站在当代的立场上,回顾历史情节,演绎历史人物,多用倒叙、插叙的叙事方式,在人称上多用第三人称。这种写法立场分明、线索清晰,但也容易导致读者独立于历史情节之外,成为历史的旁观者。但是在《石羊里的西夏》中,第一人称的“我”作为主人公贯穿全书,“我”既是现实中的“我”(自我),又是虚幻场景(包括梦境、幻觉、想象)中的“我”(超我)。在叙事过程中,时而是“自我”的现实客观叙述,时而是“超我”在梦境等虚幻场景中的叙述,随着场景的变换,读者就会“身不由己”地进入历史,感受场景变化,对话历史人物,在虚实相生的场景和情境中产生心灵的震颤。这种在“自我”与“超我”之间的自由穿越的独特的写法,在叙事方式上是一种突破,尤其对历史小说而言,的确是一种新奇而大胆的尝试。
一、“自我”意识下的叙事主线贯穿全书
小说开头写到,“我”在元大都遗址公园买到了一个石羊,这个石羊是一个工人修地铁时挖出来的。通过对修地铁的时间、地点以及场景的仔细盘问,“我”逐渐发现了石羊的历史价值和重要意义。“地铁十号线沿元大都遗址绕北三环而行……男人工服上印着某某集团公司,看上去憨厚老实,不像是骗子。”石羊出土用第一人称“我”引发出来,如同发生在读者身边,可见可闻,真切自如。在第一人称“我”的牵引下,读者自然而然地触发了对西夏王国的历史追忆,抽茧剥丝地拉出了西夏王朝的层层内幕,展开了西夏王朝曾经的历史场景。
又如,“不停地敲击键盘,使我的手指有些发酸,我停下来活动手指”,这本是第8节开头一句很平淡的叙述。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句的前文,也就是前7节,都是在叙述西夏王朝的盛世状况。当读者还沉浸在喧嚣繁华的历史故事中时,这一句现实性的描写,如同拉回风筝的线,让读者清醒并反思。“我”身边的夏教授是博学严谨的学者,陪“我”逗笑的夏雨是一个时尚靓丽的美女,在这两位人物形象的共同作用下,现实的“我”更显真切自然。再如“惊雷把我一下子拉回到现实中来。这时我才发现天已经黑了,外面下起了雷阵雨”,前一节里还在描写阿默尔记录西夏早期史的过程,这一句宕开一笔,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作者在最后一节写道:“我这才从八百年前清醒过来,认出站在面前的不是阿朵,而是夏雨。”
据统计,全文共有八处用现实情境下的“我”进行客观真切的叙述(包括首尾),这些叙述内容并不多,但这些现实情景下的“我”是全文叙述的主线,贯穿全书。这个“我”属于“自我”,和现实世界紧密相关,如同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起居中的行立坐卧,可观可见,可感可知。“自我”消除了作者与读者的心理距离,产生默契感和熟悉感,使读者很快产生认同感,使小说具有了感染力和亲和力。
二、“自我”意识中穿插大量“超我”意識,使历史场景画面呈现出扑朔迷离又一以贯之的整体感
在开头部分有这么一段文字:“许多时候,我对八百年前的西夏所发生的一切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我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好像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告诉人们八百年前曾经发生的那一切,我想把我所知道的西夏,那个属于我自己的西夏写出来,告诉世人,这是我多年的一个梦想。”这段话是个过渡,既是对情节内容的过渡,更是叙述方式上的过渡。在叙述的方向上,作者要向另一个世界出发了,穿越八百年的历史风尘,回到西夏去,重现党项民族曾经辉煌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的历史。后来历史场景的引出,是另一个“我”作用的结果,姑且用“超我”来指代。
“超我”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是指人格结构中的道德良心和理想部分。人格结构是人的思想意识长期作用的结果,把“超我”借用到人的意识活动中,有助于分析人物思想感情的流动与变化,以及在流动与变化中坚持的道德原则。唐震在《接受与选择》一书中指出,“超我”是“自我”发展的最高阶段,“超我”是孤独的“我”,“超我”是博爱的“我”,“超我”是信仰中的“我”,“超我”是完善的“我”。在“超我”的叙述角度下,穿越、梦境、虚幻等叙事方式得到了尽情发挥。
1.梦境中的穿越
荣格在《人类及其象征》中说:“人只有了解并接受潜意识后,才能把握自己的完整,而此种了解只有从梦与他们的象征里才能获得。”梦境在书中占有很大篇幅,作者把尘封堙没或者不便昭示于人的历史往事用梦境叙述,展现了另外一个独特的世界,带领读者进入前所未闻的领域,揭示了隐秘的历史角落。“恍惚中,我仿佛看见了八百年前的自己,那个叫尕娃的男孩。我也看见了夏雨,那时她不叫夏雨,叫阿朵。”在书中,“我”穿越回西夏后,身份和灵魂落在西夏末代帝王李睍身上,“我”的遭遇、思想、灵魂都以李睍贯穿。李睍出生于西夏走向没落的衰败阶段,他的童年、少年、成年时代折射出了党项民族深层次的内部争斗和变化。“我”被席卷在历史的旋涡中,情绪里经常蔓延出压抑、愤懑和悲伤之情。
“那天夜里,我迷迷瞪瞪地走进爷爷的书房。我想看看他的胸口是不是有个黑洞……原来又是一个梦。”这个梦展示了皇帝遵顼之死的详细过程,引出了凶手胭脂刺杀的细节,以及胭脂幕后的主使安全。应该说,胭脂带有很强的个人情感,她受到安全的呵护,逐渐对其产生感情,为主子报仇的想法成为刺杀的主要原因,她个体的行为对时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偶然中包含必然,她也代表了不满皇帝遵顼的很多人。在凶杀的细节描写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仇杀的必然,但过程又犹豫不决、迟缓凝滞,折射出人物复杂的心情,具有了生活的真实。
在全书中,父亲德仁是一个正直善良、刚强不屈的硬汉形象,是最能给人带来生机和希望的英雄人物。然而他的正直和勇敢却和没落王朝里滋生的阴暗腐败习气格格不入。西夏王朝的没落已是必然,身处其中的德仁只能是牺牲品。“夜里,我躺在冰冷的营帐里,恍惚中看见父亲从冰河上骑马而来……我醒来后,发现自己满脸是泪。”“我”在梦境中描写了父亲激烈反抗蒙古人的最终结局,这个结局,是我们不愿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作者用梦境预示人物结局,曲折委婉地表达了对英雄人物德仁的敬仰和尊重。
2.梦境与幻觉环环相扣
在“超我”思想意识的活动下,叙述中还出现了环环相生的写法,即一个故事展开后,又引发出另一个故事。如志怪小说《鹅笼记》、《唐人传奇》中的名篇《杜子春》,故事中再出新故事,场景不断推进变化,演绎出层层递进的奇观和风貌。
“我”在演练受伤后养病,具有灵性的羊胛骨令我担心:“想着想着,我就迷瞪了。懵懵懂懂中,我看见罗太后和废皇帝纯祐走了进来。纯祐不是已经死了吗,罗太后不是已经失踪了吗,他们怎么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梦境展开了,罗太后没有讲述自己的事,而是打开《白高大夏国秘史》,引出了更早的另外一段歷史:卫慕太后指使卫慕春刺杀第一位皇帝李元昊,结果被李元昊发现。他亲自逼迫母亲卫慕太后喝下毒酒,然后把身背石头的907个卫慕族人全部赶下了还没结冰的黄河,灭了整个卫慕部落。最后,他亲手砍死卫慕春母子,展现了一段惊心动魄、惨烈悲壮的故事。
“我从睡梦中惊醒,问她:‘你怎么又回来了?她说:‘我一直就在这里呀,我在这里已经一百多年了。”然后,小说引出了没藏皇太后的灵魂。没藏皇太后的灵魂又讲述了李元昊中了离奸计,杀死两员大将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而野利遇乞的妻子,即后来的没藏皇太后,在兄长的帮助下当上皇太后,立刚满周岁的谅祚为皇帝的一段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用梦境讲述西夏第二代皇帝的故事,和前面第一代皇帝李元昊的故事连接在了一起。在第32节《御花园里的秘密》中,没藏皇太后再次在幻觉里出现,引出第二代皇帝谅祚成人后大有作为,崇尚汉礼,增设官职,加强军事,扫除国相没藏讹庞势力的故事。谅祚在攻打宋军的战场上身亡,又引出梁太后立儿子秉常为第三代皇帝之事。秉常的皇后是小梁太后,英姿飒爽,果断干练,把7岁的儿子乾顺扶上皇位,西夏第四任皇帝出现。小梁太后亲率大军多次上战场,并取得不凡战果,后来被辽道宗派出使节用毒酒所杀。这几次幻觉在不同的时间段断续出现,但如果把这几次梦境和幻觉连接在一起,就不难发现戏中戏贯穿了西夏政权更迭变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因人物的直接现身而变得更加真切,尤其“我”不仅是历史的经历者,还是历史的对话者,多次和幻觉中的人物直接对话。“我对小梁太后说:‘我在秘史上见过你。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秋天……她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们聊着,走着,不知不觉来到了凉亭前。”“我”与梦境中的人物直接对话,环环相扣,逐渐引出一个又一个深藏宫闱的秘闻。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指出,梦“完全是有意义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达成”。
3.追忆与预言相结合
在“超我”思想意识的不断活动下,“我”在早年历史的追述中又添加了预言的成分,使得故事环环相扣,首尾连接,浑然一体,形成了似断还连的艺术效果。从这个角度讲,《石羊里的西夏》和《红楼梦》中“草蛇灰线”的叙事方式很接近。
蒙古人在占领城池之后经常屠城,大量无辜平民成了刀下冤魂。这些冤魂到处游荡,往往出现在“我”的梦境里。狼山之战后,“我”在逃跑中饥渴难耐,夜宿在一户人家里。在梦境中,一个女人给“我”喂奶,而且预言“我”是皇上。“我怎么又变成皇上了?”“你现在不是,将来是呀。”这个预言后来成真。梦境中的虚幻和史实互相印证,看似虚虚实实,实则前后呼应、首尾一体,显示了作者对结构的熟练把握。
作为西夏王朝的记录者,阿默尔知道王朝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但他只能眼睁睁地静观其变,默默用自己的笔墨记录正在发生的事件,祈求能够给后人留下忠实的记录。他把秘史保存在羊血浸泡过的石羊内。阿默尔说:“这样就可以埋在地下数百年不被虫蛀水蚀了,一直保留到另一个你出世时,人们才能看见书稿上的字迹。”在这里,阿默尔已经预言,另一个“我”将会在几百年后出生,这和小说中的“自我”贯穿起来,形成了一个看似荒诞又完全的历史穿越。
结尾时,“我”被押送到萨里川。“我醒了……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早已注定了,二十二年前就注定我会死在这个叫萨里川的地方。真是一块神奇的羊胛骨!”看似荒诞的描写把追忆与预言相结合,连接了个体的生命史,也连接了一个王朝的衰败史。
阿默尔想到用石羊保存秘史的办法后,对尕娃说:“这样就可以埋在地下数百年不被虫蛀水蚀了,一直保留到另一个你出世时,人们才能看见书稿上的字迹。”此处已经明显做出了预言,尕娃将会转世,而且在他转世的时候人们能够看到秘史。这种穿越写法,给读者留下了豐富的想象空间。
4.用史书还原场景
“我将羊血点在眉心上,然后坐在一个光线充足的地方。我翻开书,就像拉开一道厚重的幕布,很多年前的景象便呈现在眼前……”然后,小说叙述了梁太后水淹宋军取得永乐大战的胜利,演绎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生动历史画面。
三、“本我”“自我”“超我”统一于作者的历史感觉和历史感情
“本我”“自我”“超我”之间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交互作用的。“自我”在“超我”的监督下,按照现实可能的情况,只允许来自“本我”冲动中的有限内容表现出来。在一个健康的人格中,这三种结构的作用必然是均衡、协调的。《石羊里的西夏》在叙事过程中,在现实与历史、历史与想象、想象与虚幻中进行了多次自由自在的穿越。这些穿越过程是通过“自我”与“超我”之间的思维转换实现的。通过转换,小说把历史的隐秘角落展现出来,演绎出丰富生动的历史故事,使小说情节更加生动传神。“历史永远比猜测的更丰富,就像生活永远比小说更丰富一样。”
作者为什么会用这种独特而新奇的写法呢?“我征服了无边的疆土,只有你们党项人最难对付。”这句话最能反映作者内心强烈的民族情结。在结尾部分,“我”在梦境中和成吉思汗相见。失败者与成功者对话,展现了不可避免的悲剧。作者满怀党项后裔的神圣情感,把对西夏王朝的尊敬和缅怀熔铸到了自己的内心深处。在骨子里,作者深感自己是贵族的后裔,责任、热爱、缅怀、信仰等情感聚合在一起,形成了波澜壮阔、纵横捭阖的历史沉思。正是在这种深沉的大爱中,他以情感为暗线,演绎了梦境、幻境等多种场景,用个人的情感发展串联起了西夏王朝的历史。
陈德礼在《中国艺术辩证法》中说:“艺术作品都是言、象、意的统一,它们各层次间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彼此依存、相互关联的。由于它们有虚有实,虚实相生,所以可以克服物质手段的种种局限,在特定的空间、特定的形象、特定的篇幅中产生连锁反应,使作品的信息量大大增加,从而收到以少胜多、以有限表达无限的审美效果。”在“自我”与“超我”之间自由穿越,在迷离虚幻而又真切自如的场景中转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往事的追忆和思索过程。法国的尤金·尤奈斯库甚至认为:“真理只存在于梦境和幻想之中。”(伍蠡甫:《现代西方文论选》)对历史小说的写作而言,把模糊零碎的故事场景整合成清晰完整的历史过程比较容易,但是把清晰完整的历史过程打乱成碎片化的场景则复杂得多,因为那需要深厚的写作功力和娴熟的技巧,需要作者对历史独特而专注的心理情感,更需要作者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手法在《石羊里的西夏》中表现得很纯熟,形成了独特鲜明的叙事艺术,在当代历史小说中极为少见。其作为一种独特而摇曳生姿的文学现象,值得深入探讨和学习。
参考文献:
[1] 党益民.石羊里的西夏[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2] 荣格.人类及其象征[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3]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台北:至文出版社,1984.
[4] 陈德礼.中国艺术辩证法[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5] 伍蠡甫.现代西方文论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作 者: 王晓哲,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宝鸡市分校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和文学评论。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