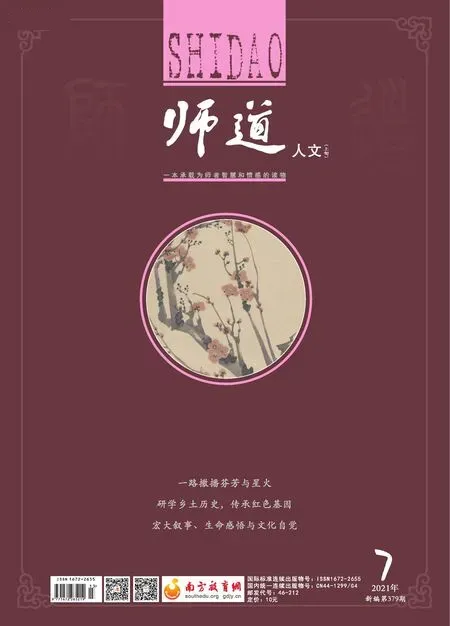『看哪走哪』:通往儿童诗的神秘河
2021-07-28李淳
李 淳
在绘本《神秘河》中,森林到了艰难的“无鱼”时期,如果小女孩卡波娜的爸爸又捕不到鱼,穷人们不仅没得吃,而且整个森林会因为 “一个人没钱,其他人也会没钱”而运转不下去。卡波娜为了解决鱼市的问题而努力思索,并请求森林里最有智慧的埃尔伯莎妈妈的帮忙,当卡波娜问“哪里可以钓到大鱼”时,埃尔伯莎跟她说,神秘河里就有非常多的大鱼, “只要你跟着你的鼻子走就行了。你看到那条河时,一定会认出它来的。”卡波娜觉得跟着鼻子走的说法 “真傻”,因为 “鼻子永远指着前方”,但她还是带着她的小狗出发了。她先是扭头去看一只兔子,这样头就转到了右边,她跟着鼻子走了一段;转头去看鸟,又朝鼻子新位置的方向走去……她终于找到神秘河,钓回了很多鱼,又用同样方式回到家,一路上还用鱼救助了一些饿肚子的动物。有了这批宝贵的鱼,鱼市重新运转起来,带动了各行各业,森林的艰难时期过去了。卡波娜又去寻找神秘河,却怎么也找不到,埃尔伯莎告诉她艰难时期已经过去,是再也找不到那条河的了,但是它会留在卡波娜的脑海,什么时候想去都可以。卡波娜闭上眼睛, “看到了神秘河,它还是那么美丽。”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涵义丰富,闪耀着灵动之光,流淌着迷离的诗意。既是对清澈且善良的童心的致敬,也是对美好生存的探索和思考。在小女孩卡波娜寻找神秘河时, “跟着鼻子走”并非指嗅觉,而是眼睛朝哪看,鼻子就会随头转去,而脚步便随去。如果说成人是“走哪看哪”,那么小孩子则是 “看哪走哪”。成人的 “走哪看哪”是路线由大脑规划,眼睛随脚步的移动而进行随意的观看——这是生活中真实的情形。 “走哪看哪”也可以作为人生态度的形象描述,表达摸着石头过河,不断予以调整的生存策略。有时,这种“边走边看”也是对自己难以把握命运的宽慰,似已无从获得开拓人生疆土的授权,走一步算一步罢了。儿童的“看哪走哪”则喷涌着活泼泼的生意,是我们常看到的儿童被东西吸引后的忘我的脚步,是视线牵引路线的随性和尽欢。可以说,“看哪走哪”正是拥抱未知、探索世界的独特的儿童路径。 “看哪走哪”是一种未经伤害的勇气,是一种可能会有不安,但是好奇胜过不安的对世界的走近和走进。被世界所吸引的孩童,以眼睛标记他在自然宝藏图的发现,未知的涌动的希望,使看似漫不经心的观看,染上七彩变幻的斑斓。
在我们看到的很多优秀的儿童诗之中,由视野的展开而推促思维的行进的例子不胜枚举,无论是儿童诗人,还是成人诗人作儿童诗,其作品都充满了观看世界的热情。这些视觉印象,使儿童独特的生命直观化。可以说, “看”开拓了儿童诗的非同一般的见地。这种“看”别于世俗常见的视角,不仅“新鲜”着我们的感知,也 “补全”着我们生命的完整——唤醒我们身上童年的品质。
我们对儿童特性的言说,总离不开对那双清澈的眼睛的“追溯”,这种清澈至少包含两种蕴意,一是真诚,二是好奇。我们认为这种真诚和好奇未受控于知识和成见,有着初生者自持的天然力量,是与世界相入相融的基本保障。人们将扑闪的眼睛作为童年的象征,不仅有着对童年价值理解的深意,同时也是具备高度形象性的。这双眼睛有如碧潭,倒映世界……世界在童眼凝眸的一瞬间定格,并具备文字意义上的转化的契机。我们经常视儿童诗为对世界常规理解的超常转移,其实只是儿童视角的正常挺立罢了。然而,这种“正常”并不是真的稀疏平常,虽然这种“正常”是自然的、非脆弱的,但却非坚而不摧,其有可能成为“非凡”之所在仍是系于观看的不受干扰以及联想的不受限制上,而正如我们都感觉到的那样,干扰和限制恰恰又是无处不在的。这种正常的同时又是“理想”的观看和联想正是儿童开展日常诗意叙述的基础,他依赖他的双眼,以及不拘泥于现实的与“迥异”的事物的感通和连接,初步完成诗意的铺垫。
“就像吞下煎饼般/太阳从铁皮屋顶慢慢下沉……” (中原中也《春天的黄昏》), “朝雾弥漫的牧场/就像大海辽阔无边……” (杉村楚人冠《牧场的清晨》)这种童诗元气饱满的感觉来自眼帘中自然图景的淋漓的盛放,没有拐弯抹角,没有过度抒发,只有认同、崇拜、呈现和移情。诗人勒内·夏尔言, “谁相信谜可重续,谁就成为谜”,儿童无意建立观赏的法则,也不面对“有用” “无用”的选项,唯享用这谜的景色,并使这样纯粹的时光成为人生一段“谜样”的存在。自然正在发生的一切令儿童惊羡,儿童诗的创造又更隆重着这种隆重。
“这条道路我何时走过?/啊,是啊,是啊,那年金合欢花/正盛开着。//这座山丘我从何时走过?/啊,是啊,是啊,白色的钟楼/高耸着……” (北原白秋 《这条路》)金合欢花和白色钟楼等作为一个个记忆的路标,只是一种如实的视觉节点的记录,却作为一种渺小然而清晰的生命印记,在叙述之中撼动诗人沉睡的时光,也惊醒我们自己的,使我们回忆起自己的脚步曾经在自然园地里热情的书写。
“我挥挥手/就有很多手//我跑步/就有很多脚//小狗朝我摇尾巴/就有很多尾巴//然后/我打秋千/就有很多我” (姜馨贺 《很多》)。这诗让人联想到一种孩子的游戏,使劲挥摆竖起来的手指叫人猜到底是伸出多少根手指。小诗人可贵是他尊重自己所看到的,并加以联想归纳。朴素生动,却令人直叹神奇。我们看这样的诗,并不会觉得“离奇”,因为成人也有这样的视觉经验,问题是在成人的世界,这些并不构成任何“迫切”或是值得回访的体验,但是对于崭新的生命,他热爱自己眼前正在展开的喜悦的思想,他的目不转睛有效地使有趣的场景得以“延迟”。儿童看到世界的好玩,而成人却看到世界的乏味,在这个意义上讲,儿童诗不仅浇灌了稚嫩的幸福,也反讽了成熟的智力。
台湾诗人林焕彰的《鸽子飞入我的眼睛里》也是深谙儿童独特的观看,小小孩数天上的鸽子,叫喊道: “妈妈,鸽子飞入我的眼睛里。”还没数清楚,哎呀——鸽子“飞出了我的眼睛”。在孩子被飞鸽完全吸引的一刻,世界除了鸽子和看鸽子的眼睛,似乎再无其他。诗人都是“贪看”之徒,杜甫在《望岳》中有“决眦入归鸟”一句,亦“看”之 “骄纵”,可比照品赏。
林焕彰还有一首《游向大海》,“鱼鳞长出眼睛/鱼鳞长出嘴巴……//每片鱼鳞/都游出一条小鱼。/……”由鱼鳞的弧度联想到鱼的身子,再到生长出这样一首诗,可以感觉到诗人沉迷于他眼皮底下变幻的游戏。他追随着一只只由鱼鳞变化而来的小鱼,一起游向大海,是多么尽兴和奇妙。童诗的梦幻园,美丽、深远和高贵,时间在此微微弯曲,我们被挪到事物的那一边……
“我在楼上看见了风/请你一定相信——/我看见风从草地上走过,/踩出一溜清晰的脚印……” (胡咏乐 《我看见了风》),就连 “风”这不可见之物也要令之可见,由此可知儿童对“可视” “形象”的特别的青睐。小诗人的眼睛用心捕捉风的踪影,终于在风过草低时做出兴奋的指认,那正是风的脚步!但,与其说那是风的脚步,不如说是孩童的脚步,那一脚脚是毫不生疏的单纯的行动,他与世界之间没有裂缝,也没有芥蒂。里尔克说, “……人所看的万物都很新鲜,甚至在观看之际,就联系着一种不断的惊奇和收获丰富的欢悦”——是彰显,不是蕴蓄,是被含纳,不是被隔离,这正是儿童的福祉。
“我的眼睛很大很大/装得下高山/装得下大海/装得下蓝天/装得下整个世界//我的眼睛很小很小/有时遇到心事/就连两行泪/也装不下”(陈科全 《眼睛》),这首诗中,小诗人对“观看”已经有了自觉性,他意识到他的眼睛的“能耐”,意识到他通过观看与世界建立的某种联系,并发出由衷的感叹:眼睛可以将世界全部装下,但却无法承受心灵震颤时冒出的泪水。这首诗的宝贵在于不仅有兴致勃勃的“外”观,还有小心翼翼的“内”观。无“外”, “内”亦觉局促逼仄;无“内”, “外”也显漫漶无边。从这种内外的对比中,你可以看到作者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诗歌写作的技巧,但即便如此,你仍旧感觉到小诗人在观看世界、感觉世界的时候愿意下笨功夫的模样,这种笨功夫往往是儿童所不自知的。但是憨拙的感觉的环绕不去,却“不害”儿童能够从某些角度感知关于人生的深刻性。
并不像普遍认为那样,儿童只能接受幼稚、浅显、喜乐的东西,儿童也是能够品咂人生和艺术诸多滋味。像我读幼儿园小班的孩子,有一天起床突然说, “每天开始都是睡醒、尿尿、穿衣、洗脸、喝水……好无聊啊!不过,就这样生活下去吧!”听完我心里不觉咯噔了一下,这么小的孩子他已经有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了,而且这种理解可一点也不肤浅。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儿童作品一味幼稚空洞重复,以为是投儿童所好,不知是在严重败坏儿童的品味。儿童诗并非就要稚态,好的儿童诗也有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只不过这种理解力基本建立在天真的想象力之上。我们不能低估儿童的鉴赏力,掐断儿童诗与高品位的东西的联系。稍加复杂的人生的况味,也在启发和锻炼儿童的思维和表达,他的独特的心灵结构并不排斥有一定深度的观看、参与和表述,只是要注意符合他的意趣和觉知状态。像金子美铃有一首诗就是很特别的凝视:“上层的雪/很冷吧。/冰冷的月光照着它。//下层的雪/很重吧。/上百的人压着它。//中间的雪/很孤单吧/看不见天也看不见地” (《积雪》)。
这样一首儿童诗,相信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都可以读出不一样的感觉,但是顺着金子美铃安静地对雪的观看,我们也似乎都变得安静了。在这份共同的安静中,每个人心里却会产生不同的不平静的感觉。可能是单纯的对自然观赏:月的冷清,雪的层次——惊讶于诗人对雪这样的“解剖”;可能会感受到不同人生的滋味,更大些的人可能会体会到关于阶层的隐喻。但好的儿童诗歌是纯粹的,仿佛随时可以卸下一切复杂的解读,回复它的轻盈,满心洁白迎接下一个读者,下一个儿童。
“什么是水/无形的镜子//什么是森林/春天的影子//什么是阳光/温暖的灯泡//什么是蜗牛/爬行的螺旋//什么是星星/闪烁的眼睛” (大嘟 《探索答案》)。这些视觉印象,感觉是慢慢在孩子眼里生长起来的,不是孩子一下子就在心里确定的,但是我们读起来,却感觉孩子在写诗的时候,几乎是瞬间抵达了这些空灵的意象,或许说,是成长的力量给他这样饱满的“冲刺”的信心。
童年必定逝去,而它又有如一个深邃的花园,当我们以精神回访的时候,为我们拂尘涤心,斟泉引花。童年的 “功效”,正是在于净化和美化,而这亦可视为儿童诗的基本功效。当诗人将一株客观的小草凝为一幅心灵的美丽图景时,与这棵小草一同获得我们情感阳光照拂的,还有自然万物,正是童心的真炽和好奇迎来万物平等的境地。有时候我们翻读一整本优秀的儿童诗集,会觉得世界的美好纷沓而至,不知是在眼睛的狂欢中,世界被重新祝福;还是世界本身的神秘,赋予眼睛诗性。
罗伯特·斯蒂文森在他的儿童诗集里告诉读者说, “就像你妈妈从屋子里看见你/在花园里绕大树做游戏那样/你也能看见——如果你的眼睛透过这本书的窗子朝里望/你也能看见另一个孩子,在远方/在另一个花园,玩得挺忙”。读儿童诗,也要“眼睛透过这本书的窗子朝里望”,这样才能紧随作者“看哪走哪”,深入一个孩子的诗园。
特别值得一提是,在 《神秘河》之中,小主人公卡波娜还是个小诗人,但是她在神秘河里钓起的确实是鱼而不是诗。诗不能够使森林的居民度过饿肚子的艰难时期,诗当不了鱼吃。但是唯有这个充满灵性的小女孩才找得到鱼,或者说就是诗找到了鱼。但是诗当然不能够找到真的鱼,而且诗之意亦非在鱼。但是,如果把鱼当 “精神粮食”解,诗就是鱼,寻诗也是寻鱼;如果将鱼儿当“灵感”解,诗也是鱼:灵动如鱼,灵动如诗。卡波娜钓鱼的鱼饵是她用粉红色的纸做的玫瑰花,可见能钓起神秘且美妙的东西的,也同样必须是美妙的东西,而花无疑是最美妙的东西了,可是谁做出和想出这样的诱饵呢,那只能是无尘的唯美的童心啊。在《神秘河》之中,作者和绘者造了一个奇妙的童境和诗境,但却不是完全的空中楼阁,而是关怀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一切。艰难的人人都犯愁的,因为无鱼而难以继续运转的社会生活——它正“辐射”到每家每户,辐射到每一个敏感的孩童。父亲的叹气孩子清清楚楚地听到耳里,卡波娜将之“综合”理解为一个“坚硬时期”。诗应是关怀日常的,儿童诗也不例外,小孩不可能完全进入到成人的世界里,完全理解他们的哀愁——那样太残酷,但是他们都感到哀愁的风吹过,或者在一些孩童的感觉里,天地已然变色,但这些是 “对的”,这正是眼皮底下的生活,它如此这般铺展着,每个人认领他所认领的——“捕鱼者”意识到要更加勤奋地捕鱼, “捕诗者”意识到他得为“坚硬时期”写点什么。捕诗者确实不能帮助捕鱼者多捕捉几条实实在在的鱼,诗确实不可充当鱼,但是在纯粹的诗人的心底,对生活的希望与春天的河水一样踊跃,对渔夫的悲悯同夕落的江面一样金赤。作为世界的开阔的一部分,诗正是一些人的鱼。无诗的世界,纵然有鱼也索然无味;有诗的世界,纵然无鱼也可不改其乐。
诗让有鱼的日子更可流连,而无鱼的日子则显得不那么糟糕。但是诗又不仅仅是这样,它也可以让有鱼的日子变得“不安”,但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提醒:还有一些生活的隐秘的关联永远在等待着诗人的确认。这一群镀上光亮的鱼在我们的童年轻轻地游动,追随它们的身影,使我们意识到正是这些强大的微小生命构织了世界的精神。
儿童诗诗人王立春曾说: “那些野野的、愣愣的、生生的、杂杂的东西,就在诗里生出了小牙齿。”我想, “看哪走哪”正是这样一种“野野的、愣愣的、生生的、杂杂的”感觉。与其说,这种充满野味和鲜味的“看哪走哪”,使儿童获得世界场景内在化的扩展,不如说在忘神的一刹那,就已经允诺将一个孩子的诗魂扩展为一个丰饶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