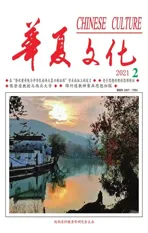《读四书大全说》的天命观简论
2021-07-28王晓磊
□王晓磊

自宋以降,中国哲学发展到了对“理气(道器)”和“心物(知行)”的争辩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宋明理学因为对理气关系与心物关系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以张载的气一元论、程朱的理一元论和陆王的心一元论为代表的三个派别。明中叶之后,程朱理学因为受到明朝政府政治上的扶持和规定而走向僵化。之后,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使明王朝走向灭亡。在这一过程中,一批进步思想家“从明王朝的覆灭中吸取教训,看到了宋明理学对社会造成的祸害,试图对宋明理学做批判的总结”(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1页)。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以顾、黄、王为三大家,其中王夫之“在救亡图存的抗清斗争中,他的思想自觉倾向唯物论,而以张载之学为依归”(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下),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10页),并“从气一元论出发,对宋明时期哲学争论的中心——‘理气(道器)’之辩与‘心物(知行)’之辩,作了比较正确的解决,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对“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做了总结”(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第205页)。因此,对王夫之思想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大有裨益,而其著作《读四书大全说》则在理学的形式下反对“俗学”和“异端”,“实际上是为了反对道学”(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前言》,中华书局,1975年,第1页),反映了当时社会变迁下的思想状况。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路下,对天的规定实质上是对人的规定,因此谈及“天”则必然要涉及到“人”。本文从其中关于天命观及其对人的影响的相关内容,来看其对理学的批判。
就本文所涉及到的问题而言,侯外庐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提到,王夫之认为“气”是宇宙的本质,其所谓的“天命”不过是“气化”的过程,在人性中所谓“天”的因素只是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的影响,因而把人性看作是“人类事件的历史产物”(参见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下)王夫之对张载气本论的继承和发展部分)。冯契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认为王夫之在天道观上对“理气(道器)”问题做了比较正确的解决,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在人道观上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成性”说,提出了“性日生而日成”的命题,比较正确地阐明了天和人、命和力、性和习的关系;在天人关系上则继承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其“成人”的学说反对了理学家的“无欲”“无情”“无我”等说教,比较注意身与心以及知、意、情的全面发展(参见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关于“理气”和人性论部分)。张茂泽先生的《中国思想文化十八讲》从儒家天命观的发展演变出发,认为王夫之的天命观突出了“天命”的理性色彩,强化了“天命”观的形而上学意义(参见张茂泽:《中国思想文化十八讲》,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儒家“天命”观部分)。在以上学者的研究中,对于王夫之天命观的研究已相当详细与深刻,然就王夫之天命观中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则似乎着墨较少。故而笔者拟就此问题略述一己之见。
一、天与天命
关于“天”的四种含义,即自然之天、义理之天、命运之天、主宰之天的说法影响颇广,已成常识,故不再赘述。谈及天为何物,首先需要从本体论对其进行判断。王夫之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而程朱理学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其内在逻辑已完全展开,同时明中叶之后程朱理学的衰落及王夫之后来从事的抗清斗争又使他的思想趋向于唯物论,因此王夫之对张载气学颇为崇奉。在《读四书大全说》中,王夫之说“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718页),所谓“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660页),“天者,固积气者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719页),“天运而不息,只此是体,只此是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69页),天只是由物质性的气流行构成的自然物,但天也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然之天,而有一定的主宰权能,这将在下文中提及。
关于“命”,朱熹解释“命,犹令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17页),指天对人事的决定意义。只有当天具备人格化的意志时,才有“命”的来源。因此“命”也通常是对“天命”的简称。“天命”一般有两种意义,即“‘天’决定、主宰人事的结果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和“‘天’赋予、命令或主宰现实世界的活动过程”(张茂泽:《中国思想文化十八讲》,第99页)。《读四书大全说》认为“若夫命,则本之天也。天之所用为化者,气也;其化成乎道者,理也。天以其理授气于人,谓之命”(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749页)。此处所说的理气“不是存在与所以存在的关系,而是存在与存在方式的关系”(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下),第918页),“理”也并不是程朱理学意义上的本体,而是指事物的本然之则,即现代话语语境中的“规律”。这种天命观乃是前一种说法的体现,即命中包含有理(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的表现。因此,此处说“天以其理授气于人”乃是指天遵循一定的规则将气赋予人,这里包含着一定的先验因素,为之后王夫之在道德伦理方面表现出唯心主义倾向埋下了伏笔。
二、人世道德秩序的维护问题
自唐朝李翱提出“复性”说之后,程朱理学也按其思路,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企图以此达到圣人境界。这种说法乃是将封建伦理纲常形而上学化,并以“天命之谓性”的形式宿命化,如此便构建起了一套理学的伦理道德秩序。然而依照《读四书大全说》的说法,“性者,天人授受之总名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3页),性乃是对天授人受关系的总称,其内涵为“仁义礼智”(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673页),但天本身却没有意志,“盖天无心成化,只是恁地去施其命令,总不知道”(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13页),世间万物只是按照其本然之则生长倾覆,即所谓“性命各正,而栽者自培,倾者自覆”(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214页),“性”便失去了其先验的道德属性,而只流于气化自然。再者,因为气的变化流行,“人日受命于天,则日受性于命。日受性命,则日生其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459页)。在这种逻辑下他的思想虽然冲击了理学的禁欲主义,但同时也否定了存在天经地义、通于古今的道德准则,因此便失去了对人性的规定,使人性不必必然善,所谓“善”的行为方式也就失去了形而上的依托。如果不能为伦理道德找到新的形而上学的支撑,则必然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崩溃。
由上所述,对义理之天的否定存在着道德崩溃的危险,因此为了保证现实世界的道德秩序,《读四书大全说》在天人关系上发挥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主张“天道自天也,人道自人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754页),使人的主体能动性与物质性的天保持区别而依然蕴含着先验道德的因素。具体来看,便是一方面,王夫之以“孔颜之学,见于六经,四书者,大要在存天理,何曾只把这人欲做蛇蝎来治,必要于他一刀两断,千死千休?”(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282页)“性为天之所命,而岂形色、嗜欲、得丧、穷痛非天之所命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747页)的说法,批判理学家对儒学克己复礼思想的异化,同时还主张“天无欲,其理即人之欲”(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248页),这种观点对人价值的肯定堪比“人是万物的尺度”。一方面又因为“人伦之事,以人相与为伦而道立焉”(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181页),承认伦理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必须性。同时因为“夫好恶必听命于中之所为主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18页),“中之所为主者”即是心,而心不同于性乃是由情所制,即所谓“性,道心也;情,人心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572页),“性一于善而情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677页),抛弃了道心便会使心流连于善恶之间,无所依归。因此,王夫之又提出虽然“天地之所以为道者,直无形迹”(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176页),不过“天但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但以元、亨、利、贞为之命”(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747页),虽然人无法直观到天地对物质的规定性,但是其以气为质料生成了世间万物,在化生过程中便已经先验地赋予了万物仁、礼、义、智的道德属性。因此,《读四书大全说》中便说道:“在天者命也,在人者性也。命以气而理即寓焉,天也,性为心而仁义存焉,人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681页)“天之命人物也, 以理以气。然理不是一物,与气为两,而天之命人,一半用理以为健顺五常,一半用气以为穷通寿夭。理只是气上见, 其一阴一阳, 多少分合, 主持调剂者理也。凡气皆有理在,则亦凡命皆气而凡命皆理矣”(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335页)。理作为气的“调剂者”,依然具备伦理道德属性,而由于人天然地具有道德属性,故而“人有其气,斯有其性……人之凝气也善,故其成性也善……气充满于天地之间,即仁义充满于天地之间”(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662页),“道也,仁也,义也,礼也,此立人之道,人之所当修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127页)。如此一来,《读四书大全说》通过对天的物质性阐述,使得理学的禁欲主义失去了理论基础,同时又通过使气具备先验的道德属性而使得“天理,人欲,虽异情而亦同行”(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717页),但如此也使得其学说本身存在着一定的自相矛盾之处。
综上所述,在关于对“天”的看法方面,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表现出与张载一脉相承的唯物论倾向,其否定天的主宰权能,肯定人的价值,对于人性的解放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要看到其在道德伦理方面依然留存着程朱理学的痕迹。究其原因,乃是由于无论何种世界观,都要为现世的伦理道德秩序提供理论支撑,而朴素的唯物论对形而上的道德依据的否定,同时自身又不具备对道德原则的理论支撑,则会为道德怀疑论的泛滥提供土壤,如此一来则容易使人丧失廉耻,沉迷于物欲之中,最终导致人间道德秩序的崩溃。因此《读四书大全说》中天命观存在的这种微妙的矛盾,乃是由于当时的唯物论还不能为人的精神家园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是理性发展的不充分。总之,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虽然因为满清入关及其高压的文化政策而没有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变革性的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这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思想史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