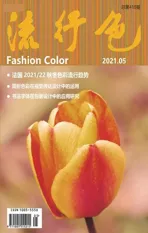敦煌早期壁画中的供养人与画工
2021-07-28杨瀚林
杨瀚林
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敦煌早期壁画主要指敦煌莫高窟北朝时期的洞窟(公元353建窟前凉——公元581年北周灭),这一时期的壁画是目前敦煌发现最早的石窟壁画,时间跨度较大,可以明显看出敦煌壁画中供养人画像的绘画方式变化。
一、画工的工作方式及与供养人的关系
敦煌石窟壁画并不是敦煌地区的画工们最早开始制作的大型壁画,在敦煌发掘的西晋墓葬中就已经有大型墓室壁画出现。画工的身份在马德老师的《敦煌古代工匠研究》中描述的非常清楚。制作大型壁画需要大量画工共同完成,因此不同级别的画工其工作分工也有不同。绘制壁画,自然在精细需要展现技巧的地方用上高级的画工,在敦煌壁画绘制中多以漏稿为主,壁画绘制上一般由熟悉佛教绘画的画工对壁画内容制作粉本,而后由学徒将粉本 “扎好谱子” ,平铺到墙壁上用颜料拍打,做标记后用浅色颜料勾勒出粗样,再经历印稿和放稿后,开始由地位高且技巧高超的高级画工绘制定稿线,并调色成色完成作品。那么对于一幅作品的好坏是否有准确的行业标准呢?从画工的级别以及民间的声望就可看出,绘画技艺是否熟练,是否有创作能力是画工晋级的标准。官府统辖的画工与寺院供养的画工有正式品级,民间画工则以能力分高下,单论佛教绘画技法的熟练度而言,前两者更能接触大量佛寺绘画,因此技巧上相对成熟。
从马德老师的《敦煌古代工匠研究》中关于画工身份问题的讨论中,笔者对关于供养人与画工之间的关系在此有猜测:画工与供养人,在小型的平民百姓私人开凿的洞窟中,是相互协商的、平等的契约关系,有着双方自由选择的权利;在由官府或寺庙出资修建的洞窟中,大部分工匠都是其管辖之下的画工,因此是被役的关系;而世家大族中的画工,部分为私人豢养的奴隶,这种是完全的被奴役的状态,是画工中最不自由的类型,当然还有聘请有名的本地画工或寻找“接私活”的官府管辖的画工和寺院供养的画工,这种情况下,画工与供养人之间也是相对平等的关系,具备互相选择的可能性。总体而言,仅有一部分画工与供养人是平等的契约关系,大部分供养人在二者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画工对绘画对象的选择性是有限的。
二、画工技艺的传承
画工与供养人的关系也从侧面反映了画工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尤其在社会地位分工上素有“士农工商”一说,愿意学习绘画的人大部分是原有的工匠阶层或有兴趣的士人阶级,绘画技艺的传承也以师徒传授、子继父业、口耳相传和粉本传承为主,这样的传承方式难免会因为各种情况如误传、粉本丢失或无继承者等而出现传承的断绝,难以保证传承的延续性。其中最容易流传的便是以粉本的方式,如现今所见的《芥子园画谱》便可作为学习绘画的训练素材,但这种方式极易造成对某一作品的程式化倾向,仅能作为绘画的参考,主要的绘画传承还是以师徒相授,子承父业为主。在较为封闭的传承方式的影响下,绘画技术的发展进度缓慢。敦煌地区的文化、绘画风格一直以来深受中原汉室的影响,画工们对汉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认同感,不论是匈奴还是鲜卑族的统治下,敦煌的文化传承始终不曾断绝,因此传承的封闭性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对本土技艺、文化的保护。
三、画工对供养人画像的绘画方式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塞,在汉朝时就属于边关要地,敦煌地区很早就已经接触到西域文化,其艺术更容易受到西域风格的影响。在北凉时期,供养人绘画的人物整体形象、姿态气韵呆板肃穆且身形健硕,受到印度佛教塑像及新疆一带壁画中供养人的形象影响较大,但在服饰绘画样式上与西域样式更为接近。令人称奇的是早期印度的佛教雕塑中的供养人以及早期新疆壁画中同一时期的供养人都以跪立姿态,而敦煌石窟从最早的北凉时期的洞窟中的供养人画像已经不见跪姿参拜的样式了。从绘制的供养人站姿来看,虔诚不失自我的样式从一开始便贯穿敦煌壁画中所有洞窟的供养人像以及故事画中所涉及的人像。西魏后,中原文化涌入敦煌地区,供养人绘画的样式逐渐摆脱僵硬,更加贴近中原地区人物画的绘画方式,神情姿态更加飘逸自由,在人物性格方面也有了表现,样式更多受到中原人物绘画的影响,敦煌对中原风格开始慢慢接受,并在东阳王元荣执政时期达到了顶峰。
有明确资料记载的壁画制作从隋唐就已经出现,饶宗颐先生编著的《敦煌白画》一书,收集整理了大量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的白画,进而探讨了“白画与敷彩”“素画与起样”“粉本模拓刺孔雕空与纸范”等“若干技法”问题,注意到作为粉本和稿本的敦煌白画。这两种粉本在古代壁画创作中都有所应用,才会形成后世所见的大量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功能建筑上的视觉图像相似的壁画创作,总体而言早期供养人画像的样式是经西域传入原始样式,本土化融合后,最终制作粉本绘制而成。
敦煌早期供养人画像中画工除了采用粉本绘画外,是否有人物画像的“写生”的意识存在?沃尔夫林认为眼睛会受到其他精神领域的制约,同时也会受到制约。画工及供养人在“观看”画像时,都会受到一定宗教信仰的影响,早期自我意识处于萌芽阶段,画工将供养人像看作装饰符号,在壁面上以“配图的功德表”的形式对供养人进行描绘,此时的供养人也没有过多的细致需求,因此在“观看”中,对画像仅有代表意义,此时的绘画并不能看出有“写生”的意图存在。从西魏时期开始,供养人对自己的画像要求更高,需要能够在壁画中有清晰的区分,而画工在供养人的要求下,将供养人画像绘制更加精细,同时由于创作压力,激发了画工对供养人画像的创新。在随后的供养人绘画中,供养人要求在进入洞窟礼佛时,以人物本身独立的形象陪伴佛侧,能够更好的区分自己与他人。画工受到数百年间中原文化的影响,已经形成固有的对绘画的理解和对绘画对象的观看方式,因此难以出现如西方壁画中那般写实的画像,对人物的绘画方式也是如此。在前文中提到了大量对画工绘画方式的探讨的文章书籍,大部分学者都以粉本为主研究画工的绘画方式,但笔者以为,画工一直以来在人物绘画上都具备一定的“写生”意识。从供养人绘画中来看,北魏以后的供养人画像,已经明显的看出画工们对出资多的供养人们给出的更多的“注视”,那般繁复的服饰纹样,以及精致的妆容,无不显示出画工写实的意图。诚然如此大量的供养人绘画无法达到全部都以“写生”的方式去绘制,但人物画像的描绘与其中所述基本一致,从这些画工精心“写生”或出现“写生”意图的画像中,可以看到普遍都是世家大族或王室官员亦或得道高僧。
画工在供养人画像的绘制中,在大方向秉承本土原则,但佛教其他人物画像一直在试图融入本土化。佛教其他人物画像追求本土化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希望佛教的本土化与佛教更容易被认同,而佛教中其他人物画像的本土化过程,也是佛教本土化的过程。早期的供养人画像从一开始从墓室壁画等作品中得到灵感,打下了供养人画像绘画为中原式画法的基础。供养人画像在佛教绘画中较为特殊,是信徒为自己及家人积攒功德,修行成佛的心理暗示型的画像,此类画像往往是包含社会各个阶层以及人物,年龄等的群体画像,早期壁画中的供养人像始终与中原绘画相联系,以当时流行的绘画方式为模板,紧扣当时所流行的人物画绘画样式来进行绘制,因此画工在供养人画像的绘制方面,在北凉时期可见的以粉本绘画为主,到北魏以后开始以粉本为主,有“写生”意图的方式为辅的绘画模式。
总结
莫高窟早期壁画中的绘画虽生涩,但已经形成规模,可知在此之前,画工行业已是存在,画工的传承大多是师徒间口耳相传,有较自由的民间画工,也有受到雇佣的官府及寺院画工,更有完全从属于世家大族的画工。绘画技巧娴熟,创作能力强的画工地位较高且受人尊重,负责壁画中难度较大的部分。早期画工手中已有可以运用于洞窟中的粉本,但供养人绘画的粉本起初为画工们依据其所知的样式与西域式的绘画相结合制作的,随后在实际操作中自行摸索,这些画工起初并不会特意为供养人作画,但随着供养人对画像需求的变化,画工开始对部分地位较高,出资较多的供养人有了“写生”的意识,不再仅仅依赖于粉本,而是加上画工自身的趣味及对供养人本身的再现。

第275窟北壁供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