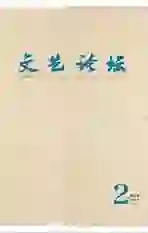还有无尽的未知可以探究
2021-07-20杜学文
杜学文
摘 要:刘洁的《戏里乾坤》是一部集中解读传统剧目的作品,采用一种“全视角”选取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剧目,梳理了这些剧目的流变,介绍了一些戏剧艺术家的演出“轶事”,既有趣味性,又有学术性,描绘出一种具体生动的文化景观,使读者感受中国传统戏曲的丰富性、生命力与艺术魅力。关于中国传统戏曲,还有无尽的未知等着我们去探索。
关键词:《戏里乾坤》;中国传统戏曲;全视角;趣味性;学术性
刘洁的散文不断在各地发表,使人们认识到了她在这方面具有的实力。她说最近有一本书要出版。我以为是一本散文集,没想到却是一部有关传统戏剧的“专著”。之所以在“专著”上加引号,是因为我们也可以把这本书看作是一部散文集。其中收集了她对四十多部传统戏剧的解读介绍,仍然用的是散文笔法。不过,对这部著作来说,却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专著”。可以说是集中对传统剧目进行解读的重要之作。实际上有关传统戏剧的著作很多。或专注于戏剧的历史流变,或集中于某一剧种、某一现象,甚或对某一艺术家或某一剧目进行研究介绍。虽然这其中会涉猎到许多剧目,但均為服务于研究主题的实证。一般而言,它们只说与所讨论话题有关的部分。从剧目的存在价值言,还缺少自身的独立意义,是依附于话语要求的存在。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否定这种研究方法,而是说,从剧目本身的独立存在来展示传统戏剧丰富性的著作,实际上还不多。至少我接触的不多。这就使刘洁的这本著作具有了独特的意义——从剧目出发,突显传统戏剧的丰富多彩,进而为读者描绘出一种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生动的而不是观念的、鲜活的而不是教条的文化景观,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生命力及其审美魅力。这也许是刘洁对传统戏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重要贡献。
让我惊讶的是刘洁对传统戏剧的熟悉。这种熟悉不是出于研究需要的熟悉——为实现研究目的而查阅资料、收罗史籍,甚至回忆与重叙剧情等等。她的熟悉与此不同,是一种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的熟悉。似乎对任何一个剧目,她随时都可以说出个一二三来。这种“随意性”的熟悉让人感叹。应该说,比那种为完成研究而形成的熟悉具有更高级的意义——使传统戏剧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进入人的日常。人们常常会说,戏剧在凋零,观众在消散,年轻的观众与爱好者越来越少——这应该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但人们似乎在这样的表象之后忽略了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传统戏剧不仅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也仍然拥有更多的关注者——作为爱好,作为传统,作为责任,以及其顺应时事变化产生的变革而表现出来的新的魅力。无论如何,我们并不能否认,由传统而来的中国戏剧仍然在城乡大大小小的舞台上锣鼓铿锵,丝竹婉转,声遏云霄。
在这样的文化现实中,刘洁把她认为优秀的剧目给我们进行了介绍。不同于一般的就某一剧种或某一类型的介绍,她采用的是一种“全视角”方法,就是在传统剧目的整体中选取了那些至少是她认为具有某种代表性的剧目。其中首先是京剧,如《玉堂春》《望江亭》《铁弓缘》《秦香莲》《龙凤呈祥》等。作为“国剧”,自然剧目甚众,名家如云,在这部书中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占有很大的篇幅。但书中也介绍了很多地方剧种的著名剧目,包括昆曲如《十五贯》,越剧如《红楼梦》,沪剧如《罗汉钱》,豫剧如《七品芝麻官》,评剧如《花为媒》《杨三姐告状》,花鼓戏亦即湘剧如《刘海砍樵》,吕剧《李二嫂改嫁》,等等。其中还有很少被人关注的剧种如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淮北梆子(《寇准背鞋》)等。自然我更感兴趣的是晋剧,如《打金枝》。从这一点来看,刘洁对传统戏剧的了解是不一般的。或者说,她在此一方面的积累还是非常深厚的。
其实要了解中国传统戏剧的剧种也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只是一种知识性积累,或者查阅一下有关资料也可以。重要的是刘洁在不经意之间突破了对剧种剧目的平面介绍。她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剧情的叙述中。事实上她不太在意对剧情的重现。她的预设前提是读者已经对剧情有了基本的了解,因而只是简单地带过,或在文中讨论相关问题时顺便提及。她最突出的贡献是对这些剧目流变的梳理。在她而言,仅只是随便一说。但就传统戏曲的沿革而言,却少有这种大面积的对不同剧种若干剧目进行的集中介绍。这也使这部著作在轻松的笔触之中具有了“史”的意味,从而表现出一种散文化的学术品格。这种梳理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某一剧目自身的演变,二是其表演的演变。比如介绍《白蛇传》,刘洁首先对其内容的演变进行了梳理。从刘邦起义前偶遇白蛇,到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再到田汉对这出戏如何进行了本质性改编,直至上世纪改革开放初被拍成电影等等。同时,刘洁也从表演的层面进行了回顾,指出梅兰芳在《金山寺》《断桥》中以昆曲的形式演出过,程砚秋、尚小云也很感兴趣,有唱片留存,荀慧生则演过全本的《白蛇传》,而今天比较常见的是梅派的表演等。不仅如此,刘洁还告诉我们,在此之前,清末时期,著名的艺术家余玉琴、李顺德就在被名为《双蛇斗》的剧目中对剑,“走旋子,大开打,全活都用上了,煞是好看”。从这样的口气来看,似乎她曾经看过他们的表演。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但由此可见在清末时,这部剧作的情节与现在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白蛇传》在拍成戏曲电影时,主演是李炳淑,也就是《龙江颂》中江水英的扮演者等等。
另一部颇具经典意义的剧目是《打金枝》,为晋剧最具代表性的剧目。就我而言自以为比较熟悉。但刘洁告诉我们,这出戏很多剧种都有演出。具体是那些剧种,她没有说,但也由此改变了我对《打金枝》的认知——这部戏不仅是晋剧的代表作,其影响也并不局限于晋剧流传的地域,它应该是中国传统剧目中具有突出影响力的代表之作。刘洁也在她的书中介绍了《打金枝》的流变,指出“旧时,大户人家办堂会,多半会以《跳加官》开场,接下来是两出喜兴的戏——《满床笏》和《打金枝》,有人认为这是一出戏,其实不然,前面那出主要是围绕着郭子仪的发家史说的,后面那出是他儿子和儿媳妇的闹剧,也有把两部分合在一起演的”。由此可以见《打金枝》的影响之大,以及其演变的轨迹。而在表演方面,刘洁强调了在上世纪拍摄电影时动用的演员,“演唐代宗的是丁果仙,沈后是牛桂英,驸马郭暧是郭凤英,公主是冀萍”,所谓晋剧之“丁牛郭冀”四大流派。她对晋剧的熟悉应该只是她了解中国传统戏剧的“冰山一角”,可以看出其积累之丰厚。
刘洁在对剧目熟悉了解的基础上,也为我们介绍了那些著名戏剧艺术家的有关轶事。这些介绍看似闲笔,却多含深意。以丁果仙言,曾有与马连良换戏的趣事。上世纪三十年代,丁果仙到北京演出,马连良看到丁果仙对自己的《四进士》很感兴趣,就把剧本拿给她,并悉心教授她怎么演才能取得好的效果。而马连良对丁果仙演出的《反徐州》评价很高。丁果仙就请其“扶风社”班子观摩自己的演出。后来马连良也移植了这出戏,改名为《串龙珠》,终成其代表作之一。他们这种相互学习借鉴、相互扶持帮衬的品格可谓传统戏剧界的佳话。在介绍《铁弓缘》时,刘洁谈到了两位艺术家。一位是关肃霜,出演剧中的陈秀英。“她可以同时用靠旗打出十二杆枪,还能用靠旗围着一杆枪自转三十圈,同时围着拿枪的人转大圈两周”。在全身装备带妆的条件下能完成如此复杂的高难度表演,确非一般人所能。而另一位艺术家盖叫天,曾经“从三张桌子的高度鹞子翻身跳下来,腿摔断了,仍然坚持架子不倒,坚持到不能坚持了才下场”。这些艺术家是真正为艺术而存在的。要掌握这样的演出技巧,并不是花架子就可以。这也使我想起了被誉为“晋剧皇后”的艺术家王爱爱。她在初学戏曲时,为了练好身段,每天都是枕着自己的双腿睡觉的。我无法想象这种姿势是什么样子,如何还能睡觉。但事实就是如此。这只能说明,今天的我们已经离艺术的精神太远了。
《戏里乾坤》对剧目的介绍并没有停留在各种史料与轶事之中。在这种看似随意的介绍中,刘洁往往做出某种概括性评价,使这部著作具备了较强的学术品格,也由此而使其文化价值得到了升华。不过,作者并不喜欢那种一本正经的表述,这与全书的风格不符。更重要的是,她一开始就没有准备写成学术专著,而是表现出一种随性淡然的姿态。也许,这样的表述更能够与读者接近,却又不失学术品性。比如,关于中国传统戏剧的类型,刘洁并不是正襟危坐地进行分析论证,而是在介绍《墙头记》时顺便提及:“中国戏曲中,一大類是才子佳人,一大类是英雄传说,再有一类就是伦理教育。”她就是这样在不经意间做了归纳,但这种归纳又是建立在对传统戏剧烂熟于心的基础之上的。又如讨论《锁麟囊》的情节,就会顺便说出某种关于剧情设计的“规律性”见解:编剧“人为编造的故事却表达出事物发展的永恒规律,万事都是有变化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看着今天的大富大贵,明天可能因为外力就荡然无存”。似在说剧情,亦似在谈人生,实际上却也表达出作者对编剧技法的某种体悟。在介绍《七品芝麻官》时,她谈到“把一出戏做得圆满,戏剧冲突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被迫原则运用得好。所有的人物都好像是被某种不得已的情况逼迫着走到了某一步,做选择的时候还不能选项很多,且要对当事人有利的原则恰恰是对剧中其它人非常不利的情况”。这里所提之编剧的“被迫原则”应该是对戏剧美学的一种贡献,是有关戏剧创作的规律性表达。
不过我感到《戏里乾坤》也还有明显的缺憾。这就是对梆子戏剧目介绍得比较少。特别是诸如蒲剧、秦腔等极为重要的剧种还涉及不多。而梆子戏在中国传统戏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从其对晋剧的介绍中可见作者对梆子戏相当熟悉。如果条件可能的话,希望刘洁能够就梆子戏再写一部专著也是很有意义的。不过,她在这本书的《跋:幻境大天地》中说到,“中国戏曲的天地之大,之宽广,还有无尽的未知可以探究”。就中国传统戏剧而言,当然还有很多的领域、内容与话题,我们要讨论的东西还很多,确是说不完的。但通过这本书,让我们走进了看似熟悉却依然茫然的艺术领域,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作者单位:山西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