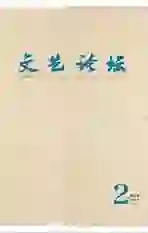建设性批评的可能性
2021-07-20龙慧萍
龙慧萍
摘 要:张志忠先生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充分体现了从问题出发的深度、审美与艺术分析的敏感、“坏处说坏”的坦诚与“文学爱好者”的热情。在他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实践中,可以看到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准确把握时代精神及与作者感同身受的能力、高超的艺术禀赋、正确的判断力。他的治学道路,展现了“建设性批评”在实践中的多种路向、多种可能性以及在当代所能触及的高度与境界。
关键词:张志忠;建設性批评;文学研究
从1982年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第一篇论文(与戴屏吉合作发表《论〈一个人的遭遇〉的成败得失》)开始,张志忠在文学批评与研究领域已辛勤耕耘近40年,出版了《莫言论》《1993:世纪末的喧哗》《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九十年代的文学地图》《当代长篇小说论略》《华丽转身——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型》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随笔、评论近300篇,其中有70余篇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转载。除此之外,还有大量论文入选各种批评文选与文丛。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创作与批评密切互动时期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张志忠的批评与研究,在追踪新潮与发现问题、理论探索与审美发掘等方面,都有相当的深度与造诣。看他的文章与著作,不仅服膺于文学“黄金时代”的批评家的深厚内功,也能感受到一种学者心系时代的人间情怀。
一、从问题出发的深度
在张炯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新时期批评家的三代人里,“五零后”的张志忠和王晓明、陈思和、南帆、吴亮、黄子平等,属于当代文学批评家队伍中最年轻的一代——第三代中比较年轻的一批(当然随着七零后、八零后批评家的成长,这个代际划分今天还有新的变化)。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在总体上属于“价值观、思维模式和批评方法上都较新锐的批评群体”。八十年代西方思潮的大量译介,使得这一代批评家在运用新理论资源时能得风气之先;但张志忠在研究中始终坚持从问题出发,绝不因追慕新潮而使理论方法遮蔽问题、脱离文本、穿凿附会。
他在莫言研究中融合卡希尔的《人论》,就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理论引入。因为在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小说创作引起文坛强烈反响时,传统理论已无法对莫言作品的新质做出有效的阐释,因而当时针对莫言作品的评论文章虽然不少,却仍然留下了“一片理论阐释的空白”。此时借鉴西方理论,从“感觉—生命—艺术”的转换过程来阐释莫言作品中蓬勃的生命意识、生命的一体化,就非常准确地抓住了莫言创作的本质方面,使研究脉络彻底贯通并与研究对象高度贴合,达到了前人所未及的深度,开创了莫言研究的新局面。
鲁枢元在《新时期40年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史》中将《莫言论》这种批评和研究的方法,归纳为“运用文化学对莫言的评论”,认为张志忠对莫言的评论与当时吴亮用叙事学对马原的评论、王晓明用文艺心理学对张贤亮和张辛欣的评论等一起,都属于将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在短时间里移入中国所产生的聚集效应中比较成功的范例,并进一步指出,这类批评实践后来形成了文学批评领域的主导力量。上世纪八十年代,绝大多数在高校求学的文科学生,都曾有过一段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理论、方法的经历,张志忠也不例外,在北大求学期间,他读了大量的西方理论书籍;同时受到李泽厚的启发,也从汤一介、杜维明等的讲座中获得一种全球性的文化大视野,并以此反观本土。这里的“反观”很关键,也就是说,他能用文化学方法做莫言研究,是长期修炼“内功”和反复思考、将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问题结合的结果。
回顾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文学和知识界的“文化热”。张志忠对莫言的研究,实际上正是基于当代文学创作新趋向的敏锐反应。因此,文化学方法不仅在他的莫言研究中有集中、突出的表现,在《试论九十年代文学的文化视野》这一类论文中,也有极为开阔的展示。而他的莫言研究,又是当代文学批评与创作同步呈现的“文化转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是有着独特贡献的。
张志忠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虽然以莫言研究影响最大,但他早期比较有影响的成果,是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连续发表的两篇论文《近年农村题材小说概论》和《论中国当代文学流派》。这两者都是他当时攻读硕士学位的成果,显示出一种开阔的视野和其对文坛重要现象的宏观把握能力。最为重要的是,这二者也都是从问题出发的。前者所针对的问题是当时农村题材小说的新趋势;后者是因为他发现当代文学的流派现象并不像现代文学那么鲜明,但各个地区的作家群落,其实又是有各自的特点的,可以当成“准流派”来研究。
正如张志忠自己所说的那样,“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需要在文学的疆域之外,具有现实的社会关怀和积极的参与热情”。他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发现文坛的新趋势与重要作家的创作动向,对其中重要的现象做出述评。这充分显示了一个学者的思想活力和知识更新能力,也是他在四十年学术生涯中未曾固步自封的内在动因。
在此基础上,他更擅长在当代文学纷纭复杂的现象中发现内在规律,看到其中隐含的问题。在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对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很多现象与问题都有长期关注。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热”,他还对军旅题材作品和表现“文革”题材的文学作品进行过长期追踪和思考,他也关注过人文精神大讨论、现代性问题、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研究问题、审美优先问题、现实主义的当代发展方向问题等,并且在这些论题下,都写出过有分量的论文或专著。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索与研究,颇能见出他作为批评家的社会关怀、持久热情与思想深度。仅以张志忠对现实主义的当代发展问题的关注为例,他思考这个问题的持续时间极长,围绕这个问题,在很多论文与著述中都进行了不同层面的研究。他在北大求学时写《近年农村题材小说概论》时就已经开始探索“革命现实主义”如何走上更广阔的道路,后续一直都有结合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的思考,如《建设“充分的现实主义”——世纪之交的社会生活新变与作家的自我更新》系列论文,即是新时代中思考的深化;在近作《重建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路遥〈平凡的世界〉再评价》中又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阐发了当下重建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重要意义。
於可训在谈当代文学批评家的个性时,将批评家分为三种类型:注重主观感受和实证分析的、长于思辨和知性分解的和具有人文学科学者特征的。在他看来,张志忠属于具有“人文学科学者的特征”的一类,擅长于“从有关批评对象的(这些)分散的、零乱的原始材料中,找出其内在的整体的关系和联系,为批评对象构造一个有关它自身的知识的系统和秩序,并把这种关于某一批评对象的知识的系统和秩序,纳入到一个更大的历史系統和文学秩序的背景之内,从更为深广的联系和更带本质性的关系中,显示批评对象的价值和意义”。於可训认为,这一类批评家很少“提供有关批评对象的具体而微的分析和评价意见”,但“对于文学的总体发展和文学史的建设,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经验参照和极为宝贵的理论借鉴”。
二、审美与艺术分析的敏感
应该说,於可训所指出的张志忠作为“人文学科学者”的特性是他治学风格的主要方面,但实际上,张志忠做文学批评和研究,针对特定作家作品的感悟是细致、敏锐的,他的评论文章中也多有具体而微、体贴文本的批评意见。在批评实践中,他特别重视作品的审美品格,在《文学批评应重视审美品格》一文中就曾指出:审美性是文学的命脉所在,在批评中应当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艺术分析。为此,他反复强调做批评和研究首先要把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文学研究不但要在作品中寻找观点,还要寻找情感、想象,包括对语言的敏感,对审美特征的敏感等,而这是需要一定艺术禀赋的。他曾说自己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谢冕老师那种充满了审美情调的文章,在这方面有意识地向谢冕学习。
实际上,张志忠自己就有一批非常出色的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充满审美情调的文章,比较典型的是《镜中之像 像外之旨——洛夫诗作中的镜像研究》一文,此文所展现出来的深厚理论功底与极高艺术禀赋都是令人叹服的,作者在分析阐释洛夫诗歌中的镜像时,真正做到了将思想性与审美性融为一炉,相得益彰。因此,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读者很容易进入它所阐发的洛夫诗歌意象的幽微细密之处,并被其中的丰富蕴含吸引。论文从洛夫《漂木》中的镜子谈起,一路引述作品,一路娓娓谈到《沧浪诗话》《管锥编》、拉康和巴赫金,其间还穿插了洛夫诗与鲁迅、杜甫、李益、冯至等作品的对照,不仅将古今中外熔为一炉,且饱含着因诗而生的种种人生、哲学感悟,逸兴横飞,妙语迭出,引人入胜。
事实上,张志忠的文本阅读量惊人,文本的熟悉程度也令人惊奇。他关注过的当代作家,从最开始的张贤亮、刘心武、朱苏进、李存葆、王蒙、贾平凹、梁晓声、马原、莫言开始,一直到铁凝、王安忆、张承志、路遥、池莉、刘醒龙、陈忠实、余秋雨、毕飞宇、韩少功、方方、毕淑敏、阎连科、严歌苓,再到年轻一代的徐则臣、红柯、宁肯、笛安……(这个名单还很长),可以说,当代文坛的较重要的或是较有特点的作家,在此几无遗漏。对这其中不少作家,张志忠都撰写过不止一篇论文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分析和讨论,对他们的创作特性、文本的思想内涵与美学风范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张志忠特别为人称道的《莫言论》,就是既有严谨的论述,也有别开生面、诗意盎然的审美分析的。而无论是其中的严谨论述还是生动的审美分析,都被后来的学者广泛、反复地引征,在此即不赘述。这里不妨来看看他对其他作家的分析与评论。
《少女的启示录——评铁凝〈玫瑰门〉》是张志忠早期的论文,文中分析《玫瑰门》的朴拙之美,就是非常出色的艺术分析:“《玫瑰门》的朴拙,是与眉眉的朴拙的童心、朴拙的认知方式相吻合的: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由人生地疏到逐渐进入情况,偶然的感触到连续的注意,由纷纭嘈杂的紊乱印象到日渐清晰的轮廓,作品的生活逻辑与叙事逻辑由此得到统一。机智、峻峭是一种美,平易、稚拙也是一种美,而且,在某些时候,它更要求相当的功力,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在分析之后,他还做了进一步的总结和归纳,将作家的创作方法上升到理论高度:“从局部出发而引出整体画面的方式,既是作品的构造原则,又是作家把握生活的审美方式。”
在《贾平凹的创作:渐进于跳跃》一文中,他又用另一种相当诗意的语言,将贾平凹那一时期的创作比拟为“充满活力的溪流”,“溪水无定体,随物赋形,少固守,多变化,少停滞,多涌动,经潭渊而深沉,遇石岩则跳跃,活活泼泼地流淌,抑抑扬扬地吟唱,在运动中获得生机,在前进中更新自我”。这样的文字,生动、优美而不失精确,能抓住作家的精神气韵,也充分地呈现了作品的艺术境界与美学特性。
另外,张志忠说余秋雨的散文《这里真安静》是“狂戾军乐、凄迷艳曲和庄重美文的三重奏”;说徐小斌的《双鱼星座》《别人》《吉尔的微笑》等作品的情节结构模式是爱情方程式(三元一次方程和二次方程);说徐怀中的《牵风记》是“穿透战火罡风的和煦清风”,设喻新颖、生动形象,且能直抵作品的本质与内核。而他对池莉“人生无梦到中年”的评价,对宗璞创作“士林心史、儿女风姿”的评价,说“阎连科是一只鸱鸮,啄开腐尸的皮毛以彰显其内在的溃烂,用其不祥的持续的啼鸣在警示世道人心”,既是出色的风格与境界品评,也从侧面揭示了理解作家精神路向(包括局限性)的途径。张志忠的文章中,这样的评论还有不少,也都是感性经验、形象思维与理论概述能力结合的范例。
三、“坏处说坏”的坦诚
鲁迅先生说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是句非常朴素的话,但在当代文坛想要做到“好处说好”不难,“坏处说坏”,却并不容易。张志忠评价当代作家作品,总体上宽厚平和,对新人新作的支持力度很大,主张用更多的艺术探索和思想探索来拓宽话语空间。但在此基础上,他又是当代少数几个敢说真话的批评家之一——从他对王蒙、贾平凹和王安忆的评论中就可以看出来。
张志忠读硕士学位期间,有以“王蒙研究”作为硕士毕业论文选题的构想。后来因为谢冕先生建议他研究宏观问题而放弃。也就是说,王蒙是张志忠比较喜欢的、也是最早重点关注的作家之一。但在1995年的《对文学的轻慢与失态——评王蒙近作〈失态的季节〉》一文中,他就对作家在语言和塑造人物方面的草率和浮滑进行了批评,并同时指出:“这位具有领率性的重量级作家,也渐渐露出他对文学的轻慢与失态的时候,他的作品中不容忽视的缺憾,那被好评如潮所掩盖的弊病,就从某种意义上表证着今日文坛的重要倾向,因此就更加值得重视。”
时隔多年,张志忠在访谈中对于王蒙《失态的季节》的缺点,仍是直言不讳的:“后来对王蒙的《失态的季节》,我就有明确的批评——倒不是为批评而批评,但总觉得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我们还是应该更清醒一点,‘爱而知其恶,不应该像有的批评家那样,毫无保留地全是赞扬。这篇文章,可以说也没有其他的考虑,就是我的‘阅读体会,就觉得他那种语言方式不但不加节制,而且很多时候‘似是而非。”
而张志忠对贾平凹和王安忆的批评,和他对王蒙的批评一样,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所敬重的当代一流作家,爱之深,故而责之切。
张志忠对贾平凹的关注也比较早,1985年就有《贾平凹的创作:渐进于跳跃》一文,对贾平凹当时超越自己“跳跃着前进”的创作态势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在1999年,在《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一文中,他就对贾平凹创作中期出现的一些突出的问题进行了批评,指出贾平凹近年来的创作有将作家个人生活与作品中人物混淆、理念大于形象、过度渲染神秘文化、女性观陈腐等缺陷。这样的评价,在当时大概要算比较不留情面的。林建法是当时刊发这篇文章的《当代作家评论》的编辑,他后来在访谈中,列举了一系列印象比较深的批评文章,里面就有张志忠的这篇论文。林建法同时指出,这些批评文字对作家和文坛都起到一定的冲击作用,对于帮助作家认识自己的局限与不足,也是大有裨益的。
早在1992年写《王安忆小说近作漫评》时,张志忠曾经顶住压力,肯定了王安忆小说中性描写的价值;同时,决不承认王安忆不是主流作家,也不承认王安忆的创作与主流文学之间存在冲突。但时隔十六年后,针对王安忆的新作《启蒙时代》,张志忠在肯定她创作的突破与对思想深度的追求的同时,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了她创作的两点缺失。其中之一即是《启蒙时代》中对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理解是错误的。对此“误读”,张志忠更执着地进行一种“索隐探微曲径通幽的追问”。他从王安忆的个人经历出发,深入挖掘了王安忆误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两个深层原因:“红小兵”心态与对上海市民生活的羡慕、认同。这样的批评与研究,道人所未道,充分显示了一个学者型批评家的见识与深度。
另外,张志忠对毕淑敏、池莉创作局限性的批评,对陈忠实《白鹿原》的缺点的分析,对石钟山《狗头金》的批评,在肯定他们的成就的同时,也都是直指问题、切中要害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作家创作的进步,因而显得相当诚恳。当然,对于自己认识上的偏误,如当年对莫言作品《丰乳肥臀》价值的认识不足,“没有特别上心”,也直言不讳。
四、“文学爱好者”的热情
张志忠常说自己是个笨人,在一众同龄的批评家中,他并非天分高绝者,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将自身的生命与情感体验融入了批评活动的“文学爱好者”。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追踪文学新潮的热情,并且认为:在面对作品时,能够把自己的情绪、情感调动起来的、身心投入的阅读是做好批评的基础。
他在访谈中说过:“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我经常有一种孩子般的好奇心,不知道在当下还是在明天,哪一位作家,哪一部作品,就会新鲜出炉,会让我们眼睛一亮,大吃一惊。……这就是追踪当代文学现象的乐趣所在。”他还将自己在浩如烟海的新作中,发现新的优秀作品的感受形容为“披沙拣金、峰回路转的乍然惊艳”。这实际上要求批评家长期坚持不懈地、系统全面地阅读每位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新作。这在新时期以来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空前繁荣的情况下,是殊為不易的。
在张志忠的评论文章中,经常能看到他在阅读新作品时为作家的进步、突破和创新激动不已,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如他当年在读完《心灵史》后,在《读奇文,话奇人——张承志〈心灵史〉赘言》一文中写道:“对于《心灵史》这样一部奇书,我的确感觉到论述它的极大困难。……我们只有由衷的崇敬和肃穆。”在文章的结尾,他更是连用四个排比句,称《心灵史》是“一部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和超度的历史”。在前面提到过的《贾平凹的创作:渐进与跳跃》一文中,他对贾平凹在短短两年之间一气推出了《商州初录》等十余部中篇和一部长篇小说赞叹不已,对贾平凹的《商州》《冰炭》等作品表现出的从写实(现实主义)到写意的跨越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进一步指出:“贾平凹正在试寻着两者的结合——在现实生活的广阔背景下赋予作品一定的写意性,在生活图画的勾勒中透出洋溢的诗情,……更准确地说,主观的、写意的倾向几乎是贯穿于贾平凹创作的全过程。”这样的文字,不仅将自己发现优秀作品的“惊艳”完全传达出来,也是对作家创作特色、风格的精准分析与把握。
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学者在进行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带有自己出生与成长的年代的印记。在张志忠这里,年代印记不仅表现为他对某些问题(“文革”)题材作品、现实主义问题)的特别关注,也表现为一种文学黄金时代的文学爱好者从创作出发的、对作家与创作规律的理解。他曾自述,他青少年时期沉迷于阅读文学作品,下乡插队前后,就开始自己写东西了。一开始主要写诗歌,后来也开始写小说。进入大学之后,才将创作的兴趣转向研究。文学创作的亲身经验让他有一些心得体会,既有社会生活的体会,也有一些创作的甘苦,这就使得他开始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时候,能充分地理解创作的甘苦,“结合自己的经验,从创作论的角度、从创作过程的体会来进入作品”,同时对作家的精神劳动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尊重。
事实上,张志忠出自谢冕老师之门,但他的主要兴趣是在当代小说研究,尤其是长篇小说。他对当代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语言、创作方法都有过非常细致的揣摩,在《什么是理想的长篇小说?》一文中,能提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者”“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外在表现”“注入世道人心之宽阔”“足够强大与自由的凝结力”“最好地反映新世界成长的趋向”这五个方面,显然是深谙创作规律的。
又如他批评石钟山的小说《狗头金》时,谈到小说的语言问题,针对将小说当做电影电视脚本来写的现象,在文章里写了这么一段:“记得当年王愿坚说过,在八一电影厂当编剧写电影剧本,把笔写坏了,小说中描写山峦景色,要费很多笔墨,写电影剧本,却只需要写一句提示‘群山,群山,群山,或者再加一句渲染,‘苍山如海;因此,写多了电影剧本,要想重新写回小说的路子,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此话可谓语重心长,非个中人不能道也。”而特意拈出这一段,作为对石钟山的批评,亦可谓深谙个中滋味而语重心长了。
他最近的论文《毕飞宇小说漫评》从毕飞宇作品的解读问题谈起,认为解读毕飞宇作品聚焦于“文化大革命”或者传统文化的桎梏,都未达到应有的深度,而“对于人生与人性的错位之高强度和多重性的描写及由此造成的强烈而不忍卒读的疼痛感”,才是研究的重点;然后在此基础上转谈创作,指出“在当下,更应该关注和鼓励他超越有限历史而及于深邃人性,实现新的突破”。很显然,这种设身处地为作家着想,将批评阐释、风格、格局分析与创作方法的考量结合在一起的行文方式,是张志忠的一大特点。
大诗人歌德曾把批评分成两种:一种毁灭性的批评和一种建设性的批评。在歌德看来,做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并不容易。他必须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准确把握时代精神及与作者感同身受的能力、高超的艺术禀赋、正确的判断力于一身。而在某种程度上,张志忠已经以他所走过的道路,展现了“建设性批评”在实践中的多种路向、多种可能性以及在当代所能触及的高度与境界。最为重要的是,他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工作,无一不是出于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关切与热心。因此,谢尚发在2017年《当代文坛》的访谈中,将他称为“当代文坛的守望者”,无疑是非常恰当的。
注释:
张炯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47页。
鲁枢元、刘锋杰:《新时期40年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史》,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88页。
於可训:《於可训文集》(第5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25页。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佘 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