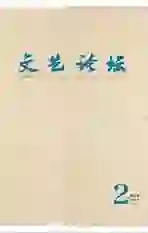青年亚文化形象、双向身份认同与解域化主体性
2021-07-20李雨谏
摘 要:近年来,《头号玩家》《勇敢者游戏》等影片的热映再次带动关于影游融合类电影的探讨。文章基于电影与游戏融合的真人电影作品,首先分析其中的电脑极客、游戏玩家及其虚拟形象的视觉呈现与叙事想象,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对人物与化身的双向身份认同论述、总结这种人物形象所产生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而探讨背后所呈现的主体性问题,指出这种新艺术想象不仅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实践,更是基于数字社会与媒介生态融合中所产生的新主体性呈现。
关键词:影游融合;亚文化;身份认同;主体性
对于学术研究来说,电影与视频游戏的融合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当《电子世界争霸战》在1982年上映时,它很快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在随后的学术研究中被认为是电影游戏化的首个关键点。此后,近四十年的时间里,电影逐渐展现出对视频游戏及其相关技术的特殊关注,而与视频游戏技术一同成长起来的电影专业人士,也逐渐在创作中使用许多游戏理念和特质,有学者指出视频游戏是导致新一代“影像制造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正在创造“非线性、新兴的(emergent)和可扩展的(extensible)”①电影,也就是说新一代影像创作者与作品都和计算机、数字文化有着不可切割的关联。
沿着汉森所提及的研究方向,我们可以将电影与游戏融合所形成的新电影形态、新电影现象作为切入点,关注其中的亚文化人物想象(与计算机有关的极客、游戏玩家与虚拟角色等)及其背后的文化征候(与数字媒介理论相关的德勒兹理论等)。综合国内目前的学术研究来看,对此类人物形象的研究尚属起步,较为重要的论述有黄鸣奋的《从反文化、救世主到安全专家:科幻电影的黑客想象》、陈旭光的《论影游融合的想象力新美学与想象力消费》等文,分别专注黑客想象问题以及影游融合类电影中的想象力消费问题,很好地为研究此类人物形象提供一定程度上的研究基础和理论支撑,尤其是后者在《论互联网时代电影的想象力消费》一文中,将影游融合类电影进行四种分类②,并指出此类电影满足兼有观众与玩家双重身份的群体,体现他们对虚拟现实和拟像世界的想象力向往和文化消费诉求。
在影游融合类电影中,我们往往会看到主人公以游戏玩家(如《头号玩家》、《阿瓦隆》《勇敢者游戏》系列等)、电脑极客(《电子世界争霸战》《创:战纪》等)等人物形象出现在故事中,并且凭借自己的各种虚拟化身在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实现一种游牧式的生存状态。虚拟角色、电脑极客和游戏玩家这三种人物想象在当下媒介文化中处处可见。在当下大众文化的各个角落,人们能看到游戏虚拟角色的各种存在形态,从报刊杂志、商业广告代言到东京奥运会的马里奥登场,丰富各异的游戏虚拟角色已经借助不同的符号化再现成功侵入现实并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而电脑极客的出现是当下社会的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它融合宅男、码农等一系列当代社群元素,从广泛意义上,它包括电脑黑客和技术宅男等,他们作为当代年轻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和存在方式,也早已小范围地存在于当代社会之中。与之相近的另一种青年亚文化想象物——游戏玩家包括参与视频游戏或各类游戏形态的游戏玩家,他们或者是经常玩视频游戏的一般用户使用者,比如主机游戏、PC的电脑用户,或者是某一类游戏比赛的参与者比喻,比如博弈论意义上的社会活动参与者等。正是源于人们日常媒介生活中的现实经验,影游融合类电影从各自不同的维度去再现这些人物形象,并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去讨论有关当代身份认同、主体性等多维度的政治学、哲学问题。
一 、作为青年亚文化想象的电脑极客和游戏玩家
在当代电影融合视频游戏的诸多电影作品里,与技术企业、政府、社会舆论相对立的极客、玩家成为数字文化中常见的主人公形象,这些主人公往往借助游戏世界中的虚拟角色代入自我认同,折射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媒介行为与网络生存状态。从社会文化的分类来看,我们可以将极客和玩家当作一种青年亚文化的典型代表,一如学者所指出的,他们也是跟随新兴数字媒介的发展而诞生出来的新文化想象,不仅对虚拟现实具有极高的情感认同,同时还以群体、社区等组织形态在媒介领域中占据着重要位置③。
1. 电脑极客与游戏玩家的虚拟想象
在影游融合类电影中,尤其是真人电影里,主人公往往具有两种身份形象,一种是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原貌,另一种则是虚拟游戏世界中的化身形态。前者通常以电脑极客、游戏玩家的身份出现,多半是尚未成熟的高中生、大学生等,或者是青年人;后者则往往是形态各异、千变万化的数码想象,有时会在外型上保持一致,有时则会完全改变主人公在现实世界中的形象。
就电脑极客来说,他们基本上就处于现实与虚拟空间二分的生活状态。现实中,他们智力超群,善于钻研计算机或沉迷视频游戏,但不爱社交,体力弱,见到女生羞涩,常常醉心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又或者是一些身手敏捷的黑客高手,运动能力出众同时擅长计算机操作。而在虚拟空间中,前者往往会化身为能力反差的游戏角色,获得不属于现实自身的差异化能力,比如《勇敢者游戏》中的勇石博士的英勇、强壮、无畏与现实呆男的胆小、局促、犹豫便形成反差,从而通过反差式人物成长去塑造人物命运走向;又比如《头号玩家》,现实中的艾奇是一个居住在拖车中的黑人女子,但游戏里却是一个拥有修理厂的半人/半机械生物。此外,影游融合类电影中的电脑极客也会在视频游戏空间内保留、延续自己的长项,使得這些长项能够帮助主角实现叙事目标、赢得游戏胜利,比如《创战纪》里,作为非程序创造者的弗林儿子,正是他的出众运动能力帮助他能够突破光盘大战,一度在摩托大战中赢得先机;又比如《天地逃生》中的少年操作员,其出色的战斗意识与游戏世界中的男主人公能力进行结合,不断逃脱死亡陷阱并赢得生死比赛。无论现实与游戏空间是否存在形象反差,但这些电脑极客在现实生活中基本上都是失意者或是一些边缘人,他们要么睡在狭小的空间中,没有任何现实生活中的朋友,要么就是浪荡子般不干正经事,要么就是宅在家里闭门玩游戏的社交恐惧者等。尽管如此,但这些极客们都在进入游戏世界后,不仅拯救游戏世界,打败游戏bug或幕后老大,还通过对于游戏世界的拯救完成现实人生的自我救赎。
作为狭义意义上的电脑极客,游戏玩家基本上是包含社会博弈在内的广义游戏参与者和视频游戏意义上的狭义参与者。对于竞争激烈的当代社会来说,生存博弈几乎是每一个社会人所必须参与的社会活动,通过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占据有利的社会位置,从而赢得生存空间和更好的发展前景。从这个角度来看,诸如《饥饿游戏》系列、《大逃生》系列、《移动迷宫》系列、《贝尔科实验》等影片都是借助虚构一种存在于未来社会中的游戏模式,展现出人类的生存意志和残酷竞争,这些影片中的主角都是带有社会隐喻游戏的参与者,也是这些社会游戏的赢家,同时还是打破社会隐喻游戏、掀起社会革命的发起者。当代电影对于这些游戏玩家的塑造重在突出他们既作为献祭者,也作为革命者的斯巴达克斯精神,因此,这些游戏玩家的实质是社会神话的当代转译者,往往在一开始只是作为游戏参与者的身份出现,在残酷竞争中生存下来后开始走向反对这类游戏制定者的道路,形成一种古典英雄式的人物弧光发展。就狭义的游戏玩家来说,他们只是作为视频游戏中的实际操作者,比如安德通过大屏幕的模拟战争显示来控制舰队的实际运动,《呆瓜的崛起》《游戏大玩家》等也都是坐在电脑前的普遍游戏玩家,他们对于游戏的直接胜利结果,往往也都是集中在表现自我救赎中,比如实现多年未完成的理想,或者克服性格弱点、走出游戏并拥抱更加真实的社会人生。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能够看到游戏虚拟角色是電脑极客、游戏玩家在虚拟现实、游戏世界中穿行的人物想象,它极大地遵从或延伸主人公对自己形象、能力等多方面的自由设计,也由此形成叙事模式上的主要套路:一、主人公通过虚拟角色的行动揭开秘密或阴谋,如《电子世界争霸战》《阿瓦隆》《头号玩家》等诸多影片都将现实世界与游戏世界进行二分,让主人公在其中进行来往穿越,以此去完成揭露阴谋、拯救世界等“游戏任务”;二、主人公自身作为广义上的社会游戏玩家,其游戏虚拟角色即是自身,并通过自身行动完成自我成长与救赎,这类影片有《歪小子斯科特对抗全世界》《我们都是小僵尸》《美少女特攻队》等,既是玩家也是游戏人物的主人公通过不停的闯关、斗争,最终在战斗中实现自我成长,明白自身的价值所在,或者解救他人,完成自我救赎;三、主人公在与虚拟想象的反差对比中完成逆向的自我成长,如《勇敢者游戏》《本X》等中弱不禁风的男主人公,游戏角色让他们最终能够面对自己的弱点与缺陷,从而完成自我成长或者获得新生。
2. 电脑极客与游戏玩家的视觉呈现与想象溯源
与游戏结合诞生出来的上述艺术想象,他们的基本视觉呈现主要表现为现实生活中的呆瓜(nerd)、生活输家(loser)/程序员造型,虚拟现实中的数字化造型,以及游戏世界中的生存家造型。现实生活中的呆瓜/程序员造型立足于对计算机或视频游戏极度着迷的现实人物视觉特点,从诸如New Balance球鞋、格子衬衫、眼镜等服装造型,到房间里的二次元海报、奇异人物手办等道具标示,再到身材瘦小与无运动能力的四肢,其整体形象几乎是在模仿日常生活中、社会流行语境中的呆瓜/程序员——害羞、古怪、没有性吸引力的刻板印象,区别于以往好莱坞商业电影中有着欲望之美的男性英雄或者女性英雄。在一般商业电影里,明星所化身的人物形象多表明一种以欲望为主、让观众可以去渴望的美感造型,如肌肉身材的硬朗帅气与前凸后翘的烈焰红唇,这些元素都成为世俗社会的审美标准,体现所有男性想得到以及所有女性想拥有的一切外在表象。但在诸如《头号玩家》《歪小子斯科特》《本X》等电影里,主人公往往是一副过于庸常和落伍的“日常”形象,让人失去了艺术加工所能达到的那种无法企及的形象美高度,失去人们想得到的或人们想成为的性欲美丽,并由此建立起一种去欲望化或者灭欲、去快感化的“自然”形象。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自然”“日常”往往并不是艺术史范畴下的自然与日常,它们并没有像安迪·沃霍尔那样重返日常美感的经验力量,而是借助电影的艺术加工完成一种质朴化的直接写实塑造,进而能够与另一极的虚拟形象形成强烈的对比、反差,铺垫这些“自然”“日常”的人物形象心中的“理想”形象。
在进入游戏世界后,现实世界中的主角往往需要化身为玩家角色(也被称为可玩角色),它是角色扮演游戏或视频游戏中的虚构角色及其虚拟身体,其动作直接由作为游戏玩家的主角们控制。不受玩家控制的角色称为非玩家角色(NPC),他们的动作通常由游戏规则和设计预先制定好。通常,视频游戏会提供一组玩家角色让人们进行选择,它们有着不同的能力、优势与弱点,也会让玩家去自己定义虚拟角色,以满足玩家对外形和能力的需求。出于电影叙事需要及游玩互动需要,绝大多数带有玩视频游戏情节的影片都将整个化身行为表现为近似角色扮演的方式,让主人公进入游戏所在的虚拟环境中,化身为生活在其中的游戏角色或是扮演自己制定的虚拟角色,比如《勇敢者游戏:丛林》里,四位高中生就分别选择四位游戏既定角色进行扮演;《头号玩家》里,韦德在绿洲里化身为自己定制好的虚拟形象;《电子世界争霸战》里,弗林进入主程序世界中则是化身具有人形化的代码。而像《战争游戏》《安德的游戏》等影片,主人公无须进行虚拟化身,但他仍然会在游戏中饰演某种角色,比如舰队指挥官、核弹控制权持有者等玩家角色。
而在诸多虚拟化身的视觉呈现里,数字化技术往往是最为常用的一种虚拟美学方式。在《电子世界争霸战》《头号玩家》《超世纪战神》等诸多影片中,真人演员都借助CGI技术完成人物形象的数字化再造,有的是通过电路、光点等元素来模拟单一程序单位的人形化,有的是通过数字装备来强化身材的科技感,有的则是完全脱离人的造型,成为半机械半生物/非人类生物/卡通生物等特殊数字形象。这些突出非人的视觉元素和造型元素,都在建构一种后人类式的未来美学价值——生命形式的非人类活力和人工化活力。在后人类语境中,当代生物技术所提供的机器人学、假体技术、神经科学和生物遗传技术,都进一步表明超人文主义和技术超验主义的人类未来图景,它们共同完成人类的生物纤维和结构转向,从而让身体能力和欲望快感降格,赋予近似永恒生命形态的人工化想象,以及非人类化的信息生命形态。
二、主角与化身:身份认同的双向交流
借助上述的艺术想象,我们能够看到影游融合类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具有一种与化身想象有关身份认同危机。视频游戏在介入电影文本之后,一些与身份认同有关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游戏玩家与虚拟化身之间的身份认同是统一的吗?如果统一,那么这种融合性的身份认同意味着什么?如果不统一,那么这样的身份认同又表明了什么?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关注身份认同这一视角在游戏领域中所产生的话语对象与话语场域。在数字实践(视频游戏可以被视为一种数字实践)所带来的新文化活动中,身份认同在早期一直围绕身份是如何在媒介使用的过程中构建,反过来媒介又如何重塑、变换身份认同的配置。而在游戏学方法介入后,特别是“ludic”(嬉戏)和“play”(游玩)这两个术语的引入,使得人们日渐关注文化活动中的角色扮演问题,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上升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游戏本体论”④视角,并结合媒介融合视角,更加关注身份在参与性文化的诸多文本中所扮演的传播意义和参与连接作用。本文所涉及的身份认同问题,主要指向经典的“媒介与身份”双重共振,探讨主人公借助另一维度上的自我化身,如何实现自我认同或者形成新的认同方向。
1. 化身的概念
在人类学意义上的诸多文化原型中,化身(Avatar)是中西方文化中共有的一种原型因子。在古希腊文明中,神与理念世界往往就是通過化身进入人间和现实世界;在希伯来文明中,耶和华就是通过耶稣化身为人,完成替世人受难的神圣使命;至于“化身”的英语来源,正是印度文明中印度教的术语Avatar,指的是无形的神灵可以通过任何形式来现身。在中国传统文学里,例子比比皆是:梁祝化蝶、《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都有许多化身的故事情节和文化内涵。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化身与变形有相近之处,但二者的指向不同——化身强调的是活在原本世界维度中的人或物,借用另一种身份形象来替代原本身份形象,从而在其他维度的世界中活动,比如日常生活中的人们通过化身进入互联网世界,位列人界之外的妖魔、佛仙借助化身在人间行走,等等。
数字时代中的化身有着特别指向,它意味着用户使用二维图像形象或三维虚拟人物形象来表明自身身份的一种行为,往往应用于虚拟世界。对于由计算机生成的虚拟世界来说,它是一个几乎可以等同于现实生活的平行世界,其终极目的是建构一种虚拟真实感,乃至最终从听觉到统觉的全方位可感世界。因此,交互性、沉浸感是虚拟世界所具有的突出特征,而人们通过化身进入其中除了获取信息、娱乐之外,更重要的是与其他虚拟生命完成互动,并尝试在数字真实感的世界中进行生活体验。在现代数字生活里,“Avatar”一词最早出现在1979年的一款名为《PLATO》的角色扮演电脑游戏中,随后在1985年被Richard Garriott用来指代游戏玩家在游戏《Ultima IV:Quest of the Avatar》里化身于屏幕中角色的行为。加里托希望玩家在虚拟世界中通过控制一个自我塑造的角色来进行活动,同时需要对这个角色负有道德责任,就如同在现实世界中一般。在1990年代的科幻小说里,Avatar/化身一词被用来具体指代网络虚拟世界中的虚拟人,由此催生人们经常将Avatar与虚拟世界化身进行具体指代关联。现如今,化身行为集中应用在游戏平台、媒介传播平台和社交平台,其中,游戏平台的化身应用较为成熟,尤其是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虚拟化身的非现实性在伦理道德层面上经常会遭遇质问,尤其是人们会吸收暴力游戏的化身经验,一方面在虚拟世界中推动暴力行为,另一方面也会给现实生活带来诸多影响,比如枪击、袭击事件等。
2. 影游融合类电影中的化身想象
对于本章所论述的“玩视频游戏”影片来说,化身意味着主角成为游戏中的虚拟角色,它不仅仅是整个叙事展开的前提基础,更重要的是,观众通过这一化身经验,完成对于主角的两重情感认同——现实人物/游戏玩家,这也是绝大多数有游戏经验的观众所面对着日常生活状态——人们在虚拟现实网络中或是以头像、或是以假名等方式与同是虚拟的亲朋好友、商品厂商等进行数字交互。实质上,我们可以将化身情结视为一种自我上帝化的尝试,或者一种自我英雄化的尝试,但无论如何,叙事行为所带来的风险代价往往都是由身为玩家的主角承担,两者往往有着一种责任连带性,比如《勇敢者游戏:丛林》中的受困玩家不能脱离游戏回到现实世界,游戏中的死亡预示着现实中的死亡;《超世纪战神》中被放出的魔王boss需要玩家去联合路西法将其封印;《创》系列里主角如果被击败,则会变成破碎数码模块且无法恢复人形,也会造成现实死亡;《阿瓦隆》里主人公如果输了就会输掉现实地位。当然,也会出现像《头号玩家》这样弱化责任连带的处理,主人公韦德在游戏世界的强势与现实世界的弱势形成对比,游戏死亡并不会影响现实人物的伦理危机。
基于影片中主人公与化身之间的关系,可以整理出这样两种身份模式:一、成长与救赎,主人公在能力上弱于化身;二、置换与同化,主人公大抵等同于化身。
第一种身份模式包含两种身份认同方式:第一是化身为拯救者,或正或反地推动主人公实现个人成长,最终通过离开虚拟化身解决身份认同,构建出现实世界中的人类完整主体;第二是化身为救赎者,弥补自己无法完成的任务,最终离开物理身体成为虚拟化身。最后,现实人物与游戏化身的双重身份两者互不影响,彼此并不分离。在《勇敢者游戏》里,四位现实生活中各有缺点的主人公在尤曼吉游戏里分别化身为弥补自身原本性格、能力缺陷的游戏角色,缺乏勇气和身材的男一号成为兼顾勇气和力量的勇石教授。此后,在游戏历程中,男一号所化身的勇石教授在一次次行动中激发男一号心中未曾有过的意志品质,并在回到现实生活后勇于面对爱情和友情。影片《超世纪战神》则是另一种身份认同方向,它通过重生来强化这种人物成长模式——作为游戏反面角色魔王的发明者夏卡,在被魔王杀害后,重生并附身于游戏正面角色GOne,不仅获得超现实数倍的能力,同时也转化为虚拟人物来延续自己的存在,并最终击败魔王完成自我救赎。
第二种身份模式中,主人公与化身并没有实际上的巨大差异,化身是主人公在虚拟现实中的行动代表,两者趋于同化或置换,显示出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技术控制论社会中的多重身份趋于统一叠合。《头号玩家》中,尽管韦德/帕西法尔在游戏内外具有相当大的身体差异,但最终通过通关和财富占有合二为一,既是绿洲系统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运营者、股东,也是绿洲系统在游戏世界中的通关第一人。与《头号玩家》不同,《感官游戏》将玩家与化身進行重合,并有意模糊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界,使得人们无法得知主人公是否最终走出游戏世界,这般带有未来预言化情节处理的背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表述现实与虚拟重叠之后的身份认同危机问题。
3. 化身与自我认同方向
在吸收上述游戏学的身份认同视角后,视频游戏影响下的电影创作在身份认同问题上首先围绕虚拟自我形象的自我认同。自我认同是指“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⑤。拥有完整稳定的自我认同感的个体,能够反思性地掌握其个人经历与生活的连续性,并能够与他人良好地沟通,甚至确立亲密关系。此个体也能建立自我保护区域,以在日常生活中去除掉那些威胁到自我认同完整性的因素。最后,个体能够接受完整性,并作为有价值的事物延续下去。与此相反,身份认同危机则是指个体感受不到自我的完整性,无法从生活的连贯性中充分唤醒自我主体意识,并为身份焦虑所累。
在游戏学的视角中,视频游戏所提供的身份认同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带有超越性质的,因为它们能够让玩家在一定程度上制定或实践其身份行为,“玩家并不认为游戏角色是一个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社会实体,而是体验自己与游戏主角的融合”⑥,这就超越目前其他媒介通过屏幕形象所提供的暂时性想象。这一点在许多电影作品中都有所表现,如《黑欲天堂》中将男主角与神秘女子的感情塑造通过现实与游戏来共同完成,两人都保持着化身与现实的身份融合;《超世纪战神》中的程序员父亲在肉身死亡后,通过程序再造完成自己不仅守卫人类社会,更守护自己家庭的身份责任。
除了身份融合,在《头号玩家》《勇敢者游戏2》等影片中,部分角色会选择进入虚拟世界(游戏世界、想象世界或者记忆世界)去获得生存体验,不愿意活在现实困境或者黑暗的生存现状中,甚至在最后成为游戏世界中的角色而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永生。这种方向上的身份认同正是当下社会语境中所反复警示的危机所在,即人们舍弃现实世界,沉醉于虚拟世界。在影片里,这样的人物命运走向往往会在一开始就给人物在精神或者身体上设置苦难创伤,让他们在极度失落的现实境遇中无法认同作为人的身份认同,转而只能投向看似更具有“人性”选择的信息生命形态,完成叙事上从人变成“非人”的身份认同轨迹。这一点在《阿瓦隆》的结尾处得到充分隐喻,对于许多人来说,与其活在废墟般的现实世界,不如活在多彩的虚拟世界。
而在另外一些电影里,游戏玩家或电脑极客对数字化身的认同则并不强调这种身份的融合,反而是通过虚拟化身所提供的游戏经历,明白化身与自我是两种具有相似性但更具有差异性的存在,或是认同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成长,或是接受现实生活中的固有坚持,如:《勇敢者游戏》中的四位主人公通过与自身能力、气质、性格反差的化身角色,最终在回到现实环境后成为更好的自我;《阿瓦隆》则借助女主在结尾处选择回归颓败现实的举动,表明人类在虚拟现实与虚拟化身的未来中存在的一种“保守”方向,不去选择拥抱数字未来,而是认同自我在现实环境的生存现状,表现出带有普遍社会教育意义的艺术表达。
三、一种解域化的主体性:基于德勒兹理论的考察
由此,无论是融合、舍弃还是回归,视频游戏及其所代表的虚拟现实为电影中的人物身份认同所提供身份建构讲述,其背后反映着玩家与电子拷贝之间的张力关系,这独特地表明一种基于数字社会、资本主义生产与媒介生态结合所产生的新型主体性形态。
在以游戏玩家和电脑极客为主体的影片里,自我身份分裂为化身与真实自我的两重性或多样化,这不仅是电影创作所展现出的社会想象,更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当代消费文化生产中所提供的一种真实感觉。尽管已经进入信息传播技术和媒介生态结合的数字化资本生产阶段,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概述依旧有效:“所有固定的、速冻的关系,以及他们古老而可敬的偏见和意见,都被扫除了,所有新形成的东西在可以僵化之前就变得陈旧了。所有的东西都融化在空气中……”⑦据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一种无止境的动态趋势,使得所有既定“身份”都变得破碎,从传统的信仰体系和意义结构到地理领土转换,从大规模的人口动荡到不断产生和推广“新的和改良的产品”,资本主义为利益驱动被认为是引起这些转变的原因。
可以说,马克思预言式的观点本质直指资本主义在各种领域中完成对个人主体身份的破坏,而其在电影作品的艺术想象中也回应着这种观点,无论是《生化危机》系列、《古墓丽影》系列,还是《电子世界争霸战》《邪恶电玩帝国》《头号玩家》,这些电影都将掌握媒介技术的资本家描述为故事世界的幕后黑手,他们都想通过新技术所生产出来的消费商品或是掌握新科技的社会应用来控制人类社会的具体运作,从而最大限度地瓦解媒介社会所提供的参与性民主和数字信息所赋予的个体生产可能。
在德勒兹与瓜塔里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说显示出一种根本的“精神分裂”倾向,其特征是持续地打碎既定身份,解散既定规范并实现领土转化——被称之为“解码”和“解域化”。这种倾向构成“精神分裂过程”,“纯粹精神分裂的解域化过程”。重要的是,资本主义虽然打破了所有现存身份,但立即强加了一种“新”身份,即以资本形象塑造的身份,并用资本形象去重新认同所有东西。这种倾向(“再域化”“重新编码”和“公理化”)不能被看作区别于资本主义打碎既定身份的倾向,因为“区分解域化和再域化可能几乎是不可能的,它们相互缠绕,或者就像同一过程的相反面向”⑧。正如德勒兹所看到的那样,“除了资本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一切都是理性的”⑨。事实上,资本主义“是疯狂的,从一端到另一端,从一开始”,这种疯狂可以看作是“它合理性的病态特征:完全不是一种虚假的合理性,而是这种病态、强度的真实合理性”⑩,并且,这种合理性被认为会导致更大范围的“剥削”“恐怖”和“残酷”,它的无情逻辑、发疯理性会吸收和驱使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追求更高的效率,永远更新利益。对德勒兹和加塔里来说,资本主义对其欲望的偏执压抑是无情的;对它的成员来说,它警告道:“尽管原理只是为你而创造,但我们一直为你在系统的拓展范围内找到一个位置。”与此相反,精神分裂分析参与到不间断的全部领土破坏中,取消任何既定身份概念、本质特征、基础或真实存在,为了去确认生成的生产过程,并对其起作用,为了去“从存在物中释放欲望,因此它能够自由地进入生成中”。然而更重要的是,德勒兹和瓜塔里不仅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取消所有的领土化,并获得一种“绝对的解域化”,而且还认为领土化对于精神分裂分析的积极或肯定的任务是必需的。如他们所言:“在不借助领土回路的情况下,精神分裂分析患者的散步或游弋甚至也不能影响伟大的解域化。”
参照这种观点,电脑极客与游戏玩家在电影作品中所持续表现的便是一种既定的身份不断解域与再域,他们在虚拟游戏世界中获得无器官身体的化身形象,然后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打破无器官身体,重新获取现实中的身体存在,正是在整个持续分裂的过程中,主人公在这种二重结构中完成自我意识的觉醒,形成一种解域化的主体性表达。在电影《安德的游戏》中,主人公安德就是通过心理测试游戏将自身解域为一只老鼠,并跟随着老鼠的通關冒险,找到虫后所隐藏的最终线索,在得知现实真相后,拒绝一种被管理者所赋予的胜利者主体性,并随后打破人虫二元对立的话语场域,带着幼虫去寻找一种新生的主体性。近似的表达也出现在影片《源代码》中,史蒂文斯上尉一次次地在技术应用中解码自身存在,但纵使获得不属于自己的无器官身体,他仍然在技术控制者的管理中完成自我觉醒,并实现永恒生命形态。由此,持续分裂的艺术形象的这种解域化主体性构建不仅是电影作品中主人公的艺术想象,更是当代现实社会中人类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进一步,按照德勒兹们的论述,解域化所带来的主体性是“一个潜在革命、解放的流量”,既作为“过度编码的自由形式和过度投资的性欲”,也作为“生产和反生产的内在系统(精神分裂化)”与“资本主义巨大精神分裂能量的生产”——这在影片《本X》《头号玩家》等影片中得到充分表现。在《本X》中,本的幻觉世界中一直存在着视频游戏的窗口编码形式(前面章节已经有所论述),也存在着他过度投入感情的一位女性形象——她一开始源于本在游戏世界中对一位女性虚拟角色的拯救,然后以具体外形出现在本面前,并与本一直进行幻觉对话。对于本来说,这些过载的欲望涌动并不是负面的,而是在积极创造和推动本,使他成为瓜塔里案例中那位通过艺术创造来重塑自己主体性的病例再现——设计一场自己的死亡游戏并且欺骗周围玩弄、轻视他的人,并带有隐喻性地呈现消除分裂状态的霸权反抗与精神分裂治愈主体性的创造性功能。如果说影片《本X》侧重于表现精神分裂主体性在个体内部的运作,那么《头号玩家》则展示出精神分裂主体性在个体外部的运作方式。作为新兴资本代表的绿洲游戏在影片开头就接管混乱社会的控制管理,人们纷纷进入这款游戏去寻求新的虚拟身份认同,但这种虚拟身份是绿洲背后资本所强加的一种新身份,其实质也是资本化的——影片将其表现为死亡后的金币状态,这便是德勒兹式的资本主义精神分裂隐喻,绿洲分解了所有现存的身份,但它立即以“商品”或“金币”的形式重构一切,从而生成关于主体身份的生产与反生产关系。更进一步,作为资本源头的绿洲系统通过寻宝的方式寻找新的管理主体,使得韦德与帕西法尔所构成的精神分裂主体状态再次解域化,他们在影片结尾处与同伴一起成为绿洲的资本掌控者与秩序管理者——这便是德勒兹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症理论目标,打破“权力的束缚,将研究带入新的集体主体性和人类的革命性愈合中”。值得注意的是,像《头号玩家》这般的精神分裂主体性在社会层面与个体层面的运作方式,也出现在《饥饿游戏》《移动迷宫》等影片中,主角们纷纷进入各自的游戏世界中,成为上层社会的祭品或试验品,并在赢得游戏或达成游戏目标后转化为革命者,成为固有社会的秩序挑战者。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主体性表述中,影游融合类电影的诸多人物塑造满足着身兼玩家/观众双重身份的人们的情感诉求,也贴合着他们对于当代社会文化与当下电影创作相结合的想象力消费。
如前所述,本文初步完成对影游融合类电影中的人物分析,并在一定程度上阐述其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同时也引申出如下一些可以深入探讨的维度与视角,比如结合影游融合类电影中的虚拟现实世界,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种叙事逻辑:作为极客与玩家的主人公们都需要最终脱离虚拟现实空间,回归现实世界,收获友情、亲情、爱情乃至自我成长、重生。在这种略带保守价值的现实关怀里,虚拟现实成为社会价值表述的他者,它外在的数字吸引力与内在的价值批判形成一股张力,使得电影中这种虚拟质感和娱乐性越是加强,故事的价值引导和主人公的命运走向则越是走向这种娱乐和虚拟的反面,并最终形成一种较为隐秘和贴合社会现实诉求的价值表述,即虚拟现实是毁灭真实和现实原则的“致命性策略”,任何理性主体的栖身之处都应该是糟糕的现实,而不是非现实。正是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中,影游融合类电影中的人物研究可以进一步围绕社会价值规训等话题去讨论这类影片对极客、玩家的媒介经验再造等话题,从而更加广泛地探讨影游融合类电影的内在文化征候。
注释:
Matt Hanson, The End of Celluloid: Film Futures in the Digital Age . RotoVision, 2004, P9.
②陈旭光:《论互联网时代电影的想象力消费》,《当代电影》2020年第1期。
③[美]大卫·帕金翰著,张建中译:《童年之死:在电子媒体时代成长的儿童》,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④Raessens, Playful identities or the ludification of culture. Games and Culture, 2006,Vol.1, P54.
⑤[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5页。
⑥Klimmt, Christoph, Dorothe?e Hefner, and Peter Vorderer. 2009. The video game experience as “true” identification: A theory of enjoyable alterations of players self-percep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19(4): 354.
⑦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6页。
⑧⑨⑩ Deleuze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and New York, 2004, P258, P262, P373, P315, P34, P589.
陈旭光、李雨谏:《论影游融合的想象力新美学与想象力消费》,《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年第1期。
*本文系国家重大招标课题“影视剧与游戏融合发展及审美趋势研究”(项目编号:18ZD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