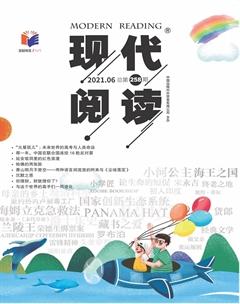从拒绝专业运动员到全面商业化的奥运会
2021-07-20
现代奥运肇始至今,不过125年;然而,因为4年一度的盛会众所瞩目,因此竞赛规则演化精致的速度,远快于法律缓慢的蜕变。
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尝言:人生如竞赛,而竞赛的规则有很多种。有的规则,是让生手也能上场一较短长;有些规则,是让运气的成分加重,增加竞赛过程的起伏;有些,则是让弱势的人也能参与,等等。
法学所探讨的法律,也是众多游戏规则之一。
现代奥运由1896年开始举办,至今不过一个多世纪,中间还因为战乱而中断。然而,奥运的竞赛规则,在某些方面,是人类社会最精致的规则之一。奥运规则的性质和变迁,对于法学研究有许多启示。
规则的变迁
奥运的项目烦琐,历年来竞赛规则有许多变化。有3个重要的规则变迁,和整个奥运有重大的相关。其中之一,已经尘埃落定——放弃对业余参赛的坚持;另外两者,还处在蜕变的过程里——辨认性别和禁药检测。
1.弃守业余
现代奥运伊始,强调运动精神,坚持参与者必须是业余身份。获得奖牌的选手,如果被查出曾经接受金钱,奖牌将被取消。最有名的例子之一,是十项金牌得主,美国的吉米·索普,被检举曾接受报酬参加半职业的竞赛,取消金牌,以致潦倒酗酒终生。
然而,随着体育和商业关系日益密切,厂商以各种方式,“赞助”明星运动员。业余的坚持,名存而实亡。另一方面,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以政府之力长期培训的运动员,早已不再是“业余”。再加上,各种职业球赛(美国的棒球和篮球、欧洲的足球),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商业利益可观。这些球员参加奥运,将带来数以亿计的观众和以百亿美元计的衍生利益。
在这些因素的交互运作之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终于决定,從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开始,放弃“业余参赛”的限制。奥运大门打开之后,观众人数、转播和广告收益等,果然大幅增加。和“业余时代”相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放弃业余限制,至少有两点启示:首先,在奥运早期,当各国多数的运动员都是业余身份时,要维持业余的资格限制,相对容易。可是,当职业选手(由政府或观众资助/支持)成为多数时,4年一度的奥运会要捍卫业余这种非主流价值,难度愈来愈大。其次,奥林匹克精神里,其实包括许多成分,业余身份,只是其中之一。其余的价值,诸如公平竞争、激发潜能、追求卓越等,也很重要。放弃其中之一,并不致损灭奥运精神。相反的,职业球员/选手加入后,奥运的娱乐性上升,全球民众参与程度增加,是其他价值的发扬和提升。
2.性别之辨
在股票市场里,不会对男女投资者作出区分;在超市车站戏院机场里,也不会。可是,奥运会自举办以来,一直是男女同场,但是分开竞技(除了混合项目之外)。
在观念上,区分男女争议不大——男女分开竞技,比较公平。然而,在实际操作上,随着科技的进展,这项工作反而愈来愈困难。
早期,区分男女的方式直接、粗糙而原始。在外观上,以喉结、胡须、胸部等直接判断。因为性别问题只针对女性参赛者,后来要求所有女性脱去衣物检查。这种做法,当然引发争议。而后,是根据染色体来区分,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男女的染色体结构,有明显的差别。
然而,地球上几十亿人口里,能在奥运场上竞技的人,只是极少数的人。这些人在体能方面,和绝大多数人不同。同样的道理,在这些人里,就是有极其特殊的染色体结构,是居于男女之间的模糊地带。要归入男性,又有女性的特征;反之,亦然。因此,即使援用最先进的生化科技,在这些极其少数的特殊个案里,都不能有一刀两断的判断。自2000年奥运会起,国际奥委会采取的最新做法是:针对有争议的个案,由专家委员会分别认定,而不是明定区分男女的标准。
3.禁药问题
某些(化学)物质,会影响运动员的表现,基于公平竞赛的原则,禁止使用,完全合情合理。然而,观念上简单的事,在操作上却并不容易。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国际奥委会目前的做法,是公布“禁用物质”以及和禁用物质“相关”的物质。检验的方式也愈趋严谨。然而,道高一尺,有些问题确实难解。
譬如,有些药品(如莫达非尼),是用来发挥医疗作用的。可是,这些物质也有副作用,对运动员的体能有增进的效果。因此,使用这些药物的人,必须先提出声明。经过查证,竞赛资格和成绩都有效;如果事先不声明,事后验出,将取消成绩。问题的微妙处,就在于某些药品,在一般人口中施用的比例很低,可是,在奥运选手里,施用的比例却远高于普通人施用的比例。那么,如果其中有些人确实是“造假”——假借医疗理由达到增强体能的目的——如何区分?或者,这些奥运选手,本来就是人口结构中的特殊群体,比例高于一般人口无可厚非?
由此也可见,高举公平竞争的目标,当然众议佥同。可是,要实现到何种“程度”,却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经济分析
由经济分析的角度,奥运规则具有怎样的意义?
经济分析里,探讨行为者(个人、家庭、厂商)时,通常会明确地界定行为者的目标函数。消费者,通常追求效用最大;厂商,通常追求利润最大;政策规划者,往往追求社会福利最大。
在最高的层次上,奥运会的目标是追求“运动精神”,同时追求“更快、更高、更强”。而后,随着职业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衍生的商业活动和利益,奥运的目标也掺有其他的成分,譬如,主办国借机展现国威、刺激经济;奥委会则是维持世界体坛共主、独霸的地位,享受垄断者的荣宠和优渥!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在奥运竞赛项目这个层级,“公平”是重要的目标函数,游戏规则的设定和调整,都是试图使竞赛更为公平。两个例子,可以稍稍反映。对于花式溜冰、体操、水上芭蕾等,由一群裁判各自打分,再集体加总。为了过滤掉偏心和“爱国裁判”等因素,最高分和最低分略去不计。还有,跆拳道项目,4个裁判分坐比赛场地的4个角落;选手击中对方得分,必须有3位(及以上)的裁判,在1秒钟之内同时按按钮,才算有效。毫无疑问,奥运竞赛对于“公平”的毫厘计较,和法律对于“正义”的追求,有许多相通、可以彼此借鉴之处。
不过,即使“公平”是奥运规则的重要目标之一,还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譬如,男女分开竞技,是为了公平;跆拳、拳击、举重、柔道等,依体重分级,也是为了公平。可是,为什么田径(特别是短跑、跳高等),不依选手的身高分级竞赛?为什么三铁(铅球、铁饼、标枪),不依体重或身高分级?
在21世纪初的今天,奥运的发展与推行除了各国政府之外,主要是由各种职业竞技组织(足球、篮球、桌球、乒乓、田径、自行车、高尔夫等等)支持。职业联盟,又由相关的产业(衍生产品、转播、广告代言等等)所支撑。市场经济,可以说已经成为奥运最主要的支持力量。当然,这意味着利弊掺杂。一方面,选手的待遇收入提升;器具、设备、训练等条件,大幅改善;运动员(和衍生行业),已经成为像演员一般的一个行业。另一方面,商业考虑和专业化的发展之下,奥运(和体育竞赛)已经愈来愈像另一个演艺事业。这种情态和奥运早期以“竞赛”为主的理念,在性质上显然有很大的差别。科技的突飞猛进,也给奥运和奥运规则带来重大的影响。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各地经济蓬勃发展,战乱威胁相对减少;因此,消费品的市场大幅扩充,民众所得上升之后,自然增加对娱乐的需求。各种职业联赛,提供民众一年四季的娱乐。4年一度的奥运,和常年进行的职业赛事之间,刚好是互补品和替代品;而且,彼此鱼帮水,水帮鱼,互蒙其利。推动时代巨轮的主要驱动力,是市场和经济活动;对奥运和奥运规则的变迁轨迹,也是如此。
奥运和法学
由经济分析的角度着眼,奥运规则和法学存在如下关联:
1.公平和正义
毫无问题,奥运规则的主要特性,是追求“公平”;公平,当然是一种特别的价值。同樣的,法律的主要特性之一,是追求“正义”;正义,自然也是亘古以来人们追求的重要价值。
公平和正义之间,至少有两点可以提出,而由奥运的规则和演变上,更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点。首先,公平所强调的,通常主要是在过程,而不在结果。相形之下,正义所强调的,则往往是结果。以奥运会为例,公平是指在竞技时,彼此在起跑点上是公平的,竞赛的过程也是公平的,至于在终点,谁摘金谁夺银,并不是关注的重点。正义则不然。对于起跑点和过程,正义这个概念不直接相关,但是,对于终点的“结果”,却会评估是否合于“正义”。
其次,既然公平和正义都是价值,在追求时自然要作出价值判断,也就是要作出取舍。但是,因为公平强调过程,而正义强调结果,因此,两相对照,公平是比较中性的概念,没有明显的道德成分。结果是否合于正义,明显地需要借助相关的价值考虑,因此,正义的道德性成分,要浓厚清晰得多。这种对比,由奥运规则和一般法律(特别是刑法),可以清楚地感受得到。
相形之下,司法体系,无论是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都是在操作法律——正义的量尺。那么,法官们所操的量尺,比较像奥运会3种裁判规则的哪一种呢?形式上,司法体系的裁判,和3种竞技都有共同之处。基层法院里,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一位法官决定是非,像是跳高和撑竿跳;中级人民法院里,3位法官(或法官和人民陪审员)议决,好像是拳击赛;高级和最高人民法院里,合议庭由3到7人组成,又像是花式溜冰和体操的裁判。
2.实质和程序
奥运的竞赛项目,有些着重“质”,有些着重“量”。量的刻度,可以透过度量衡的仪器决定;质的刻度,透过人(裁判)的判断。
一旦对“量”的度量衡有争议,就表示涉及的是更根本的“质”的问题。这时候,既然不能在实质上处理,只好诉诸程序。奥运对性别的处理,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重要的体会。对于亿万人口中的极少数体能和天赋迥异于常人的、染色体结构极其特殊的奥运选手,奥委会的专家们经过长时间尝试,希望能找出明确有效的标准,以区分当事人的性别。然而,反复尝试之后,奥委会发现徒劳无功。最后(也就是现在)的做法是组成专家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考虑各种资料证据,再作出最终的判定。很明显,这是以“程序”的方式,处理棘手的“实质”问题。
对于法学而言,这当然有重要的启示:官司的真相未必能昭明,但是借着严谨可靠的“程序”,司法体系希望能够维持法律的有效运作。
3.规则和工具
奥运的竞赛规则,希望使竞赛更为公平,但是,除此之外,也含有其他的考虑,虽然着重的程度有大小之分。譬如,规则可以使竞赛更为紧凑(乒乓球由一局21分,改为一局11分),对选手更为安全(拳击、跆拳、击剑等戴上护具),使观赏娱乐性更高(沙滩排球和水上芭蕾等),使参赛者范围扩大(“刀锋战士”等)。规则的调整,发挥了不同的功能,希望发挥或达成某种目标,或实现某种价值。
由此可见,在性质上,奥运规则是一种“工具”,是有功能性的内涵。就近取譬,对法律也有许多解读。“法律是艺术”“法律是国家暴力”“法律即生活”等不一而足。然而,“法律即规则”无疑是很有说服力的一种阐释。结合前面这两者,就得到对法律较完整的认知:法律即规则,规则即工具!还有前面提到,公平和正义这两个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抽象来看,就是“概念即工具”——借着运用不同的概念,希望发挥某种作用,实现某种价值。
这3点体会——法律即规则;规则即工具;概念也是工具——要直接由法律条文(法学)归纳提炼,并不容易。然而,借着奥运规则本身和奥运规则的变迁,反而比较容易中性、客观、不带道德情操地烘托出这3点智识上的结晶。由奥运规则到法学研究,确实可以带来许多启示。
总而言之,奥运规则追求的是公平竞赛,法律追求的是实现正义;公平重视过程,而正义重视结果。奥运的竞赛项目,有些着重“质”,有些着重“量”。“量”的多少高低,可以借助度量衡的仪器;一旦对“量”和“质”有争议,就可以透过“程序”来处理量和质的“实质”问题。无论是奥运规则还是规则的变迁,对法学而言,都反映出“规则即工具,概念也是工具”。
(摘自东方出版社《完美的正义——熊秉元谈法律经济学》.作者:熊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