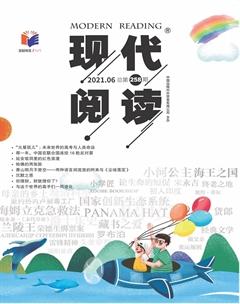青山明月不曾空
2021-07-20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新的文化整合中,呈现了自己新的文化特质。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文学回到了自己文化的流脉中,从自己民族的文化视角、文化态度和民族生活加以描绘,从中折射出民族理想和品格,一扫过去小说中凌空高蹈的口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9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代》选发了一部分。我们是这样宣传《尘埃落定》的:
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儿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
小说故事精彩、曲折、动人,以饱含激情的笔墨、超然物外的审视目光,展示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神秘。
《尘埃落定》通过对民俗生活的深入把握,鲜明地表现康巴藏族的民族特点和文化特质,在对历史传奇生活的冷静超然的叙事中,将哲学意识融会其间,恰如陶渊明东篱采菊的悠然,又似佛教禅宗迦叶禅师的拈花一笑。羚羊挂角,诗意超然。哲理性与生命状态水乳交融!
《尘埃落定》因其文化内涵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荣获了茅盾文学奖。
根据《尘埃落定》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热播,并在当年金秋获电视剧金鹰奖。接着,阿来又应邀到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演讲。
阿来慢悠悠、从从容容地走上讲台,很轻松潇洒地对听众笑了笑,然后口若悬河地开始了他的演讲。令台下各国作家惊异的是,这位中国藏族小伙儿,对世界文学竟如此熟悉,那些经典的文学信手拈来,而且评价极见眼光。阿来最后说:“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从童年时代起,一个藏族人注定就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这种流浪。我想,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
读到《尘埃落定》的时候,我刚阅读了威廉·福克纳的作品不久,正在为后来我出版的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即人学》作准备。我发现,《尘埃落定》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交相辉映。比如,它们都讲述当时社会的转型,表达对故乡世界的乡愁与缅怀,都强调了岁月在传统文化衰败中的消解作用。同时,它们又都借用“傻子”来讲“非常态世界”的驳杂的故事。“约克纳帕塔法”世界,与阿坝藏区“嘉绒部族”世界,都渗透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并都以貌似愚笨的却是客观的形式来呈现复杂纷繁的外部世界。而阿来和福克纳的作品又各有特色。《喧哗与骚动》中的主人公班吉,作为叙述者,只有直白的记录,其叙述成为展现他人个性的舞台,没有个人情感和主观判断。《尘埃落定》的主人公“傻子”二少爷的叙述,像是梦,以“傻”作为自我保护,在权力斗争中找到生存空间,以大智若愚,牢牢掌控故事情节的发展。福克纳的作品,充满爱恨交织的张力,游走于对过去的批判和眷恋,并寻找解决之道。相对于福克纳,阿来始终以局外人示人。《尘埃落定》对传统的逝去,只透出淡淡的无奈的忧伤,笔调细腻,深沉地对逝去之物进行追思,对昔日之人进行缅怀。他只是通过二少爷的眼睛超然于时空物外来看待世事的纷争。阿来学习前辈,是为了超越。
认识阿来之前,便听人说阿来爱喝酒,且酒量惊人。他有时半个月粒米不沾,只喝啤酒,他说酒也是粮食。他常常从高原马尔康坐汽车,沿着险象环生的岷江走两天,毫无半点儿车马劳顿倦容地赶到成都,寻到文朋酒友,边喝酒,边摆“龙门阵”:谈他走进高原的收获,红四方面军过草原时被人遗忘的故事,他感兴趣的宗教,他考察地方政权的思考……
一次,阿来随一群本地作家,陪北京来的各文学期刊组稿编辑,去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海螺沟,爬了冰川,观了风景。当地好客的县委领导,调来几位酒中魁首,在欢迎酒会上摆开了阵势,非要灌倒这些文曲星不可。作家们在主人殷勤的款待下,仓促上阵,很悲壮地抵挡了几个来回,终于拱手告饶,败下阵来。唯一一直不显山露水的阿来,神情自若,慢悠悠地沉着应战。十多轮的推杯换盏之后,只见县委一干人马前仆后继地倒下去。海螺沟一战,阿来名声大震。从此,大凡各地文友、编辑到阿坝办笔会,总要拉上阿来。阿来血液里流淌着藏族康巴汉子的热血豪情,这腔热血和豪情,一直支撑着他在文学之路踽踽独行,并成了他小说的筋骨。他说,书与酒是他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书给他智慧,酒给他灵感和天马行空的想象、豪情。
关于阿来爱读书,我社的一位同仁告诉我,她风尘仆仆地赶到阿坝去看阿来的经历。当晚,阿来携妻挈儿搬到别处,把自己的小木楼让给她。清晨,她看到窗前的海棠花开得正艳,而屋里来不及收拾的书籍散落在窗台、地面、书桌上,大都是当下世界最深奥的有关文化、宗教、文学艺术方面的著作。人的脑袋里装满飘落不定的知识尘埃,学问就如同一柱光线,穿过那寂静而幽暗的空间,照见细小的微尘在飘浮,看到茫茫宇宙的星辰在运行。书是照亮人们前进的灯塔,让阿来在文学之路自由前行。
办笔会大都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出版社或杂志社花了不少钱,让作家们游山玩水,实则是一个索稿的温柔陷阱。作家们吃了,喝了,玩了,对不起各位作家大爷,请慷慨解囊,奉献大作吧。阿来从不拖欠文债,所交作品大多在刊物上頭条发表,最让大家受用的是,他交了作品、饮了酒之后,还要放声歌唱。听阿来那低沉、浑厚而又有些苍凉的歌声悠悠回荡在山谷里,早就有些微醺的作家、编辑,仿佛随着歌声到了他生长的阿坝藏乡……
1959年,阿来出生在四川大渡河上游,一个叫“四土”,很早以前由4个藏族土司管辖的地方。他1976年初中毕业,算是生不逢时,连上山下乡的荣幸都没捞到。好不容易恢复高考了,又因学历不够,怀才不遇地上了中专师范,毕业后当了民办教师,后又当诗人。阿来的老婆是个汉人,儿子的户口随母亲,也是汉族。有人劝阿来把儿子改为藏族,将来高考时有照顾,阿来不为所动,只是沉静一笑,在他眼里,汉藏是一家人,如同眼前的青山和绿水。
藏族农民的儿子阿来,偏偏自幼爱上文学,人们大惑不解。尤其让谁都搞不懂的是,阿来常常一个人徒步从阿坝走向远方,一走就是好几天。有时,在长满鲜花的草原上,阿来会与一群诗友铺上毯子,摆上酒肉,一边大快朵颐地吃喝,一边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或举杯对天,或长吟短叹。一片云彩飞来,洒下雨,他们赶紧收拾东西,再跑到只有蓝天白云的草场。远处悠闲的牧民,赶着牦牛,看惯了白云聚合流散,却怎么也弄不明白这群年轻人在干什么。
很少人知道,给阿来带来巨大声誉的《尘埃落定》出版时经历了多么艰辛的旅程。
《尘埃落定》完成之后,曾黯然而漫长地辗转了多家出版社,直到有一天我的那位女同事,到成都参加四川青年作家笔会第一次见到陌生的阿来,幸运之云才飘向了这位才华横溢、埋在深山人不知的阿来。
很多参加笔会的年轻作家,利用一切机会,接近由京城去的国家最大的出版社女编辑,向她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创作情况。但阿来只顾微笑着,默默地为大家搭帐篷、摆座位,聚餐时远远地一言不发,却认真听人谈笑。
直到笔会接近尾声,我的同事出于礼貌,找到阿来,问他最近在写什么。阿来说,没写什么,不过有一部连续被多家出版社退稿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话已说到这儿,我的同事一笑,说,拿给我看看吧。于是便有了轰动文坛的《尘埃落定》横空出世。幸运也同时落在这两位头上。当然,阿来的《尘埃落定》即便再次被埋没,总有一天也会傲然立于中国文学史。即便不是这位有双慧眼的编辑发现这一小说瑰宝,总会被另一位同样有双慧眼的编辑发现。
随着我们的阅读从极度兴奋最终归于释然和平静,你不能不由衷地惊叹,《尘埃落定》瑰丽而又神秘,且富有诗性之美。你同时会为阿来那出神入化,如流水无首无尾,似流星划破夜空,精灵般的语言天赋击节叫好。不可否认,阿来的《尘埃落定》从内容到技巧,都借鉴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阿来自己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文学……代表当然是福克纳”。如前面所说,《尘埃落定》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都书写当时的社会转型,表现对故乡世界的追思与缅怀,流露出浓郁的乡愁……
《尘埃落定》改变了阿来的命运。《尘埃落定》登上了世界文坛,已被翻译成近20种语言。仅英译本就有3种,其中一种版税就有15万美元之多。该书的电影版权先被中国香港购得,美国哥伦比亚公司也紧锣密鼓地筹备电影改编事宜。这些毫无疑问会给阿来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据说阿来曾对朋友开玩笑说:“真没想到,每天醒来就有钱挣。”
写作给阿来带来了声誉和财富,但阿来拒绝当专业作家,尽管他清楚,专职写作会让更多白花花的银子滚滚流入他的腰包。在阿来看来,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成名之后,阿来一直殚精竭虑地主编科普杂志《科幻世界》。自他接手以后,该杂志的发行量翻番增长。他还特地在《科幻世界》给自己开了一个融科学与文学为一体的专栏,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结集成《阿来科学随想》一书出版,发行量不俗。
创作无疑是快乐的,创造更是一种幸福,写作需要沉淀,文学需要距离。办刊物的同时,阿来积累的生活也在发酵。
自《尘埃落定》后,阿来又写了几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因为,写作已成为阿来生命的一部分。文学流浪将贯穿他的一生。他那张扬的生命力在电脑键盘上疯狂地跳跃。阿来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一双人性的眼睛、一个智慧的头脑、一个健康活泼的心灵,让他的小说有马尔克斯至大至美的境界,又服从昆德拉所说的那种游戏的召唤:在生活中挖掘,又巧妙地玩虚构游戏。
2018年,阿来的中篇小说《遥远的温泉》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他在获奖感言中说:“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以善的发心,以美的形式,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
是年,阿来还出版了多卷本长篇小说《机村史诗》,以挽歌式的笔致将记忆深处曾藏在大山里的机村风景,做了抒情化的描写,恢复了中国深远内陆少数族群赖以生存繁衍却在现代化进程中渐渐消逝了的、具有神性的一种风景。在阿来悲痛的充满怀念和敬畏的对往昔生活家园的回忆和凝视中,机村风景依旧如新,《机村史诗》被赋予极为丰富的意义。莽莽苍苍的风景仿佛凝固,成为一个隐而不彰的主题,思考的是过去,也是未来;是悲歌,也是史诗。《机村史诗》是一部尚未被深入开掘的文学宝藏。
2019年,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阿来的新作《云中记》。为此,有关方面组织了一次阿来与30个国家的汉学家关于“故事沟通世界”的对话活动。阿来多次参加中国作家与国外汉学家的对话活动,已能从容睿智地应对。他围绕新作《云中记》,以他惯有的幽默个性和博学的才华表示,在文学活动中,除了创作,他还是个“译者”。从文三十多年,他每次写作,都是一次翻译过程——作为一个在汉藏两个语系中流浪的作家,他从藏语到汉语、从方言到普通话,不断地转换、融合。
他说,很多讀者说我的作品中有一些普通话不常见的表达,比如“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此语在藏文中乃是一种祝福辞令。西藏多山,人生也一样,一生多歧路。这句话实际上是祝对方在世上万事一帆风顺。
在谈到西藏时,阿来说,不少人对这块不老圣土并不十分了解,其实“西藏并非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烟火人间,和其他地域一样。天堂是光明的,地狱是黑暗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从艰难中发现希望,哪怕世界艰难,也要写出美好,要去发现人性最伟大的地方”。
(摘自现代出版社《我们的8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文人》 作者:汪兆骞)
(图注:《尘埃落定》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