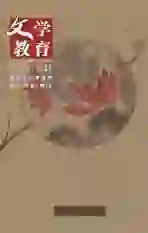电影《比利·巴德》的叙事策略及美学价值
2021-07-16聂庆娟
聂庆娟
关键词:《比利·巴德》 叙事策略 美学价值
麦尔维尔是19世纪美国文学史上一位独具魅力的作家,他的作品多数以航海为背景,通过描写异域风情、航海生活揭露现代文明的弊病,在世时因其作品主题庞杂、善于用典、语言艰涩、思想深奥而屡遭病垢。中篇小说《比利·巴德》是其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死后三十多年才被发现并出版。1962年英国导演彼得·乌斯蒂诺夫在E.M.福斯特版《比利·巴德》歌剧剧本的基础上,以20世纪60年代欧美各国风起云涌的权力运动和性解放运动为背景,将小说《比利·巴德》成功搬上荧屏,呈现出一场权力运动场域内上演的同性恋景观,以满足当时社会语境中目标受众对电影的观看期待。影片堪称一部乌斯蒂诺夫式的美学经典,并荣获第35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饰演比利·巴德的20岁英国年轻演员特伦斯·斯坦普首次出演就荣膺奥斯卡新人奖。
影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导演乌斯蒂诺夫运用高超的叙事策略成功实现了由小说到电影的转换。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小说与电影在呈现介质、叙事策略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依靠语言修辞塑造人物、呈现事件、表达意义;电影是视听的艺术,以影像和声音为媒介通过图像组合变换、声音等讲述故事、传递意义。叙事策略方面,小说主要采用叙事、描写、议论、抒情等方式,而电影主要采用蒙太奇、通过图像的拼接展开叙述。因此从小说到电影改编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叙事策略的重置与转换。在小说《比利·巴德》的电影改编中,导演主要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个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因素在叙事时空、叙事主题和叙事语言三方面进行了或置换、或重构,从而实现独特的叙事目的,表现独特的叙事意义和美学价值。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乌斯蒂诺夫如何在电影美学框架下通过叙事策略的重置与转换呈现影片独特的美学价值。
一.叙事时空的转换
小说与电影的差异表现在对时空的把握上。小说主要是时间艺术,具有历时性特征,作者主要借助文字表现时间进程和空间转换,而电影是时空综合艺术,通过画面的组合转换在时间的推移中展现空间,在空间流转中呈现时间。因而文学与电影的叙事时空方式截然不同,需要创作者进行艺术上的创新,绝不能对小说生搬硬套。
麦尔维尔的小说《比利·巴德》叙事情节简单,主要围绕比利和克莱加特的善恶冲突展开,时间跨度从1797年“诺尔大哗变”、特拉法加战役到若干年后维尔船长被炮弹击中不治身亡,中间经历了比利从“人权号”被强征到“战威号”,到被诬告并被绞死,穿插了两次麦尔维尔惯用的“离题”——长篇大论看似与主题无关的叙述。小说具有强烈的时间感,但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所——航行于茫茫大海的“战威号”的空间感却并不明显,电影的时空叙事很好地弥补了小说空间感的不足。镜头通过“战威号”的航行即空间的移动表现时间的变化。影片伊始,长镜头拍摄的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大海迅速将观众带入了故事发生的广阔空间,而对船头三个大字“战威号”的特写镜头一下子完成了小说需要长篇大论进行描叙的空间展示,呈现出电影叙事中强烈的空间感。镜头继续推进,“战威号”的整体面貌缓缓进入观众的视野,仿佛听到了1797年英法战争期间震耳欲聋的枪炮声,英国皇家海军战舰的雄伟气魄展露无遗。“战威号”属于英国皇家海军三级战列舰,装有74门大炮,伸出的炮筒像“七十四个美人正从战舰舷窗探出鼻子”。鼓起的风帆、排列整齐的舷窗、密密麻麻的绳索、上下结构的船舱,供舰上军官活动的后甲板、普通水兵活动的上下双层炮甲板、舰艉楼、拥挤不堪、空气污浊的水兵舱,值班嘹望的前桅楼等故事发生的主要空间通过几个短镜头轻松完成。这些长镜头、短镜头以及特写镜头的使用不仅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地点,而且营造了厚重的历史感,观众瞬间被拉回到18世纪英国海战的年代。
电影囿于时间长度有限,因此在叙事速度上与小说并不对等,在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过程中往往需要对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有选择性地压缩或凸显,以便突出重要人物和情节。比如小说中对“诺尔大哗变”的描述、对纳尔逊船长的描写以及对比利死后报纸的报道等历时性事件在电影中均被删掉。尽管这几起事件对小说主题及隐含的历史意义的呈现具有重要作用,但对于导演着力表现的同性恋主题和权力关系并无太大帮助,因而电影改编中遭到删除。相反,对于有助于表现电影主题的时空则得到了放大和凸显。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泼汤事件。小说中的泼汤事件重在表现克莱加特的邪恶,空间感不足,而影片中的特写镜头聚焦于克莱加特的双腿。随着他的双腿猛然前倾,一碗汤洒到了甲板上。镜头随即转向洒满汤的甲板,影片的空间感迅速得以表现,小说到电影转换过程中叙事时空也得到巧妙的置换和选择性地凸显。
二.叙事主题的重构
戴锦华认为,“每一次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不仅意味着一次再创造,而且意味着一次后结构主义意義上的‘重述。”小说的电影改编是一个艺术再生产过程,宏观上受制于时代、社会、历史等客观因素以及改编技术、电影创作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微观上与创作者生活经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此在电影改编过程中,改编者往往对原始素材进行重新整合,在保留原著中心事件的基础上删除从属事件以及不利于视觉呈现的事件,增加具有强烈戏剧冲突的情节,即对叙事主题进行重构,对小说主题做出新的阐释。
小说《比利·巴德》充分体现了麦尔维尔一以贯之的杂陈叙事。作家引经据典,将比利与克莱加特善恶冲突这个情节极简的故事分别置于历史、神话、圣经、同性恋四个框架下,呈现出多声部、多义性的文本空间,再加上大段离题犯戒与“离题”章节,虽然这些特质赋予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对电影改编却构成了困难。因此要改编成一部既叫好又卖座的影片势必需要导演在尊重原著基础上进行大胆的艺术创新,适当增删叙事情节,重构叙事主题。“电影不同于小说,影片出于商业目的,电影制片人需要很好地对时代的文化气候做出回应,将故事升级或者压缩”。而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的创新必然与创作者生活的时代背景和个人思想观念密不可分。20世纪60年代正值美国民权运动、性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并迅速波及欧洲国家。作为一名英国导演,乌斯蒂诺夫无法排除巨大的社会运动对个人的冲击,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与当时的社会运动相呼应,因而在影片中着力表现同性恋主题,即将比利与克莱加特的冲突置于权力运动和性解放运动的时代背景下,试图以模糊暖昧的方式呈现比利与克莱加特之间的善恶冲突,同时围绕善恶冲突展现“战威号”这个微型社会中的权力运作。
保琳高度评价电影《比利·巴德》主题的改编方式,认为“这是一部不错的电影,情节紧张,没有试图告诉观众一切……如果电影叙事线索不够明确的话就会出现小说中主题的含糊性。不同于小说营造的多义性空间,电影主题明确,突出历史语境下的同性恋这条主线,小说中的神话与圣经等主题遭到删除,这可以从影片中比比皆是的同性恋暗示得到印证。从“战威号”的上尉来到商船“人权号”征兵初见英俊水手比利时将“战威号”船舷探出的炮筒称呼为“美人”这样充满性挑逗的话语,到老水手丹斯克称呼比利为“宝贝儿”,再到克莱加特与比利数次对视,直至维尔船长也几乎难以控制对“英俊水手”的性欲感觉,把比利想象成为一个“人种的绝佳标本,他的裸体或许可以为表现堕落之前的年轻亚当摆个姿势呢”,可以看出,在全部由男性构成的水手世界中,海上生活的寂寥以及性压抑致使船员将英俊潇洒、脸蛋漂亮、像“红艳艳的雏菊”的漂亮水手比利想象为女性,从言语、视觉上满足个体的心理甚至生理需求。
影片的主要情节即比利与克莱加特之间的冲突始终伴随着多次对视和暖昧的眼神交流,仿佛要将影片导向同性恋。克莱加特初见比利时,一个细微的动作暴露了克莱加特的内心。邪恶的克莱加特正享受着水手被鞭打的快乐,猛然一抬头发现了站在对面的比利,先是向后一个踉跄,面露惊愕,也许克莱加特惊异于世间竟然有这样的美,继而目不转睛地盯着比利,他被比利深深的吸引。最能体现同性恋主题的情节是导演增加的核心一幕:比利与克莱加特夜间甲板上的“浪漫约会”。缓缓漂流的“战威号”、哗哗的海浪声、甲板上柔和的灯光、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微风吹拂着比利的头发,营造出浪漫的气氛。比利凑到克莱加特身边挑起话题,克莱加特问比利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俨然情人之间的谈话,比利回答道,“你在自嘲,……人们经常会做错事,像傻子一样,你一定也恨自己”。比利好像看穿了克莱加特的内心,他那无法控制的自我憎恨使他失去了爱人的能力,比利的到来唤醒了克莱加特内心的情感。克莱加特瞬间被软化了,脸上露出从未有过的笑容。比利趁机提议,“夜晚很安静,你一定很孤独,以后每个晚上不值班时我们都来甲板上碰面,我陪陪你”。“为什么不呢”,克莱加特脱口而出,然而他随即强迫自己清醒过来,他发现自己正掉入美与善的陷阱,厉声呵斥比利走开。比利的单纯与善良使克莱加特无法自已,他发现自己正慢慢爱上比利,内心对爱的渴望被唤醒,这让克莱加特感到害怕,因为无法控制的内在邪恶剥夺了他爱人与被爱的能力。为了自救,他只能选择将美与善或者能引起性欲的比利毁掉。第二天天刚亮克莱加特就开始诬告。盛怒之下的比利将克莱加特一拳击倒。死前一瞬间,克莱加特脸上露出了笑容。是为能够死在爱人的手下而感到高兴还是预见到自己的死亡能够杀死比利,和心爱的人一起死亡呢?导演将这个问题留给了观众,开启无限的遐想。
影片还关注了当时海军盛行的鞭刑以及海军战舰等级森严的制度,权力的运作与实施、上级对下级的规训与惩罚等主题,突出了深厚的的历史感。“战威号”俨然一个微型社会,不同等级的军官和水手在各种权力关系中监视与被监视、惩罚与被惩罚。全体水手在军官指挥下有条不紊地工作,各司其职,分批换班、值班、训练有素。他们就像一群被剥夺了尊严的犯人一样,只能服从,就像维尔船长对全体训话时所说的那样,“服从命令是最高的职责”。鞭刑可以称得上是海军军官最伟大的发明,他们通过对不服从命令者进行鞭打实施权力的控制,对水手进行规训和惩罚,使他们成为服从命令接受规训的劳动者。影片花大力气表现了鞭刑场面。违反纪律或者渎职的水手被绑在甲板中间的大炮上,克莱加特手持警棍监督,军官站在后甲板军官活动区域,高高在上俯视一切,普通水手围绕前甲板整齐地站成一圈。这里就像一个圆形监狱,有犯人,有行刑者,有狱警,还有官员,更有接受规训的普通大众。导演通过鞭刑突出表现了权力部门是如何控制水手,如何运用权力维护权威,如何将水手训练成为没有反抗意识、唯令是从的水兵。船长作为最高权力长官在审判比利时表面上作为目击者不参与审判,实质上却扮演了主审法官的角色,迫使其他三位陪审团成员按照自己的权力意志做出决断,为防止兵变、维护稳定,判处比利绞刑。
此外,影片对小说权力关系主题的呈现还体现在对小说泼汤事件的重构上。小说中比利不小心将汤洒在甲板上,克莱加特说,“干得好,但长的漂亮不如干的漂亮”,表达对美好事物的憎恨。但影片中克莱加特故意打翻比利手中的汤,主要目的是对不服从命令的水手詹金斯实施报复,要求詹金斯将洒落的汤舔干净,借此对其当众羞辱。影片借助泼汤事件表现了船舱这个微型社会下层空间中权力的实施与等级森严。同样克莱加特逼迫生病的詹金斯值班,导致詹金斯的死亡,并报复为正义挺身而出的水手肯深深体现了长官对水手的规训与惩罚,表现出下层社会普通水手生活的悲惨,深刻抨击了海军战舰上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和权力实施。
三.叙事语言的转变
小说用文字传递意义,表现主题,而电影则使用镜头,借助图像,声音,色彩、照明、服装传递。小说叙事具有明显的历时性,一个时间内只能讲述同一件事,读者的感知因而也具有历时性。电影用蒙太奇手法即画面的切换来表现时间的流动,因而需要借助空间的变换表现时间,展开叙事,因而电影的叙事具有时空共时性特征,银幕画面是電影语言的基本元素,图像、色彩、声音、照明、服装成为电影语汇的基本构成要素,摄影机的运动和不同镜头的组接切换产生的蒙太奇成为表现时空转换的主要手段。
影片《比利·巴德》最具特色之处是黑白屏幕的使用。彩色电影技术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现并且日趋成熟,但导演选择黑白屏幕呈现,既“有助于表现电影纪录片特征,又旨在强调人类遭遇的困境而非大海的美丽,同时更好地表现善恶之间的冲突”。电影以1797年英国大海战为背景,着力表现特殊历史和政治语境下人性善恶之间的冲突,黑白色调的使用赋予影片厚重的历史感。在黑白色调的衬托下,茫茫的大海显得更加阴暗,充满危机,为比利与克莱加特之间的冲突做了铺垫。一艘战舰孤独地在海上漂泊,也衬托出海上生活的单调乏味。更为重要的是,黑白色调的使用反衬出比利作为善与美的代表与克莱加特恶与丑的代表之间的冲突,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影片中恶的代表克莱加特总是一袭黑衣、黑帽、黑皮鞋,再配上帽檐压低半遮掩的脸,更让人捉摸不定、讳莫如深。相比之下,比利服装以浅色调为主,白色上衣、浅色裤子,配上一头浅黄色卷发以及一张明媚、漂亮的脸蛋,活力、阳光与善良的天性展露无遗。黑白色调的运用使比利与克莱加特在形象气质上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灯光的使用也有效传递出人物的内心活动和个性特征,主要体现在比利与克莱加特月光下甲板上“约会”的场景。灯光从克莱加特的背后打过去,照在比利天真灿烂的脸上,克莱加特背对灯光,处在阴影之中。比利窥探到克莱加特的自嘲,克莱加特感觉内心世界得到了理解,灯光适时地打在克莱加特舒展的脸上,表情变得柔和。当比利最终指出克莱加特的自我憎恨导致孤独并提出愿意在寂寥长夜陪伴克莱加特时,克莱加特的心好像被融化了,目光哀伤,表示夜晚太长太孤独,谈话是解决孤独寂寥的好办法时,这时灯光在克莱加特的脸上不停的闪烁,好像有意暗示克莱加特的顿悟。这时灯光突然昏暗,克莱加特的脸一下子陷入阴暗之中,清醒过来的克莱加特发现自己正掉人善的陷阱,随即原形毕露,表情狰狞。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灯光的闪烁变化映衬出克莱加特内心活动,侧面反映出克莱加特无可救药的邪恶。
除了色彩、图像、服装、灯光等叙事语言外,音乐的使用对于表现主题、烘托人物、推动情节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摄影机的移动以及镜头的变换也为烘托人物内心活动、表现冲突做了铺垫。例如长镜头用于表现奔流不息、汹涌澎湃的大海以及孤独的无法掌握命运的船只,短镜头则主要为特写镜头,着力表现人物的面部表情。长短镜头捕捉的若干场景通过蒙太奇手法拼接在一起,体现时空的变换和场景的变换,有效传递出影片的主题。
导演乌斯蒂诺夫根据麦尔维尔经典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比利·巴德》被评为1962年最优秀的影片。麦尔维尔的作品往往以晦涩难懂、主题庞杂、语言艰涩、充满哲思而著称,改编成既较好又叫座的电影非常困难。约翰·休斯顿1956年改编自麦尔维尔代表作《白鲸》的同名电影因完全忠实于原著而导致彻底失败就是有力的例证。休斯顿说,“我不想对小说进行阐释,我只想忠实于原著”。正是对原著的过度忠实导致电影沉闷乏味,惨遭失败。毕竟,电影与小说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乌斯蒂诺夫巧妙地规避了忠实为电影改编带来的弊端,在《比利·巴德》改编中依托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有效融入了个人对小说的理解,在叙事时空、叙事主题和叙事语言上进行了成功的冒险与尝试,呈现给观众一部人物形象丰满、符合时代特色的优秀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