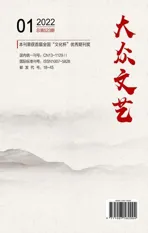历史的打碎与重构
——《我的帝王生涯》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2021-07-13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00)
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一批新历史主义小说作品在当代文坛兴起。《我的帝王生涯》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本,苏童以其特有的诗意神秘的文学语言,荒诞先锋的故事情节,践行着新历史主义的理念,构建出一个带有个人私密性质的虚构的历史文本。
一、历史的打碎
首先历史的打碎体现在将经典故事打碎重组上。《我的帝王生涯》中的朝代地点,人物形象,完全依赖作家的创造,无从考究。苏童在前言中说:“年代总是处于不详状态,人物似真似幻”“是按我喜欢的配方勾兑的故事”,这是强调了作品本身的虚构性。但是读者从中也不难发现一些熟悉的经典剧情:彭王后与蕙妃争宠将其所产胎儿换成白狐,完整上演了狸猫换太子的戏码;端文谋反篡位成功,端白流落民间最后出家,似乎是靖难之变的翻版;至于外敌入侵国破城荒则是诸多朝代的结局。少年为王、假传遗诏、后宫专权、伶人行刺、兄弟阋墙……这些在历史上常常上演的剧情在书中齐聚一堂,这一个个碎片化的小情节本就脱胎于各种正史野史,让整个故事显得亦真亦假。蕙妃沦为妓女让人联想起北齐成武帝的皇后胡氏;帝王端白沉湎于男女情爱时作词写诗所流露的文人气质极像词人皇帝李煜,从帝王沦为一介草民又有了末代皇帝溥仪的影子;起义失败的李义芝让人想起勇猛善战的李自成;忠心耿耿陪端白流浪赴死的宦官燕郎恰似陪崇祯赴死的王承恩。因此,纯虚构的文本并不意味着不能表现真实的历史,读者恰恰能从假的情节中读出真的历史。既然客观的解读无法达成,那么索性摒弃,全盘虚构,作品追求的并非事实的真实反映,而是历史本质的真实呈现,体现历史的文本性。
消解传统历史的崇高,同样可以打碎陈旧的史观。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历史小说中,作者往往宣扬忠孝节义与正统儒学,迎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而《我的帝王生涯》,则从消解王权崇高和正统儒学崇高打碎传统。
作品中“我”即端白是帝王,虽然拥有万人之上的尊贵地位,但是他却以自白的方式说:“我很敏感,我很残暴,我很贪玩,其实我还很幼稚”。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让读者无限贴近端白这个人物,得以窥探他的私密空间。他私生活中的性压抑与阳痿,他心理上反复无常的喜怒忧惧,他居此高位的身不由己——被人在嘴里塞上丝绢,双手被缚在龙椅上,或是被强行安排出驾西巡,打破了传统中高高在上的皇帝形象。王权的实际掌握者皇甫夫人和孟夫人,也是通过戏谑与荒诞的形式被消解了她们所代表的崇高。皇甫夫人霸道专横,转头就会扇孟夫人一耳光,或者是用紫檀木寿杖打人,孟夫人则大骂“老不死的东西,早死早好”,接着又是许多粗鄙下流的市井俚语,皇甫夫人气得浑身哆嗦,用寿杖捅着孟夫人的嘴。贵为太后与太皇太后,又掌控国家大权,却犹如市井泼妇一般叫嚣斗殴,不成体统,让人觉得荒谬可笑,颠倒错位。与王权相关的朝堂,在书中却写为,“与其听皇甫夫人和冯敖他们商讨田地税和兵役制,不如听郡王的一声响屁”,不再是惯常概念中秩序森然,谨言慎行的议政之所。王权被拿来玩笑,打破了其不可冒犯的凛然形象,使得传统历史中的崇高崩塌一地。在作品末尾,端白说道“黑豹龙冠的骗局蒙蔽了多少人的眼睛,曾经头戴龙冠的人如今已经逃离了那口古老的陷阱,而宫墙外的芸芸百姓却依然被黑豹龙冠欺骗着”,在封建社会人人顶礼膜拜唯其独尊的王权在作品中被贬为虚假的骗局,消解了王权自古而来的神圣与崇高。
正统儒学在书中的代表是《论语》一书。僧人觉空教“我”从小读《论语》,借其正统儒学来维护封建统治。在端白篡位时“我”手握这本《论语》,但是它所代表的儒学没有救作为落魄帝王的“我”,也没有挽救倾颓的国势。这本书几乎陪伴了“我”的一生,在作品最后,“我”用了无数个夜晚静读《论语》,有时觉得这本书包容了世间万物,有时却觉得一无所获。“包容世间万物”指的是它作为应世法则能够在封建体制这样的意识形态内起到一定作用,“一无所获”则是从更大的角度来说,跳出意识形态来看,面对历史的无理性无常性,《论语》所带表的正统儒学则显得渺小无力,那么它先前的崇高地位也就此消散了。
二、历史的重构
首先是故事的重构。《我的帝王生涯》将朝代史写为个人史。
作品摆脱传统史学的大局观,选用第一人称叙述中的体验视角,“我”即是历史的参与者,“我”在塑造历史的同时也被历史所塑造,因而构成一种内视角。帝王端白,即小说中的“我”,是整个故事的主角与中心,读者能够体验到端白的切身感受,所阅读到的故事也全部是透过了端白的主观滤镜。小说中夹杂了大量的心理描写,端白孩子气的幼稚独白让读者真切感受到他的情绪流动,“我不喜欢他们”“我一点儿都不快乐”,此时读者与端白和历史的距离拉到极近,种种细节都愈发丰富细腻,在跟随“我”的故事的推进过程中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代入感与亲切感。
这样的写作手法也同样使读者受限于他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端白在皇宫内无法看到外面的战争场面,读者所获知的也就是大臣在朝堂上上报的寥寥几语,端白沦为庶民在民间流浪,我们就彻底失去了端文作为新帝如何治国理政的信息。整个故事的时间轴同样是以端白的个人时间感知为依据的。在品州城内的微服私访令端白大开眼界印象深刻,因而描写所用篇幅较长,读者感受到叙事进度明显放慢,而端文率领叛军入侵的情节只用了数行带过,似乎是作为叙述者的端白不愿提及。因此读者所读到的文本是经过叙述者主观取舍后的结果,是叙述者想让我们看到的内容,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以此种新历史主义观念所创作的文本,不再像过去传统的历史故事一样,个个都力求贴近史实,最终导致千篇一律,而是选择在大历史下关注个人命运。
其次是历史观的重塑,“历史的空间可能就是一个布满岔路口和歧路的迷宫,偶然性、荒诞性和神秘性才是它真正的属性”,《我的帝王生涯》通过颠覆传统史观,重塑新的历史体验。
作品在呈现过程中借助荒诞情节等元素有意凸显一种虚构性,借以表现叙写的历史是一种文化产物,引导读者像阐释文学文本一样解读历史。例如端文头上莫名出现的“燮王”刺青,端白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老疯子孙信的宿命式寓言,端白与生俱来的走索天赋,都是非常理能解释的内容,风格呈现戏剧化。作者在叙写历史的时候不再是被动叙述,而是富有能动性地呈现,历史叙述是“语言凝聚、替换、象征化和某种贯穿着文本产生过程的二次修订的产物”,实现了以新方式阐述历史的可能。
同时,作品还着力表现历史的无常性与非理性,苏童自己说道“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做了皇帝,一个做了皇帝的人最终又成了杂耍艺人”,他本应当是改朝换代时最该死的人,而死亡的邀请却独独遗漏了他。历史的分配并非沿才授职,每个人分配到的角色都具有随机性,每个人的命运走向也不一定都能自己掌控,昏君端白被赶出王宫后成了走索王,而夺回王位的端文却被入侵的外敌烧死在宫中,历史本身的安排就体现出一种荒诞虚无之感。传统历史所宣扬的“把握历史规律,顺应历史潮流”在此被颠覆,历史的规律本身就是无可探求的,历史的潮流随时可能转向,所谓的顺应潮流不过是事后的回溯总结,身处历史洪流中的渺小个人更多地体会为一种无力感。端白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永远是被时代裹挟而走,渺小个人在命运齿轮的转动前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因此他说“害怕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漫长的黑豹龙冠之争终于结束,我们发现双方都是被历史愚弄了的受骗者”。这也是苏童针对人类命运面临的永恒困境所做出的的探寻。
历史的非线性与非进步性在作品中同样有所体现。非线性指的是,历史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线性演进,每个历史事件也不是由原因直接通向结果的单行线,历史事件的发生体现为一种偶然性。端文夺位后民间受灾是偶然,端白在流亡开始遭遇剪径也是偶然,但是在当时的境遇下则形成了必然的致命性打击。在这种不可掌控的偶然性中,个人只能悲叹“可怜,可怜的生死沉浮”。历史的非进步性是指历史并不一定是前进的,我们并不是在迈向更好地明天。看似更加具有王者风范的端文做了皇帝,仍然无法挽救燮国衰颓的命运,国力更加强大的彭国统治了这块土地,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因此改善,又迎来了与陈国、狄国的交战。废墟上建立起的不过是另一个燮国,等着下一个新彭国来将它毁灭。历史仿佛就是循环往复原地踏步,上演着重复的剧情,人类似乎只是在原地兜圈子,身处其中的我们处于某一阶段之时则会误以为在前进。
中国古代就有历史小说的传统,小说这种文学类型是基于历史发展起来的,应当说,中国的小说比任何其他地区都更加具有历史情结,因为他们本就依附历史而生。这使中国小说在追求真实性的同时忽略了小说本质所更加强调的虚构性。而在近代革命过程中,历史小说更多地包含一种权力话语,作为意识形态塑造的政治工具在革命中发挥宣传鼓动作用,以达到一种政治目的,此时对历史的书写已经不自觉地包含一种主观性,已有一种塑造历史的意味。到《我的帝王生涯》出世时已体现了较为成熟的新历史主义特点,以纯虚构的方式创造历史故事,是对传统史观的挑战与反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在表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虚无主义与不可知论的倾向,在解构意义与历史真实性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过于悲观的态度。“新历史小说试图避开历史本体来寻找人类,试图通过一种任意的主观解释来寻求人类价值,这未免使新历史小说的努力变成了自欺欺人的把戏。”如果消解了所有的意义,那么一切的存在都毫无价值。我们无法把握神秘的历史,那我们是否一切的作为都是徒劳,永远都是被动的非自由的存在?新历史主义实现了反叛,提出了问题,却未曾为我们指明道路,或者说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说,我们根本就无路可走。这未免失之偏颇。因此对于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及其背后的新历史主义观点,我们在解读时也应当抱有较为客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