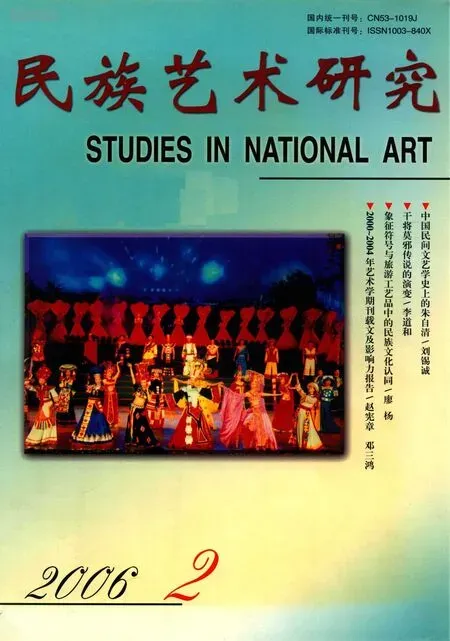中元节大理南村洞经谈演仪式的文化内涵与自我呈现
2021-07-12陈丽媛
陈丽媛
关于洞经音乐,许多学者对其做过研究。张兴荣所著的《云南洞经文化——儒释道三教的复合性文化》①张兴荣:《云南洞经文化——儒释道三教的复合性文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考证了云南洞经的历史源流、发展衍变、思想渊源及洞经乐曲、主要洞经会的基本情况等问题。尹懋铨、张启龙撰写的《云南洞经音乐》②尹懋铨、张启龙:《云南洞经音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概述了云南洞经音乐的文化背景、云南洞经会产生的历史源流等。陈复声的《昆明洞经音乐》③陈复声:《昆明洞经音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对昆明洞经音乐的渊源、衍变及发展、洞经音乐的类别、昆明洞经会及洞经人物的简况等做了详细地阐释。这三本著作对云南洞经音乐的概况考察得较为全面翔实,从中可以了解云南洞经音乐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底蕴。此外,一些学者侧重研究洞经会的组织形式和机构设置,还有一些学者重点讨论了洞经音乐如何传承与保护的问题。从关于洞经的学术成果可看出,学者们的研究对洞经音乐的历史源流、洞经音乐的类型、洞经组织等情况已经考察和记录得较为完善。然而从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理论视角来分析洞经谈演的文化含义的研究成果还有待提升。
一般来讲,洞经谈演仪式的过程呈现主要以洞经音乐为载体,所以洞经谈演的研究成果中,大多是从民族音乐学对仪式音乐的信仰、仪式行为、仪式音声的三维合一的信仰体系出发来研究洞经谈演仪式。比如,《大理洞经音乐的表演与记谱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④滕祯:《大理洞经音乐的表演与记谱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人民音乐》2013年第2期。一文从民族民间音乐学的研究视角,结合田野调查收集到的乐谱资料,对大理的洞经音乐在演奏和记谱中出现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云南个旧市大屯镇洞经音乐三首套曲分析》则通过对个旧市大屯镇洞经谈演的三首套曲的旋律结构的讨论,从中阐释出了“传统乐曲‘长大结构’类套曲的结构特点。”①张伯瑜:《云南个旧市大屯镇洞经音乐三首套曲分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与民族音乐学研究仪式音乐的理论视角不同,人类表演理论流派主要从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视角来研究仪式。人类表演理论的各个流派都有各自的观点,但他们所持观点有着共同的特征,即认为仪式是一个可以看作是文化表演或文化展演的行为过程,并强调用人类表演理论阐释角色扮演者在表演场景中的交流互动行为或者说仪式主体在仪式展演过程中如何呈现自我。仪式主体通过恰当的行为和技巧的展演,提升仪式的文化表演效果,从而在自我的呈现过程中揭示出隐喻在仪式表演背后的信仰的思想。
笔者试图在本文中运用人类表演学、表演人类学及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相关理论,将洞经谈演仪式置入一个仪式主体以行动者的符号互动身份来自我呈现的戏剧场景中,通过仪式核心要素呈现自我的特征分析,来解释大理南村洞经会在中元节举行的洞经谈演仪式的深层次文化内涵与文化意义。
一、中元节大理南村的洞经谈演仪式
洞经音乐在大理的历史源远流长,是大理地区岁时民俗中普遍流行的民间音乐。大理洞经乐的溯源,大理南村洞经会会员ZML②ZML:男,73岁,大理南村人。认为:“大理洞经古乐始于南诏国时期的宫廷音乐和祭祀音乐。兴盛于明、清两代,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儒释道三教的祭祀音乐,而完善于道家的道场,以演奏大洞仙经为主调,故称为洞经音乐。”
大理地区的洞经谈演融入了当地汉族、白族民众的民间信仰和习俗文化,并运用了诵、讽、唱、奏等民族音乐的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来体现其中的文化内涵。在中元节用谈演洞经的方式祭奠和超度祖先是大理地区从古沿袭至今的仪式传统,这种将音乐元素融入仪式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大理的民间信仰习俗中普遍存在。
2019年中元节,笔者对大理南村洞经会在本村本主庙中举行的中元节洞经谈演仪式进行了考察和调研。
(一)南村洞经会会员的职务分工
大理南村洞经会的洞经谈演仪式由南村洞经会会长ZWT③ZWT:男,76岁,大理南村人。主持。洞经谈演仪式的主要参与者有:①仪式主持者1名。由洞经会会长ZWT担任。②经生2名。其中1名经生由洞经会会长ZWT兼任,另1名经生由南村的洞经会会员WYI④WYI:男,68岁,大理南村人。担任。③司乐生若干名。司乐生即为洞经乐器演奏者,均为南村的洞经会会员。④司香生1名。当日仪式的司香生为南村洞经会会员XYG⑤XYG:男,63岁,大理南村人。。
(二)南村洞经会会员的谈演程序
1.布坛
洞经谈演仪式之前,南村的洞经会会员先要布设祭坛和经坛。
祭坛要布设本主祭坛、天地坛、祖先祭坛。洞经会会员先在南村本主庙大殿内的本主神像的祭坛上给本主献祭香炉、红烛及斋饭、水果、茶水等祭品。另外,在大殿正门外的台槛上布置了一座天地坛,在大殿外的南侧台槛上还布置了一座南村已故村民的祭坛,并在这座祖先祭坛和天地坛上供奉与本主祭坛上同样的祭品。
经坛的布设紧靠大殿内本主祭坛,在祭坛前的左右两边摆放平行的两排桌椅。经坛上摆放经书和引磬、木鱼、碰铃、大镲、小镲等法器,经书和法器都是经生在谈经时交替使用的物件。其他司乐生则围坐在经坛周围,在经生谈经过程中配合经生演奏各自的乐器。
2.开坛
布坛准备就绪之后,洞经会谈演者按照相应的位置落座。仪式的主持者、经生之一ZWT敲击了一下引磬,司乐生再敲过起坛鼓,即表示开坛,开坛也称为起坛。
接着ZWT边敲木鱼边念唱《开坛卷》,司乐生则有节奏地演奏乐器配合ZWT谈经。《开坛卷》谈演完后,ZWT再次敲击引磬,行开坛的敬香仪式,另一名经生WYI举起本主祭坛上的香炉敬了三下。敬香毕,ZWT敲击了一下引磬,说道:“开经大吉”。
3.请神
请神仪式,主要由洞经会会长ZWT谈经《礼请卷》,礼请神祇亲临现场,接受供奉。ZWT在念唱《礼请卷》的同时,根据经文内容使用不同的法器,时而敲击引磬,时而敲木鱼,时而摇铃铛,时而打镲。司乐生也要根据经文内容进行相应乐器的演奏。《礼请卷》谈经毕,请神仪式结束。接着开始《太乙经》上卷的谈演。
4.《太乙经(上卷)》谈演
《太乙经(上卷)》的谈演,经生先念开经偈,然后念开经咒,再念“消劫救苦演经篇”,最后念收经偈,《太乙经(上卷)》谈演即结束,经生谈经过程中司乐生配合奏乐。
5.《太乙经(中卷)》谈演
《太乙经(中卷)》谈演的主要内容是“十供养”。“十供养”的意思是给神祇献祭经文中的十样供品。“十供养”谈演仪式的主要过程是边谈经、施乐,司香生XYG边在本主祭坛上给本主敬献相应的供品。“十供养”谈演有固定的顺序,依次为:花供养、香供养、灯供养、水供养、果供养、茶供养、食供养、宝供养、珠供养、衣供养。
6.《太乙经(下卷)》谈演
《太乙经(下卷)》谈演,经生先念过下卷的开经偈,接着念唱“太乙天尊救苦咒”,然后念唱“金光真人颂”,俗称“老人颂”。经生谈经过程中,司乐生演奏洞经乐器配合谈演。《太乙经(下卷)》经文谈演结束时,经生仍然要念过收经偈,方可收经。
7.收经撤坛
下卷谈演毕,ZWT击打了一下引磬,表示下卷收经。接着,ZWT打着大镲,其他司乐生继续演奏乐器。谈演了一会,乐声又止,ZWT说道:“朝拜就位,伏立于圣前,请圣送驾上香礼跪,司香生出发,炉中三敬香”,话毕,司香生XYG走向祭坛,端起香炉敬了三下。
敬香仪式之后,ZWT向众人说道:“撤坛,大众圆揖”,然后敲击了一下引磬。此时,谈演《太乙经》祭祖和超度亡灵的仪式全部结束。
二、中元节大理南村洞经谈演仪式的文化内涵
大理南村的洞经会会员在中元节举行的洞经谈演仪式隐喻了中元节的核心释义,包涵着中元节祭祀祖先和超度亡灵的文化内涵。
农历七月十五在道教中称为中元节,是天、地、水三官中的地官为亡魂赦罪之日。中元节俗称盂兰节、七月节。中元节是道教的说法,中元是三元之一,名起于北魏。“三元”是“三官”的别称。三官大帝,即天官、地官、水官,亦称“三官”,又称“三元”,为道教较早供祀的神灵。
在民间信仰中,中元节又称“中元地官节”,是中元赦罪地官清虚大帝诞辰。地官大帝在农历七月十五,即来人间,校戒罪福,为人赦罪。并为狱囚地狱受苦众生除罪簿、灭恶根、消死名、上生籍。
大理各地在古时的中元节已经形成了传统的信仰习俗。《淮城夜语》中,有对明代中元节大理民间习俗的一些记载。书中有载:“言及阴司办事与阳间同。社稷野鬼,不归地府,由当地神司所管。中元为假月,群鬼可入人家户受子孙飨,享受人间香烟。地祇社稷神游巡人间,防野鬼胡为。有功者扬于阴榜,过者枷之。”①大理州文联:《大理古佚书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238页。另外,《大理县志稿》(三十二卷·民国六年铅印本)载:“七月,朔至十四日,俗皆曰‘中元节’。祭先祖,荐时食,凡花果、蔬菜,争购新鲜之品,惟恐不获。虽素尚俭约之家,亦必力从丰腆祭先,诚意人所同也。新丧之家更为周备。”②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下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858页。《鹤庆州志》(三十二卷·清光绪二十年刻本)也载:“七月,初十至十五日为‘中元节’。供先祖,荐时食,香烛、菜果各备,新丧之家更为整齐。姻戚送纸包,主人设肴馔以待。各乡作‘盂兰会’,荐拔亡人。”①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下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866页。可见,“七月半中元节祭祖、祭亡灵的中心活动是招魂,即引魂归家。招魂首先招的祖魂,民间相信,七月十五是祖魂归家的日子。其次,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在这一天也要受到祭奠。所以可以说,七月十五的中元节,是一切死去的亡灵的节日。”②张铭远:《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30页。
这些古代的中元节传统民俗延续至今,中元节期间,大理民众普遍的民俗活动除了日常的家庭祭祖仪式外,最重要的仪式就是超度亡灵。中元节的超度仪式主要是大理各村的洞经会会员在本主庙以谈演《太乙经》的形式集体超度本村各家各户的祖先亡灵,目的是普度地狱众生,给亡灵赦罪解厄、加持功德、早日超生净土。民众会在中元节加紧超度亡灵,希望通过替亡者向中元地官的虔诚祈福,能够在农历七月十五的中元地官诞辰之日,地官大慈大悲大愿赦免亡魂之罪时,对遭受地狱之苦难的祖先减轻生前罪过,从而尽快脱离地狱苦海。
南村洞经会会员在中元节举行的洞经谈演仪式中,谈演的《太乙经》经文内容是阐释中元节祭奠和超度祖先亡灵的文化内涵的重要媒介。如:《太乙经》上卷中谈演的经文:“消劫救苦演经篇”,主要谈演超荐救拔亡灵的各种劫难,有:“消瘟疫;消水劫;消火劫;免饥馑;除旱魃;薦宗亲;免刑狱;免盗贼;解冤结;度孤魂。”中卷谈演的“十供养”中也有祈请太乙天尊普度众生,消劫救苦赦罪度幽魂的经文内容。中卷经文中有曰:“‘花供养’:採德上林花,缤纷燦彩霞,枝枝陈法座,朵朵献仙家,天尊说经见,玉女信手斜,真灵来下盼,火翳化莲槎。‘灯供养’:佛前供明灯,灯光灼灼腾,辉煌常不灭,福禄寿至臻,九幽无黑暗,六道早超生,一盏今献上,金刚化朱陵。‘衣供养’:仙衣合地裳,供养荷思光,娱亲堪戏无,共友乐辉煌,上下昭垂覆,幽显庆帧祥,文肃今上献,阿鼻化莲塘。”下卷中谈演的经文:“太乙天尊救苦咒”,主要内容仍然是太乙天尊救拔亡灵的苦难,有:“救三灾苦、救四煞苦、救五鬼苦、救六害苦、救七伤苦、救八难苦、救九结苦、救十缠苦、救刀兵苦、救瘟疫苦、救水灾苦、救火燄苦、救霹雳苦、救饥馑苦、救崩压苦、救产难苦、救流离苦、救饿鬼苦、救枉死苦、救诸狱苦、救轮回苦、救胎生苦、救卵生苦、救湿生苦、救化生苦、救一切苦。”另外,下卷经文中还有太乙天尊救赎亡灵脱离的地狱,有:“愿救风雷狱、愿救火翳狱、愿救金刚狱、愿救溟泠狱、愿救镬汤狱、愿救铜柱狱、愿救屠割狱、愿救火车狱、愿救天牢狱、愿救阿鼻狱。”
中元节洞经谈演超度亡灵的仪式是在洞经音乐传入大理之后,在明、清至近代以后才逐渐形成并融入中元节祭祖的传统仪式中。这种将音乐元素融入仪式中的文化表演形式,能够更生动形象地表现仪式的文化内涵。显然,南村的洞经会会员在中元节举行的谈演《太乙经》的仪式,其含义是力图通过经文的唱诵和洞经乐器奏乐的加持,以达到荐拔亡灵,救赎亡灵脱离地狱苦海、超生净土的目的。“也就是说,某些特定的动作可以用来表达一定的含义,而这些含义是用歌曲或词句来表现的,人们用身体的动作和口头的言辞表达某些强烈而有节制的感情,而当语言具备一定感情的时候,也就形成一定的形体动作。”③[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页。南村的洞经会会员在中元节谈演《太乙经》的音乐艺术表现形式,很好地诠释了中元节超度亡灵的核心释义。正如格尔茨分析到:“对于任何事物——一首诗、一个人、一部历史、一项仪式、一种制度、一个社会——一种好的解释总会把我们带入它所解释的事物的本质深处。”④[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三、中元节大理南村洞经谈演仪式的自我呈现
“洞经音乐,是由宗教性民间音乐社团——洞经会组织谈演的宗教性民间音乐。顾名思义,它是‘经’与‘乐’的融合。谈经演教如仪奏乐,即是洞经音乐特有的文化内涵。”①张兴荣:《云南洞经文化——儒释道三教的复合性文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洞经音乐既可以通过演奏洞经乐器供人们娱乐欣赏,又可将谈经与洞经乐器演奏紧密结合起来,以谈演的艺术形式来呈现民间的日常仪式。用洞经音乐的艺术表演形式来演绎仪式,使民间信仰的超自然成分减少,仪式的神秘性逐渐消失。民众在音乐文化表演的艺术感染力之下,使得仪式过程以一种娱神、娱人、娱己的自娱自乐的表现形式逐渐实现了由神圣走向世俗的日常自我呈现。
(一)仪式谈演者的自我呈现
“在巫术和宗教两种仪式中,人们都必须诉诸最有效和最有力的方法,以造成强烈的情感经验。照我们刚才所说,艺术的创造,正是产生这种强烈的情感经验的文化活动。因此,我们常常见到,丧葬的礼节和仪式化的哭泣、挽歌、殡殓以及戏剧性的表演相联在一起。”②[英]马凌诺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95—96页。同样,大理南村的洞经会会员在中元节举行的洞经谈演仪式中,经生与司乐生在仪式展演时谈经说唱与演奏各种乐器的行为也呈现出了生动形象、赋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艺术效果。
“对‘参观者’来说,宗教表演在这里,就案例的本质而言,仅仅是一种特殊宗教观点的展示,因而可以对其做出美学的分析或是科学的剖析。而对于参加者来说,宗教表演还是宗教观点的规定、具体化和现实化——不仅是他们所信仰的东西的模型,而且是为对宗教观点的信仰建立的模型。在这些具有可塑性的剧目中人们在刻画的同时也获得了信仰。”③[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140页。在大理,中元节举行的超度亡灵仪式中的重要内容——洞经谈演,就是一种通过仪礼性文化表演的形式来呈现民间信仰的仪式过程。谈演者表演的核心紧紧围绕举行仪式的目的而展开,通过谈演经书来呈现仪式目的。
中元节的洞经谈演仪式,《开经卷》和《礼请卷》的谈演是仪式的开头部分,《太乙经》上、中、下三卷的谈演是仪式的高潮部分,而《收经偈》的谈演则是仪式的结尾部分。
事实上,用音乐表演形式来演说宗教的仪典,在古代早已有之。佛教中常用的“变文”就是以说唱结合、韵白交错及接近口语化的通俗语言方式来演绎佛教中的经文经义、佛经故事。佛教僧侣运用“变文”这一音乐表演的艺术表现形式使得晦涩难懂的佛教经义、教理变得生动通俗,从而使得民间百姓易于理解和容易明白。这正是宗教信仰或民间信仰之所以乐于运用说唱表演、乐器演奏等艺术手法来诠释教义、经典等的原因。
洞经谈演仪式的文化表演与“变文”这一由散文和韵文交错组成的说唱文学形式有相似之处。“表演者使用个人前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这种前台允许他以他想要表现的那样呈现自己,而是因为他的外表和举止能够适应更为广大范围的场景。”④[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可见,洞经谈演者在谈演仪式中自我呈现出的前台表演的艺术特征,主要还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观众,并且期望仪式中隐喻的信仰的思想在经过洞经谈演的艺术表现力作为媒介转换为通俗易懂的形式后,能够被世俗社会中的民众所接受。
(二)仪式经书与曲目的自我呈现
南村洞经会会员在中元节用洞经谈演的形式来呈现祭祀和超度仪式,最关键的是洞经乐器的演奏要能够与经书的说唱相得益彰地协调在一起。中元节的洞经谈演仪式,司乐生奏乐的顺序与《太乙经》经文谈经的顺序保持一致。其中,《太乙经》的经文反映出了中元节祭奠祖先和超度亡灵的主旨,这也是中元节选用《太乙经》作为洞经谈演仪式经书的原因。
《太乙经》经文由散文和韵文交错构成,韵文的体裁又分为诗章和词章等。其中,诗章有绝句和律诗等,大多能与乐曲演奏合唱。而词章中常用的词牌有开经赞、开经偈、大洞神咒、吉祥咒等,均能与洞经音乐配合唱诵。仪式过程的展演需以《太乙经》谈经为主体依托部分,然后根据经文的章节顺序和内容配以相应的曲目,由司乐生根据曲谱演奏洞经乐器配合经生谈经。另外,司乐生在洞经谈演中演奏的曲目仍然是仪式谈演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修饰经书的作用,可以烘托经堂氛围。一般来说,“曲牌主要用于谈经时的各种礼仪,如开坛迎神、收坛送神、供献祭品等场合演奏,相当于背景音乐的作用。”①张兴荣:《云南洞经文化——儒释道三教的复合性文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洞经谈演时的曲目多融入了古代宫廷音乐、戏曲音乐、民间传统音乐及本地民歌的音乐元素,所以洞经音乐在谈演过程中既不失庄重典雅又体现古朴平和,其优美的旋律通俗流畅地表达出的仪式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使得民众更易于理解和接受。比如:中元节时,大理洞经会会员谈演洞经常用到的曲目《南洋洲》《双诗章》《小桃红》《双吉祥音》《月调》《吉祥奏章》等受到民间百姓的喜爱。
司乐生在洞经谈演仪式中用曲目的演奏配合经生的谈经,音乐成分的加入使得仪式谈演的经书——《太乙经》在曲目演奏的修饰、点缀与衬托下,将《太乙经》中晦涩难懂的经文内容变得生动形象起来。在乐器演奏的艺术感染力下,再加上经生用合适的唱腔来通俗浅显的唱诵经文,枯燥的仪式过程有了活跃的灵动感,更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三)仪式乐器的自我呈现
南村洞经会会员在中元节举行的洞经谈演仪式,洞经谈演者用于谈演的乐器有:碰铃、木鱼、引磬、镲、大钹、大锣、铛锣、大鼓、堂鼓、板、铓锣、唢呐、笛子、三弦、大胡、二胡等打击乐器、吹管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据说,钟能通天官、鼓能应地官、磬能感水官,法器能召将通神。”②张兴荣:《云南洞经文化——儒释道三教的复合性文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谈演者在仪式表演过程中运用各种乐器,目的就是为了发挥乐器演奏作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的功能。
洞经乐器的演奏采用旋律感较强和抒咏色彩较浓互相交错的声部及曲牌互相交织、错落有致的演绎形式,配合经生说唱经文时缓急结合的节奏感极强的唱诵腔,从而提升仪式展演的艺术效果,活跃经堂气氛,吸引并持续围观群众的注意力。这种艺术效果,博厄斯阐释道:“既然韵律或节奏都有感情特色,那么,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只要和感情有关的都会出现有韵律或节奏的现象。宗教歌曲和舞蹈中的韵律和节奏发生感化人的效果;战歌的节奏使人们的士气受到鼓舞;抒情歌曲的旋律和节奏给人以舒适安逸之感,无论是在歌曲或装饰艺术中,都可以看到节奏的美学价值。”③[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98页。
“追悼死者的仪式上使用的各种哀乐可以产生一定的感情效果,这是可以理解的,倘若没有这种特定的环境,同样的旋律也许还会产生另外一种效果。”④[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25页。在去世后的中元节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为亡者举行的仪式,洞经谈演者在仪式过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正是谈演者将洞经音乐置入了追悼死者的特定环境中,他们才能用谈经与乐器演奏和谐配合的旋律,演绎出以祭奠祖先和超度亡灵为核心主旨的文化内涵。
可见,“许多动作是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有时讲述者用适当的手势加强语言的效果,歌唱者也通过各种动作把歌曲的含义表达得更为生动。”⑤[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29页。中元节的洞经谈演仪式,相当于经生的伴唱的司乐生根据相对固定的曲谱演奏乐器的动作行为,将中元节的文化含义演绎得更为生动,实现了作为仪式表演道具的乐器在文化表演过程中的自我呈现。
南村的洞经谈演者将中元节的超度仪式放在一个文化表演的场景中,整个文化表演过程围绕经书内容和曲目谈演,节奏如行云流水般流畅,无杂乱无章之感。洞经谈演仪式通过对表演场景、表演情节、表演效果等的恰当地自我呈现,演绎出了中元节民间信仰仪式的文化本质。
结 语
南村洞经谈演仪式的自我呈现,使得我们可以比较出人类表演理论与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洞经谈演仪式的异同。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以仪式中的信仰观念、仪式行为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并将仪式隐喻的意义分析作为研究的主要目的。然而,主要的区别体现在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研究对象是音乐,关注文化中的音乐,在洞经谈演仪式研究中侧重将仪式中出现的音声作为阐释的主要对象,将仪式展现的各种音声行为置于信仰与仪式的情境中,注重分析音声作为仪式行为符号的文化含义,探寻音声体系的结构元素、音声在仪式展现中的功能等问题,力图通过信仰、仪式、音声三维合一的互动关系模型来解读仪式中音声的内涵和意义。而人类表演理论更侧重将仪式主体在仪式文化表演中的自我呈现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且更加注重研究几个核心问题:一是洞经谈演过程如何组织,即文化表演事件发生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仪式参与者的分工、仪式场域空间的布设及仪式道具的准备等;二是阐释仪式文化表演的功能与意义。
特纳把仪式看作是一场戏剧化的表演,并解释道:“社会戏剧的阶段性结构并不是本能的产物,而是行为者头脑中所带有的模式和隐喻。”①[美]维克多·特纳:《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刘珩、石毅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可见,隐喻“既是一种本能又是艺术品,而从这一本能的产品中衍生出的一套范畴的体系就是‘推论的艺术品’。”②[美]维克多·特纳:《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刘珩、石毅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2页。
大理南村洞经会会员在中元节举行的洞经谈演仪式的自我呈现隐喻的功能和意义主要体现在,经生唱诵的经文内容恰当地诠释出了民众中元祭祖和超度祖先亡灵的信仰。经生边谈经边使用的碰铃、镲、钹、铛锣、堂鼓、木鱼、引磬等打击乐器及司乐生演奏的二胡、三弦、笛子、唢呐、大鼓、大锣等传统民间乐器增强了仪式的艺术感染力,将中元节的核心观念——祭奠和超度亡灵,融入了洞经谈演中。洞经谈演仪式的自我呈现,使得艺术中的音乐元素与仪式象征有机地契合在一起,从而在洞经谈演中阐释出了中元节隐喻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