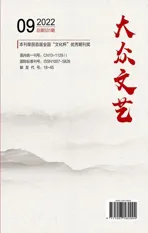被扭曲的“他们”
——浅谈《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男性形象
2021-07-12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
五四时期,无数青年知识分子投身于“思想启蒙”“精神解放”的运动之中,一批具有自由思想与女性意识的女性作家浮出历史地表,开启了反叛传统男性书写的女性主义创作。丁玲便是“五四女作家群”中一颗不容忽视的明星,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塑造了“莎菲”这样一位不屈服于传统两性关系中的卑弱地位,追求性解放与灵肉一致的新女性形象,使其成为文学史上无可磨灭的一道倩影。光芒之下自有阴影,莎菲耀眼的光环之下是这部作品中的三位男性人物——苇弟、凌吉士和云霖。在丁玲的笔下,这三位男性被剥夺了男权社会所赋予的不可违抗的自信和独占的话语权,他们或卑弱,或低俗,或平庸,与丁玲主要塑造的女性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结合文本对这三位男性形象进行细致的分析,我们可以试图窥探丁玲男性人物书写特点、意图与其间隐藏的女性意识、对两性关系之看法等等。
一、柔弱化的乞情者——苇弟
苇弟在小说中是一位对莎菲极其痴情、言听计从,爱得十分卑微的男性,丁玲没有对他的外貌体态施以过多笔墨,而是着重凸显了他卑弱、忠愚的个性。我们根据一些微末细节可以推断出苇弟是一位家境殷实,追逐大众潮流的普通青年,本当值意气风发,苇弟却始终在莎菲面前处于乞求、受人摆布的状态,虽然我们可以在传统的男性书写中找到“乞情者”形象的前迹,例如《聊斋志异》中孙子楚、王子服,《西厢记》中的张生,他们通常都以柔弱的书生形象出现,而丁玲在沿袭这一传统之上更着重了男性人物脆弱、怯懦的一面,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苇弟的“哭”。
莎菲对于苇弟的哭通常是秉持着鄙夷与轻蔑的态度,她甚至对苇弟所展现的脆弱带着一种折磨般的快感,文中写道“野人一样得意地笑了”“请珍重点你的眼泪吧”“又尽他唯一的本能在哭”,苇弟越卑弱,莎菲越冷酷,也越站在双方关系的制高点上,丁玲通过弱化苇弟这一男性人物来达成莎菲挣脱被男性掌控的命运,甚至成为掌控者的女性主义幻想,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人物塑造同样透露出了丁玲本身所受的男权社会的影响,男性就应该是坚强、不露声色且不会轻易受情爱左右,而这种刻板印象的对立面便是对苇弟形象的刻画,标准的反面不是颠覆,而是在构造另一种标准。
丁玲不仅通过苇弟这个男性形象向男权写作宣战,还在传达着自己对爱情与两性观念的思考。例如苇弟的第四次哭,他由于莎菲对凌吉士的过分关注而感到嫉妒,丁玲借莎菲之口表达了对爱情真义的理解:“这种无味的嫉妒,这种自私的占有,便是所谓爱吗?”,爱不可与占有欲、肉欲或是其他欲望混为一谈,爱是灵魂与肉体的合一,丁玲极其注重思想上的共通,她曾设计情节让莎菲给苇弟读自己的日记以试探两人精神世界交流的可行性,但显然苇弟是不懂莎菲的,这让莎菲更加痛苦,她不再相信人与人之间存在有效的理解,这里的文本意义又从爱情超拔到了人类社会普遍的交往与沟通或是现代人心灵的孤寂感上。
总体来看,丁玲对苇弟这个男性形象是可笑亦可怜的,虽有厌弃之处,但她亦借莎菲之口赞美了其痴情、忠诚、可靠的一面,“忠实的男伴”“一生的归宿”已是文中出现的最高评价了。这一面让苇弟的形象更为立体丰富,同时反映出丁玲在性别倒置的写作中的冷静思考,她并没有完全将男性人物作为达成创作意图和凸显女性人物的工具。
二、异化的诱惑者——凌吉士
凌吉士这个人物的很多面类似于传统小说中女性心目中的“理想对象”,他们往往俊美优雅,家境优渥,接受过新式教育或是有过留洋的经历,但丁玲笔下的这位“理想对象”却是充满着冲突感的。
对于苇弟和凌吉士的描写,丁玲的侧重点并不相同。她将大量的笔墨施与到了外貌和仪态描写上,常用“漂亮”“美”“高贵”“妩媚”等形容女性的词汇来描摹这位南洋人,这种使男性人物女性化的写作特征在张爱玲的笔下也十分常见,可见当时的五四女作家有意识的通过性别互置的方式来打破男权写作的传统模式。丁玲不仅让莎菲观察凌吉士,还是带着强烈欲望和念想的目的性的审视,从而打破传统女性“被看”的模式,扭转了两性关照上不平等的局面,让凌吉士成了被观赏者,而莎菲成为掌握主动权的审视者,男性被物化,女性的欲望与天性得以释放,而这种欲望的抒写又显得极其纯洁、懵懂甚至带着某种母性的特征,而不至于让人难以接受。丁玲将凌吉士的面容躯体描写的充满诱惑性,从而试图解构女性最原始的性欲与冲动,同时这种欲望纾解是夹生着矛盾感的,莎菲在日记中常常流露对自己一些冲动的反思与犹疑,“但我知道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准许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无论这于人并没有损害的事,我只得忍耐着”,丁玲所还原出的是女性意识与社会规约冲突间一种真实的挣扎与游离。
丁玲虽女性化了凌吉士的面容仪表,但这位具有阴柔美的男性却并不褒有女性细腻丰富的心思,相反的,他的灵魂极其低劣、庸俗,凌追求金钱名誉和低级享乐,并且对女性存在着传统话语权影响下天然的偏见与轻视,他对莎菲的暧昧、关心,只是为了能满足自己的私欲。外貌的美与灵魂的丑结合在一个人的身上,他个人的冲突感引发了莎菲的内心情感的冲突感,本我被激发的原始欲望与理性之下的自我约束轮流抢占上风,丁玲塑造的凌吉士形象放在当代社会仍旧存在着现实意义,欲望解放、人性解放是值得提倡的,但此处的解放仅仅针对的是压抑人性的规约或是传统,女性自身并不能完全受最低级的性欲望操纵,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理性的选择与判断,怎能重皮囊而舍灵魂呢?
三、平庸化的失语者——云霖
云霖在文本中出现的次数不少,但其自身的性格、形象却并未被丁玲充分刻画出来,他常作为关爱莎菲的好友、莎菲与凌吉士交往的桥梁等偏向于工具型的身份出现,并且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与毓芳捆绑在一起。云霖这个角色在文本中缺乏话语权,有被模糊化的倾向,但即便如此,依据丁玲的叙述细节,我们依旧可以窥探出这个人物的一些代表性特征。
由于日记体裁的限制,作为读者更多的是通过莎菲的主观视角去认识云霖这个人物。莎菲对云霖的态度是既感激又轻蔑的,一方面云霖是好友毓芳的爱人,他们之间平淡的爱情是莎菲所赞赏的,云霖对莎菲也是关怀备至,不管是平日里的照顾与探望,还是积极的帮助搬家、住院等举动都令莎菲十分感动;但另一方面莎菲对云霖的平庸和守旧有一丝轻蔑的态度,在将其与凌吉士比较时,她使用的是“委琐”“呆拙”等字眼形容云霖。云霖为了预防婚前性行为,主动放弃了与毓芳同居,引发了莎菲的嘲讽,莎菲讽其为“禁欲主义者”,并表示不相信爱情能如此理智、科学,可见云霖与莎菲追求自由、真实的个性是不太合拍的,她于云霖关系的维系更多在于毓芳和云霖相对更多的付出。
莎菲对云霖的态度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对他的多次欺骗。“欺骗”首先意味着云霖在莎菲心中是比较容易受骗的,并且即使知道真相后也不会在两人之间出现不可解决的矛盾,莎菲所预想的后果是云霖会因为被“爱惜的小妹妹”欺骗而伤心,毫无疑问云霖是个好脾气的老实人,就连苇弟因莎菲的仓促搬家而不满都可以随意向云霖置气;其次便说明云霖并不深谙人情世故,他并未参透莎菲种种谎言与借口背后那颗努力想要抓住爱情的萌动之心,他也并未看出凌吉士对莎菲并非单纯的欣赏或恋爱之情,而是自私的欲望在蠢蠢欲动,云霖被动地成为两人之间的传声筒和靠近彼此的桥梁,缺乏自主的立场与判断。
文本中唯一表现出云霖稍显激烈的性格的是在他与凌吉士关于莎菲何时出院的分歧上,但这属于同性之间的关系,在与异性歧意的情况下,通常是云霖作出妥协,比如莎菲想要尽快地搬家,他虽觉得不合适但还是同意了莎菲的请求,又或是他并未拒绝毓芳搬来与他同住,却在那之后主动搬离,由此可以窥见丁玲试图让云霖成为一个在两性关系中缺乏立场、主见的失语者,他妥协、屈服于另一方的声音,作为女性的附庸生存着,在传统的男权书写中,许多女性形象往往带有着这样的特征,丁玲采用“逆向性别歧视”的写作方式将其转移到了男性人物身上,表达了她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对男权书写的反叛精神。
四、小结
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塑造的三种男性形象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化——弱化、异化或是平庸化,他们与传统的男性形象和丁玲笔下的女性人物都形成了反差,并且丁玲借莎菲之口对男性一些卑劣、庸俗、软弱的特质进行评判,冲破女性作为男性附庸或是男性臣服者、崇拜者的传统定式,以此来表达对男权社会固有观念和单一话语权的反叛。但她也并未完全将男性人物作为构造意图的工具,相较之下苇弟的形象还是有其丰满之处的,可见丁玲在性别互置的书写上深入的思考。与此同时丁玲还通过男性人物形象的构造透露出自身对爱情、两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等话题的思考、认识,让文本的主题具有了超拔性。
注释:
①华维勇:灰色的亚当[D].暨南大学,2012:72.
②丁玲.丁玲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7.
③丁玲.丁玲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7.
④丁玲.丁玲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
⑤丁玲.丁玲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3.
⑥丁玲.丁玲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6.
⑦丁玲.丁玲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6.
⑧丁玲.丁玲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9.
⑨杨玲.女性意识演进后的局限——丁玲、张洁女性小说比较[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7(S1):18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