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一年
2021-07-06时潇含
○时潇含
提交了留法申请表的那晚,我紧张得翻来覆去,一晚上都没有睡好。
我们学校提供了很多出国交流的机会,大一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加丰富,怎么说也要走出去看看。于是从大一开始,我就学起了法语,铆足了劲申请去法国做一年交换生。
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好学的学生,但我已记不清有多少个周末早上7时就从被窝爬起来,到小树林里读课文、背法语单词,等到9时再到课外补习班上课,直到19时才回到学校。那时候我的手机屏幕都是法语单词的变位,桌子上密密麻麻贴着便利贴,我恨不得把上铺的床板底下也贴上单词变位,这样一睁眼就能看到。
悦悦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她总是打趣地说:“平时上课都没见你这么认真,也就只有在系主任的课上,能看到你这么认真听课了。”
我“啊”了一声,说:“兴趣使然呀,每天早上起床学习我动力十足。”
后来,悦悦将从我们学校保研去国内一所名校时,她说要是我把学法语的劲头用到学本专业上来,这个保研名额还不知道是谁的呢。
可我是非常任性的女生,就像高考之后我毅然决然选择了历史学类专业,又在这个冷门专业类别里选择了世界史专业一样,我只相信脑袋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声音,那些小心翼翼的权衡都是对自己的背叛。两年前的我,既没有钱也没有本事,甚至连优于他人的知识储备也没有,这个世界在我的心里只是一个朦胧的剪影,能相信的只有理想。三岛由纪夫说:“二十几岁就像一个分水岭,将人生隔成了咸水湖,水的盐分骤然变高,似乎可以轻易地在其中仰泳。”其实,我们这些刚刚二十岁的孩子,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由,只有勉强泅水的能力,哪里谈得上如鱼得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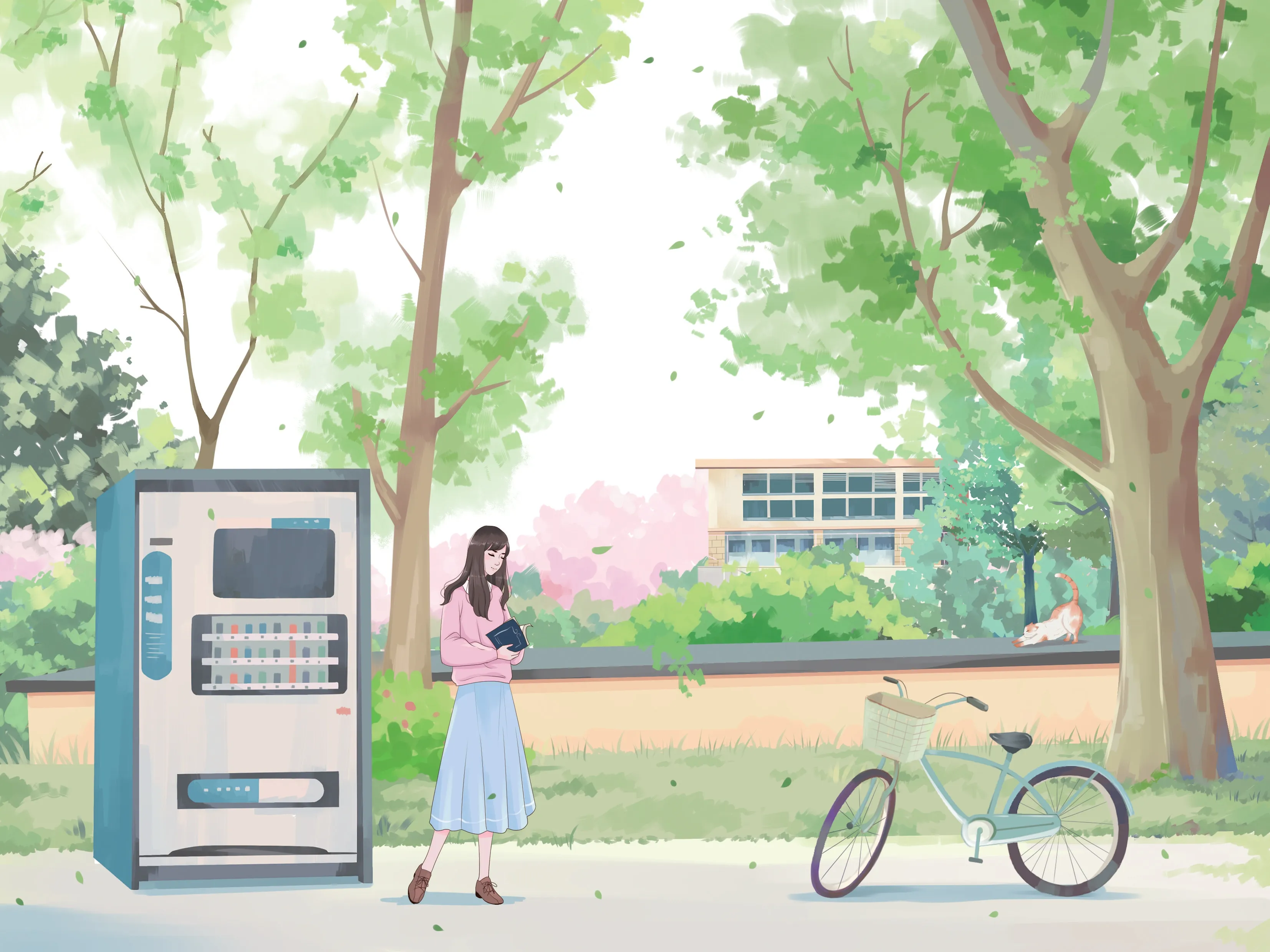
所以,半个月之后,当我和三个即将一起去法国里尔读书的同学坐在一起聚餐时,还觉得整个人晕晕乎乎的,生怕猛然一站起来梦就醒了,我又变成那个在冬天里因为寒风凛冽而干到脱皮的灰姑娘。
亚昕瞪大眼睛说:“我都没有见过别的专业的学生参加我们的项目,你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
千万不要误会我是什么聪明伶俐的优等生,纯粹是我的运气好。和我校合作的学校是法国最好的政治学校,萨科齐、奥朗德、马克龙都是从那所学校毕业的。有些人因为害怕不能顺利毕业,所以连名都不敢报,这倒是被我这个门外汉捡了个大便宜。
在里尔的那段时间,我经常到亚昕家里蹭饭,她会包馄饨和做寿司。我们在宿舍里煮火锅吃,过年的时候还邀了几个朋友一起来家里包饺子,一群人边玩边包,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了面粉,像圣诞老人一样长出了白胡子。
亚昕告诉我做咖喱时要往里面放一点黑巧克力,我诧异地问:“怎么要往咖喱里放巧克力?”她说:“你不懂了吧,做饭和生活一样,都要讲究平衡,巧克力的苦和咖喱的甜会让整道菜的味道更有层次感。”
我在她身边切洋葱,说:“怎么,难道你还嫌生活不够苦吗?还要更苦一点才好?”
不过亚昕做的饭的确好吃,只要收到她的消息,我便会风雨兼程赶到她家。虽说算不上大厨,但是来自祖国的味道,总能解我的莼鲈之思。
悦悦在微信上看到我发回的照片,颇有几分羡慕地说:“要不是知道你们是去留学,我还以为你们去读了新东方烹饪学校呢!”
我们一起买菜做饭,一起逛街买花,装饰我们并不大的家,还一起逛了五六个国家的圣诞集市……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心大于宇宙,第一次离开家,借留学完全独立自主地生活,心底滋生出一股毫无由来、无所不能的错觉:我觉得桌前的台灯就是日出,手里的笔可以直接画出一条让我走得更远的路……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布包,上面写着:“我们手中的笔,就是对抗这个世界的武器。”
如果那时的我能够预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一定会好好珍惜那段轻松的时光。
现在还记得,我们这一群非欧盟学生和教授产生了巨大冲突的那节课。那节课的内容是“欧洲悬而未决的思想难题”,是一节哲学课。教授是一个老年人,看上去就有几分傲慢,他在课堂上说:“欧洲之外没有哲学。”这下可好,班里立即热闹起来,大家耸肩、摊手,叽叽喳喳地聚在一起,开始议论纷纷。
亚昕凑到我边上说:“这不明摆着是欧洲中心论吗?这种话上课也能说出来?”
我也有些不平地说:“他这话怕不是要把孔子和王阳明气得跺脚。”
有位性格直爽的学生直接站起来问老师:“这话是什么意思?”原本闹哄哄的教室瞬间安静下来,大家都抬起头等教授的回应。
教授并不着急,也没有针锋相对,反而示意让他坐下来,说:“下节课就专门留给大家讨论这个问题,顺便给你们留一个阅读、了解哲学含义的机会。”
这样也好,大家都回去翻资料了,然后凝聚出共通的认识,这样据理力争才有说服力。我们班有个聪明绝顶的波兰人,他简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经常和我们在学校门口一起吐槽该教授。那天我们一起聊天时,他说:“老教授的话没有错,虽然听起来很难接受,但是‘哲学’就是源自希腊的词语,在西欧的语境里哲学是需要严谨推论的一门学问,东欧和亚洲语境里的哲学家对所谓正统哲学世界来说,只能算是思想家,不被别人认同,也很正常。”听到这句话,我有如五雷轰顶,原来我们是鸡同鸭讲啊。
的确,我们所说的哲学和他们所说的哲学完全是两样东西,我们会把道教、佛教的内容称为哲学,哲学在东方是一种泛化的概念。我们也要承认,老教授只是直接地站在学术的角度看问题,而当初听到他那句简单的论断时,我简直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被他漠视了,因此气恼得不行。其实,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有不少文化冲突是因为误解,是因为语境、文化的不同,还因为并不复杂的问题不断发酵后形成解不开的结。
几十年前,胡适在《容忍与自由》里写道:“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所说的容忍,指的应该是一种开放的眼光吧。
有一次,那个聪明绝顶的波兰人捋着他的络腮胡子对我们说:“我们现在学的东西其实我早就学过了,我只是想看看在东欧和西欧,对同一件事情的叙述有什么不同。”
我的捷克室友也是这样说的,她在捷克学了法律,但还是决定来法国学习国际政治。她声音和表情有些落寞,她说:“对于整个世界,东欧的发展太慢了,如果我们想要走得更远,让捷克发展得更好,那我们需要倾听别人的声音。”
虽然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一起嬉闹玩耍,但真情流露的时候,还是会让人震撼的。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现实与这个世界的需要重合了。
我和捷克室友都是公园爱好者,我们经常去里尔市中心的集市花一欧元买一本薄薄的小书,再去买一瓶红酒,躺在公园的阳光下静静地读。书读完了,第二天就会互相交换一本,再带上一瓶新的红酒,躺在公园的同一棵树下阅读。
最后,那树下的草坪被我们压得有几分稀疏了。三岛由纪夫说:“但在冬天光线过于充足的日子里,我透明的心甚至也有光线爬进。”我真的怀疑他是不是也在同一棵树下沐浴过这样的阳光。
我的法语进步飞快,在短短一年内,我已能跟人用法语聊天了,已能读完原版加缪的《局外人》了。我能品读波德莱尔和艾吕雅的诗歌,还能去美术馆看莫奈、雷诺阿和凡·高的画展,虽看不出名堂,但买了几双印着凡·高的画的袜子回家,也算是心满意足。
后来,新冠肺炎疫情来了,学校直接宣布国际生结束学习离开法国,我们的课程停了,我的留学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