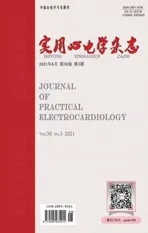可穿戴式心脏除颤器与远程心电监护的联合应用
2021-07-02顾菊康
顾菊康
我国每年约50 万人发生猝死,猝死的黄金抢救时间是4 min 以内;若超过10 min,抢救成功率几乎为0。 如何在4 min 以内有效开展急救,是当前医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 目前猝死急救的有效措施有如下几种:①训练志愿者掌握心肺复苏技术,一旦周围人群中有昏迷者,在1~2 min 内实施心肺复苏;②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车站、机场、大型商场等)安放自动体外除颤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AED),由志愿者对晕厥者施行 AED 急救;③为猝死高危人群安装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ICD);④ 猝死高危人群采用可穿戴式心脏除颤器(wear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WCD)。
WCD 为一种新型的自动体外除颤器,最早在1980年研制出样机,直到1998年由德国研制成功并投入生产。 当时这种形似背心的WCD 重约2.7 kg。2002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ZOLL 公司的 WCD(LifeVest 2000) 上市。 2014年,WCD 第4 代产品(LifeVest 4000)获得 FDA 批准。目前,LifeVest 已在欧洲、美国和以色列上市。 WCD的设备重量也已从2.7 kg 减小到0.6 kg。 自2002年LifeVest 上市以来,至今已有超过10 万例患者使用过LifeVest。 由于 WCD 对除颤、传感器、算法等要求很高,目前仅ZOLL 一家公司生产的WCD 产品(LifeVest 系列)通过了 FDA 的批准[1]。 ZOLL 公司于2012年被日本旭化成公司收购。
中国也已开始研究WCD 的生产技术,2015年杰升生物科技(上海)公司的罗华杰等在《中国医疗器械杂志》上发表了由该公司开发中国自主研制的“可穿戴式心脏除颤器”的硬件和软件技术成果,并在家兔心室颤动(室颤)模型中进行除颤,取得成功[2]。 但尚未见人体研究报道。 山西大学商务学教授张杰明在2016年申请了《背心式智能除颤器》发明专利,但目前尚未见到生产的产品。
1 临床应用简介
由于WCD 无须手术植入,可以随时佩戴、随时脱卸,深受猝死高危人群的欢迎,很快在欧美各国应用和推广。 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已有超过76 000 人次佩戴和应用WCD。
国外曾有文献介绍WCD 的平均使用时间是124 d,首次放电成功率接近100%,在有症状性心力衰竭患者中成功率稍低。 另外,WCD 误放电率较低。 若患者在使用WCD 期间猝死,多是因为处于WCD 脱卸间期或穿戴不正确。
在欧洲心脏病学会(ESC)2014年会上发表的WEARIT-Ⅱ研究观察了WCD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项注册研究入选了美国2 000例患者,研究起止时间为2011年8 月至2014年2 月。 受试者中既有缺血性心肌病患者(40.3%),也有非缺血性心肌病患者(46.4%),还有少数遗传性心脏病患者(13.3%)。WEARIT-Ⅱ研究结果显示,在所有人群中,WCD 平均穿戴时间为90 d,其间共发生41 次心律失常事件;WCD 治疗22 次,均获复律。 德国德雷斯顿大学医学院的 Wabning 教授对404 家中心的6 043例WCD 穿戴患者进行研究,患者平均年龄57 岁,男性占78.5%;其中有94例(1.6%)患者用 WCD 除颤器来治疗室颤或室性心律失常,均能自动除颤。 美国克利夫兰诊所对PCI 术后EF 值降低者采用WCD 90 d,对照组的死亡率为13%,而采用WCD 组的死亡率只有2%,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表明WCD有明显保护效果。 美国Chuang 等报道WCD 3 569例,每人每天平均佩戴19.9 h,共有80例发生持续性室速(颤),首次除颤成功率100%,但转复成功后,仍有8例死亡。曾有对美国Chuang 和德国Klein关于WCD 的研究报道的比较,认为二者观察对象的病因有所差异。 德国该组研究WCD 适应证中,最多的为心肌梗死后的患者,占39%(美国研究组中仅占12.5%);其次为冠脉搭桥后的患者,占25%(美国研究组中仅占9%)。 由于观察病因不同,两组的可比性较差。
2014年间美国曾有研究介绍2 000例WCD 的使用结果,使用中误除颤仅为10例(占0.5%);WCD 使用期间死亡3例,均与室颤或室速无关。 该研究基于上述数据认为WCD 的使用是安全和有效的。
2 可穿戴式心脏除颤器的组成和结构
ZOLL 公司生产的LifeVest 系列WCD 的结构见图1 和图2。

图1 ZOLL 公司生产的LifeVest 系列可穿戴式心脏除颤器Fig.1 LifeVest series of wear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 by ZOLL Medical Corporation

图2 穿戴可穿戴式心脏除颤器穿好衣服前后的照片Fig.2 Comparison among photos with wear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 worn before and after getting dressed
WCD 主要由除颤电极、导线和除颤主机组成。它的除颤背心中包含前胸的1 个除颤电极、后背的2 个除颤电极以及4 个心电图感知贴片电极。 除颤主机位于腰部,上面有功能键和心电图显示屏。 电极板上有10 个自破型导电凝胶胶囊帮助感知心电活动。 心电图感知贴片电极检测到患者的心率超过设定的治疗频率(一般在120~250 次/min,通常为150 次/min)、快速心律失常超过设定的时间(通常为5~6 s),仪器将心电图和模板进行比对,判断是否确实为室速(颤),若为室速(颤),WCD 将发出震动警报和灯光闪烁提醒患者,患者认为是干扰而不是室速(颤),即可按下RB 按钮,而终止此次治疗;若室速(颤)持续,除颤器自动充电,并且警报声音持续增大、继续充电,并自动击破电击的导电凝胶,发出警告,语音提示即将电击除颤治疗,旁人不要靠近患者。 当执行除颤治疗时,WCD 将发出双向除颤波,可发出连续5 次电击,能量可达150 J。 图3为1例患者经WCD 除颤的心电图。

图3 可穿戴式心脏除颤器除颤的心电图案例Fig.3 ECG cases defibrillated by wear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
3 临床应用范围
从设计特点可以看出,WCD 具有无须手术、使用简单、短期使用费用较低、降低ICD 随访费用等优点,可作为ICD 短暂移除时的替代治疗和等待心脏移植术前等的保护措施使用。 它可用于包括急性心肌梗死后早期高危人群、血运重建治疗后室速(颤)的高危人群、非缺血性心肌病发生急性心力衰竭的高危人群、等待心脏移植或需要心室辅助装置治疗的人群、怀疑为快速心律失常所致晕厥的人群、ICD 治疗中断或ICD 植入前需要保护的人群。
3.1 可穿戴式心脏除颤器适应证
美国心脏协会提出的 WCD 的适应证包括:①心肌梗死后早期(40 d 内)伴有严重左心功能不全(LVEF <35%);②急诊血管再通治疗后(3 个月内)伴有LVEF≤35%;③新诊断的非缺血性心肌病LVEF <35%;④ 等待心脏移植的猝死高危患者;⑤由于感染等原因暂不能植入ICD 者;⑥有猝死家族史合并原因不明晕厥者。
3.2 中国第1例可穿戴式心脏除颤器的应用
中国第1例应用 WCD 的患者为2018年6 月28 日在北京阜外医院治疗的1例男性患者。 该患者反复意识丧失2年余,2014年就诊,并诊断为Brugada 综合征,植入双腔ICD;2018年2 月患者双上肢用力后,出现起搏器囊袋红肿,经抗感染治疗无效,后予ICD 电极导线拔除术,择期再行全皮下ICD 植入。 考虑患者有猝死的高风险,及时应用了 WCD[3]。
由北京阜外医院牵头的我国国内共5 家医学中心参与 WCD 的研究。 入选2018年6 月至2019年10 月接受WCD 治疗并完成随访的患者共54例。收集患者的基本资料,随访穿戴依从性、反馈的问题、除颤治疗效果等。 接受WCD 治疗的患者中男47例(87.0%),年龄(55.2 ±17.6)岁。 其中冠心病患者31例(57.4%),持续性室速(颤)发作患者19例(33.3%),急性心肌梗死早期(40 d 内)伴LVEF≤35% 患者18例(33.3%),等待心脏移植且具有心脏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SCD)发生风险患者9例(16.7%)。 患者平均穿戴天数为(51 ±34)d,最长145 d。 18例患者随访3 个月期间坚持穿戴WCD 超过1 个月。 穿戴过程中感觉到的不适主要为除颤背心影响睡眠和无故报警。 1例患者随访过程中监测到13 次室颤发生,均予1 次除颤治疗,成功转复。 无1例患者发生误放电。 6例患者植入了 ICD[4]。
WCD 的中国临床观察性研究较为系统地介绍了54例中国患者应用WCD 的临床特点和使用情况,为进一步加强对患者 SCD 的预防及加深对WCD 的认识提供了初步经验[4]。
3.3 远程心电监护是可穿戴式心脏除颤器的双保险
设计时在WCD 上安装蓝牙装置,将WCD 患者的心电信号发到“云端”,再由远程心电监护中心将这些实时动态心电信号下载到计算机监视器中,同步记录、实时显示和储存心电信息,也可实现人机对话,和WCD 佩戴者及其家属、佩戴处方医师进行对话交流,制定更加合理的精准治疗决策。 当有室速(颤)事件出现,计算机自动报警,立即人工干预,协助WCD 佩戴者决策是否启动除颤装置和是否除颤,并由监护中心工作人员按动除颤键,以达到精准除颤,消除误判和误除颤。 对于已发生晕厥患者,在人工监控下除颤,可大大提高除颤精准性。 利用WCD 的自动程序进行操纵,再加上远程心电人工干预,必将进一步提高WCD 的疗效及其安全性、减少误操作、提高心脏除颤精确度、挽救更多生命[5]。 远程心电监护模式见图4。

图4 远程心电监护模式示意图Fig.4 Diagrammatic sketch of remote ECG monitoring mode
WCD 受检者为用户,用户通过网络系统将数据发送到云端;心电监护分析中心将患者心电信号下载到心电分析中心,由计算机初判,一旦发现可疑的室速(颤)信号就立即报警,然后人工分析确定。 如确诊为室速(颤),立即按下除颤按钮对患者进行放电除颤。 心电分析中心医师可以随时发现穿戴WCD 患者的心电变化情况。 一旦出现室速(颤),就立即自动报警,分析中心医师立即人工判断是真正的室速(颤)还是伪差。 如确定是室速(颤),立即启动除颤按钮精确除颤,从而避免伪差和误除颤的影响,大大提高了除颤的精准度和猝死抢救的成功率。 目前WCD 每天的佩戴时间在 19~22 h,每天有 1~5 h 的WCD 脱卸间期。 对WCD 脱卸间期的选择,可通过人机对话征求远程心电监护医师的意见,尽量安排在心电活动稳定期,避开电风暴的活动期,以减少脱卸期间的风险。 远程心电分析中心医师可以与WCD 处方医师交流心电活动规律,协助处方医师更好地了解WCD 佩戴者的病情。 通过心电散点图分析技术,远程心电中心每24 h 或定期出具一份WCD 佩戴者的动态心电图分析报告,供WCD 处方医师参考;还可发送心电散点图报告,更加直观、快速、准确地揭示WCD 佩戴者的心律失常发生规律。
4 可穿戴式心脏除颤器的不足之处及推广应用的局限性
4.1 可穿戴式心脏除颤器的不足
WCD 设备本身要依靠进口,价格较昂贵,一般患者很难承受,目前我国国内只有少数三甲医院在试推行中。 我国的国产产品正在研发中,还要经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通过,最快也要到2023年才能上市;届时可以大力推广应用,造福于心脏危重病患者。
4.2 可穿戴式心脏除颤器推广应用的局限性
由于WCD 是穿戴式设备,不可能几个月都24 h穿戴在身上,患者需要洗澡、擦身等。 根据国外经验,患者每天穿戴21~22 h,那么就有2~3 h 未能穿戴,在未穿戴间期仍有较大风险。 只有家属密切配合,才能规避风险。 如果与远程心电监护相结合,WCD 穿戴者就可以和心电监护中心联系,尽量选择在心电监护的稳定期脱卸设备和清洁身体,避免在电风暴危险期脱卸设备[6-8]。
5 小结
早在2017年美国就有超过76 000 人次佩戴WCD,目前我国只有54例 WCD 应用病例。 随着WCD 的推广和技术的不断成熟,相信我国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从WCD 应用中获益。
我国应该将WCD 和远程心电分析中心的优势结合起来,发展有中国特色的WCD 服务体系。将计算机程序和人工监测相结合,以人机对话方式与患者及其家属和处方医师交流,进一步提高WCD 的实用效果,提高除颤的精准性、安全性,并帮助了解病情演变、提供脱机期间安全建议、提供动态心电分析报告(包括心电散点图),为我国危重心脏病患者救护、猝死预防,创立更为有效的急救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