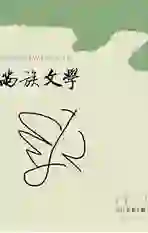再造异同:文化变革时代的青年写作
2021-06-29唐诗人
唐诗人
何谓文学的新颖?
今天,我们談论青年作家的时候,最经常听到的一种声音可能就是现在的青年作家并没有写出什么让人耳目一新的代表性作品出来,认为青年作家们可能写了很多很多,名字出现在朋友圈、刊物目录上的次数非常多,但故事普遍都不够新鲜,作品内在的思想也不够锐利……对于这些观点,我们已经见惯不怪,不管是不认同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有同感,多数时候也只是应和几声,认为这只是聊天需要的话题而已,并不对各自的观点太较真。但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在这些“没有新东西”和“不够锐利”等一类声音背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文学心态,是没看到新故事,还是再怎么新的故事都无法让现在的人感动和震惊了?抑或是,在这个焦躁而功利的时代,我们阅读文学的目光早已无法过多地停留在这些未经时间淬炼的新鲜文本之上?这是一个新的崇拜经典的时代,在各种教育人士、机构和出版商的营销下,今天被冠上“经典”的作品已经数不胜数。繁忙的时代,阅读的时间本来就少,留给经典的时间已经远远不够,如何又能让更多人愿意匀出一些“余光”停留在年轻作家的作品上?这些其实都是今天的青年写作需要面对的时代性问题。
没有时间品读、细读,我们对文学作品的“新鲜感”判断必然会出现问题。多数时候,文学层面的新鲜感都会指向故事、内容、情节方面的新颖和奇特。故事太简单,内容太平淡,情节太日常,这些问题当然是作品缺乏新鲜感的表现。但是故事不简单、内容很新奇、情节很突兀,似乎也不能说明这个作品就足够新鲜。人之为人,我们都有着喜欢听奇闻异事、看奇葩人物的人性基因,所以通俗小说向来都有大量的读者,怪诞新闻也都能获得很可观的点击率,而且我们往往也能从各种市场通俗读物和各类新闻事件中感受到各种挑战我们接受限度的新故事和新消息。如果我们直接把这种人性趣味上的猎奇感与文学阅读中的新颖性需求进行对比,很容易就能分辨出它们不能相提并论。但很多时候,人们对一些新作品只匆匆掠过几眼就下判断说不够新颖,这种“新颖”是不是相当于猎奇感层面的“新奇”?可以肯定,很多人抱怨说青年作家的作品故事陈旧,这个“陈旧”就是不够奇葩、不够怪异,不能比社会上光怪陆离的新闻事件更抓人眼球。文学不是新闻,小说也不直接等于社会故事,如果是这一层面的新鲜需求,这一所谓不新颖的抱怨也就难以成立。
显然,对于更为专业的读者而言,并不会把文学层面的新颖、创新等同于故事、情节方面的新奇与怪异,更多的时候是指向一种文学经验意义上的缺乏新意,更深入一些则是文学思想、文学观念层面的陈旧。在经验层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很多差异,所以生活经验也跟这个世界上的树叶一样,不可能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也不可能有两个生活经验完全一致的人。如此,从生活经验差异来言说文学经验的差异性,认为文学经验的创新是来自于作家个体的生活经验层面的独特,这也是不能成立的,起码它是不够充分的。文学经验不等于生活经验,那它会是何种意义上的“经验”?很多人都知道高尔基说过“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句话也成了很多文艺青年的口头禅,这“来源于生活”可以理解成我们每个人的具体的生活经验,但这“高于生活”该如何理解,却是众说纷纭了。最简单的理解是概括、提炼生活经验,深入一点的理解则可能是从文学意蕴、思想价值层面来重组经验,把具体、琐碎的生活经验升华为文学想象力统筹之下完整的、有精神意义的文学经验。但真正升格为文艺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经验,则一定是融合了作家、艺术家想象力之后的、带有创造性品质的经验。如此,经验问题可以转移到作家的想象力问题。真正决定一个青年作家创造力、创作水平的因素,往往并非作家个人有多少独特的生活经验,而是作家的想象力和思想能力。
想象力作为思想力
文学的新颖,最重要的不是经验故事意义上的多么独特、怪异,而是想象力和思想性层面是否足够创新,这应该是我们判断青年作家创作价值的核心所在。先说想象力,对青年作家想象力的认知,也有类似于文学经验与生活经验差别性的误解,它也经常性地被言说为奇谈怪论意义上的故事想象,而非生活细节、故事逻辑和人物内心意义上的想象能力。文学的想象力,可以表现在故事内容方面,这对于通俗小说、类型化的网络文学创作而言显得特别突出,它们的确需要作家放开一切禁忌去架构各类可能与现实生活完全不一样的或奇幻或诡异或历史虚构的故事,引导读者进入一个纯粹虚拟的故事空间,沉浸其中体验到阅读的爽感,也感悟到一些基本的生活体悟和生命哲学。但对于我们今天探索的纯文学意义上的青年作家而言,考验他们想象力的不是故事内容的虚构想象,而是对自己所书写的生活本身的想象能力。何谓对生活本身的想象能力?这关联的是思想能力的问题。
文学创作的想象力是离不开思想能力的,作家有多深刻的精神洞察力,对生活对现实有怎样的文学感觉和思想认知,这会决定一个作家的想象力通往何方。鲁迅写阿Q、写孔乙己、写祥林嫂,等等,为何专注于揭示这些人物的无知、愚昧和被压迫、被伤害的一面,这些都源于鲁迅深刻地洞察到了当时国人精神深处的奴性问题。鲁迅要通过这些方面的故事情节虚构和人物性情想象来完成一种国民性批判,为的是唤醒当时人的反抗精神,有着清晰的思想启蒙和民族革命意识。我们当然不能说鲁迅生活的那个年代到处都是阿Q、祥林嫂这样的人,更不至于认为鲁迅只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但鲁迅对历史、对当时的国民性有属于他自己的清晰的精神判断,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深刻的思想洞察力,他才能明晰自己该如何组织各类直接或间接的生活经验,以及如何结构故事的精神逻辑和叙事逻辑。想象力在这个过程中,不是天马行空地随意虚构一些自以为独特的情节故事,而是被思想见地、被精神逻辑所指引。想象阿Q被打后不愿说自己“是畜生”而选择说“我是虫豸”,这类细节都服务于小说的精神主题,并非可有可无的、作家随性安插到小说中的零碎经验。还如当代的莫言、贾平凹、陈忠实等小说家,他们塑造的一些经典性的人物形象,像《红高粱》中的“我奶奶”、《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废都》里的庄之蝶,等等,这些形象的出现,并非简单的因为这些作家有这类经验,更是因为作家书写这些作品的时代、现实“督促”着他们去完成这样的角色塑造。所谓时代现实,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更直接地表现为文化语境,比如莫言八九十年代之所以会塑造出一系列原始的、野生而真实感突出的英雄人物,这是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影响之下中国作家在文学观念和人性认知等方面都发生巨大变革之后的选择。莫言愿意把目光转入自己家乡的历史故事和英雄传奇,这也与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化寻根思潮有关系。包括贾平凹写《废都》,背后也是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物欲时代开始来临等历史文化语境。贾平凹作为一个传统的乡土知识人,他对欲望都市的人性发展有自己的精神判断,对传统知识人遭遇现代都市必然会发生的故事也有自己的思想结论,这些精神判断和思想结论决定了他的人物设定和故事性质,自然也就支配着作家如何发挥想象力去组织素材和安排情节。
文学想象力勾连着文学思想,而文学思想又必然离不开作家创作的历史背景和時代语境,详述这一内在的文学创作逻辑,为的是回答文章开端处关于青年作家创作的新颖性问题。青年作家若想自己的作品真正站立在当代文学史长河中,要完成的必定是植根于当今社会现实语境下的创造性突破。这种创新突破,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青年作家要去展现某种独特的生活经验,也不是让青年一窝蜂地通向网络文学的“爽点宇宙”,而是指向一种青年人对于今天这个时代的精神认知和思想见解。没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和思想层面的宏观把握,青年的经验就永远是琐碎的、零散的情节或事件,无法成为能链接历史、穿透现实和通往未来的文学经验,如此写出数量再多的作品也难给人深刻印象。只有零碎的个体经验,而无针对当前时代的宏观判断,写作就缺失了最关键的创新品质,谈何进入文学史长河?
通往宏大经验
宏大性的时代精神判断,它可以彻底改写我们日常经验的文学去向,也决定了当代人生活经验的性质和价值。但形成与确立一种宏大的思想并不容易,这也是无数作家梦寐以求的头脑知识。尤其在今天这个知识过量的时代,关于“思想”本身的知识就已纷繁芜杂,我们又如何确认某一种思想可以升格为具备时代感的宏大判断?又谈何某一个作家呈现的个体经验超越了琐碎性而具备了时代性?这些都是当前文学界正在直面的思想困境,不仅是作家创作的精神难题,也是评论家评论写作的思想难题,换句话说,这是整个文学界需要着力的所在。
其实,时代性的、宏大化的精神内容,并不是一个毫无征兆、隐迹于生活世界的诡秘观点,而往往是我们生活中那些感触最深的部分。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名家谈文学创作时会建议青年作家要往内心深处看,像里尔克写给青年诗人的信里就表达过这种观点。这种“向自己的内心看”的写作,如何能够与宏大的时代性精神问题牵连起来?这里面的“内心”,绝不等于浮在表面的、零零碎碎的心理情绪,而是剥离开日常事务的烦恼进入内在灵魂的一面。换句话说,真正值得我们去凝虑的问题并非局限于一日三餐如何解决这一类具体事务本身,而是深入到“我”以及更多人为何会一日三餐都解决不了这样一类普遍性问题上来。最内在的内容一定是问题的最根本所在,最根本的困境也必然与最普遍的问题有关系。对于作家而言,最个体的经验并非自己经历过何种别人没有经历过的世俗生活,相反,作家反而要注重那些自己与其他人所共享的日常生活经验。但不同的是,作家能够看到普遍性生活背后的根本性困境,能用故事、用文学的语言把握住这些日常化、普遍性生活内部的普遍性情绪和精神逻辑。对于评论家而言,最感兴趣且能阅读下去的一定是那些能产生共鸣且最终能有所启发的作品,没有共鸣就引发不了兴趣,没有启发也就意味着作品缺乏创新。评论家是专业读者,但开始阅读的那一刻也可以是一个普通读者,对于多数青年作家而言往往还是最有效的阅读者。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文学共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合作”问题。青年作家可以从评论家的阅读评论中了解到自己的写作是否具备,或者具备何种意义上的普遍性精神观照。发现超越个体的、他人也在思索亦有同感的普遍性问题,这是通往宏大经验的重要一步。
走出个体经验的迷思,通往新历史时代的宏大经验,意味着作家要重新理解经验问题,要重构我们关于文学经验异与同的内容理解。重构的缘由在于时代的变化。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无论是生活世界的日常事物,还是知识层面的思想文化语境,都与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有了巨大的改变。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推崇解构的时代已然过去。新世纪之后,不管是社会生活还是知识话语,都逐步进入了一个建构的时代,各个行业、知识领域都在强调创新和重建。有心的作家、评论家还会发现,这些年所推重的创新和建设,其基本的精神逻辑都是回归到我们自己的、本土化的生活和思想,是用我们最真实的心理经验去重构历史故事和西方知识,是以当下性为基点来融合古今中外的知识话语,以锻造全新的、对我们生存现实有深刻洞察的思想见解。
“和解”作为时代命题
今天,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物质现实与从各类渠道中接触到的文化现状,都处于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状态。尤其近十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知识语境,已经清晰地展示出了这一时代性的精神脉络。比如政治话语提倡的文化复兴,也如人文哲社科研究领域盛行的“中国话语”,这一类时代性的知识状况,是作家需要去直面的最清晰可见的现实语境。遗憾的是,这类宏大性的精神主题,经常被一些作家简单地理解成一种政治话语,以至于刻意地被回避。作为新一代青年,应该放弃前几代人因为特殊历史原因而形成的那种简单刻意的话语成见,去直面我们正在遭遇着的时代性问题,包括当下性的政治文化语境,等等。我们若从宏观性的历史判断和时代精神来思考问题,会明白一个清晰而不可忽视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常识: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而言,任何时候都忽略不了政治文化话语。中国是政治文化大国,文化政治语境往往是作家开展文学创作时最需要去直面的问题背景。这里的文化政治指向的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现状和文化治理展望,它具有较为间接的社会问题针对性,与更清晰的时代性文化精神判断和文明史发展前瞻性顾虑。关注文化政治问题,从文化政治视域来把握今天中国人所关注的问题所在,这是作家与当前社会现实问题和文化问题保持同步思考的重要方式。
面对当前这一全新的文化政治语境,我们的作家能够提供何种意义上的精神诊断?又能够凝练出别样的思想见解吗?它们能在何种意义上改变今天作家的文学经验和作品风貌?这些疑惑都等待着今天的青年作家去解答。一种宏大化的知识语境、文化氛围的转变,对于敏锐的作家而言,必然是一个重新建构自己文学理念的契机。文学理念的改变,也就意味着进入文学内部的生命经验会被改写。其实,这些年我们已然看到很多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发生了这样的转型。比如,深圳作家吴君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万福》,小说写出深圳城市发展如何改写了一些个体、家庭的命运。当年“逃港”到香港的人,面对家乡的迅速发展,自身却错过了这样一种发达的机会,他们再无可能“衣锦还乡”。当年的“逃港”是求发达的选择,如今的“回乡”是失败还是赎罪?他们该如何去与故乡、与乡亲达成“和解”?这是一个包裹着宏大历史与个体情绪的故事,吴君最终让他们实现了“回乡”与“和解”,完成了一个真正的“万福”结局。其实,这种“和解”对于《万福》这个小说故事而言总有一些突兀,但作家这种结局设置,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时代性的宏大的情感需求——和解。人的和解问题是近些年文学作品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的精神主题,尤其在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中,多数还能够表现得特别自然。如马拉的《鲨鱼》、蔡东的《伶仃》、温文锦的《家族事件》《旅馆女孩》、宋阿曼的《堤岸之间》《白噪音》、王哲珠的《何以归》等。《鲨鱼》中的男女去海边吃鲨鱼肉,本是要感受“刺痛”,但小说写得隐忍,最后鲨鱼刺并没有浮出水面,反而抵达了内心的平和。蔡东的《伶仃》也一反之前专注于写现代人分裂感,开始写个体与家庭与生活的和解。《家族事件》里的女孩,家庭突遭变故,但作者并没有夸张地去写这个女孩的绝望,而是写她如何逐渐接受现实,包括如何接受突然之间来到身边照顾自己的“外人”,这种平静感、和谐感,看似不太真实,却似乎也是新一代人面对不幸时所普遍具有的心理素质。《堤岸之间》的一对老夫妻,相处了一辈子,各自对对方的怪毛病都了如指掌了,但无论心里怎样嫌弃,最终表现出来的行为选择还是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另外,还有很多青年作家的作品都在“和解”主题上展现了感人的故事和精深的思考。
或许,在“和解”这样一个精神主题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一代八零后、九零后青年作家作品中感受到一种共通性。青年对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时代的“和解”问题如此关注,这难道不是一个普遍性的思想问题?而且,这一精神主题也契合着当前时代的政治文化语境。现代人都追求独立,都在努力确立属于个体的独特性,这种追求并不是问题,如今也还在继续。但此前的追求是要经过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完成的,即必须经历一种撕裂,但这种撕裂显然是如今青年不再需要的。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力量都开始趋向科学、理性,甚至是人性化了。青年寻找自己的价值不再需要刻意去与某种力量形成激烈的冲突,人与人之间有差异、有矛盾这一人性状况已是人们相处的基本常识,谁再去为丁点的性格差异、观念差异而纠缠不清就显得可笑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和解”成为青年一代作品中普遍性的思想主题也是顺理成章的。
“和解”作为时代性精神主题,这必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代际文化,更可以是一个贯通历史、面向未来的文化话题。陈来在论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时曾指出:“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机械论的宇宙观相比,古典中华文明的哲学宇宙观是强调连续、动态、关联、关系、整体的观点,而不是重视静止、孤立、实体、主客二分的自我中心的哲学。从这种有机整体主义出发,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每一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故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与文化应当建立共生和谐的关系。”(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第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和谐”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大精神传统,“共同体建构”更是一个宏大的文化政治问题。文化变革时代,青年完全可以在“和解”问题上做出更多的思考,青年作家可以通过文学创作与这个时代的文化建构关联起来,用更完整更系统的知识重构我们时代的文化脉络,以更为阔大的经验再造我们生活中的异与同。文学不仅仅是人学,它也是文化的学问;人学也不只是个人的学问,它更是人类的普遍性的知识。文学可以以小写的、个体的人为精神起点,但终点不应该还是小写的人、个体的人。身处互联网时代,万物已经互联,人与人如何能满足于割裂?作为最贴近人的内心、与灵魂最近的文学,它可以思考更普遍的人心,也需要观照更宏大的世界。
【责任编辑】邹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