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楚辞学研究学术特色发微
——以《楚辞校补》为中心
2021-06-29吴静艺
吴静艺
《楚辞》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对其研究一直是历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内容。20世纪前的楚辞研究受到宗经及比附义理的思维模式影响,缺乏对发展过程的总体把握,限制了发展。20世纪后,在“西学东渐”的时代大背景下,涌现出许多重要的楚辞学研究人物,楚辞研究焕发新的活力。其中,闻一多有诗人、学者、斗士多重身份,自认为“文学史家”,其楚辞研究形成独特鲜明的学术风格。闻一多研究楚辞,以扎实的校勘与训诂作为根基,《楚辞校补》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目前,学界关于闻一多楚辞研究的著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之纳入闻一多学术生涯的一个部分进行总体概述,如刘煊及张巨才、刘殿祥。但刘煊对楚辞学研究的介绍比较简略[1],张巨才、刘殿祥对其楚辞研究成果则主要突出对作家作品的新阐释方面,较为单一[2]。另一种则从其楚辞研究的整体内容,联系其学术背景、生活状况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如闻立树、闻立欣称扬闻一多在艰难的战时仍不失学者风范,但对《楚辞》研究的各项成果没有展开具体论述[3]。李中华、朱炳祥指出,闻一多《楚辞》工作主要在文字校正、词义诠释以及从民俗学、神话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指出其研究中立论不够精确等不足之处,较为公允客观[4]。
但是,针对闻一多楚辞学研究中最基础、不可或缺的工作——校正文字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探究其学术特色则罕有,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本文主要立足于闻一多楚辞研究中基础性和代表性的校勘类著作——《楚辞校补》,详细分析其版本校勘方面的特色,以小见大,总结闻一多的学术思想特色与价值,以彰显其楚辞学研究的独到之处。
一、《楚辞校补》内容提要
闻一多在《楚辞校补》引言中归结了较古的文学作品难读的三种原因,《楚辞》正是集合了这三种困难的一部古书,因而在研究时,他据此定下三项课题:说明背景,诠释词义,校正文字。限于时间,他在《楚辞校补》书中着重校正文字,这也是解读《楚辞》的基础性工作;诠释词义与文字校正相结合而兼有,说明背景一项则几为略。闻一多在《楚辞》上花费的时间已近十年,故此书确有重要学术价值。
(一)文字校勘
《楚辞校补》以洪兴祖《楚辞补注》为底本,参考引用王逸、刘师培等大量古今诸家旧校材料,并新采校勘材料,亦采用古今诸家成说之涉及文字者。其主要论列内容有五方面。一是今本误而可据别本改正者,如“终然殀乎羽之野”。闻一多指出,鮌非短折,不当称殀,殀当从一本作夭,夭之为言夭遏也,夭遏止之不得反于朝之义。王《注》误训为蚤死,后人始改正文以徇之。唐写本及今本《文选》并作夭。二是今本似误不误,当举证说明者,如《离骚》“举贤而授能兮”。朱骏声谓授为援之误,闻一多按朱说非也。受、授古同字,授能犹用能也。援、授二字因形近而古书多相乱,当据本篇及《庄》《荀》之文以订正,朱氏反欲援彼以改此,疏矣。三是今本用借字,别本用正字,可据别本以发明今本之义者,如《离骚》“又重之以修能”。闻一多指出,按朱校,能一作態。能、態古字通。并征引《怀沙》“非俊疑杰,固庸態也”,《论衡·累害篇》引作能等例,说明能或为態的假借,修能当为修態,谓容仪之美。四是各本皆误,而以文义、语法、韵律诸端推之,可暂改正以待实证,如《天问》“逢彼白雉”。按雉当为兕,声之误也。闻一多多举典籍中雉、兕混用之例,并以文献等印证此义,此处当为兕而非雉。五是今本之误,已诸家揭出,而论证未详,尚可补充例证者,如“纷独有此姱节”,按节与服不叶,朱骏声谓当为饰之讹,是也。闻一多举《韩非子·饰邪篇》“国难节高”,今本误作饰等并作补证。盖饰节形近,往往相乱。对于诸家已精确,而论证亦略备,无可附益者,此书概不征引。
(二)诠释词义
闻一多诠释词义基本建立在校正文字的基础上,如对于《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王逸《章句》释“顾”为“顾望”,后世多承其说,而闻一多在《天问释天》一文中取证十一项,说明此“顾”字不当作“顾望”解释,“顾菟”即是“蜍蟾”的异名。后又在《天问疏证》里进一步修正了自己的研究。闻一多提出,“顾”疑当读为“踞”,月中有踞菟,盖犹日中有踆乌。月中蟾兔,长跪捣药之状与踞相似,而有此义。最后,还推测先秦可能已有月中白兔捣药的传说。
(三)错简重定
在《楚辞校补》书中,闻一多亦进行错简重定。他提出《九歌》十一章皆祀东皇太一之乐章,“吉日兮辰良”与“成礼兮会鼓”二章分别为迎、送神曲,其余各章皆为娱神之曲,各以一小神主之,诸小神两两相偶,共为一类。则东君与云中君皆天神之属,宜同属一组,其歌亦当相次。今本二章悬绝,义不可通,可见应为错简。闻一多提出《东君》当在《云中君》前,而《少司命》可与《河伯》首尾相衔。
二、《楚辞校补》中体现的治学方法与态度
(一)传统朴学的秉承与审慎严谨的态度
闻一多精于中国传统治学研究方法,深受清代乾嘉朴学影响。由此,他在面对版本繁杂、异文纷出的《楚辞》时,以文字校勘作为基础。《楚辞》传世本汉王逸《楚辞章句》和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历代以来多校注,导致众说纷纭。因此在《楚辞校补》中,闻一多运用多种版本的文献进行校勘文字,同时以训诂、音韵等传统小学的方法综合分析,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与严谨务实的学术作风。
在研究过程中,闻一多广泛征引古今诸家成说达二十八家,搜集据以校勘的材料六十多种,再结合训诂之法等分析,足见其审慎严谨的学术态度。对于可改错讹、似误不误、发明假借义等,闻一多则综合文字、音韵、考据等多方面分析后而改之。对前人正误之说有理可依者,闻一多征引其说,并补充材料以佐充之。如《天问》“何罚何佑”,闻一多首先陈列刘说以肯其实,继而又补王《注》以进一步佐证,可见其慎[5]170。而对于疑各本皆误,据文义、语法等推之而暂无实证者,闻一多亦不强解,只是陈列一说,以待后鉴。如《离骚》“览察草木……谓申椒其不芳”,闻氏陈明苏、艾之事同类相邻与总评分置首尾以相呼应之理,提出疑虑,不下决断之言,而俟后达[5]137。凡此诸类,都可以体现他实事求是、审慎严谨的治学态度。从总体上看,闻一多先生继承了王念孙父子等朴学大师治学精严的精髓。古人治学过程中所时常出现思维僵化和过分阐释等问题,闻一多却做了很好的改进,因此可以说他的楚辞研究是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却又不会因此拘泥于古人研究的有机传承[6]。
(二)近代研究成果的利用与开拓创新的精神
闻一多接受过西方社科教育,这使得他能够采纳西方学术的长处,思维方式开阔。他较早运用许多近代的研究成果与理论,从考古、神话、民俗等多方面对《楚辞》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创新性。首先,考古方面,闻一多积极利用当时新兴的出土甲骨材料,将其记载的内容与《楚辞》文本内容进行比照,对许多疑难问题提出了新解。如《天问》“逢彼白雉”,闻一多征引《殷墟兽骨刻辞》多次记载获白兕之事,推言周初承袭殷俗,以获白兕为盛事,以此作为一个旁证,说明此句所写昭王逢遇,当是兕而非雉。其次,闻一多关注到了神话对于古代文学创作的影响,并总结出一些神话形态在文学创作中的流变。如《天问》篇“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闻一多按当从一本作“应龙何画,河海何历”,指出应龙画地成河之说,汉魏以降,流传不绝,不得以先秦古籍罕言而疑其晚起。再次,闻一多运用民俗学的知识,将楚文化的地方特色以及民间习俗等和《楚辞》内容关联,从而研究语词运用以及分析词义。他把民俗学和社会学等新理论引入传统典籍注释中,突破了之前经学家专重文字义理训诂而脱离语境、不切实际之弊。如《离骚》“索藑茅以筳篿兮”,闻一多指出,疑此亦以藑为正。古卜筮之具或用竹或用草,故此云“索藑茅”当为以草卜。闻一多综合运用多种新方法研究古代传统文献,在此基础上提出许多新观点,具有很大创造性。这些观点几乎都建立在扎实充分的论证上,故而对后来的研究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总结来说,闻一多治楚辞学之研究,恰如郭沫若所言:“他(闻一多)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5]432
三、《楚辞校补》的学术价值、影响与不足
闻一多研究楚辞近十年,可谓用功甚巨而成果颇丰。其《楚辞校补》的学术价值,大致可从考定旧说与提出新解两方面来归结,前者主要包括文字校勘方面的匡正前人错讹,破除假借,发明似误而不误之义和补充阐明论说之未备者;后者主要包括对于错简重定、基于新的研究方法提出的新观点等。事实上,这两方面的内容之间紧密关联,此处加以区分仅为说明之便。
一是考定旧说方面,闻一多广集校勘材料,参引诸家成说之涉及校正文字者,对于前人字误、音误、义误等进行细致考定,所成《楚辞校补》一书可谓《楚辞》校勘集大成者。字误如形近而误,如《远游》“玄螭虫象并出进兮”,闻按“象疑当为豸,字之误也。豸豸俗作,与象形近,故误为象”[5]201;音误如失韵之误,如《天问》“玄鸟致贻女何喜”,闻按“喜当从一本作嘉。嘉与宜韵,若作喜,则失其韵矣”[5]165。二是提出新解方面,闻一多基于学术思想与方法而提出的新观点,广泛涉及文字、文义等多方面。文字方面,如《天问》“胡终弊于有扈”句,闻校“案王氏谓扈为易之误,是也,其说易字所以致误之由则非,易卜辞作,金文作,右半与篆书户字相似,而有扈字本只作户”[5]166;文义方面,如基于民俗学方面,古人形容美貌,独重视笑,故每以目与口齿并言,提出《湘君》“美要眇兮宜修”,按修疑当为笑,声之误也[5]141。
简言之,闻一多补正旧说,裁定错简,提出新解等成果,为后人研究《楚辞》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他将古典文献研究与近代社会科学的方法结合,开阔传统研究的思维方式,他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对推进《楚辞》学研究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当然,闻一多的研究中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过度追求句式、内容的整齐条理而擅改典籍文本,否认古籍产生和流传过程中的自然规则,违背古籍校勘尊重原貌的基本原则。二是部分新解实证不足,有待进一步考证确认。三是过度借助通假训释字词,而这一般难以有确证(1)笔者此处观点受杨庆鹏2008年发表的硕士学位论文《论闻一多的楚辞研究》与袁謇正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4期的《闻一多〈楚辞〉研究的基本层面》两篇论文重要启发。。但总体来说瑕不掩瑜,闻一多楚辞学研究的方法与成果对后世的积极影响是最主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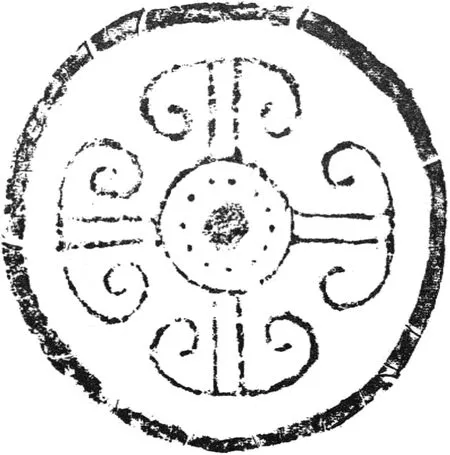
秦 云纹 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出土
四、结语
20世纪楚辞学研究的新发展中,闻一多出色地将传统朴学的考据方法与近代研究成果、理论结合,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同时持有积极开拓创新的精神。闻一多倾注十余年心力于楚辞学研究,尤以文字校勘为研究的首要课题。《楚辞校补》作为其文字校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鲜明地体现了闻一多传承与超越、融旧与开新的综合性学术特色。闻一多楚辞学研究考定旧说,推陈出新,具有重要价值。他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共同为后来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对推动楚辞学研究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