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的“ 去世俗化”:贝多芬是位圣乐作曲家吗?
2021-06-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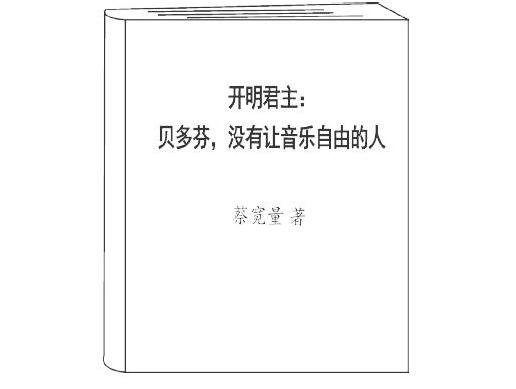
摘 要:在西方音乐的叙事之中,世俗化的贝多芬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神话吗?讲座探索了贝多芬的“圣乐”这一音乐类别与他启蒙运动倡导者这一身份背后的意识形态之间所形成的张力。如果这种世俗性的观点是可疑的,那么这是否会将贝多芬逆转成为一位保守者?这是否会让许多已被公认的音乐学术成果烟消云散?或者,是否还有另一条前进的道路呢?
关键词:贝多芬;圣乐;启蒙运动;自由;《庄严弥撒》;《槌子键琴奏鸣曲》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2172(2021)01 - 0003 - 16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1.01.001
引 子
非常荣幸能够在四川音乐学院做这次主旨讲座,以此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非常不幸的是,因为2020年的新冠疫情,我不能亲自到场,与你们面对面地交流。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做讲座,而且在座还有众多杰出的中国学者。我倍感压力,所以得好好表现,一定要给诸位带来一次非常棒的主旨讲座;因此,这篇文章我下足了功夫。事实上,为了准备这次讲座,我甚至写了两篇文章—— 一篇短的,一篇长的。如果你们之前听过我的讲座,或许你们会希望我讲短的那篇。但那篇短的文章实在是非常短。事实上,它只有6个英文单词。当然了,我花了很长时间把这几个单词串起来——我精心挑选了这些词语,它们都非常有深度——但如果我的演讲比我的标题更短,这似乎不太对劲。
我今天讲座的标题是《贝多芬的“去世俗化”:贝多芬是位圣乐作曲家吗?》(De-secularizing Beethoven: Is Beethoven a Sacred Composer?)(共7个英文单词)。
而我的这篇短文全文如下:贝多芬不是位圣乐作曲家。(Beethoven is not a sacred composer. ) (共6个英文单词)
由于我觉得自己这篇演讲过于简短,这样很糟,所以我决定给短文加上两个英文单词,让它比我的标题更长:贝多芬不是位圣乐作曲家。完结。(Beethoven is not a sacred composer. The End. )(共8个英文单词)
但是除非我们需要大量时间来提问,否则我还是决定要讲讲我那篇非常长的文章。这篇长文正好是以短文中的悖论开头的——这场讲座关于圣乐,但却聚焦于一位非圣乐作曲家。事实上,我加上的这个“完结”是相当合适的,因为正是贝多芬导致了圣乐的完结。与其说贝多芬不是位圣乐作曲家,倒不如说他不能成为一位圣乐作曲家。
贝多芬通过重新定义“圣乐”,将自己排除在这一领域之外。这是他的无心之举,他无意在自己的接受史中制造出这样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个神话,就像大多数有关贝多芬的叙事一样,也就像大多数神话一样,它的“半真半假”会强有力地生成意义与行为。这是个重要的神话,因为它通过重新定义圣乐,将圣乐置于贝多芬音乐所代表的一切的对立面。
一、世俗策略
在20世纪来临之时,艺术家们如麦克斯·克林格(Max Klinger),简直就是将这位作曲家放在了神龛之中,贝多芬神一般的地位与“神圣”之间并非良性的对照(见图1)。他是个对手。要解开圣乐的问题,其关键就在于理解这一神话如何起作用;因为在对圣乐的重新定义中,贝多芬处于核心位置。
在贝多芬之前,西方的圣乐就仅仅是圣乐而已。它是欧洲基督教信仰(包括天主教与新教)的核心。这种音乐专为荣耀上帝而存在,“为神圣崇拜的仪式而创作”。它是音乐“最高的”感召,它与俗乐的区别在于俗乐目的较低——不管这些俗乐形式是否被视为世俗的、堕落的或可以作为宗教用途的。一些音乐学者今天仍然相信这种关于圣乐的高定义,但他们只是一群过时的老古董,挤在一些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的西方古老大学里。但总体说来,学者们不再信仰圣乐了。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答案就是“贝多芬”,但这不仅仅是“贝多芬”,而是一个特定的“贝多芬”,与之相随的是一句口号:贝多芬,“让音乐自由了的人”。这是一本出版于1929的書的标题,作者是美国作家罗伯特·黑文·肖弗勒;但从那时起,这个标题便脱离了这本书,成了一句关于英雄性贝多芬的流行格言。①当然,在中国,人们所接受的也正是英雄性的贝多芬。关于这句格言在贝多芬神话中的地位,已故的K. M.尼特尔曾用圣经典故这样描述道:“正如摩西带领他的人民走出埃及一样,贝多芬也是如此,是‘让音乐自由了的人。”②
如果你觉得将贝多芬比作摩西听起来太夸张,那么你应该听听肖弗勒自己是怎么说的:“贝多芬犹如耶稣一般 —— 他创立了一个宗教。”①而且这并不是个宗教隐喻,他的书中反复出现的这种说法取自贝多芬的一句俏皮话,这句话出自伊格纳兹·莫谢勒斯(Ignaz Moscheles)为《菲岱里奥》所改编的钢琴缩谱。莫谢勒斯虔诚地写道“在神的帮助下完成”②,在这句话的下面,贝多芬又附上了一句 “世人啊,帮助你自己”。这句俏皮话被肖弗勒严肃地当成了信条。他写道:“贝多芬所说‘世人帮助自己的精神越来越多地鼓舞着人性。从‘伟大战争以来,德国和奥地利实际上开始出现一种强烈的倾向,朝着一种力量和自力更生的现代宗教前进,而贝多芬正是这种宗教的创始者。”③
贝多芬究竟做了什么,让他获得如此宗教般的赞颂呢?
让我们先仔细看看,说贝多芬是“让音乐自由了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请注意,这个头衔并没有指明音乐是“从哪儿被解放自由的”或是“为什么而被解放自由的”,就好像这是不言而喻的一般;肖弗勒把这个神话视为理所当然,仅仅抛出了一句流行语而已。头衔中的“自由”一词实际上既是主语,又是宾语,又是动词,又是形容词……实际上,它什么都是。“贝多芬,这个自由的人自由地让音乐为了自由而获得了自由”才是这个头衔真正的意思。这是一种对“自由”的混淆和异文合并。“自由”既是手段,又是终点。贝多芬既是解放者,又是被解放者,还是解放的。正是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将贝多芬置于克里斯托弗· 施沃贝尔所谓的“现代普遍性”之中。贝多芬是“自由”的人格化身,施沃贝尔写道,自由“在现代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本原则”④。
这又给我们带来了第二句流行语:贝多芬,让音乐自由了的人,不仅仅是“某个”人,而是“人类”,因为他所呈示出的“自由”定义了人类何以成为“人类”。的确,在汉斯·海因里希·埃格布莱希特所著的《贝多芬接受史》中,作者认为有一个“接受常量”将所有各种各样的历史材料汇集起来,就好像这全都是由一位作者所作;而这个“常量”就是“人类”。⑤“自由与人性”是这个神话的意识形态核心。作为自由的象征,“自律”成了人和音乐的本质,而贝多芬作为“让音乐自由了的人”则让这两个概念合而为一。这就是为何肖弗勒的标题在贝多芬神话中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回响并成了这个神话中的格言之原因所在。
然而,正是这个神话般的贝多芬重新定义了“圣乐”。在贝多芬的统治之下,圣乐的反面不再是俗乐,而是自由。那么音乐中的自由又是什么呢?一部从性质上来说自律且“非功能性”的作品——这种音乐能自由地作为其自身而存在,不为其他任何目的而存在。一旦被解放,音乐就成了一种自治的客体,康德会认为这是一种“无利害的关注”。“音乐的功能就是无功能”,它的用处就在于它的无用,它的利益就在于它的无利益。这种极端的异化正是为了保护它的自由本质,似乎任何对它的“利用”侵蚀都是滥用。
想象一下,当圣乐被定义为这种音乐的反面时,会有什么危机呢?将贝多芬视为音乐的自由斗士,圣乐便站在了“现代普遍性”和“自由之存在”的对立面。圣乐突然就成为了对自我和自由的威胁。
二、神话策略
鉴于这些高风险,我们应当检视这个神话是如何运作的,以便看清在这一“重新定义”之中,圣乐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这个神话中,有三个策略性的步骤:
1.为重新定义打好基础的前提假设;
2.驱动其价值观的意识形态;
3.为其加上各种可供选择的叙事,以便为观点提供历史证据。
(一)前提假设:非功能性 vs 功能性
这个前提假设非常简单,而且似乎是中立的。基本上来说,它是一种对立关系,即非功能性和功能性音乐之间的对立。这第一步是个简化的策略。在这个二元对立关系之中,圣乐的所有属性都被简化成了功能,似乎它的定义就只是它的用处而已。这意味着,圣乐所有与众不同的价值此时都被归入了一个平淡乏味的范畴之中;曾经专门用于宗教的音乐,现在与其他本来就具有功能性的音乐类型归为一类。所以现在圣乐与世俗的进行曲和舞曲混为一谈,特别是与其他具有更高目的的音乐(即用来展示王权的“宫廷音乐”)出双入对。那么,贝多芬所做的便是以非功能性音乐的“非”来否定教堂和宫廷音乐。贝多芬著名的怒视仿佛是在看着圣乐并说道“不是这个”。
(二)意识形态:自由 vs 奴役
下面是第二步——意识形态。圣乐被简化成仅仅是功能性音乐,在这一前提假设确立之后,又加上了一个意识形态价值观,将非功能性音乐从一个否定的概念,即用“不是这个”来反对圣乐,转化成了一个肯定的概念,即用“而是这个”来肯定非功能性音乐。为了让非功能性音乐变成一个正面肯定的概念,这个术语被等同为“自由”;相反,功能性音乐便被默认为等同于其负面否定的形象——“奴役”。
当这一意识形态组件归位之后,我们现在便有了“現代性”与“进步”的解放性叙事,而对立面现在则成了线性且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音乐史中,贝多芬将音乐从王权的奴役中解放出来。音乐不再被音乐之外的、由教会或宫廷制定的法则所束缚,正如路德维希·蒂克所说,它现在“指定自己的法则” ①;又根据康德所言,指定自己的法则,正是“自律”的定义。一旦被赋予成为其自身的自由,便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因此,肖弗勒口中的头衔使用了过去式——贝多芬让音乐自由了,这是个单次的、决断的动作。
在这场意识形态分割之中,圣乐站在了错误的一边,与光明的自由相比,它现在变成了一个黑暗的政权。在这个解放性的叙事中,圣乐被烙上了罪名——从政治上来说是可疑的,从人性上来说是压抑的。如果现代世界要进步,它就必须被禁闭于过去之中,任何复兴其地位的企图,不仅会被视为不可持续的,从道德上来说也是可疑的。
(三)叙事
一旦意识形态确立,各种可供选择的叙事就可以安插到计划之中,好让它的推测变成具体的历史。有许多可供选择的叙事,此处仅举出3种被当成历史事实,用来支撑意识形态观点的叙事:一种哲学的叙事、一种经济的叙事和一种政治的叙事。
叙事1:“启蒙”的哲学叙事
音乐从王权的奴役中被解放出来,这相当于康德在回答他著名文章标题中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启蒙?”启蒙是让人性从“固步自封”中解放出来。康德说,获得启蒙即是“独立思考”,“敢于求知”则是他的著名格言。①这种求知便是一种仅以理性为基础的“破除神话”行为,这种行为对牧师和君主强加于人的公认智慧和既有结构提出质疑。那么,要成为真正的人,其决定性因素就是要拥有生成于主体核心的理性自由。因此,音乐的解放便是使其进入启蒙状态,使其能够自律地参与到人类的公共领域之中。相反,圣乐是非理性和私人化的,并非共享公共话语的一部分,它无法超越自己的特异性,没有普适的正当性。
叙事2:高文化经济的叙事
音乐新发现的自由是一种经济上的自由,这种自由将“无用性”留作音乐最高的价值。这种逻辑很奇怪,但也非常熟悉。
首先,作曲家的雇佣身份被斥责为奴役——雇主将艺术家变成了一种功能;第二,自由作曲家的身份被赞扬为艺术上的自律——只有自由职业才是自由;第三,只有当从事自由职业的自由艺术家的产品在市场上没有价值时,他们才是自由的,因此他的自由艺术家身份便等同于失业;最后,艺术家会在贫困中悲惨地死去。
在这套经济体系之中,音乐最高的价值是由自由市场来衡量的,这个市场中的文化价值与其通货价值成反比。在音乐史中,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被用于这种经济的寓言故事中。这个神话差不多是这样的:莫扎特,这位功能性的教会作曲家,在成为自由作曲家之后,葬身于贫民窟墓地,但他物质上的贫困只不过证明了他音乐上的精神财富。这是因为一旦莫扎特从物质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他便不再工作,他只是在玩耍。他的音乐是轻松自如的、非功能性的、无用的,因此也是自由的。另一方面,作为典型的宫廷作曲家,海顿的功能便是工作。只有工作,没有玩耍,这让海顿成为一个迟钝但勤勉的作曲家。接下来是贝多芬。不像海顿和莫扎特,贝多芬从教会和宫廷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他是解放作曲家的典范,他在莫扎特的玩耍之中又结合了海顿的勤勉。②他代表了利迪亚·戈尔所称的“作品概念”,即基本上是玩耍般劳作的产物,这是一种在美学想象中流通的智力通货。③于是自律的艺术作品变成了一种身份象征,一种智力上的财富。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会将其分类为一种文化通货,其使用者是有手段夸耀“无价之物”的那些人。
有鉴于自律艺术的地位,圣乐便几乎丧失了文化价值。它是教会雇佣的产物,因此便是一种功能性的商品,既不能超越市场,也无法追求作品-概念的崇高地位。相反,圣乐现在被划分为“特殊场合”音乐,为某个场合付费而作,只在某个场合具有正当性。这样的应景之作尤其不具有普适性的要求。从其地位上来说,圣乐属于文化的下层阶级。曾经的崇高使命,现在成了低下的使命;曾经对上帝的奉献,现在成了过时的通货。
叙事3:革命的政治叙事
在一个政治革命的时代,贝多芬正是音乐上的革命。“自由”的呐喊建立起了新秩序。当音乐批评家A. B.马克斯 (Adolf Bernhard Marx) 將《英雄交响曲》赞颂为新的“艺术纪元”,他让这部交响曲的英雄性自律成了“解放”的决定性动作。这部交响曲就是革命,它引领着新纪元,使贝多芬成了“让音乐自由了的人”。因此,贝多芬在美学领域中实现了法国大革命在政治领域中没能实现的目标——自由。① 德国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失败的反应,会将革命理想内化为某种审美化的思想或是精神上的革命。贝多芬的音乐是个典型的例子,展现出艺术如何能够以其最纯粹的形式保留“自由”,并将其作为未来的政治希望。席勒如是说道:“艺术便是未来的模样。”②
在这种革命美景之中,圣乐又处于何地呢?它只能代表古旧的政权。从此刻开始,任何对圣乐的回归,都将会被建构为保守的反抗,它的存在只能是人类进步的阻碍。圣乐中的末世论被抛到过去之中,让位于人类的历史目的论。因此圣乐绝不可能是革命性或是进步性的;它在历史进程中总是扮演着“追赶者”的角色,远远落后且缺乏远见,还与人类社会的构造无关。圣乐简直没有任何新鲜可言了。
我举出了3个可以匹配这一意识形态的强力叙事。这3种叙事,无论单独使用还是结合起来,都可以被用来将圣乐置于无关紧要的古旧价值观范畴之中,让它成为自由、进步、人性的敌人。之前在非功能性和功能性音乐之间的对比变成了一种道德秩序,将圣乐的地位从最高的善,颠倒变成了不可靠近的恶。以下词汇概括了贝多芬与圣乐之间的竞争。
三、反向策略
我在一开始提到过,作为俗乐作曲家的贝多芬这一说法是个神话。在过去的200年里,这种强有力的叙事结构已经塑造了这位作曲家的接受史,那么有没有可能避开这个神话、反转历史并重新发现宗教化的贝多芬呢?
不幸的是,这并不可能,因为这个神话是“真实的”,或者至少它足够真实。从3个意义上来说,它都足够真实。首先,它决定了我们思考圣乐的方式,也因此决定了我们在过去200年间的话语和实践,所以毁坏已经造成了。第二,这个贝多芬神话是一个更大叙事的一部分,这个叙事有关于世俗化和现代化,它比贝多芬这个话题更加宏大——即使推翻贝多芬神话也推翻不了这个元叙事;所以,神话仍然是真的。第三,这个神话并不完全是谎言,它至少有部分是真实的。它或许不细致且简单化,但最基本的观点却足够真实,以至于要分清孰真孰假变得极端困难。要逆转这些毁坏,没有明确的答案。
如果我们无法取消或逆转这个神话,那么至少让我来做做我十分擅长的事情:让我们来把这摊水搅浑吧。那么在这次讲座的后半部分里,我将会举出一个逆向策略,来让这个神话变得复杂化。就像本文目前为止提到的每件事一样,这个策略有3个组成部分。
第一步,打破这一神话的稳定,使其历史化、相对化,使其迷失在相互矛盾的叙事之中。第二步,检验这一神话,将这个贝多芬的神话用到贝多芬这个人身上,看看两者之间是否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有,那么我们便进行第三步。第三步,重新使其语境化。
(一)第一步,打破神话的稳定
这个神话最完整健全的形式需要贝多芬作为启蒙世俗人文主义者,并有着对自由和进步的革命愿景。要使这一观点相对化,最简单的方式便是追溯它的发展历史,即检视其建构,而不是接受这一命题。鲁斯·索里已经追踪到这一神话在19世纪的策动者。她将这一世俗人文主义者神话的起源归功于“瓦格纳的追随者、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者、美国超验论者,还有那些倾向于激进政治的人”①。他们是梦想家和激进者。换句话说,他们都是高声之人,所以称为主导的声音也不足为奇。但是,正如索里展示出的,在这段历史中还有其他众多的声音,这些声音形成了不一样的叙事,这其中包括一些宗教的声音。
但当有人想要在接受史中确定贝多芬的政治或宗教倾向时,便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多么不确定、不一致。你没法儿把贝多芬的信仰牢牢钉在任何确定之事上面,这就意味着各种各样似乎矛盾的事实有可能带来选择性的聆听和意识形态上的诠释。
例如,从政治的一端上来说,贝多芬的音乐在过去200年间已经沾染了政治光谱上的每种色彩。历史学家戴维·丹尼斯将这种政治上的混杂归功于贝多芬反复无常的政治身份。丹尼斯提到,贝多芬作为“开明专制的支持者……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拿破仑的崇拜者……(以及)拿破仑的敌人”,能够让所有派别的政治评论者沉迷于某种“选择性的净化和再诠释”,以便于制造出他们想要听到的贝多芬。②
宗教的这一端情况也很类似,甚至更加令人困惑。以下列出的是到目前为止,学术文献中提到的贝多芬的宗教背景。他是有神论者,自然神论者,泛神论者,无神论者,人道主义者,世俗主义者,世俗人文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不虔诚的天主教徒,文化天主教徒,秘密的新教徒,带有印度倾向、埃及倾向、佛教倾向、伊斯兰教倾向和共济会倾向的东方神秘主义者。作为华人音乐学家,我觉得有义务指出,贝多芬有着某种特定的儒家倾向。有位评论家的确指责作品131中的“大赋格”听起来像中国音乐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把儒家也放进去!所以任你挑选——他可以是其中之一,或者是其中几个的结合。
你看,这个宗教性的贝多芬,就像政治性的贝多芬一样,都像丹尼斯所描述的一样,易于进行“选择性的净化和再诠释”③。我们可以凭空造出又一个神话了!
那么这便是第一步——使其相对化、历史化,这样便能打破神话的稳定性。
(二)第二步,检验这一神话
在这个步骤中,我们在这一新创造的相对化空间中检验这个神话,看看它所声称的东西是否比其他与之匹敌的叙述更加强有力。如果神话与人相一致,那么神话便有可能是真实的;但如果两者不一致,那便需要对这个神话进行修正,或是在这个神话的崩塌之处将其替换掉。
如果这个神话将要崩塌,那么它便是贝多芬与圣乐的交汇之处。无可争议的事实是,贝多芬写过圣乐。诚然,写得不多,但哪怕只有一部圣乐作品,对这个神话来说也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如果这个神话是真的,那么理想地说来,贝多芬不会创作出诸如宗教清唱剧《橄榄山上的基督》或《C大调弥撒》或《庄严弥撒》一样的作品。
所以如果你相信“贝多芬这个让音乐自由了的人”这种说法,那么这些作品就必须从经典作品中剔除出去。那么我们检验的便是,剔除它们这一做法是否具有说服力。对于那些给这个神话添砖加瓦的人来说,要贬斥《橄榄山上的基督》相对更加容易——用简·斯瓦佛德的话来说,它是一部“匆忙写就的作品”,从审美上来说无足轻重。① 而带有礼拜仪式功能的《C大调弥撒》则可以被简单地归类成为特定场合创作的“应景之作”,今天我们表演它只是因为“它是贝多芬创作的”;如果它是其他人写的,那么它很可能不会引起大家的兴趣。正如哲学家特奥多·阿多诺所说,《C大调弥撒》充其量只会被简单地误认为是“缺乏说服力的门德尔松”②。所有这些全都与贝多芬对《C大调弥撒》的高度重视不相符合,与他为弥撒和清唱剧所赋予的个人意义不相符合,也与一个事实——这些作品在贝多芬生前经常上演——不相符合。这种“不符”是不合理的。这些碍眼的事实必须用“世俗”这块遮羞布加以掩飾。
但这块遮羞布可遮不住《庄严弥撒》,它真的太大了!对于那些为这个神话添砖加瓦的人来说,《庄严弥撒》便是贝多芬作品中的问题所在。要是它能被解释成一部“应景之作”——为贝多芬的赞助人及学生鲁道夫大公于1820年3月荣升奥尔米茨大主教而作,那么这首弥撒便能够被贬低为贝多芬神话中的一个临时变化。但是,贝多芬在这部作品上投入了如此多的精力,以至于他在交稿截止日期之后3年才写完它,而贝多芬自己也声称这是他“最伟大的作品”。《庄严弥撒》是贝多芬的巨著,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其贬损为一部应景之作。这正是这个神话崩塌之处。
这个神话将《庄严弥撒》变成了一个不必要的问题——许多学者对这部弥撒的反应令人震惊,就好像贝多芬背叛了自己似的。在简·斯瓦佛德于2014年出版的传记中,《庄严弥撒》一段的开头并不是事实陈述,比如“贝多芬创作了《庄严弥撒》”,而是提出了争议——这位疑心的传记作者问道“为什么?!”“为什么贝多芬写了《庄严弥撒》呢?”③
我的反应则会是“为什么不呢?”有什么问题吗?他不就是写了部弥撒嘛。但结果却需要用错综复杂的方式来证明创作这首作品的正当性,以便将这首弥撒放到这个神话中合适的位置,证明它不是一首圣乐作品。为了将这部作品放进他的世俗音乐范畴之中,斯瓦佛德总结道,这部弥撒“不是为教众而作,而是为人性而作”。①
于此,斯瓦佛德仅仅是跟上了肖弗勒的步伐——“贝多芬:让音乐自由了的人。”肖弗勒关于《庄严弥撒》的章节,其标题为“贝多芬让弥撒自由”。但你读到这一章的末尾时会发现,贝多芬只让这部弥撒的50%获得了自由。②
肖弗勒一开始便承认,贝多芬将《庄严弥撒》视为自己最好的作品,而以前的传记作家们也已经“与(作曲家)达成一致……将其称为大师职业生涯中的皇冠”。接下来他又写道:“是时候忘掉所有人关于这部弥撒所说的一切了……要在我们今日所被赋予的光明之中,严格彻底地检视它的自身价值。”③ 这“光明”是什么呢?那便是音乐自律性的火把。
肖弗勒宣称,“这部弥撒一开始是部应景之作”,而不是一部自律的作品。肖弗勒的功能音乐策略有两个方面——他将其称为“内部的”和“外部的”标准。外部的标准即鲁道夫大公荣升这一特定场合。肖弗勒嗤之以鼻地说道:“这种外部动机几乎从不会促成贝多芬最好的作品。”所以在这一前提之下,这个神话将这部弥撒降级至次等的应景之作和功能性作品的范畴之中,以此来还击贝多芬认为这部弥撒是自己最好作品的说辞。此时,它与其他的应景之作归为一类,这其中包括粗制滥造的政治宣传作品《惠灵顿的胜利》和为维也纳会议创作的《荣耀时刻》。
这便是外部标准。肖弗勒的“内部标准”指的是贝多芬在一封1824年的信件中所提到的,他渴望用《庄严弥撒》向听众长久地“灌输宗教情感”。肖弗勒写道:“如果这(即宗教功能)是真的,便能解释为何这部作品中差不多有一半相对来说都是失败的。”50%!现在,《庄严弥撒》的50%都因为宗教被贬斥为一种失败。为什么呢?接下来便是“解放”的意识形态了。肖弗勒问道:“难道你能想象,贝多芬坦白说他写作《英雄交响曲》一类作品的主要目的……是有关道德、哲学、宗教或其他什么,而非纯音乐目的吗?”④ 好吧,我能想象,而且他的目的的确如此。但这便是这个神话的力量之所在,它让肖弗勒能够问出这样的反问句,并理所当然地觉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即使结果荒诞古怪。只有纯音乐作品是自由的,这便是这个反问句的含义。但这就意味着这个神话现在需要这部弥撒成为一部纯音乐作品,这既矛盾又不可能。从定义上来说,弥撒不是交响曲。然而肖弗勒仍然总结道:“尽管(这部弥撒)有一半相对来说不足,这部弥撒仍然在继续着解放的事业,这正是这位创作者在他的许多器乐作品中所从事的事业。”
此时此刻,肖弗勒部署好了最后的策略——世俗人文主义的叙事。作为被解放的音乐,贝多芬的器乐作品代表着人性。于是,尽管贝多芬没有从字面意义上解放弥撒,他还是从精神意义上解放了它。肖弗勒宣称,就像器乐作品一样,《庄严弥撒》不是为教堂而作的,它是人性的证明。肖弗勒总结道,贝多芬“将弥撒从教会惯例本身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庄严弥撒》属于真正的宗教,有如全人类一般宽广,个体在此处与无限的生命密切相关,而他正是这无限生命的导火线。”① 在不那么华丽的辞藻中,《庄严弥撒》成了一部具有普适性的、关于独立自律的人文主义弥撒。
很明显,这是个古怪且荒唐的结论。但这仍是贝多芬研究的标准。这个神话需要被彻底否认。尽管贝多芬的圣乐作品十分正统(实际上,在贝多芬的任何圣乐作品中,都没有任何从神学上来讲不正统的东西),但为了维护这个神话,这些作品仍是悄然地产生了不正统性。
这一否定最大的受害者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特奥多·阿多诺。他是20世纪最精明的知识分子之一,他认为贝多芬的音乐比黑格尔的哲学更有高度;但在他关于《庄严弥撒》的文章中,他比肖弗勒更早提出了后者书中的一些观点。贝多芬是“让音乐自由了的人”——阿多诺的用词更加学究,他称其为“人性与破除神话”。也就是说,为了解放人性,贝多芬破除了圣乐的过去这一神话。问题在于,《庄严弥撒》被默认为刚好相反。所以,就像斯瓦佛德一样,阿多诺的反应便是问道“为什么?!”他断言:“贝多芬创作了一首弥撒,这件事本身便是个悖论。”但与斯瓦佛德不同的是,他更加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正如阿多诺在他的笔记中潦草写道:“贝多芬绝不会犯错。”那么,阿多诺认为,最要紧的任务便是“解释为何高度解放的贝多芬……会被(弥撒的)传统形式所吸引”②。于此,阿多诺改编了某种熟悉且古怪的论点:应该以纯音乐的观点来判断这部弥撒,这部弥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不是一部交响曲,这部弥撒为了他律性放弃了自律性,这部弥撒无法被辨认为是贝多芬的音乐。
接下来阿多诺更进了一步。他写道,贝多芬从他自己的作品中“清除了他自己”。这位让音乐自由了的人,故意让他自己变得不自由。③
接下来便是阿多诺论证中的反转——“失败”便是贝多芬想要传达的信息。身处“后奥斯维辛”的优势地位,阿多诺能太清楚地看到,现代进步所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非自由;启蒙运动已重新變回了统治支配,自律性已变成了暴政。贝多芬的失败正好成就了阿多诺对自由的批评。所以,《庄严弥撒》不关于神,它以逆向的方式仍与人性相关。换句话说,《庄严弥撒》是一部具有普适性的、关于自我毁灭的人文主义弥撒。
但阿多诺与肖弗勒不同,因为他从未完成他那本关于贝多芬的著作。他的音乐哲学非常核心的部分并不完整。他坦白道:“……主要是因为,我的努力总是在《庄严弥撒》这里失败。”④在这位哲学家的内心深处,总有那么一些事情让《庄严弥撒》与他对贝多芬的想象无法调和。阿多诺未能完成他的贝多芬写作计划,这便是他对于贝多芬研究最大的贡献。不过这一点我将放到今天讲座的结论部分进行解释。在这里,我们先承认阿多诺察觉到了第二步中的不一致性,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步,重新语境化!
(三)第三步,重新语境化
我们已经检验过这个神话,并发现它有所欠缺。第三步的任务便是提供另一种叙事。是否有一个可供替换的语境能够解开这一困境,好让贝多芬这个解放了音乐的人,不带任何矛盾地写出《庄严弥撒》?现在,这个神话需要某种语境来证明其观点的正当性。如我在前面所大致描绘的一样,这种语境包括启蒙时期的知识界氛围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语境。在1800年前后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中将这两者合并起来,是相当可行的,实际上,是相当有必要的。但宗教在这一语境中担任了什么角色呢?
这个神话的奇怪之处在于,它是关于法国的。法国大革命与法国启蒙运动相混合,必然会带来一种反教会、反君主的叙事。在这一法国语境之中,自由的敌人是天主教教会和绝对君权,这两者将艺术占为己用。但贝多芬从未踏足法国。如果你问自己“在18世纪的日耳曼公国,启蒙运动的典范是什么?”那么你将会得到一个自相矛盾的答案——开明君主专制。比如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或是奥地利的约瑟二世,这些君王同时也担任天主教会的宗教权威。我们甚至可以说,贝多芬自己也有一位稍微开明的专制君主——鲁道夫大公,《庄严弥撒》正是为这位皇家红衣主教所作。那么,启蒙运动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便是宗教。德语中的“启蒙运动”是一种宗教性的启蒙运动,是由天主教君主所挑起的改革,从定义上来说,它们当然不可能反教会、反君主。他们改革了自己所代表的建制,但他们不会反对这些建制。
在这样的语境之中,这种从教会和王权中被解放出来的音乐的叙事(这种叙事将圣乐放逐到公共话语的边缘地带),就再也说不通了。贝多芬神话的意识形态基础开始崩塌,《庄严弥撒》不再是反常之物。
(四)第四步,未实施的步骤
现在,我们来到了第四个步骤,如果你之前有认真听讲,会注意到我并未提到这一步,因为这是我们不该走的一步。但是,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论述的逻辑结果。在第四步,我们给贝多芬重新贴上标签。
在打破这一神话的稳定并将事实重新语境化之后,我们便可以给贝多芬别上新的徽章了。变化了的语境难道不需要对作曲家作出新的定义吗?现在,贝多芬可以与教会和宫廷结盟了,他的功能性音乐也由此得以开脱并被严肃对待。最后,他可以是一位正统的、拥护君主制的天主教徒。而且不止他一人如此,大多数激进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都在19世纪的前20年里回归了教会。问题解决了。我们拯救了圣乐。
但如果我们实施了第四步,便会产生以下的问题。近年来在学术界,已经有学者,诸如尼古拉斯·马修和史蒂芬·伦夫,在重新评估热心政治的贝多芬时,给这位作曲家重新贴上了标签。①在这样的学术研究中,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功能性作品成了理解非功能性作品的镜头。或者至少,这些研究心照不宣地刺破贝多芬“让音乐自由了的人”这一肿胀膨大的形象,使其得以收缩。那么,这个贝多芬远非让音乐自由的人,他是个服务于维也纳皇家的保守派;那个有如普罗米修斯般叛逆的贝多芬变成了“俯首称臣”的贝多芬,在皇家统治面前卑躬屈膝。
同类型的学术研究可以被很简单地运用在贝多芬的宗教信仰之上,尤其是因为王朝政治与教会政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要在政治混合物中加入宗教,贝多芬那关于自由的神话就可以被否定掉。
但在我们实施这一步骤并拯救圣乐之前,我们必须得问问我们自己,重新贴标签这一行为之中,究竟有什么危险呢?即便我们已经破除了“让音乐自由了的人”这一神话,这个神话仍然作为一种价值继续存在着,一种贝多芬没能实现的价值。这个神话以否定的形式留存了下来。这个步骤的意义即为,贝多芬的自由是个谎言,是他接受史中的伪造物。事实证明,他是个没有让音乐自由的人。你们真的想让我写这样一本书吗?
这样一本书暗示着贝多芬没有解放任何东西。他的圣乐作品便是证据。
四、回到起点
所以,我们不去实施被禁止的第四个步骤,而是要回到起点,再次讨论这个神话,再将贝多芬回炉重塑为“让音乐自由了的人”。
不管他的政治或宗教倾向如何,贝多芬当然是信仰自由的。贝多芬在1819年开始创作这首弥撒时,向鲁道夫大公这样写道:“自由(与)进步是艺术世界的目标,正如它们也是整个浩瀚宇宙的目标一样。”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贝多芬将自己视为“让音乐自由了的人”。所以,与其否定这个神话,不如我们提出两个问题:贝多芬将音乐从什么之中解放了出来?他让音乐自由是为了什么呢?不幸的是,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再花上30页的篇幅,但我会试着用短短几段文字来回答。所以,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咯!
在18世纪,音乐符号必须被清晰地分类,要么是有歌词的,要么通过模仿外部事物来确定它们的意义和情感。理解音乐,要以一种参照性符号的理论为基础,按照语言的或是模仿的方式来进行。这样一来,它便能够以教诲的且令人愉悦的方式进行交流了。
贝多芬所做的则是破除这种分类。这就是为什么他称自己为音乐诗人,而不是作曲家。“让音乐自由”不再是作曲,而是为其赋予诗意(poeticize)。作为创制(poiesis)的音乐,是一种拥有无尽构思与感受的创造性力量。这些构思与感受无须参照外部世界,它们在贝多芬所谓的“思想帝国”中流通传播,这便是自由的领域;主体在这一领域中崭露头角,意识到其自身即是一种表现形式。简单来说,他将音乐从具体实在的标签中解放出来,以揭示出更高的真理。
所以,例如贝多芬为维也纳会议而创作的《惠灵顿的胜利》。这部贝多芬的政治宣传作品中有加农炮声和军号声,它是模仿式的,而非诗意的(poetic)。作为参照性的符号,它也许会赞美自由;但从审美上来说,它是不自由的,因为在这首作品中,音乐符号的功能是命题性的——“这是加农炮”或者“这是军号声”。除了它们代表的东西,这些符号无法揭示更多的内容。
而《英雄交响曲》在开始处也有加农炮(第1—2小节)和军号声(第3—6小节),但是一旦你在音乐中贴上这些标签,音乐中诗意的自由便遭到了破坏。(谱例1)
所以,问题在于圣乐作品到底属于哪一边呢?是《惠灵顿的胜利》 (即具象表现之作)这边还是“英雄”(即诗意之作)这边呢?当然,它们属于“英雄”这一边!圣乐作品是诗意的作品。换句话说,当贝多芬解放音乐之时,他也解放了圣乐。所以,圣乐并不是这个神话的反转,关于“解放”的神话之中反而包括了圣乐。的确,宗教元素不止存在于贝多芬明确的宗教作品之中。他的歌剧、交响曲、协奏曲、四重奏中都充满了赞美诗、祈祷和祷告歌曲。因此,将圣乐解放为俗乐,也是贝多芬对诗意自由的整体设想的一部分。他将宗教元素诗意化了。
但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该将圣乐作品视为忏悔声明来为其贴标签。这样做会混淆诗意的真相和命题性的陈述。贝多芬的圣乐作品不是对教义进行解说,其目的不是为了证明作曲家的信仰,进而解决宗教元素的问题,就好像宗教是可以被代表的事物一样。
实际上,圣乐的解放完全无法解决我们在最开始提出的问题。它反而加剧了这个进退维谷的困境——的确,这个折磨阿多诺的问题,让他挣扎着想要调和“解放的贝多芬”和《庄严弥撒》。通过解放圣乐,贝多芬使其现代化,好让宗教元素参与到现代性的危机以及现代性对自由的宣言之中。
《第五交响曲》和《第六交响曲》正象征着这个神学上的困境。这两部极其不同的作品在1808年的同一场音乐会中接连首演,阿多诺将它们称为贝多芬的集约型(intensive)和扩展型(extensive)风格。《第五交响曲》的集约型风格以完全自律性的、普罗米修斯式、英雄式的贝多芬为模型。与之相反,《第六交响曲》的扩展型风格被表现为一首田园诗,一种对大自然的田园诗般的想象。我们从贝多芬祷告词中得知,他将大自然视为彰显上帝荣耀的宇宙,因此《田园交响曲》是一部感恩的宗教作品。从末乐章乐谱手稿上的原标题来看,贝多芬把这一点表达得非常清楚:“牧人的赞美诗:感激之情结合着暴风雨之后对上帝的感谢。”①
这两部交响曲所代表的,正是这个时代在“自我”与“世界”之间最核心的冲突。一方面,像《第五交响曲》一样的作品代表着“自我”的新概念,即独立于宇宙的绝对意志。这个“自我”将自由展示为一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为了控制世界而抵抗着它。对于这个主体来说,宇宙没有其本质固有的意义,它存在于此就是为了被征服。另一方面,在《田园交响曲》中,“人”通过其与宇宙的关系来定义自身,而“人”正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有助于人类繁荣发展的客观道德秩序。所以在一部交响曲中,你可以看到一个具有自律性的主体,这个主体为了追求道德上的自由被逐出了大自然。而在另一部交响曲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他与道德宇宙合而为一,但却失去了他自己的自律性。
贝多芬通过将两部交响曲分隔开,从而栖息于这种矛盾之中。阿多诺洞悉到,贝多芬的晚期风格正是集约型和扩展型两种风格的融合,可以说是合并起了《第五交响曲》和《第六交响曲》。贝多芬让分隔开的两者向内爆破,即让主体和客体在不调和的状况下互相碰撞。他正是这样牵制着神学的张力。从神学上来说,神与人是互相冲突的——这个现代的“自我”渴望着统一,却被它自己的自由分割开来。
所以,在最后,我要试着解读一部贝多芬的晚期作品,将这种神学上的冲突举例说明为一种他在音乐中的詩意构思。
五、 《槌子键琴奏鸣曲》
那么,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田园交响曲》,“田园”在贝多芬的晚期作品中是一种宗教范畴。在《庄严弥撒》中,“降福经”和“请赐平安”是田园诗式的,以“救赎”和“感恩”的田园牧歌准则,代表着作为上帝羔羊和好牧人的基督。当田园准则与晚期风格中的英雄性相冲突之时,这两者便统统被扔进了令人费解的混乱动荡之中。而这正好发生在《槌子键琴奏鸣曲》之中。
首先,说这首奏鸣曲是这种宗教主题的载体,似乎是高度可疑的做法,但贝多芬自己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在靠近第一乐章草稿结尾的地方,他写下了“我的弥撒的前奏曲”①。贝多芬习惯于在他的草稿上潦草写下各种话,没有理由认为这句描述与这首奏鸣曲或是与《庄严弥撒》相关,特别是当他在1818年的前几个月写下这句话时,他还尚未开始计划写作《庄严弥撒》。②但是,这首奏鸣曲仍预先“引用”了《庄严弥撒》,就好像它是一首隐喻性的“前奏曲”一样。的确,如欧文·拉茨所说,这些“引用”是如此独特,它们引发了对形式的阐释性压力,需要从《庄严弥撒》的视角来解读这首奏鸣曲。③
有两处预先“引用”。它们来自《庄严弥撒》中的两个田园式的元素,即“降福经”和“请赐平安”。确认这一推断的原因,并不是要证实这首弥撒与这首奏鸣曲之间有着某种直接联系,而是要说明,这些田园式元素的功能是带有基督性内涵的圣歌。
慢乐章以一首挽歌开始(谱例2)。开头主题有着非常明确的内省性,以至于它的织体变得越来越阴暗,浓密厚重的和弦将自身紧紧包裹,直到它们变成无法穿透的音簇,陷进自己的阴暗之中;如威廉·冯·伦茨所说,它是一座“阴森陵墓”。
但是接下来,相当出人意料地,这个主题张开了它的双眼(第14—15小节、第22—23小节)。音乐中插入了一个遥远的和声区域。突然,只有那么两个小节,“降福经”中的小提琴独奏似乎要从未来穿越而来,带着相同的动机,以相同的调,让这个转瞬即逝的时刻变成了《庄严弥撒》无意的“前奏曲”。罗伯特·哈腾写道,这种超然的姿态,是“乍现的灵光”,展现出了“恩典美景”。①
这转瞬即逝的美景会将这个乐章从阴森的陵墓转化成一个奇迹。但“槌子键琴”一开始是部英雄性的作品,而且赋格式的末乐章也想要重拾第一乐章的英雄性,但田园愿景与英雄自决之间的对峙让音乐走向了彻底的毁灭。赋格式的末乐章是英雄性的形式,但这一形式无法维持自身的统一。第二个来自《庄严弥撒》的“预先”引用,它有多么出人意料,便有多么转瞬即逝。它强调了一点,即赋格无法吸纳田园准则,使其成为英雄性自我生成的一部分。两种元素都被撕成了碎片。在音乐史上,象征着秩序的赋格头一次分崩离析,转而象征着英雄般的精疲力竭和毁灭。尽管末乐章用上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对位技巧,以重建英雄性的形式,但这个乐章最终却空空如也。正如尼古拉斯·马尔斯顿所写的,“音乐中展开的物理攻击,是在试图通过发狂般的表层活动来清除掉潜伏其中的空洞与缺失”。他总结道,最后的终止“与其说是结束,更多的是在终于公然承认了它本质上的虚伪之后,瘫倒在地。如果这里有英雄性,那便是一种英雄式的自我欺骗”②。
贝多芬将“宗教性”解放为“世俗性”,由此他没有让《槌子键琴奏鸣曲》成为关于信仰的告解,而是让其诗意地揭露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一个需要对其进行诠释性回应的真相。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给田园般的插入贴上“基督”标签,因为诗意从不会依照字面意义,它也不具有虔诚敬拜的功能。如果在贝多芬的作品中有基督的存在,那么,如我在别处所写,那必然是隐姓埋名的基督。③ 其存在不是为了被识别出来,而是对毁灭主体这一威胁所做出的回应。贝多芬在他的书桌上留下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埃及塞伊斯神庙中的铭文,从某种意义上说,若我们认真看待这句话,那么这便是贝多芬所想要做的事——“我是过去、现在、将来的万事万物——还没有凡人揭开过我的面纱。”
如果贝多芬的音乐是在尝试着揭开面纱,那么它所揭示的便不是一个标签,而是一种凡人不应该看到的真理。这个世俗人文主义的神话,通过驱逐宗教性,尝试着抵消音乐中的危险;因为如果我们瞥见了隐藏在贝多芬面纱之后的宗教性真理,那我们最终有可能变成“槌子键琴”中的赋格。我们会被毁灭。
而这也正是阿多诺面临《庄严弥撒》时所发生的事情——他关于贝多芬的整个哲学都因为这部作品而毁于一旦。他遗留下来的关于贝多芬的残篇便象征着这种彻底毁灭。这也正是为什么“无法完成贝多芬写作计划”这件事本身便是他对贝多芬研究最大的贡献;因为他对宗教性问题的反应,不是在他自己的体系之中对其进行解释或拉拢,而是像赋格一样,即使用尽浑身解数,也无法维系自己关于贝多芬的英雄性哲学。他被毁灭了。
那么,要对贝多芬进行“去世俗化”,便会被贝多芬伤害致残。所以我要以一个警告来结束自己的讲座:要想对贝多芬“去世俗化”,后果请自负!
本篇责任编辑 钱芳
收稿日期: 2020-12-04
作者简介:蔡宽量(Daniel K.L.Chua)(1966— ),男,博士,香港大学教授。
译者简介:何弦(1983— ),男,博士,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四川成都 610021)。
① 贝多芬的评注“我的弥撒的前奏曲”由Gustav Nottebohm记录在他所写的有关现已经遗失的“Boldrini”草稿本的文章中,参见Nottebohm, Zweite Beethoveniana (Leipzig: Verlag von C.F. Peters, 1887), p. 353. Nottebohm评论道,这句话出现在草稿本的第75页,靠近作品106第一乐章草稿的结尾以及第二乐章草稿,这些草稿很可能完成于1818年的前几个月。因为此时尚未构思《庄严弥撒》,Nottebohm认为这句话很可能指的是贝多芬的第一首《C大调弥撒》,作品86。这番证据太过牵强,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但贝多芬用了“前奏曲”这个词,这对于10年前创作的弥撒来说似乎有些问题。与这首奏鸣曲相比,《C大调弥撒》似乎无法承载如此庞大的一首“前奏曲”。Erwin Ratz观察到了奏鸣曲在主题上引用了《降福经》,并将这句话视为对《庄严弥撒》的直接评注,这需要从《庄严弥撒》的视角来对奏鸣曲进行诠释性解读。用贝多芬的这句话来联系他“最伟大的奏鸣曲”和他自认为“最伟大的作品”,即《庄严弥撒》,尽管这样做更讲得通,但从历史记录上来说,很难将这两部作品匹配起来,除非贝多芬在构思《庄严弥撒》之前已经计划写作一首弥撒。我们知道,1818年,贝多芬在一条日记中提到,他已经在考虑为教堂写作一首作品,如Maynard Solomon所述,“受助于Friedrich August Kanne、Karl Peters、Joseph Czerny,并得以使用鲁道夫大公与Lobkowitz亲王的图书馆,他研究了从格里高利圣咏到帕莱斯特里那与巴赫的圣乐”。不管情况究竟如何,对贝多芬来说,《槌子键琴奏鸣曲》明显带有某种宗教内涵,而作品106与《庄严弥撒》以及其他晚期作品中重复出现的主题材料也表明,贝多芬在他的晚期风格中发展了一种带有神学修辞比喻的主题网。参见Erwin Ratz ,“Analysis and Hermeneutic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Beethoven,” translated by Mary Whittall, Music Analysis 3(1984): 243–54. 关于贝多芬这首奏鸣曲现存的草稿,参见Nicholas Marston, “Approaching the Sketches for Beethovens‘HammerklavierSonat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 44/3(Autumn, 1991). 贝多芬日记中关于圣乐的评注,参见Maynard Solomon, “Beethoven's Tagebuch of 1812-18”, Beethoven Studies 3, ed. A. Tys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p. 284.
② 如果以现存的草稿为依据,贝多芬很可能在1817年12月开始写作《槌子键琴奏鸣曲》。《庄严弥撒》的创作周期比贝多芬计划完成的事件要长得多,最终完成于1823年。鉴于1818年的草稿本并未得以留存,我们并不清楚贝多芬合适开始创作《庄严弥撒》。1819年的“Wittgenstein”草稿本中有现存最早的草稿,但如前注中提到的,贝多芬在1818年的日记条目中已经提到在为教堂构思一部作品。
③ Erwin Ratz,“Analysis and Hermeneutic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Beethoven,” translated by Mary Whittall, Music Analysis 3(1984): 249-254.
①Robert S. Hatten, Musical Meaning in Beethoven: Markedness, Corre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pp. 15-16.
② Nicholas Marston, “From A to B: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the ‘Hammerklavier Sonata,” Beethoven Forum 6/1 (1988):119-120.
③ 參见Daniel K. L Chua, “Beethovens Other Humanism,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 62/3 (2009):621-632.
